瘟疫与人.pdf
http://www.100md.com
2020年2月4日
 |
| 第1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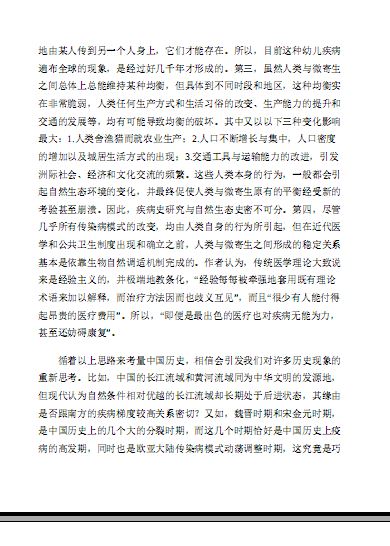 |
| 第10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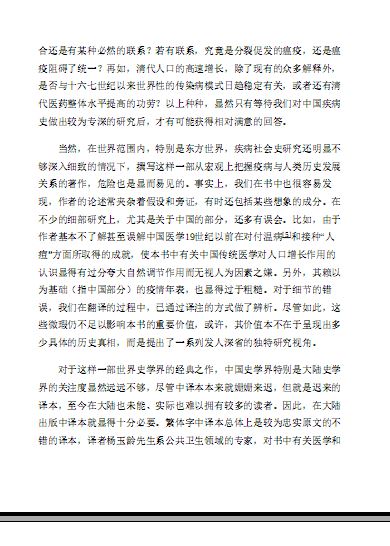 |
| 第11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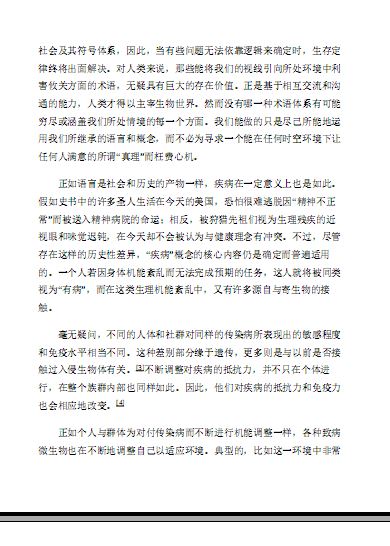 |
| 第28页 |
 |
| 第44页 |
 |
| 第104页 |
参见附件(5362KB,391页)。
瘟疫与人是作家威廉麦克尼尔写的关于瘟疫的书籍,主要讲述了传染病与人类的关系,关于瘟疫的跨国交流,近代医学的实践以及疫情历史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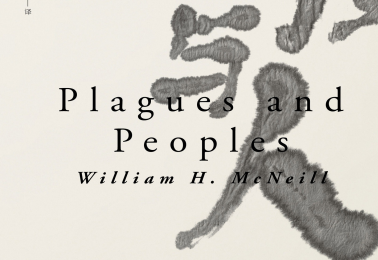
瘟疫与人内容提要
疫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一代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从疫病史的角度,以编年的手法,从史前时代写至上世纪前半叶,详实探讨传染病如何肆虐欧洲、亚洲、非洲等文明发源地,而这些疾病又如何塑造不同文明的特色。他率先将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重新解释人类的行为;他将传染病置于历史的重心,给它应有之地位;他以流畅的笔调、敏锐的推理和高超的技艺,娓娓道出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瘟疫与人》是威廉·麦克尼尔备受欢迎的一部经典作品,也是宏观论述瘟疫与人类历史关系的史学佳作。《纽约书评》称 “此书从此扭转了人们看待世界历史的角度”,《纽约客》则认为此书是 “一部真正的革命性作品”。普利策奖得主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盛赞它提出了“富有创新也具有挑战性的历史概念,影响深远”,而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有言:“看待历史的崭新观点,我从《瘟疫与人》中受益匪浅。”
瘟疫与人作者信息
威廉麦克尼尔,一代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在全球史方面的研究卓然有成,德高望重,与斯宾格勒、汤因比齐名,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开辟了一个西方世界史学的新时代。
1963年,威廉麦克尼尔以一部《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一举成名,并因此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此后,他笔耕不止,迄今已出版30多部作品。 1996年,因其“在欧洲文化、社会和社会科学领域里做出的杰出贡献”荣获伊拉斯谟奖。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他颁授国家人文勋章,以表彰其在人文科学研究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
瘟疫与人读者评价
这本完成于40年前的著作,在国际学术界取得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不过其对中文学界的影响可谓姗姗来迟,直到20世纪末,才首次出版了中文繁体字版,简体字版的正式面世也才不过几年时间。但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近些年来,该书在国内学术界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注目。十余年来,国内已经有三家出版社相继购买译著版权,大概就是很好的证明。这对于我们译者来说,在感到荣幸和欣喜的同时,也更多了一份对作者的敬意,以及对进一步推动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向前发展的责任和期盼。
瘟疫与人截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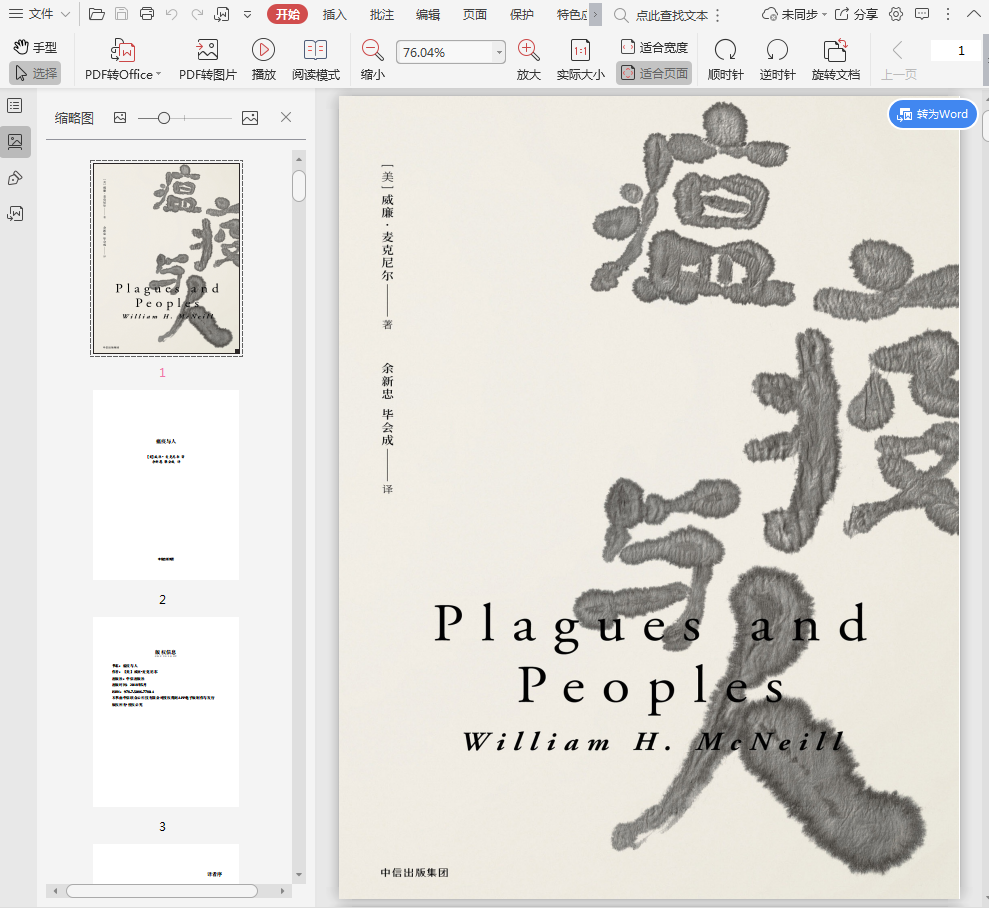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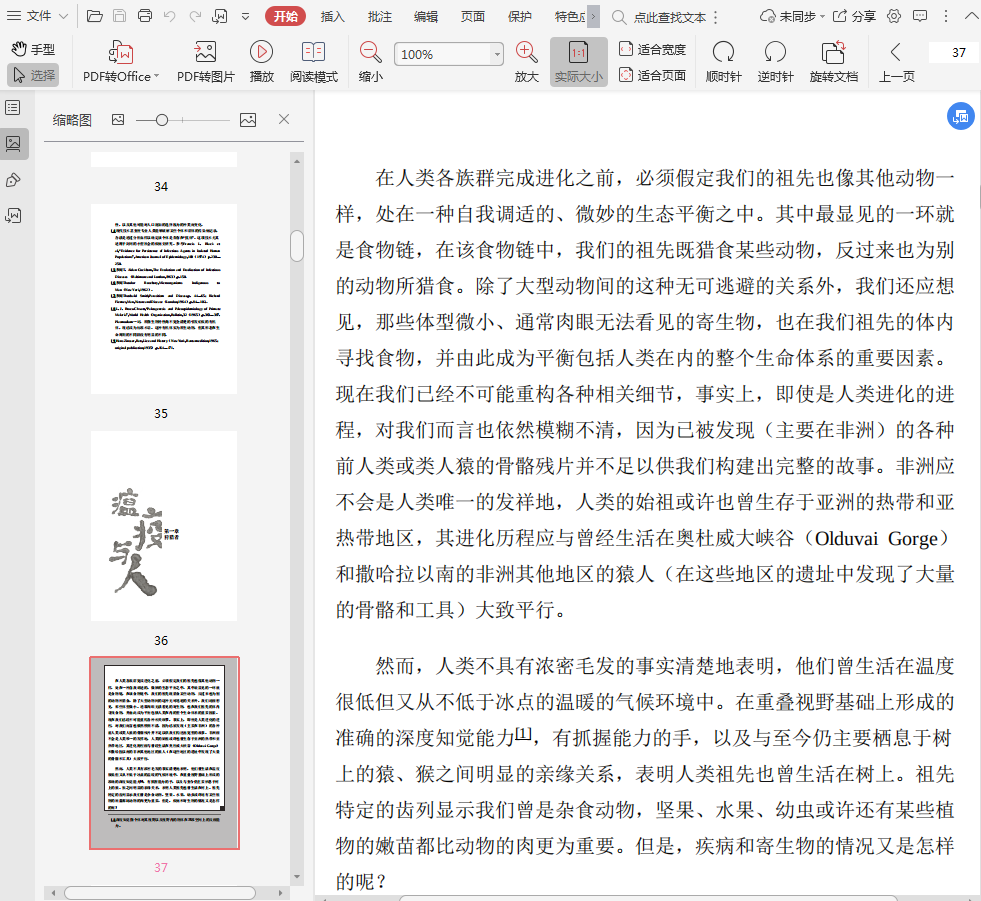
瘟疫与人
[美]威廉·麦克尼尔 著
余新忠 毕会成 译
中信出版集团
书名:瘟疫与人
作者:【美】威廉·麦克尼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5月
ISBN:978-7-5086-7780-4
本书由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译者序
在学术史上,借由精深的研究,就某一具体问题发前人所未发,甚
或提出某些不易之论,这样的成果虽然不易取得,但也不时可以见到;
而那种能从宏观上洞察人类思维的某些疏漏,从而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知
识上都能给人以巨大启发和触动的研究,却总是微乎其微。威廉·H.麦
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的《瘟疫与人》,可以说正是这类微乎其
微的研究中的一种。“原来我们对历史的呈现和解读疏忽了如此之
多!”清楚地记得,数年前,当我集中精力读完这一著作后,感受到的
不仅仅是欣喜和激动,还有一种对学术心灵的震撼。毫无疑问,它已成
为我开展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最初乃至持久的动力之一。
作者麦克尼尔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曾以著作《西方
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而蜚声世界史林,是美国当代最具声名
的历史学家之一。本书在西方早已不是一部新著,最早于1976年出版于
美国,翌年和1979年两次再梓于英国,1994年被“企鹅丛书”收入并再
版。作为一部学术著作,以如此高的频率一版再版,其影响之广泛已不
言而喻。而且,其影响显然并不局限于西方世界,本书出版不久,陈秋
坤就以中文书评做了介绍。[1]
1985年,日译本正式出版。[2]
韩文版也于
1992年出版。而中译繁体字版直到1998年才问世。[3]
本著作无疑是部极具开创性的论著,英国牛津大学的基思·托马斯
(Keith Thomas)教授曾在书评中指出:“他(指麦克尼尔)是第一位把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起来,重新解释人类行为的学者,也是第一位把传
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它应有地位的史学工作者。”[4]
即使时至今日,相信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本书仍会让人耳目一新。他从疫病史的角度对
人们习以为常的众多历史现象所做的解释,往往与以往政治史、经济
史、文化史乃至社会史的分析大异其趣。比如,在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
的历史中,1520年,科尔特斯只带了不到600名随从,就征服了拥有数
百万之众的阿兹特克帝国,个中原因,麦氏认为过去种种解释都不够充
分,最为关键的因素还在于“新大陆”居民遭遇了从未接触过而西班牙人
却习以为常的致命杀手——天花。他指出,就在阿兹特克人把科尔特斯
及手下逐出墨西哥城的那晚,天花正在城中肆虐,连那位率队攻打西班
牙人的阿兹特克人首领也死于那个“悲伤之夜”。正是传染病这一可怕
的“生物武器”,帮助西班牙人消灭了大量印第安人的躯体,还最终摧垮
了他们的意志和信念。又如,过去在人们论述公元前430—前429年雅典
和斯巴达争霸战中雅典的失败时,往往将其归因于政治体制的不同等因
素,然而,麦氏却指出,雅典陆军在这段时间,曾因一场来去无踪的瘟
疫折损近四分之一的官兵,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瘟疫改变了地中
海后续的政治史。同样,在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中,瘟疫也至少部分
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当时,天花使得两万法军失去了作战能力,而普鲁
士军人由于做了预防接种而未受影响。当然,麦氏全新的观察并不只是
为了给某些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插入一些偶然性因素,以增加历史的
不确定性。实际上,作者采取的是一种真正从整体上审视人类文明发展
的大历史观,本书“旨在通过揭示各种疫病循环模式对过去和当代历史
的影响,将疫病史纳入历史诠释的范畴”,“并把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中的
角色还置于更为合理的地位上”。从这一视角出发,作者对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重要现象做出了合理而意味深长的诠释。比如麦氏指出,非
洲热带雨林和邻近大草原温暖湿润的气候和丰富的食物十分有利于人类
最初成长,但同时也孕育了极其复杂多样的致病微生物。在这片生态体
系最严峻而多样化的地区,“人类为缩短食物链所做的尝试仍未臻成
功,依然以不断感染疾息的方式,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一点,比其他任
何方面,都更能说明,为什么非洲与温带地区(或者美洲的热带地区)
相比在文明的发展上仍显落后”。又如,作者认为,在另一个微寄生物
特别复杂多样的地区——印度,由于大量微寄生物耗去了当地农民相当
的能量,使得印度的城市及统治者从他们身上攫取的物质与世界其他地
区相比,总显得相对稀少。正是这种表面富足、实则贫穷的现象,让印
度的国家结构总处在一种脆弱而短暂的状态之中,同时,向往来世的人
生观的形成与践行,也就势在必行了。
以上所举不过是作者众多匠心独具的历史阐释中的寥寥数例。在论
述其他诸如罗马帝国的崩溃、佛教和基督教的兴起、欧洲的扩张、印度
种姓制度的形成,以及大英帝国的崛起等种种历史现象时,麦氏均能通
过一般的因果解释,认识到疫病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这些现象表明,疾病,特别是其中的传染病,乃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
一”。然而,如此重要的内容何以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历史学家的冷落
呢?作者认为,“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同样的疫病在熟悉它并具有免
疫力的人群中流行与在完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中暴发,其后果差别巨
大,以往的历史学家才未能对此给予足够重视”。另外还因为,历史学
家往往会在历史中刻意突出那些可预计、可界定且经常也是可控制的因
素。“然而,当流行病确乎在和平或战争中成为决定性因子时,对它的强调无疑会弱化以往的历史解释力,故而史学家总是低调处理这类重要
的事件。”其实循着麦氏的思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史学研究者
对历史问题的兴趣,基本来自现实生活的体验,即使是受过严格训练的
职业历史学者,往往也会在不经意间就以当今世界的经验来理解历史现
象,特别是对那些自己缺乏深入探讨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一方面,疾
病尽管直接关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但人们习以为常,很难想象它会对
一系列重大事件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现在乃至过去的一些经验,一般会使人把疫病当作一种纯粹自然的现象,因此也就难以引起专注于
人类社会文化行为的历史学者的关注。此外,在史籍中,此类资料零
散、不够丰富,这可能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由于过去相关研究的缺乏,人类疾病史上的众多细节问题必然还不
够清楚。在这种状况下,要完成这样一部从宏观上论述瘟疫与人类历史
关系的大作,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技艺。作者正是凭借他深厚
的世界史功力,借由敏锐机智的观察和推理,娓娓道出了传染病在人类
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通过深入的分析和流畅的笔触,作者把传染病如何在人类历史上影响到整个人类的迁移、民族的盛衰、战争的胜败、社会的荣枯、文化的起落、宗教的兴灭、政体的变革、产
业的转型、文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等,做了完整的论述,堪称经典。
全书除“引言”外,共分六章。第一章“狩猎者”,介绍史前时代人类
在征服自然过程中与传染病的关系及传染病对人类文化形成的影响。第
二章“历史的突破”,探讨了公元前3000—前500年人类所遭受的疫病以
及与疫病逐渐调适的过程。第三章“欧亚疾病的大交融”,论述公元前500—公元1200年的疫病史,提出地中海岸、印度和中国间的贸易,在
公元200年左右已运作稳定。这暗示着在交换物资的同时,传染病也一
并交换。由于天花、麻疹和鼠疫等一些原产于印度或非洲的传染病在东
西方相继出现,使其在公元3世纪前后,出现了疫病的多发和人口的减
损。而后,大约在900年,欧亚大陆发展出了相当稳定的疫病模式,人
口再度增长。第四章“蒙古帝国颠覆旧有的疾病平衡”,阐述了1200—
1500年世界各地遭受的疫病。这一时期,蒙古骑士东征西战,使得鼠疫
杆菌等致病微生物轻易地穿越河川等天然屏障,造成了东西方传染病模
式的再度失衡,新一轮的疫病大流行在欧洲以及中国等地出现,特别是
欧洲的黑死病影响至深,直到1500年前后,新的平衡才在各地陆续达
至。第五章“跨越大洋的交流”,讨论1500—1700年世界疫病状态,主要
探讨了欧洲人在征服美洲过程中,由其引入的传染病在其中所起到的巨
大作用,它在摧垮美洲印第安人的信念和与其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
要远甚于武力等人为因素。在这一时期,世界各地的传染病模式还出现
了均质化倾向,即世界各地的致病微生物与人类共生模式更趋稳定,疫
病主要以儿童病、地方病的形式出现,流行频度增加,杀伤力减弱。以
文明族群的大规模成长和疫病隔离群落的加速崩解为主要特征的“现
代”疾病形式逐渐形成。第六章“近代医学实践的影响”,探讨1700年以
后的人类疾病史。随着天花接种的发明推广、近代医学和公共卫生制度
的出现和发展,人类第一次能够通过科学原理在卫生行政上的运用,彻
底打败因类似的科学原理运用到机械运输上而导致的逾越传统地理疆界
的传染病。但疾病与人类的竞争依然存在,直到今天,而且还将会和人
类长久共存。麦克尼尔从病理学和历史学相结合这一独特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和
阐释了人类历史,纵横捭阖,左右逢源,确实提出了众多独具匠心且发
人深省的认识。如果说,这些具体的认识还有重新探讨,至少是进一步
论证的必要,那么,作者在具体的论说中表明的一些基本原理,不管是
否完全正确,都值得每一个历史研究者重视并认真思考。按照笔者的理
解,这些原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人类大部分的生命处
在一种介于“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之间的危险平衡之
中。“微寄生”泛指各种侵害人体的致病微生物,“巨寄生”为对人类能够
开展战斗、抢劫和收税等活动的天敌,包括各种大型动物和其他族群或
阶级,主要为其他族群或阶级,比如征服者、统治者等。自然的变迁和
人类活动往往会导致其中的一方过度发展,使原有的均衡遭受威胁,而
一旦这种均衡被打破,人类的生命也就面临着难以延续的危机。不过人
体的自然免疫力、人类的理性以及自然的有机调节能力又会形成某种合
力指向修弥和维持这种均衡。所以人类的成长,尽管多有波折,但总体
上保持着发展之态势。其次,微寄生与人类宿主之间,主要依靠生物的
自然调适能力,双方才长期维持一种内涵上不断变化但却不失均衡的关
系。这种自然调适可能是为了避免物种的两败俱伤而形成,因为微寄生
如果过分肆虐,则有可能找不到下一个宿主而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从
而中断传染链。所以,传染病在同具有一定规模的人群接触后,其毒力
和致死力会逐渐减弱,以免与人类同归于尽,从而确保在宿主族群中的
永续寄生;而痊愈的宿主一旦增加,即会提高族群的集体免疫力,促使
传染病从流行病转变为地方病乃至儿童病,比如天花、麻疹、流行性腮
腺炎等。不过,这类疾病的形成,必须以人口聚居规模的扩大为前提,因为,只有在数千人组成的社群中,大伙交往的频繁足以让感染不间断地由某人传到另一个人身上,它们才能存在。所以,目前这种幼儿疾病
遍布全球的现象,是经过好几千年才形成的。第三,虽然人类与微寄生
之间总体上总能维持某种均衡,但具体到不同时段和地区,这种均衡实
在非常脆弱,人类任何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改变、生产能力的提升和
交通的发展等,均有可能导致均衡的破坏。其中又以以下三种变化影响
最大:1.人类舍渔猎而就农业生产;2.人口不断增长与集中,人口密度
的增加以及城居生活方式的出现;3.交通工具与运输能力的改进,引发
洲际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频繁。这些人类本身的行为,一般都会引
起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并最终促使人类与微寄生原有的平衡经受新的
考验甚至崩溃。因此,疾病史研究与自然生态史密不可分。第四,尽管
几乎所有传染病模式的改变,均由人类自身的行为所引起,但在近代医
学和公共卫生制度出现和确立之前,人类与微寄生之间形成的稳定关系
基本是依靠生物自然调适机制完成的。作者认为,传统医学理论大致说
来是经验主义的,并极端地教条化,“经验每每被牵强地套用既有理论
术语来加以解释,而治疗方法因而也歧义互见”,而且“很少有人能付得
起昂贵的医疗费用”。所以,“即便是最出色的医疗也对疾病无能为力,甚至还妨碍康复”。
循着以上思路来考量中国历史,相信会引发我们对许多历史现象的
重新思考。比如,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但现代认为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长江流域却长期处于后进状态,其缘由
是否跟南方的疾病梯度较高关系密切?又如,魏晋时期和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大的分裂时期,而这几个时期恰好是中国历史上疫
病的高发期,同时也是欧亚大陆传染病模式动荡调整时期,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有某种必然的联系?若有联系,究竟是分裂促发的瘟疫,还是瘟
疫阻碍了统一?再如,清代人口的高速增长,除了现有的众多解释外,是否与十六七世纪以来世界性的传染病模式日趋稳定有关,或者还有清
代医药整体水平提高的功劳?以上种种,显然只有等待我们对中国疾病
史做出较为专深的研究后,才有可能获得相对满意的回答。
当然,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东方世界,疾病社会史研究还明显不
够深入细致的情况下,撰写这样一部从宏观上把握疫病与人类历史发展
关系的著作,危险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我们在书中也很容易发
现,作者的论述常夹杂着假设和旁证,有时还包括某些想象的成分。在
不少的细部研究上,尤其是关于中国的部分,还多有误会。比如,由于
作者基本不了解甚至误解中国医学19世纪以前在对付温病[5]
和接种“人
痘”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本书中有关中国传统医学对人口增长作用的
认识显得有过分夸大自然调节作用而无视人为因素之嫌。另外,其赖以
为基础(指中国部分)的疫情年表,也显得过于粗糙。对于细节的错
误,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已通过译注的方式做了辨析。尽管如此,这
些微瑕仍不足以影响本书的重要价值,或许,其价值本不在于呈现出多
少具体的历史真相,而是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独特研究视角。
对于这样一部世界史学界的经典之作,中国史学界特别是大陆史学
界的关注度显然远远不够,尽管中译本本来就姗姗来迟,但就是迟来的
译本,至今在大陆也未能、实际也难以拥有较多的读者。因此,在大陆
出版中译本就显得十分必要。繁体字中译本总体上是较为忠实原文的不
错的译本,译者杨玉龄先生系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对书中有关医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内容有较好的把握,译文也显得颇为精当。但其对历史知
识则相对隔膜,故而以专业历史研究者的眼光视之,译文在历史名词乃
至历史事件的把握方面,仍有不小的改进空间。而利用最新的研究对书
中的相关问题做出辨析这样的工作,自然更是无从谈起了。另外,该译
本在标题方面对原书做了不少调整,虽然比较醒目,但似乎也有不够忠
实原文之处。特别是完全删去原书的注释,颇让人感到美中不足。故
此,我们感到仍有重新翻译的必要。当然,在译完初稿后,我们参考了
这一译本,并借鉴了其中不少精当的译法,特此说明并致以诚挚的谢
意。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始终以忠实原文原意为第一要义,原著行文流
畅而优美,不禁令人深感钦羡,尽管也做了尽可能的努力,但限于时间
和水平,我们的译笔显然仍远无法与原文畅美的笔调相提并论,同时还
可能存在不少不足乃至误译之处,这是需要向读者致歉并敬请读者不吝
赐教的。
本书从开始翻译到现在出版,经历了不少波折,也为我们留下了不
少需要感谢的人物。如果没有中国人民大学夏明方和北京师范大学梅雪
芹两位教授提议和促成,本书的译成和出版,或将是不可能的事。在翻
译的收尾阶段,汪敏(Katherine Robinson)和吾妻惠清楼两位女士在文
字的校订方面做了不少重要的工作。在后来几次修订中,叶慧女士、梅
雪芹教授和孙健先生给予了许多十分有益的指教。另外,第六章的修订
曾得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张瑞和张华的襄助。对于以上师友和同
道的情谊和帮助,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当然,本书翻译中存在的
问题均由译者负责。长江后浪推前浪,人类的知识和对具体问题的认识无疑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不断更新,但凭借知识的累积和个人的敏锐与智慧提出的某些
认识维度和思考方式却似乎可以超越知识更新本身,具有长久的魅力。
二十多年过去了,对书中那些具体的观点,相信不同领域的专家大概都
可能提出异议,不过,书中揭示的研究视角与基本原理,不仅在过去较
深地影响了世界史学的发展,而且也是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者,特别是
医疗社会史和环境史的研究者不应忽视的。在世界范围内,疫病社会史
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二十多年来,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就。不
过就中国史而言,似乎才刚刚兴起。[6]
希望麦克尼尔这部大作的再版,不仅有利于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而且可以促进更多人重新省思认识和
探讨历史的视角与方法。
余新忠
2004年6月初稿于京都大学国际交流会馆
2009年6月修改于南开大学
今年4月下旬的一天,我无意从网上得悉本书的作者麦克尼尔先生
已经于去年7月8日仙逝。一代史学宗师的故去,自然会让如我这般深受
启益的后学晚进感到哀伤。不过,更令我感怀的,似乎还是他再也不可
能知道,由他推动兴起的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影响远播,业已成为中国
学界颇受瞩目的新兴研究,21世纪以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早已不再是
他写作此书时几无成果可资利用的情景了。八年前,麦克尼尔先生为该
书的中文版慷慨赠序,在感动和深受鼓舞之余,也不免对作者对中文学界的相关研究依然缺乏了解感到些许遗憾。想起这些,并不是觉得作者
有什么不妥,而是感到,中国学术虽然近些年取得了不小的发展,但放
眼国际,无疑还远没有可以沾沾自喜的资格。
这本完成于40年前的著作,在国际学术界取得了广泛而深远的影
响,不过其对中文学界的影响可谓姗姗来迟,直到20世纪末,才首次出
版了中文繁体字版,简体字版的正式面世也才不过几年时间。但令人感
到欣慰的是,近些年来,该书在国内学术界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注目。
十余年来,国内已经有三家出版社相继购买译著版权,大概就是很好的
证明。这对于我们译者来说,在感到荣幸和欣喜的同时,也更多了一份
对作者的敬意,以及对进一步推动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向前发展的责任
和期盼。
承蒙中信出版社和马晓玲编辑的见爱,本译文有机会再次出版。为
此,马编辑做了大量工作,敦促我们尽可能全面地修正译文。在译文的
修正中,我的研究生宋娟、朱绍祖和王沛珊给予了重要帮助,谨此说明
并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余新忠
2017年7月19日又记于津门寓所
[1]陈秋坤:《人类造就了瘟疫——介绍麦克尼尔教授新著:〈瘟疫与
人〉》,载陈胜昆:《中国疾病史》《附录》,台北:自然科学文
化事业公司,1980年。
[2]《疫病と世界史》,佐々木昭夫译,东京:新潮社,1985年。[3]《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杨玉龄译,台北:天
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
[4]此处内容见陈秋坤:《人类造就了瘟疫——介绍麦克尼尔教授新
著:〈瘟疫与人〉》,载陈胜昆:《中国疾病史》《附录》,第
251页。
[5]温病是中国传统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是指外感热病,即感
受温热病邪所导致的疾病,包括现在的各种疫病和感冒等。
[6]参阅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
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世纪明清疾
病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中国疾
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年第
4期。中文版前言
在我写的所有著作中,无论在历史学家和医生们那里,还是在普通
民众中,《瘟疫与人》受欢迎的程度都是最高的。当它于1976年首次出
版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别的什么书在讨论传染病在整体上对人类历史的
影响。尽管我常常依靠推论来重构交通的变迁如何导致传染病的跨区域
传播,但要解释这种疾病的发生机制,以及测算出人口伴随幸存者血液
中的抗体的增加而恢复增长所需要的时间,则只能依赖传染病学上的最
新进展。
疫病的历程揭示了人类事务中曾被忽视的一个维度;在本书付梓之
后不久,由于偶然的原因,艾滋病引发了广泛的公众注意力。两相结
合,扩大了《瘟疫与人》的读者群,且至今仍在美国及其以外的读者中
深受欢迎。
中国的读者将会看到,为了尽力发掘中国的瘟疫史料,我只能求助
于他人。我不懂汉语,但知道有两本专业的百科全书和所有的正史都谈
到了(中国)瘟疫暴发的地理区域和严重程度。那时还是一名研究生的
约瑟夫·H.查(Joseph H.Cha)教授热心地查阅了这些中国典籍,并把他
查阅的结果整理成一个详细的附录,时间从公元前243年直到公元1911
年。这些工作无疑表明了瘟疫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并使我有可能结
合黑死病时代及其后亚欧大陆其他地区的情形,对此做出适当的推断。
我希望并且相信这个译本将激发今日中国的一些读者,能比我更为细致地来探讨疾病这一类因素在自然环境中的角色,更正和充实我所写
下的结论,并将对中国历史的科学研究提升到堪与前人比肩的水平做出
贡献。
威廉·H.麦克尼尔
2009年6月19日致谢
本书初稿完成于1974年春夏,于1975年春季校订完稿。此间,书稿
曾分送下列专家以求教正:亚历山大·本尼希森(Alexandre
Bennigsen)、詹姆斯·鲍曼(James Bowman)、弗朗西斯·布莱克
(Francis Black)、约翰·Z.鲍尔斯(John Z.Bowers)、杰尔姆·贝勒比尔
(Jerome Bylebyl)、L.沃里克·科普莱逊(L.Warwick Coppleson)、艾
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Alfred W.Crosby,Jr.)、菲利普·柯廷(Philip
Curtin)、艾伦·德布斯(Allen Debus)、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何炳棣(Ping-ti Ho)、拉弗内·库恩克(Laveme Kuhnke)、查尔斯·莱斯莉(Charles Leslie)、乔治·勒罗伊(George Leroy)、斯图
尔特·拉格兰(Stuart Ragland)、康纳德·德劳利(Donald Rowley)、施
钦仁(Olaf K.Skinsnes)、H.伯尔·斯坦巴克(H.Burr Steinbach)、约翰·
伍兹(John Woods)。本书还受益于美国医学史协会1975年5月召开的
一次小组讨论会,在这次会上,索尔·贾科(Saul Jarcho)、芭芭拉·G.
罗森克兰茨(Barbara G.Rosenkrantz)、约翰·达菲(John Duffy)以及
京特·里斯(Guenter B.Risse)等就他们阅读的部分给予了指教。随后,在1975年秋季,芭芭拉·多德韦尔(Barbara Dodwell)和休·斯科金
(Hugn Scogin)分别校阅了本书的第四章和中文资料部分;他们还共
同修正了本人对有关黑死病传播方式的理解。幸运的是,在本书付梓的
最后时刻,这些修正得以体现于文中。
上述情况表明,本书的很多论断和结论多少带有尝试的性质,有待在疫病方面通过对中文以及其他古代文献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后加以进
一步的完善。诸多建议者的指正使本书在许多细节上得以改进,并使我
避免了许多愚蠢的错误;当然,不用说,全书所有的内容,包括许多遗
留的谬误,均由本人自己负责。
承蒙小约瑟·玛西基金会的慷慨赞助,我方能摆脱一些日常的事务
性工作而专事本书的写作。还应感谢爱德华·特纳(Edward Tenner)博
士帮助查阅有关的西文资料,感谢约瑟夫·查博士帮助查阅有关中文和
日文资料,并汇编了附录部分的中国疫情年表。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
的成稿将费时更多,尤其是书中有关远东的论述将会更为粗疏。感谢马
尔尼·维特(Marnie Veghte)以令人满意的准确性和令人钦佩的速度,将书稿打印了两次。道布尔迪(Doubleday)旗下的安科尔(Anchor)
出版社的查尔斯·普里斯特(Charles Priester)提出了一些非常有针对性
的问题,使我在原稿的基础上做了重要的修改和提高。
对上述诸位,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威廉·H.麦克尼尔
1975年12月15日引言
缘起
将近20年前,为撰写《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The Rise of
the West:A History of Human Community)一书,我开始涉猎西班牙征服
墨西哥的历史,以充实相关史料。众所周知,埃尔南多·科尔特斯
(Hernando Cortez)凭借其区区不足600人的兵力就征服了人口数以百
万计的阿兹特克帝国(Aztec Empire)。如此少的兵力何以能横行异
域?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通常的解释似乎都很难令人信服。如果说蒙特祖玛[0]
和他的同盟者
开始时将西班牙人视作神明,然而一经直接接触,现实情况就自然会让
原有的迷信不攻自破;如果说西班牙人的战马和枪炮在初次交战时令对
手惊慌失措,那么一旦短兵相接,这两种武器的局限性不久也自会暴露
无遗——当时的枪炮其实相当原始;当然,科尔特斯联合其他印第安民
族的“以夷制夷”之术对胜局意义重大,然而除非科尔特斯的那些墨西哥
的印第安人盟友认定他一定取胜,又怎么可能与他结盟?
实际上,征服墨西哥的传奇只不过是更大的谜团中的一部分——不
久,皮萨罗(Pizarro)同样不可思议地征服了南美的印加帝国。相对而
言,越洋抵达新大陆的西班牙人并不多,然而他们却把自己的文化成功
地强加给了人数多得不成比例的美洲印第安人。欧洲文明固有的魅力以
及西班牙人无可否认的技术优势似乎并不足以解释古老的印第安生活方式和信仰的全面崩溃。譬如,为什么墨西哥和秘鲁的古老宗教消失得如
此彻底?村民为何对那些多少年来一直庇佑他们的土地丰收的神祇和祭
典不再虔诚了?或许,在基督教教士们的心目中,基督教的真理性是如
此显而易见,以至他们认为使几百万印第安人成功皈依根本就无须解
释,但事实上,他们的布道以及基督教信条和仪式的内在吸引力似乎并
不足以解释这一切。
不过,在有关科尔特斯征服史的诸多解释中,有一项不经意的说法
(我已记不起具体出处了)令我茅塞顿开,而后通过进一步缜密思考这
一解释及其背后的含义,我的新假说逐渐变得合理而有说服力了。因
为,就在阿兹特克人将科尔特斯的军队逐出墨西哥城,并予以重创的那
天晚上,天花这种传染病正在城内肆虐,那位刚刚率领阿兹特克人对西
班牙人展开进攻的将领和好多人一道死于那个“悲伤之夜”(noche
trista,西班牙人后来以此称呼这场疫病)。这场致命的传染病所造成的
毁灭性后果恰好解释,为什么阿兹特克人没有乘胜追击,而让敌人得以
喘息并获得卷土重来的机会,进而联合其印第安盟友完成对城市的合
围,赢得最后的胜利。
值得关注的,还有这场只杀死印第安人、对西班牙人却毫发无损的
疫病对当时人们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对这种明显的偏袒,当时只能从超
自然的角度加以理解,很明显,在这场战争中哪一方得到了神明的助佑
似乎已不再是问题。在西班牙人的神祇展现了其“超自然的能力”之后,那些以古老的印第安神祇为中心构建的宗教、祭祀制度和生活方式也就
很难维持下去了。难怪印第安人会如此温顺地接受基督教,并向西班牙人俯首称臣。显然,上帝站在西班牙人一边,而且以后每一场来自欧洲
(不久后也来自非洲)的传染病的造访,都在重复这一经验。
可见,传染病一边倒地只对美洲印第安人造成伤害这一史实,为我
们理解西班牙何以能轻易征服美洲(这种征服不仅是军事上的,同时也
是文化上的)提供了一把钥匙。不过,这一假说一经提出,马上就会引
发相关问题:西班牙人何以且何时获得了这种使他们在新大陆如入无人
之境的免疫力?为什么印第安人没有属于自己的本土疫病以对付入侵的
西班牙人?只要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随之而来的就将显现一个尚
未被历史学瞩目的人类历史中的新领域,即人类与传染病的互动史,以
及当传染病逾越原有界域侵入对它完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时,所造成的
深远的影响。
由是观之,世界历史其实已经提供了许多与十六七世纪发生于美洲
的这一幕类似的事例。本书就将描述这些致命性遭遇的梗概。我的结论
可能会使许多读者大感意外,因为在传统史学中很少受到关注的事件却
将在我的叙述中占据核心地位。之所以如此,主要就在于,长期以来那
些学识渊博的学者在皓首穷经于各种遗存的文献时,对于人类疾病模式
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缺乏敏锐的洞察力。
自然,传染病首次袭击某族群的著名案例从来没有被欧洲人遗忘,14世纪的黑死病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其次是19世纪的霍乱大流行,后者
虽然破坏性大为降低,但因更接近于现代而留下了比较完整的记录。尽
管如此,历史学家却从未将其归为重大疫病暴发的普遍模式,因为那些
人类与疫病惨烈遭遇的案例都已湮没于时间隧道中。那时资料残缺不全,以致事件发生的规模与意义都很容易被忽略。
在解读古代文献时,历史学家自然会受到他们自身疫病体验的影
响。经历过各种病史的现代人,已对那些常见的传染病拥有了相当程度
的免疫力,这使他们能很快地终止任何一般性疫病的流行。生活在这样
的背景下,受过严格训练的历史学家只能认为那些疫病造成大规模死亡
的说法未免夸张。事实上,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同样的疫病在熟悉它
并具有免疫力的人群中流行与在完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中暴发,其造成
的后果差别巨大,以往的历史学家才未能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确实,如果现代医药出现之前的传染病均与欧洲的传染病模式并无二致,那么
又有什么必要关注疫病的历史呢?因而,历史学家也往往以一种不经意
的笔调处理这类记载,一如我在那本描述科尔特斯征服史的著作中所读
到的那样。
于是疫病史便成了偏好“掉书袋”的老学究们的专利,他们热衷于就
手头掌握的资料摘录一些实质上并没有什么意义的信息。不过,毕竟还
有黑死病以及其他一些事例,在这些事例中,军营里突发的疫情不仅扭
转了战局,有时甚至决定了战争最终的胜负。这类插曲自然不大可能被
遗漏,但它们的不可预见性却使历史学家深感不自在。我们都希望人类
的历史合乎理性、有章可循,为了迎合这一普遍的愿望,历史学家也往
往会在历史中刻意突出那些可预测、可界定且经常也是可控制的因素。
然而,当流行病确实在和平或战争中成为决定性因素时,对它的强调无
疑会弱化以往的历史解释力,故而史学家总是低调处理这类重要的事
件。不过,还是有诸如细菌学家汉斯·津瑟(Hans Zinsser)这样的圈外
人士,搜集一些表现疾病历史重要性的史料,扮演了抬杠者的角色。他
在那本极具可读性的大作《老鼠、虱子和历史》(Rats,Lice and
History)中,描绘了斑疹伤寒的暴发如何经常打乱国王和将领的如意算
盘。但是,这类著作并未试图将疾病史纳入更宏大的人类历史的背景下
考察,与其他著述一样,它们仍将疫病的偶然暴发视为对历史常态突然
而不可预测的扭曲,本质上已超出史学的诠释范围,因而也就很难吸引
以诠释历史为本业的职业历史学家的视线。
本书旨在通过揭示各种疫病循环模式对过去和当代历史的影响,将
疫病史纳入历史诠释的范畴。我在此提出的许多猜测和推论仍是尝试性
的,对它们的证实与修正还有待有关专家对语言晦涩的古代文献做进一
步地爬梳。这类学术性的作品既需要提出一个正面的主题予以确证,又
需要提出一个反面的靶子以便有的放矢,我在本书所做的推理与猜测应
该符合这一要求。与此同时,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引起读者关注那
些人类历史的传统观念与当下认识之间存在的鸿沟。
除了我必须描述的细节外,想必大家都会同意,更加全面深入地认
识人类在自然平衡中不断变动的地位,理应成为我们诠释历史的组成部
分。而且毋庸置疑,无论过去与现在,传染病都在自然平衡中扮演着至
关重要的角色。
关键概念
在叙述故事之前,对寄生、疾病、疫病以及相关概念的解释或许有
助于避免读者的混淆。对所有的生物来说,疾病和寄生物几乎无所不在。当寄生物从某个
有机体身上成功地搜寻到食物时,对后者(宿主)而言,就是一场恶性
感染或疾病。所有的动物都以别的生物为食,人类也不例外。对于人类
的觅食以及觅食方式变迁的论述充斥于经济史的著述中,相反,避免为
别的生物所食的问题却比较少见,这基本是因为人类自从远古时代起,就不怎么畏惧狮子和狼之类的大型食肉动物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
以认为,人类大多数的生命其实处在一种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
巨寄生构成的脆弱的平衡体系之中,而所谓人类的巨寄生则主要是指同
类中的其他人。
微寄生物(microparasites)是指微小生物体(病毒、细菌或多细胞
生物),它们能在人体组织中找到可供维生的食物源。某些微寄生物会
引发急性疾病,结果,或者很快杀死宿主,或者在宿主体内激发免疫反
应,导致自己被消灭。有时,此类致病生物体不知怎的寄生到某个特殊
的宿主身上,使后者成了带菌者,能够传染给别人,自己却基本不受影
响。而且,还有一些微寄生物往往与人类宿主形成比较稳定的平衡关
系,这种感染无疑会消耗掉宿主一定的体能,但却无碍于宿主正常机能
的发挥。
巨寄生物(macroparasites)也呈现出类似的多样性。有些会迅速致
命,像狮子和狼捕食人或其他动物那样;另一些则容许宿主无限期地生
存下去。
早在远古时期,人类捕猎的技巧和威力就已超越了其他食肉动物。
于是人类攀上了食物链的顶端,也就很少再有被天敌吞食的危险了。不过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同类相食几乎构成人类相邻族群间相互关系
的重要内容,这意味着人类作为成功的狩猎者,几乎与狮、狼处于同等
的水平。
后来,当食物的生产成为某些人类社群的生活方式时,一种较温和
的巨寄生方式才成为可能。征服者从生产者那里攫取并消费食物,由此
成为靠生产者为生的新型寄生者。尤其是那些出现在土地肥沃地区的事
实表明,人类社会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巨寄生模式是完全可能的。事实
上,早期文明就是建立在这一模式之上,胜利者只是从臣服族群那里掠
取部分收成,而留下足够的粮食让被掠夺者年复一年地生存下去。在早
期阶段,这种人类文明的巨寄生基础还相当严峻和明确,后来随着城市
和农村间互惠模式的日趋发展,只是上缴租税所体现的寄生单向性才逐
步消除。尽管如此,在开始阶段,那些饱受压榨的农民,供养着神甫、国王以及跟随这些阶层生活在城里的仆从,除了受到某种不确定的保
护,以避免遭受其他更加残忍和短视的掠夺者的侵扰之外,他们所得到
的回报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食物与寄生物之间的共生共存关系,曾经巩固了人类的文明史,类
似的情形亦可发现于人体之内。白细胞是人体内防御疫病感染的主要元
素,它们能够有力地消解人体的入侵者。它们不能消化的部分就变成了
寄生物,反过来消耗人体内对它们来说有营养的东西。[1]
然而,就入侵特定人体的特定生物来说,这不过是影响其能否顺利
侵入并在其中繁殖的极端复杂的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事实上,尽管
医学在过去百年间成就辉煌,但还是无人能完全说得清它们间的相互关系。在机体组织的各个层次(分子[2]
、细胞、生物体和社会)上,我们
都可以碰到均衡模式。在这种均势中,任何来自外力的变动都会引发整
个系统的补偿性变化,借以最大限度地减缓全面的震荡,当然,如果变
化突破了特定的“临界点”,也会导致原有体系的崩溃。此类灾难,既可
能将原系统分解成更简单、更微小的单元,这些单元又都各自形成自己
的平衡模式;或者相反,将原有相对较小的单元组合成更大或更复杂的
整体。实际上,这两个过程也可能同时共存,就像大家所熟悉的动物消
化过程一样,捕食者把食物中的细胞和蛋白质分解成更小的单元,只是
为了把它们合成为自身体内的新蛋白质和新细胞。
对此类机制的解释,显然简单的因果分析远远不够。既然同时存在
许多变量,它们又不间断地交互作用,而且还以不规则的频率改变它们
的规模,因此,如果我们只是将注意力集中到某个单一的“原因”上,并
尽力将某个特定的“结果”归因于它,结果往往是引人误入歧途。对多过
程的同时态研究或许有助于我们的理解更接近真实,但这样做,无论在
观念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都存在巨大的困难。对大部分组织层次而言,仅仅是对组织模式的确认及观察其存在或崩解,就让人感到有些力所不
逮了,更何况在包括社会在内的某些层次上,连哪种模式值得关注或者
能够被可靠地观测,也都存在深刻的不确定性和争议。不同的术语会引
导人们关注不同的模式,然而,要想找出一个逻辑上富有说服力并能为
各方所接受的试验方案,用以测定一套术语是否优于另一套,通常是不
可能的。
然而,缓慢的进化过程不仅适用于人类的身体,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及其符号体系,因此,当有些问题无法依靠逻辑来确定时,生存定
律终将出面解决。对人类来说,那些能将我们的视线引向所处环境中利
害攸关方面的术语,无疑具有巨大的存在价值。正是基于相互交流和沟
通的能力,人类才得以主宰生物世界。然而没有哪一种术语体系有可能
穷尽或涵盖我们所处情境的每一个方面。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己所能地运
用我们所继承的语言和概念,而不必为寻求一个能在任何时空环境下让
任何人满意的所谓“真理”而枉费心机。
正如语言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一样,疾病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如此。
假如史书中的许多圣人生活在今天的美国,恐怕很难逃脱因“精神不正
常”而被送入精神病院的命运;相反,被狩猎先祖们视为生理残疾的近
视眼和味觉迟钝,在今天却不会被认为与健康理念有冲突。不过,尽管
存在这样的历史性差异,“疾病”概念的核心内容仍是确定而普遍适用
的。一个人若因身体机能紊乱而无法完成预期的任务,这人就将被同类
视为“有病”,而在这类生理机能紊乱中,又有许多源自与寄生物的接
触。
毫无疑问,不同的人体和社群对同样的传染病所表现出的敏感程度
和免疫水平相当不同。这种差别部分缘于遗传,更多则是与以前是否接
触过入侵生物体有关。[3]
不断调整对疾病的抵抗力,并不只在个体进
行,在整个族群内部也同样如此。因此,他们对疾病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也会相应地改变。[4]
正如个人与群体为对付传染病而不断进行机能调整一样,各种致病
微生物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典型的,比如这一环境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虽然不是全部)就是宿主体内的状况。毕竟,对于包括病
原体在内的所有寄生体来说,都必须经常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宿主几
乎都是互不相连的独立个体的情况下,它们如何才能成功地转移?
人类宿主和病原体之间在经历了许多世代,以及数量可观的族群的
长期相互调适后,会产生一种能让双方共容共存的相互适应模式。一个
病原体如果很快杀死其宿主,也会使自己陷入生存危机,因为这样一
来,它就必须非常迅速和频繁地找到新的宿主,才能确保自身的存活与
延续。反过来,如果一个人的抗感染能力足以让寄生物无处藏身,显然
也会对病原体造成另一种生存危机。事实上,正是由于上述这类极端情
形的出现,使得许多与疾病为伴的关系未能延续至今;而一些曾经恶名
昭著的病原体,由于全球范围内普遍的疫苗注射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的
推行,正在濒临灭绝——如果某些踌躇满志的公共卫生官员的言论是可
以信任的话。[5]
对寄生物与宿主来说,较为理想的状态通常(但非必然)是,两者
都能在对方存在的情况下无限期地生存下去,并且互相不会对对方的正
常活动造成重要的损害。这类生物平衡的例子不胜枚举,譬如,人的肠
道下端通常带有大量的细菌,但这并不会引起明显的病征。在我们的口
腔中和皮肤上,也附着了众多通常并不会对我们造成实质性影响的微生
物,其中有些可能有助于消化,另一些则被认为能够防止有害生物在我
们体内的恣意繁殖。不过,一般来说,对于或许可以称之为“人类感染
生态学”的这类论题,我们目前还缺少确凿有力的数据来加以论证。[6]
不过,从生态学的观点看,我们似乎仍可以说,很多最致命的病原体其实还未适应它们作为寄生物的角色。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依然处在
与人类宿主的生物调适进程的早期阶段;当然,我们也不应就此假设,长期的共存必定导致相互间的和谐无害。[7]
譬如,引发疟疾的疟原虫可能是人类(甚至前人类)最古老的寄生
物,[8]
但它至今仍给人类宿主带来严重的使人四肢虚弱的发热病。至少
有四种疟原虫能感染人类,其中又以镰状疟原虫(Plasmodium
falciparum)最具杀伤力。不难想见,由于镰状疟原虫侵入人体血管相
对较晚,所以它们还无法像其他疟原虫那样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人类宿
主。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宿主与寄生物之间的进化调适,还会因宿主
的多样性而更加复杂,而寄生物为完成生命周期又不得不适应宿主体内
的环境。而且,有利于疟原虫长期寄居于人类红细胞中的调适,对其实
现在不同宿主间的成功转移并无助益。
事实上,在通常主导性的转移模式中,人体一旦为疟原虫感染,红
细胞就会成百万地周期性坏死,由此导致宿主怕冷发烧,并让疟原虫得
以在血管中自由运动,直到一两天后,它们重新寄居在新的红细胞里。
这一过程会给宿主带来热病和四肢疲软的症状,但同时也会让疟原虫以
一种独立自由的形式趁着疟蚊饱餐人血时“搭便车”转移到别处繁衍。疟
原虫一旦进入疟蚊胃部,就会展示出不同的行为方式,最终完成有性生
殖(sexual replication)。结果是几天后,新一代的疟原虫就会游移到疟
蚊的唾液腺里,以备在疟蚊下次“就餐”时侵入新的宿主体内。
就目前能够观察到的情况看,疟原虫在被疟蚊以如此巧妙的方式从
一个宿主转移到另一个宿主时,并不会对疟蚊造成伤害。疟原虫生活史的完成有赖于疟蚊体内组织的滋养,但这对疟蚊的寿命及其活力却并无
不利的影响。这样说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疟原虫要被成功地转移
到新的人类宿主身上,携带它的疟蚊必须拥有足以供自己正常飞行的精
力。一个沉疴在身的疟蚊不可能将疟原虫成功运送到新的人类宿主以助
其完成生活史。但是,一个身体虚弱、浑身发烧的病人却丝毫不会妨碍
疟原虫完成其生活周期。因此毫不奇怪的是,这种古老的传染病对疟蚊
毫发无损,却一直维持着对人类的杀伤力。
人类其他一些重要的传染病也像疟疾一样,病原体必须让自己适应
多个宿主。假如人类之外的宿主对这类寄生物更为重要,其适应性行为
的重心将会集中于同非人类宿主达成稳定的生物平衡上,一旦它们侵入
人体,则可能对人类造成剧烈的伤害。腺鼠疫(bubonic plague)就是这
样,引起这种疫病的鼠疫杆菌(Pasteurella pestis)通常只感染啮齿动物
以及它们身上的跳蚤,偶尔才染及人类。在穴居啮齿动物群体当中,这
种感染可以长期延续下去。鉴于同一洞穴中可能混居着不同的啮齿动物
宿主,这类感染及康复的模式必定极端复杂,我们对此至今也未能完全
了解。然而,不管怎样,对生活于“地府”中的某些穴居啮齿动物来说,腺鼠疫就像城市居民习以为常的天花、麻疹一样,乃一种常见“儿童
病”(childhood disease)。换言之,啮齿动物与这种寄生杆菌之间已经
形成相当稳定的适应模式。只有当疾病侵入从未感染过该病菌的啮齿动
物和人群时,才会酿成惨剧,就像历史上曾令我们的祖先倍感惊恐的腺
鼠疫大暴发。
由于血吸虫病(通过钉螺传染)、昏睡病(通过采采蝇传染)、斑疹伤寒(通过跳蚤和虱子传染)以及其他一些疾病的病原体拥有两种甚
或更多的宿主,以致它们与宿主的适应模式极为复杂。因此,这类疾病
对于人类来说,仍然十分可怕。斑疹伤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品系相
同或近似的引发斑疹伤寒的立克次体(rickettsial organisms)能稳定地
寄居于某些种类的壁虱身上,代代延续而且基本相安无事;当老鼠及其
身上的跳蚤被感染后,虽会发病,但可以自行康复,也就是说,它们在
感染后可以通过自我调适将入侵的病原体拒于身外。但是,一旦伤寒寄
生菌转移到人体及人身上的体虱,总会导致体虱毙命,而对人来说,也
常常是致命的。上述模式暗示斑疹伤寒病原体曾存在这样一种渐进式的
转移:从最初与壁虱稳定的共存,再到与老鼠及其身上跳蚤的次稳定调
适,最后到与人及其体虱间的极端不稳定适应。这似乎也意味着该病原
体直到晚近才感染人体及其体虱。[9]
当然,也有一些人类疾病并不需要传播媒介便可直接在人类不同宿
主之间迅速传播。结核病、麻疹、天花、水痘、百日咳、流行性腮腺炎
和流行性感冒等都属于这类疾病。事实上,它们也是现代人极为熟悉的
传染病。除了结核病和流行性感冒,人类只要被这类疾病感染一次,即
可获得长期乃至终身的免疫力。于是,这类疾病通常只感染孩子。这在
那些没有采用疫苗接种或其他人工方法改变天然的疾病传播方式的地
区,依然如此。
这种儿童病一般不会特别严重,通常只要精心护理就可以康复。然
而当其侵入以前从未接触过它们的族群时,则可能导致大面积的发病和
死亡,而且正值盛期的青年人比其他年龄层的人更易感染并导致死亡。换言之,一旦某一“处女”族群初次接触这些传染病,极有可能使整个社
会遭受严重的甚至毁灭性的打击,就像天花和随后的其他疾病对阿兹特
克帝国和印加帝国所造成的影响一样。
毫无疑问,无论是慢性传染病、精神紊乱,还是老年性功能衰退,它们对今天人类造成的痛苦会更多,它们构成了一直存在于人类生活中
的某种“背景杂音”(background noise)。近年来,随着人们的日趋长
寿,这种痛苦变得更加显著。不过,我们祖先所经历的疾病模式与我们
今天熟悉的情况根本不同。在先祖那里,不时暴发的瘟疫不论以何种形
式出现,都会给他们造成恐惧和无时不在的震慑力。尽管我们无法得到
统计和临床资料(即便到19世纪也是零星的),以对19世纪以前瘟疫的
发生情况做出准确说明,比如何种瘟疫在何时何地杀死了多少人,但是
我们仍有可能把握这些疫病流行模式的基本变化轨迹。实际上,这也正
是本书的主旨。
[0]Montezuma,阿兹特克帝国皇帝。——译者注(以下除非特别注
明,均为译者注)
[1]请参阅Thomas W. M. Cameron,Parasites and Parasitism,(London,1956),p. 225;Theobald Smith,Parasitism and
Disease(Princeton,1934),p.70。当白细胞破坏侵入人体的细胞结构
时,并不能产生有助人体细胞生成的能量或物质,因此,这个过程
只相当于消化过程的第一阶段。
[2]请参阅Wladimir A. Engelhardt,“Hierarchies and Integration in
Biological Systems”,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Sciences,Bulletin,27(1974),No. 4,p.11—23。Engelhardt把蛋白质一
类复杂分子自我复制的能力归结于分子间作用力量的弱小;他进一
步提出,这些正在强化的有机体总在消耗可利用的能量。从这一观
点上看,人类刚刚完成的跳跃性发展,即利用取自矿物燃料(fossil
fuels)的可用能量,把成百万人口聚集于工业城市的过程,似乎只
是把成百万原子聚合为较大的有机分子这一过程的最近的和最复杂
的展现。的确,正如我们可以想见的,人类城市,因为比起蛋白质
的出现要晚得多也少得多,其结构的精致程度自然不及较大的有机
分子,更不用说细胞和有机体了。但要说同样的法则也适应于我们
生活和活动其中的所有层次的有机体,至少是可以讨论的。
[3]使一类人区别于另一类人的遗传性差异,就疾病抵抗力而言,可能
缘于其先人与特定病原体长期接触所造成的差异。由此产生的基因
对初期感染的那些个体所表现出的或促进康复或延缓康复的不均衡
性,到时将产生对该病的内在抵抗力。这种“物竞天择”般的演化有
时会非常快速;而且,传染越致命,选择也越快。同样严峻的淘选
过程也自然发生于寄生体一方,它们通过基因和行为的调整以趋向
于形成与宿主间更稳定的适应关系。参阅Arno G.
Motulsky,“Polymorphisms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in Human
Evolution”,Human Biology,32(1960),p.28—62;J. B. S.
Haldane,“Natural Selection in Man”,Acta Genetica et Statistica
Medica,6 (1957),p. 321—332。对特定疾病形成抵抗力的基因也
可能对人类产生各种不利影响,因此一个群体的理想状态是“生物
协调的多形性”,这意味着有些人会有抗病基因,而有的人没有。
携带抗病基因的个体比例,将依据对该病抵抗力的选择上的多样性,以及其他可能对人口施加的选择压力的种类而变化。
[4]现代技术甚至使专业人员能够破解某些个体和群体的传染病记录,办法是通过分析血样以确定该个体是否存在“抗体”。这项技术尤其
适用于封闭的小型社会的疾病史研究。参考Francis L. Black et
al.,“Evidence for Persistence of Infectious Agents in Isolated Human
Populations”,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100(1974),p.230—
250。
[5]参阅T. Aidan Cockburn,The Evolution and Eradica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Baltimore and London,1963),p.150。
[6]参阅Theodor Rosebury,Microorganisms Indigenous to
Man(NewYork,1962)。
[7]参阅Theobald Smith,Parasitism and Disease,p. 44—65;Richard
Fiennes,Man,Nature and Disease(London,1964),p.84—102.。
[8]L. J. Bruce-Chwatt,“Paleogenesis and Paleoepidemiology of Primate
Malari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Bulletin,32(1965),p.363—387.
Plasmodium一词,原指生物特性尚不完全清楚的引发疟疾的有机
体,现已成为标准术语。这种有机体实为原生动物,但其形态在生
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有明显的不同。
[9]Hans Zinsser,Rats,Lice and History(NewYork,Bantam edition,1965;
original publication,1935),p.164—171.第一章
狩猎者在人类各族群完成进化之前,必须假定我们的祖先也像其他动物一
样,处在一种自我调适的、微妙的生态平衡之中。其中最显见的一环就
是食物链,在该食物链中,我们的祖先既猎食某些动物,反过来也为别
的动物所猎食。除了大型动物间的这种无可逃避的关系外,我们还应想
见,那些体型微小、通常肉眼无法看见的寄生物,也在我们祖先的体内
寻找食物,并由此成为平衡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命体系的重要因素。
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重构各种相关细节,事实上,即使是人类进化的进
程,对我们而言也依然模糊不清,因为已被发现(主要在非洲)的各种
前人类或类人猿的骨骼残片并不足以供我们构建出完整的故事。非洲应
不会是人类唯一的发祥地,人类的始祖或许也曾生存于亚洲的热带和亚
热带地区,其进化历程应与曾经生活在奥杜威大峡谷(Olduvai Gorge)
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其他地区的猿人(在这些地区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
的骨骼和工具)大致平行。
然而,人类不具有浓密毛发的事实清楚地表明,他们曾生活在温度
很低但又从不低于冰点的温暖的气候环境中。在重叠视野基础上形成的
准确的深度知觉能力[1]
,有抓握能力的手,以及与至今仍主要栖息于树
上的猿、猴之间明显的亲缘关系,表明人类祖先也曾生活在树上。祖先
特定的齿列显示我们曾是杂食动物,坚果、水果、幼虫或许还有某些植
物的嫩苗都比动物的肉更为重要。但是,疾病和寄生物的情况又是怎样
的呢?
[1]深度知觉指个体对其视野以及视野内的物体在三维空间上的反应能
力。人类与寄生物
今天流行于猴子和树栖猿的传染病可能与伴随远古人类祖先的寄生
物种群相似。尽管一些重要的细节仍不得而知,但至少可知侵扰野生灵
长类的寄生物的种群多得惊人。除了各种恙虫、跳蚤、壁虱、苍蝇和蠕
虫之外,野生猿、猴身上显然还寄居着一大堆原虫、真菌和细菌,更不
必说还有150种以上的所谓的“肢节病毒”(arbo-viruses,即arthropod-
borne viruses的简称。它们往往借助于昆虫或别的节肢动物,在温血宿
主之间转移)了。[1]
在感染野生猿、猴的微生物中,有15~20种[2]
疟原虫,寄生于人类
的疟原虫通常只有4种,但猿类仍可能被人类的疟原虫所感染,同时,人也有可能感染来自猿猴的某些疟原虫。除了各种疟蚊能在热带雨林的
树冠层、树干层和地面层之间形成自己的专属栖息地外,[3]
这类种属差
别,也表明了有关三者之间——灵长类、疟蚊和疟原虫——经历过一段
相当长时期的相互调适。不仅如此,根据当前的疟疾和已知古时疟疾的
地理分布情况来看,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似乎一直是这种寄生形式进化
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中心。[4]
在地球上各类自然环境当中,热带雨林可谓是最富生物多样性的地
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干燥、寒冷地区拥有更多的生物物种。故
而,至少直到近代以前,并没有任何一种动植物能够主宰热带雨林,甚
至包括人类。许多无法耐受冰冻和干燥的微生物在热带雨林地区却十分
繁盛。在这种暖湿的环境中,单细胞寄生物通常在宿主体外也能长期存活,有些具有寄生潜能的生物甚至可以以独立个体的形式无限期地生存
下去。这意味着数量不多的潜在宿主族群也可能经历普遍的感染,即便
因为宿主太少而暂时无法寄居,寄生物也可以等待。就人类而言,这意
味着,即使我们的祖先在自然平衡体系中的地位无足轻重,但作为个体
仍可能在一生中感染所有的寄生物。这种情形至今如此,人类征服雨林
的主要障碍仍在于丰富、多样的寄生物潜伏其中,静待入侵者。[5]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前人类和准人类祖先长期性地处于生病
的状态呢?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大量的热带寄生物发展到致病程度是一
个缓慢的过程,一如其缓慢地消失;换言之,热带雨林支持每个层次上
的微妙的自然平衡:寄生物与宿主之间、竞争的寄生物之间、宿主与食
物之间,都是如此。可以肯定地说,几百万年前,即在人类开始改变热
带雨林的生态环境之前,食者和被食者的平衡从长时段看是稳定的或接
近稳定的。
因此,我们的远祖消费的品类繁多的食物,无疑都对应着五花八门
的与他们分享食物的寄生物,而这些寄生物未必一定会导致我们认为
的“生病”的症状。一般的寄生物可能有时会削弱先人的体力和忍耐力,当严重的伤害或灾难(比如饥馑)扰乱了宿主的生理平衡时,轻微的感
染也可能引发致命的并发症。但如果没有这些,健康状况应该还是不错
的,一如今天森林里的灵长类。
只要人的生物进化同寄生物、食肉动物和猎物的进化保持同步,这
张精密编织的生物网(web of life)就不会出现特别重大的变化。源自
基因变异与选择的进化是相当缓慢的,以致其中一方的任何变化都会相应地伴以另一方的基因或行为方式的改变。然而,当人类开始对另一类
进化做出反应,把习惯性的行为转化为文化传统并纳入象征性的意义体
系时,这些古老的生物平衡便又开始面对新的失衡。文化的进化开始对
古老的生物进化方式施以空前的压力,新近获得的技能使人类逐渐能够
以无法预见的、意义深远的方式改变自然平衡。于是,新兴的人类的患
病方式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第一个明显的巨大变化源于可杀死大型食草动物的武器和技术的发
展,这些食草动物充斥着非洲热带草原(可能还有亚洲的同类地区)。
这一转变的准确时间至今不得而知,但可能早在400万年前就已经开
始。
第一批下到地面的灵长类恐怕只能捕获羚羊一类弱小的动物,为了
从狮子等更有力的食肉动物吃剩的腐肉中分一杯羹,他们不惜与鬣狗和
兀鹫争食。这些前人类成天游荡于集中的食物源——比如非洲热带草原
上的大批食草动物——周围,[6]
任何能够提高狩猎效率的基因变异都意
味着巨大收益。丰厚的回报正在等待着那些能够用身心技能在狩猎中进
行有效合作的群体。通过改进有助于危急时刻互相支持的交流方式,以
及有助于更新弥补肌肉组织、牙齿和爪子之无力的工具和武器,新兴的
人类赢得了由此带来的嘉益。这样,新的更有效的特性通过多方面进展
的生物进化迅速累积着,而任何新的变化都成功地扩大了食物的供应,拓展了生存的机遇。
这类进化中的突变在生物学上称为“直向进化”(orthogenic),通常
意味着进化到新的更有利的生态龛。[7]
尽管不能指望厘清该过程在前人类中引发的所有的基因变异,但当变异特别成功时,一类族群通常被另
一类更厉害的狩猎族群所取代。在冲突中越勇敢、狩猎中越有成效,生
存的机遇也就越大。
在接下来的进化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就是语言的进化。主管大
脑、舌头和喉咙形成的基因的变化,对人类通向发音清晰的语言之路是
必需的;而语言的形成又极大地提高了社群的合作能力。不断地谈论周
围世界,由此不断地规定和重新规定各种角色,能够使人类事先尝试和
完善各种技巧,从而在狩猎和其他合作性活动中达到其他方式难以达到
的准确度。随着语言的产生,把生活技能系统传授给他人成为可能,而
这些技能自身又可以进一步地精致化,因为语言可用来为事物分类、排
序,以及表达对环境适宜的反应。简言之,语言第一次将狩猎者提升为
完全的人,启动全新层次上的社会——文化进化,这一进化不久将对人
类赖以形成的生态平衡产生巨大的、至今仍无可比拟的影响。
在上述相对迅速的进化中,疾病的情形如何呢?显然,任何居所的
变化,比如从树上下到地面,在广阔草原上奔走,都牵涉人类可能遭遇
的疫病的变化。当然,某些传染病可能未受影响,比如,靠身体接触传
播的大部分大肠菌。而另外的,比如需在潮湿环境中才能完成宿体转移
的寄生物,在不适宜其生存的草原环境里就少得多了。然而,随着雨林
型的传染病的日益减少,新的特别是来自与草原兽群接触而引发的寄生
物和疾病,则必定已在影响正在快速进化的人类肌体。
但我们无法准确地说出这些疾病的名字。当今天我们食用食草动物
时,可能不经意地吞食了某些寄生物的胞囊形状的卵,这些附在食草动物身上的寄生虫就这样传到人类身上。古代的情形也大致如此。
今天在非洲许多地区引发昏睡症的锥虫,就是当时遭遇到的一种非
常重要的病原体。它是寄居在羚羊类动物身上的“普通”寄生虫,通过采
采蝇(tsetse fly)传播。它在苍蝇或其他动物宿主身上并不会引发明显
的病症,因此属于较稳定、适应性较强、可能也是非常古老的寄生物。
但一旦它进入人体,就会造成人体的极度虚弱,事实上,某类锥虫甚至
可以在几周内置人于死地。
正是因为昏睡症曾经并且至今仍对人类具有极大的破坏性,非洲草
原上的有蹄类畜群才会生存至今。如果不是借助现代的疾病预防方法,人类根本无法在采采蝇肆虐的地区生活。因此,直到晚近,这些地区的
大量草食动物仍是狮子及其他适应性强的食肉动物的猎物,但与猛兽中
更有破坏性的新来者——人类,除偶然的例外,它们并无过多的接触。
似乎可以肯定,假如在我们的先祖下树之前,导致昏睡症的锥虫已经存
在于有蹄类动物中的话,它肯定会在非洲草地上划出鲜明的界限,人类
只能在界外捕获猎物。同理,在采采蝇活动的区域内,类似前人类时代
的某种生态平衡也延续至今。[8]
顺便说一下,把人类在与其他生命关系中的生态角色视为某种疾
病,这并不荒谬。自从语言的发展使人类的文化进化冲击由来已久的生
物进化以来,人类已经能够颠覆此前的自然平衡,一如疾病颠覆宿主体
内的自然平衡。当人类一次又一次蹂躏别的生命形态到达自然极限时,往往就会出现一种暂时稳定的新关系。然而,或早或晚——而且以生物
进化的尺度衡量还总是在极短的时间以后——人类又掌握了新的手段,把此前无法利用的资源纳入可利用的范畴,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其他生
命形态的摧残。所以从别的生物体的角度看来,人类颇像一种急性传染
病,即使偶尔表现出较少具有“毒性”的行为方式,也不足以建立真正稳
定的慢性病关系。
[1]Richard Fiennes,Zoonoses of Primates:The Epidemiology and Ecology
of Simian Diseases in Relation to Man(Ithaca,NewYork,1967),p.121
—122.
[2]权威的说法各有不同。Fiennes在前引书73页中分别列出5种猿类易
患的疟疾和10种猴类易患的疟疾;L. J. Bruce-Chwatt,“Paleogenesis
and Paloeepidemiology of Primate Malari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Bulletin,32(1965),p.368—369提到20种猿类和猴类易
患的疟疾,并说多达25种疟蚊可以充当疟疾在人类和灵长类中传播
的病媒。
[3]Fiennes前引书,第42页。
[4]Bruce-Chwatt前引书,第370—382页。
[5]参阅F. L. Dunn,“Epidemiological Factors:Health and Disease in
Hunter-Gatherers”,in Richard B.Lee and Irven DeVore,eds.,Man the
Hunter(Chicago,1968),p.226—228;N. A. Croll,Ecology of
Parasite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66),p.68。
[6]F. Boulière,“Observations on the Ecology of Some Large African
Mammals”,in F. Clark Howell and Fran?ois Boulière,eds.,African
Ecology and Human Evolution (New York,1963). [Viking Fund
Publication in Anthropology No. 36],p.43—54.据此书估算,在今天的非洲热带草原上,早期人类能够得到的非洲有蹄类动物和其他猎物
的总量远远超出其他地区;而且,在现代条件下,食肉动物对如此
巨大的食物储存库的争夺并不特别激烈,比如,狮子的实际数目就
远远小于潜在的食物供应能够维持的数目。因此,当人类的祖先第
一次离开树丛,冒险进入草原搜寻更大猎物时——如果远古的情况
与现代相似——则可以说他们正步入一种就生态意义而言的部分的
真空地带,自然收获颇丰。
[7]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长颈鹿伸长了的脖子,使它可以吃到别的动物够
不到的植物。参阅C. D.Darlington,The Evolution of Man and
Society(London,1969),p.22—27。
[8]参阅Frank L. Lambrecht,“Trypanosomiasis in Prehistoric and Later
Human Populations:A Tentative Reconstruction”,in Don Brothwell A.
T. Sandison,Diseases in Antiquity(Spingfield,Illinois,1967),p.132—
151。Lambrecht认为,一种源于鱼鞭虫感染的昏睡病已经向着与人
类宿主相适应的方向进化,产生更温和的慢性疟疾形式;但在有蹄
类宿主大量存在的热带草原,演化压力导向与羚羊而不是与类人猿
的适应,永久性造成某种对于人类致命的疾病形式。因此,与人类
宿主的适应事实上将减少(甚至毁灭)那些温良的畜群,使鱼鞭虫
在生物意义上的全面成功化为泡影。人类狩猎者与环境相对稳定关系的建立
第一批成熟的狩猎人群对非洲大草原(或许还有亚洲类似的地方)
的统治,还只是将来事态的不甚凸显的先兆。无疑,当时突然将这些不
太显眼的灵长类动物推到食物链的顶端,确实够剧烈的。作为技艺高超
又令人生畏的狩猎者,人类几乎很快就不再害怕其他的敌对动物了,我
们最早的完全意义的人类祖先就此摆脱了制约人口增长的基本因素。不
过,当大草原内适宜居住的领地都被人类狩猎者占据后,人类便开始了
自我竞争。至少从这时起,人类的自相残杀又同样具备了制约人口增长
的效果;其他限制人口增长的机制也可能就出现了,比如弃婴。无论如
何,今天的狩猎者和采集者所拥有的传统的保持人口与食物供应平衡的
方法,可能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1]
就在人类的发祥地非洲,人类狩猎者确立了与环境相对稳定的关
系。人类对大动物的猎获在大约50万年前的非洲就开始了,尽管装备着
石制和木制武器的人类的全部潜力迟至公元前10万年时还未能充分显
现。虽然偶有危机,比如在随后几千年间由于一些珍贵猎物的灭绝而引
发的危机[2]
,但是人类继续与其他物种分享这块土地。即便后来的农业
革命的确导致了急剧的人口增长和环境变化,但非洲的许多地区仍然是
一片荒蛮。最近几千年间被驱逐到不适合农耕的边缘地带的狩猎团体,仍继续在部分地区固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甚至直到今天。
换言之,其他生命形式的补偿性调整以如此顽固和复杂的方式包围
着人类社会,以至于即使在人类发展出完善的技能之后,文化进化所产生的新效力仍不足以征服和彻底革新孕育人类自身进化的生态系统。也
许减缓人类对其他生命形式的最初冲击力的最显著因素,正是非洲传染
病(infestations and infections)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丰富性和侵害性
——寄生物的进化亦伴随着人类自身的进化,其对人类的侵害随着人类
数量的增长而日益加剧。[3]
肆虐于非洲的很多寄生蠕虫和原虫并不引起免疫反应,即并不在血
液循环中形成抗体,这有助于确立敏感的和自动性的生态平衡:当人类
数量增加时,受感染的概率也会增加;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大,寄生物获
得新宿主的机会也就增加了。当这种趋势越过关键性门槛,感染就会一
发而不可收,严重地阻碍人类的正常活动。像倦怠、腹部疼痛等慢性病
征,如果普遍蔓延的话,就会严重地妨害进食、怀孕以及抚养孩子,这
反过来又会削减人口,直到当地的人口密度下降到过度感染的门槛以
下。然后,随着病征的消退,人类的精力开始恢复,进食和其他活动也
趋于正常,直到下一次,别的传染病大行其道,或者人口密度再次超越
过度感染的门槛。
上述这些生态紊乱自然会影响到人类的猎物以及人体内的寄生物。
过多的狩猎者越来越难以找到合适的猎物。于是营养不良就与寄生物的
过度滋生一起削减了人类的体力和生育孩子的能力,直到再次确定接近
稳定的平衡。
相互依赖的物种也会同时对气候和物质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干
旱、草原大火、暴雨,以及其他紧急状况都为所有的生命形式设定了生
长的限度;而这种数量的上限通常远远低于其在较有利的情况下增长的可能性。换言之,生态系统维持的是一种松散的、不断变动的平衡,尽
管这种平衡可能偶尔或暂时在时空上有一定的变化,但却能有效地抵制
剧烈的、大的变动。人类狩猎者虽然登上了食物链的顶端,他们以其他
动物为食,又不致为别的大型动物所食,但这并不能实质性地改变这些
恒久的生态关系,人类虽以胜利者的姿态取得新的生态地位,但总体来
说并没有改变生态系统本身。
形成并维持这种变动中平衡的相互作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
极端复杂的。虽已历经了几代人的科学观察,疾病、食物、人口密度、居住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在非洲或别的地方仍未被完全弄清,更不用
说对于致病机制来说,疾病的虫媒与各宿主的数量和分布意义了。而
且,当今非洲的环境也并不能够完全匹配人类社会中全然依赖狩猎和农
业而尚未打破古老的自然平衡的环境中的感染模式。
然而,热带非洲的生物多样性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个大陆的
生物平衡曾顽强抵制了来自温带的农业生产方式的输入,这是有据可查
的。事实上,直到晚近(比如5000年前),在非洲,人类在与其他生命
形态的交往中只扮演着很普通的角色。人类无疑是主要的掠食者,但在
这一自然平衡状态中是相对稀少的,就像与人类争食的狮子和其他大型
食肉动物一样。
其实,不是这样才显得奇怪呢。假设(这很有可能)人类起源于非
洲,那么,当猿人缓慢地进化到人类的同时,周围的生命形式有时间调
节自己以适应人类活动所带来的危险和其他可能性。反之,出现在非洲
的人类寄生物的极端的多样性,也暗示着非洲才是人类的主要摇篮。从未见过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调适达到生物上如此的精妙程度。
除了非洲雨林和草原之外,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如何呢?可能早在
150万年前起,旧大陆的若干地区就已出现这些可怕的类人猿狩猎者。
在中国、爪哇和德国发现的有关遗存表明,这些动物在骨骼上存在极大
差别,但这些少量的发现还不足以把它们与非洲发现的较多的人类和前
人类的遗骸明确联系在一起。在亚洲南部和东南部的某些地区可能存在
着从共同的远古灵长类动物的血统中延伸出来的平行的进化路线,因为
即使没有非洲那种提供大型猎物的环境,增大的大脑、直立行走和使用
工具的手也会带来巨大的嘉惠。
由于证据不足,我们所做的推论可能会产生误导。目前,对有关地
区的考古研究仍然相当粗略,甚至一个新的遗址(比如非洲奥杜威峡
谷)的发现,就可能全盘改变我们已有的认识。尽管如此,已知的不多
的情况似乎仍表明,亚欧大陆上的前人类和准人类族群的出现晚于非洲
全盛期的猿人。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10万~5万年前,完全现代型的人
(fully modern types of human beings)的横空出世,则急剧改变了此前
地球上的生物平衡。
关于智人最早从哪里开始进化的证据仍然太少。一些不能确凿地归
于智人的骨头碎片,可上溯至10万年前的东非,在别的地方,现代的人
类遗存仍要等到公元前5万年才出现,而且当现代人出现的时候,此前
存在的原始人类,像西欧著名的尼安德特人,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4]
在非洲内部,像这样成功的人类族群的出现并没有导致像在别处出现的那种剧烈的变化。但一些大型猎物和敌对的类人猿的消失,若是可
以正确地归因于智人的出现的话,仍然展示了人类高超的狩猎能力。当
人类能够通过把握火种和披戴动物毛皮以预防严寒时,更可观的后果出
现了。
衣服的发明有助于狩猎者进攻北部草地和森林里的动物,其效果就
好比人类祖先第一次从树上下到地面。也就是说,一种新的、更准确地
说是一系列新的生态龛等待新来者去占据;并且随着他们学会利用他们
的技术开发出新的食物来源,一种全球范围的生态关系的快速转型就接
踵而至了。大约公元前4万~前1万年间,狩猎者占据了地球上除南极洲
以外的所有陆地板块。他们在4万~3万年前进入澳大利亚;0.5万~1.5
万年后又越过白令海峡从亚洲进入美洲。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人类扩张
到南北美的所有气候带,在大约公元前8000年前到达火地岛[5]。
此前从来没有一种支配性的大型物种能够散布全球,人类做到了,因为他们学会了如何在极端不同的条件下创造适合于热带生物生存的小
环境。衣服与住房的发明,使人类的生存不致受到极度寒冷天气的威
胁。换言之,文化调适和发明创造降低了面对多样环境时调整生物机能
的必要性,由此,在地球各陆地板块的生态平衡中,引进一个本质上带
有破坏性的且不断处于变化中的因素。
当然,尽管对自然环境的文化调适对于公元前4万~前1万年间人类
的大举扩张具有决定性意义,但也仍然存在另外的重要因素。在走出热
带环境的同时,我们的祖先也远离了很多前人已经适应了的寄生虫和病
原体,健康和活力也相应得到了提升,于是人口的增加也变得规模空前。[6]
人类在温带、寒带的自然生态中的位置与在热带地区的截然不同。
如前所述,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人类继续受到生物上的制约,这种
制约即便在人类的狩猎技术已经颠覆了大型动物之间古老的自然平衡之
后,仍然相当有效。但当人类社会能够在温带条件下生存与发展时,他
们面对的是相对单纯的生物环境:总的来说,较低的环境温度意味着生
存适宜度的降低。结果适宜于温带和北方气温的动植物种类要少于热带
条件下的动植物。因此,当人类狩猎者第一次闯入这里时,迎接他们的
是一个不太复杂的生命之网。温带的生态平衡后来证明更容易被人类的
活动所破坏。这一地区起初缺少或几乎缺少能够寄生于人体的生物,但
这只是一个暂时现象,很快,正如我们不久将要看到的,在生物学和人
口统计学上都有重大意义的疾病也开始在温带人类社会中发展起来。但
生态平衡易受人类摆布的脆弱性仍是热带以外地区的永恒特征。
因此,人类在温带地区的生物统治,从一开始便呈现出一种特殊的
类型。作为温带生态系统的新成员,进入新环境的人类宛若刚被引入澳
大利亚的野兔,既没有天敌,又没有自然的寄生物,再加上至少在开始
的时候食物丰沛,澳大利亚的野兔数量急速增长,不久就开始影响到人
类的牧羊业。当欧洲人首先到达美洲时,也出现了类似的外来的生物,诸如猪、牛、马、鼠以及各种植物大量侵入的情形。但是,这些早期不
受制约的繁殖,不久就开始自我矫正了。[7]
若从一个足够长的时段来看,扩张到温带生态中的人类也是如此。
但就我们所习惯的时间长度来说——如百年或千年(而非十亿年)——物种之间一般的生物调适似乎还不足以制约人口的增长。原因在于,产
生和支撑人类进步的与其说是生物的调适,不如说是文化的调适,于
是,每当一两种关键性资源被耗尽、人类利用自然的既定方式面临困境
时,他们的智力总能帮他们找到新的生活方式,利用新的资源,由此一
次次扩展我们对有生命和无生命大自然的统治权。
猛犸象、巨大的树懒以及其他大型但缺乏经验的动物遍布各地等着
人类去猎杀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实际上,曾有人估计,富有技巧而
又浪费的人类狩猎者只花了一千年的时间就消灭了南北美洲大部分的大
型动物。根据对美洲历史的这种认识,狩猎者成群结队,沿着能够发现
大型猎物的界线向前推进,每到一个地方,只需几年的时间,就清空了
各种兽类,以致他们只能不断向南推进,直至美洲大部分的大型猎物物
种都趋于灭绝。[8]
这样灾难性的结局,当然只会在熟练的狩猎者遇到完
全无相应经验的猎物时才会出现。旧大陆就不曾发生过这种戏剧性的对
抗。在那里,人类的狩猎技术只是逐步应用于北方的大型兽群,这可能
只是因为,随着每一次向北的推进,狩猎者都不得不去适应更严酷的气
候和更困难的冬季。而美洲正好相反,移动的方向是从北向南,从严寒
到温暖,结果新大陆大型猎物的灭绝,远比旧大陆来得突然和广泛。
随后的新技术的发明,使人类得以不断地重演这种轻易地采集和迅
速地耗尽资源的边界现象(frontier phenomenon)。目前中东以外地区
的石油短缺,就是人类这种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的最新例证。不过,作
为石器时代定居温带和亚北极地区的结果,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的共存
关系也进入了一种新的更长久模式——这一模式在以后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人类这种跨不同气候带的分布,造成了在不同社群间产生
出一种可称为“梯度寄生”(parasitic gradient)的现象。毕竟,随着气候
上寒冷与干燥的加剧而呈现的生物多样性的降低,就意味着能够侵入人
体的寄生物的数量和种类的减少。而且,随着温度(和湿度)的降低、日照时间的缩短,寄生物在宿主间的转移也变得更加困难。于是就形成
了如下的感染梯度:居住在暖湿区域内的人口若前往干冷地区,有可能
很少遭遇不熟悉的寄生物,而潜伏于南部暖湿区域内的病原体,则往往
威胁着来自寒冷北方或干燥沙漠地区的入侵者。
反过来,这种梯度或许也可以这样描述:人类越深入寒冷或干燥气
候带,他们的生存就越直接地依赖于他们与大型动植物的生态关系,与
微寄生物系统的平衡在热带如此重要,而在这里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我们由此不难做出重要的引申,几乎所有的微型寄生物都小得用肉
眼看不见,这意味着在显微镜这类提高人类观察力的发明出现以前,没
有人能理解或控制与它们的接触。尽管人类在处理可见的和可实验的对
象上拥有智慧,但同微型寄生物的关系,在19世纪之前很大程度上仍停
留在生物性的层面上,也就是说,人类无法对其有意识地加以控制。
然而,在微型寄生物还不那么普遍和重要的地方,智力仍可以自由
地利用人类生命中诸多重要的参数,只要这群男男女女发现新的食物和
对手,他们就能发展出新的方式来对付它们,这样他们不再是狩猎方式
下数量稀少的掠食者,相反,在原来只能养活几千个狩猎者的地方,现
在狩猎者却能成百万地繁衍。因此,脱离热带生命摇篮,对人类后来在
自然平衡当中扮演的角色具有深远的意义,它赋予了文化创造以更大空间,远比孕育赤身裸体的原始人的紧密的生命网要广阔得多。
当然,地域性的状况也能够扭曲这种普遍性的方式,人口密度、水
源、食物和住所的特征与品质,以及人际交流的频率和范围,所有这些
都会严重地影响疾病的模式。直到近代,即使是坐落在凉爽或干燥气候
条件下的大城市,也总是不卫生的。尽管一般说来这种生态关系的局部
性变异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生物梯度规律,即感染的多样性和频率会随着
温度和湿度的增加而增加。[9]
旧石器时代的狩猎者在温带和亚北极地区的扩张,造就了人类在生
物意义上的空前成功。但是等到所有的可供狩猎之地都被占据之后,古
老地区最适合的猎物便惨遭滥杀,有时甚至被屠戮殆尽。
作为食物源的大型猎物的消耗殆尽,显然会给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地
区的狩猎者带来生存危机。与此同时,这场危机又恰巧遭遇了由最近一
次冰帽(ice cap)退缩引发的气候异动(公元前2万年以来)。这两大
因素的重合为狩猎社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环境挑战,只要惯用方法失
灵,就会促使人们去进一步寻找食物和尝试新的可食之物。比如,对沿
海的勘探,促进了造船和渔业的发展;采集可食的种子使另外一些族群
走上发展农业的道路。
旧石器时代的狩猎者和采集者可能粗略地重新体验了最早的猿人在
热带摇篮时的经历。那就是,一旦新的生态龛位显而易见的可能性被利
用,某种大致的平衡就形成了,各类制衡因素亦接踵而来,制约着人口
的增长。这些都因地、因时、因群体的不同而不同。不过,在人类完成自我进化的热带地区以外,病原体并不特别重要。那些可以通过直接的
身体接触而在宿主间传播的寄生物,像虱子、雅司螺旋体(the
spirochete of yaws),仍可以在温带地区流动的狩猎小群体中生存下
来。只要传染进程缓慢,又不对人类宿主产生突然的重创,这些寄生物
可以随同狩猎群体迁出人类的热带摇篮走向全球。但这些感染与它们在
人类最古老的热带居住地的繁盛景象相比,则已大为衰减了。
结果是这些温带地区的古代狩猎者尽管寿命不长,但却可能是身体
最健康的族群。[10]
这一推论还可从当代澳大利亚和美洲狩猎者的生活
状况中得到印证。除了最近因同外部世界接触而产生的可怕疾病外,这
些人似乎不受传染病和多细胞寄生物的感染。[11]
其他一切都是令人惊
讶的,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让缓慢的生物进化以及从宿主到宿主的转移
模式适应阴凉、干燥的条件,而只有有足够的时间,才能使进入温带和
亚北极气候区的相对孤立的狩猎群体维持热带水平的感染。
在上述调整影响人类生活之前,新的关键性的发明再一次使人类与
环境的关系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食物的生产使得人口数量迅速增长,而
且很快推动了城市和文明的兴起。人口一旦集中到如此大的社群中,就
会为潜在的病原体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其情形一如非洲草原的大型猎
物为我们的远祖提供食物来源那样。在人类的村庄、城市和文明的发展
所创造的新环境中,这回轮到微生物猎食美味了。微生物如何利用人口
聚居所带来的机会,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1]Mary Douglas,“Population Control in Primitive Peoples”,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7(1966),p.263—273;Joseph B. Birdsell,“OnPopulation Structure in Generalized Hunting and Collecting
Populations”,Evolution,12(1958),p.189—205.
[2]参阅Darlington前引书第33页中所列的灭绝物种。这些(以及后来
灭绝于北美的)物种的灭绝与人类活动间的关系尚待澄清,参阅
Paul S. Martin H. E. Wright,eds.,Pleistocene Extinctions,the Search
for a Cause(New Haven,1967)中的讨论。在灭绝的诸物种间,Darlington并没有考虑曾生存于非洲的各种类人猿;但很清楚,类
人猿族系中较为温顺的种类也最为脆弱,结果,到公元前2万年
——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该族系中只有一类,即智人,存活下来。
[3]关于原生动物和蠕虫在撒哈拉以南地区极度泛滥,请参阅
Darlington前引书第662页中的图表。
[4]有关这些说法,系参考以下论著而来:David Pilbeam,The Ascent of
Man: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Evolution(New York,1972);Frank
E. Poirier,Fossil Man:An Evolutionary Journey(St.
Louis,Missouri,1973);以及B. J. Williams,Human Origins,an
Introduction to Physical Anthropology(New York,1973)。
[5]Tierra del Fuego,位于南美洲的南端,今属阿根廷。
[6]Joseph B. Birdsell,“Some Population Problems Involving Pleistocene
Man”,Cold Spring Harbor Symposium on Quantitative
Biology,20(1957),p.47—69,该文估计只需2 200年就足以住满澳
大利亚。也参考Joseph B. Birdsell,“On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Generalized Hunting and Collecting
Population”,Evolution,12(1958),p.189—205;——,“Some
Predictions for the Pleistocene Based on Equilibrium Systems AmongRecent Hunters-Gatherers”,in Richard B. Lee Irven DeVore,eds.,Man
the Hunter,p. 229—240。
[7]关于澳大利亚野兔,可参阅Frank Fenner F. N.
Ratcliffe,Myxomatosis(Cambridge,1965)。关于美洲的情形,可参
阅Alfred W. Crosby,The Columbian Exchange: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Westport,1972)。一般性概况可参阅Charles
S. Elton,The Ecology of lnvasions by Animals and Plants (New
York,1958)。
[8]Paul S. Martin,“The Discovery of
America”,Science,179(1973),p.969—974.
[9]N. A. Croll,Ecology of
Parasite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66),p.98—104. Croll主要探
讨的是多细胞寄生虫,但他的结论也适用于所有的寄生形式,尽管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文明人口中产生最重要传染病的病毒性和
细菌性有机体的分布,主要受制于潜在宿主的密度,因而与受气候
影响的分布方式大大不同。F. L. Dunn,“Epidemiological
Factors:Health and Disease in Hunter-Gatherers”,in Richard B. Lee and
Irven DeVore,eds.,Man the Hunter,p.226—228,关于不同气候下的生
物多样性与人类传染病的关系也有有趣的见解,另可参阅René
Dubos,Man Adapting(New Haven,1965),p. 61。
[10]根据对克罗马农人和尼安德特人骨骸的研究,可以尝试性地确定
死者的年龄。根据Paul A.Janssens,Paleopathology:Diseases and
Injuries of Prehistoric Man(London,1970),p. 60—63中收集的材
料,88. 2%的克罗马农人遗骸在死时不到40岁,61.7%不到30岁。尼安德特人遗骸的相应比例分别是95%和80%。然而这种计算的统
计学基础不能令人满意,推算死者年龄的标准也经常是含糊的。
[11]参阅Saul Jarcho,“Some Observations on Diseases in Prehistoric
America”,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38(1964),p.1—19;T.
D. Stewart,“A Physical Anthropologist’s View of the Peopling of the
New World”,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16 (1960),p.256
—266;Lucille E. St. Hoyme,“On the Origins of New World
Paleopath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21(1969),p.295—302。J. V. Neel et al.,“Studies of
the Xavante Indians of the Brazilian Mato Grosso”,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16(1964),p.110.注意到在他所研究的部落中,男
人“相当健壮”,远离疾病困扰,尽管妇女并非如此。大量游记也强
调原始人在起初与外界接触时的健壮,尽管其可靠性尚可置疑,参
阅Robert Fortuine,“The Health of the Eskimos as Portrayed in the
Earliest Written Accounts”,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45(1971),p. 97—114。另外,在可能作为人类最早发源
地的热带地区,许多种疾病仍肆虐于较大的封闭的族群。参阅Ivan
V. Polunin,“Health and Disease in Contemporary Primitive Societies”,in
Don Brothwell A. T. Sandison,Diseasesin Antiquity,p. 69—97。有观
点认为,在与欧洲人接触之前,澳大利亚土著的身体状况也是良好
的,请参阅B. P. Billington,“The Health and Nutritional Status of the
Aborigines”,in Charles P. Mountford,ed.,Records of the American-
Australian Expedition to Arnhem Land,(Melbourne,1960) I,p. 27—
59。第二章
历史的突破大型猎物的灭绝,开始于5万年前的非洲,继之以2万年前的亚欧大
陆,然后在1.1万年前的美洲达到高潮,这一过程对于以猎杀大型动物
为业的狩猎者来说,肯定是一次严重的打击。[1]
大型动物的先后消失可
能导致各地人口的急剧减少。对一群人来说,在一周或更长的时间内依
靠一只猛犸象为食是一回事,但另外,要每天猎杀足够的小型猎物来供
养同样数量的一群人,就不那么容易了。同时,气候的变化也改变了自
然平衡,像在北方沿着冰川退却的边缘地区,而在亚热带地区,信风的
北移使以前适合狩猎的非洲撒哈拉和西亚邻近地区出现了沙漠化。
[1]种类很多(200种食草动物和相关的食肉动物),包括北美诸如马
和骆驼这些潜在有用的动物。参阅Paul Schultz Martin H. E.
Wright,Pleistocene Extinctions,p.82—95。最近对非洲——这里大型
动物的灭绝比别处要缓慢得多——生物量的估算,表明大型猎物的
消失意味着多么巨大的食物损失。比如,单是大象和河马就构成非
洲草原整个动物界生物量的70%;甚至在斑马和牛头羚作为最大食
草动物的地方,这两类动物也至少构成动物界生物量的50%。请参
阅F. Clark Howell Fran?ois Boulière,African Ecology and Human
Evolution,p.44—48. Vernon L. Smith,“The Primitive Hunter
Culture,Pleistocene Extinctions,and the Rise of Agricultur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3(1975),p.727—756,对过度滥杀导致的灭绝
现象进行了有趣的经济学分析。如果发生在更新世(Pleistocene)
的灭绝现象系与人类狩猎者的行为有关,则古代灾难性的滥杀与现
代工业对化石燃料的滥用非常相似;不同的是,现代人毁灭其生存的能源基础的时间可能少于史前祖先对他们的能源基础的毁灭。农牧业的兴起
在每一个地方,古代的狩猎者都必须不断调整他们的习惯以更充分
地利用正在变化的环境。当大型动物灭绝时,就必须找到可替代的食
物。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的祖先再度成为杂食动物,就如同他们的猿
人祖先,开始食用各种各样的动植物。特别是,海边和海洋的食物资源
第一次被系统地利用,这一点可从被抛弃的软体动物的贝壳和不那么显
眼的鱼骨堆中得到证明。不仅如此,人类还发展出了制作食物的新方
式,比如,某些族群认识到,长时间的浸泡可以除掉齐墩果和木薯中的
有毒成分,从而可以食用;另一些蔬菜通过碾磨、蒸煮和发酵,会变得
更可口或更容易消化。[1]
然而,所有这些补偿性措施与通过畜牧和种植发展起来的食物生产
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地球上不同地区的社群都朝着这一方向前进,不
过产生的结果,则随着各地最初的野生状况中可资利用的动植物的不同
而存在差异。一般说来,新大陆相对缺乏可驯养的动物,但有用的植物
却不少,旧大陆则为人类的创造力提供了大量可驯养的动物和大量令人
印象深刻的可能的粮食作物。
我们对早期驯化的细节仍不清楚。我们必须假设,在人类与可种植
和驯养物种之间存在着相互适应的过程,这包括被种植和被驯养的动植
物会出现快速且有时影响深远的生物特性上的改变,这是因为人类对它
们的某些生物特性做了偶然或有意的选择;反过来,我们也必须假设,人类自身也做出了根本的(即使很少是有意的)选择。比如,那些拒绝从事辛苦的农业劳作的往往难以生存下来,而那些不能或不愿为来年的
耕作备足种子而宁愿吃掉所有余粮的人,也将很快被依靠每个年度的收
成生活的社会所淘汰。
牧人、农夫以及各种各样的驯养和种植的动植物,依其气候、土壤
和人类技能的不同,以不同的方式与动植物的野生背景相适应。而其结
果,在村与村之间、地块与地块之间,甚至同一地块内部都存在着明显
的差异。
不过,仍有一些普遍现象值得注意。首先,当人类以增殖某些动植
物的方式改变自然景观时,另一些别的动植物也就被取代了,其一般性
影响是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和区域内的动植物渐趋单一。与此同时,当人
类的活动降低了其掠食者的角色,而又把越来越多的食物储存起来仅供
人类自己消费时,其食物链也就缩短了。
食物链的缩短将人类拖入了永无休止的劳作当中。保护畜群和庄稼
不受动物掠食者的侵害,对于熟练的猎人来说,虽然要求其始终保持警
惕,但算不上是什么大问题。然而,要防范来自人类自身的侵害就不同
了,防范同类掠夺的努力正是催生政治组织的主要动力,这一进程至今
仍未完成。
但对人类生活更重要的还是除草工作,即试图消灭那些与驯养和种
植的动植物争夺生存空间的敌对物种,这是因为其需要整个族群大部分
人持续不懈的努力。以手除草似乎真的是“农业”的最初形式,但当人类
学会了刈除自然界中最茂盛的植物而为他们喜好的作物拓展生态空间,从而更彻底地重塑自然环境时,人类的力量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有
两种方法证明这些手段有助于达到上述目的:对干燥的土地实施人工灌
溉,以挖掘和犁地的方法机械地改变土壤的表面状况。
灌溉有助于淹死竞争的物种。一段时间内土地淹在水下,而在其他
时间里则放水以晾干土地,当这样安排农时时,杂草就不再是大问题
了。很少有植物能在极湿与极干环境的交替下还能照样生存;而当农夫
只通过开关巧妙设计的水闸,便可以随意调整旱涝以适应作物需要时,此时能存活下来的杂草就更是少之又少。当然,只有在浅水中能长势良
好的作物才能获益于这种方法,水稻就是最好的例子。不过,对别的不
那么有价值的根茎类作物,这一耕作方法也同样适用。
以铲子、锄、锹或犁等机械力量来改变土壤的做法,更为西方人所
熟悉,因为这种农耕方式最早出现在古代近东,随后被传入欧洲。此
外,它也盛行于美洲和非洲的早期农业中心。在更早的刀耕火种的阶
段,人类是用剥掉树皮的方法来毁掉落叶林,这有助于阳光直射森林地
面,在没有杂草竞争的环境下促进谷物的成长。然而,即使可以靠焚烧
枯树来更新土地的肥力,这种耕作方式也不够稳定,风中洒落的种子不
久就会在森林空地繁殖起蓟及类似杂草,只需一两年不受控制的疯长,这些入侵者就会完全鸠占鹊巢。于是,最早的近东人、美洲印第安人和
非洲农夫只有另寻处女地,重新开始新一轮只有第一年没有杂草的种
植,才得以生存下去。
公元前3000年左右,随着犁耕的发明,最早的局限首先在古代近东
取得了突破。犁耕可以年复一年地有效地控制杂草,从而使土地无限期地得到耕种。原因很简单:犁耕用畜力代替人力,这样就能让古老的近
东农夫可以耕种两倍于他们所需的农田,多余的土地则处于休耕状态
(即在生长季节犁耕以毁掉杂草),以便为来年的作物生长预留适宜的
生态龛,而不致被杂草所侵扰。
大部分教科书仍然对休耕是如何让土地通过休息来恢复肥力进行解
释,这种说法证明了人类的泛灵论倾向。任何人只要稍做思索就可以认
识到,在一个季节里地质气候的变化及随后的化学变化,无论过程怎样
都不会对来年的植物生长造成显著的差别。诚然,在“旱播”的情况下,呈裸露状休耕的土壤更容易保有水分,否则水就会通过植物的根系和叶
子从土壤里发散到空中,在由于水分不足而影响作物产量的地方,休耕
一年可以通过积聚底土里的水分以提高肥力。而在别的水分并不对植物
生长构成关键性制约的地方,休耕的巨大好处在于可以用犁耕阻断杂草
的自然生命周期,使其枯死。
翻土(或引水灌溉)自然能达到相似的结果;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单凭人的体能尚不足以翻掘足够的耕地,以允许一家人只靠耕地的一半
收成就可以维生,而让另一半休耕。当然,特殊的土壤和生态环境确实
容许出现某些例外,两个最重要的例外是:第一,在中国北部,肥沃而
易碎的黄土使人们无须借助畜力即可以小米维生;第二,在美洲,玉蜀
黍和马铃薯比旧大陆的小麦、大麦和小米一类作物含有更多的单位热
量,所以,即使这里的土地不像中国的黄土那样容易耕种,仍能达到相
似的结果。[2]
上述的技能的确令人钦佩,人类借助它们在以激进的方式重塑自然的过程中发现并利用了其原有的种种可能性,成倍地提高了食物供应,尽管这也意味着人类从此将不得不持久地接受没完没了的劳作的奴役。
毫无疑问,一旦在犁耕中使用了畜力,那么耕作者的生活就要比东亚的
稻米生产者轻松得多,后者需靠自身的体力来完成水田劳作的大部分内
容,包括引水和犁土。但辛劳——日常性的、没有尽头的、与狩猎经历
所造就的人类天性严重冲突的辛劳,仍然是所有农业人口的命运。只有
如此,农夫们才能成功地改造自然的生态平衡,缩短食物链,提高人类
消费能力,增加人口数量,直到这个在自然平衡中原本相对稀缺的物
种,成为称霸于广大农耕地区的大型物种。
人类同杂草(包括可以称为“杂草”的动物,如象鼻虫、鼠类)的斗
争需借助于工具、智力和经验;尽管其过程还了无尽期,却已经为人类
带来了一系列胜利。然而,农业对生态平衡的破坏,还有另一方面:缩
短食物链,增加驯养和种植的动植物的数量,也为寄生物造就了潜在的
更集中的食物源。更重要的是,由于大部分重要的寄生物都微不可见,长期以来人类仅凭智力无法有效地对付它们的滋扰。
因此,在现代科学和显微镜出现以前,先祖对杂草和敌对的大型掠
食者的胜利,尽管成果辉煌,但也遭遇了劲敌。这种微寄生掠食者在农
夫成功改造的环境中找到了更多的生存机遇。实际上,一种或少数几种
物种引起的超级大侵扰,可谓是生命之网中的自然平衡发生突然的和影
响深远的改变的正常反应。杂草往往就是利用灾患对正常的生态系统所
造成的缝隙而生存,在不受干扰的自然植被中,杂草总是稀少和不显眼
的,但一旦当地的终极群聚期[3]
的植被毁坏,它就能够快速地占领因此而产生的空隙。既然很少有物种能够有效地利用这些机会,结果就使得
仅有的几种杂草在裸露的地表上肆虐开来。然而杂草并不能长久维持这
一强劲的势头,复杂的补偿性调节很快就出现了,在缺乏进一步外部干
扰的情况下,程度不同的稳定而多样化的植被将重新出现,通常仿佛回
到破坏前的样子。
只要人类继续改变自然环境,并使之适合于农业,他们就会阻挠重
新建立自然的终极群聚期的生态系统,因此仍会随时遭受杂草泛滥的困
扰。[4]
如前所述,当对付人们可见和可控的大型生物时,观察和试验让
早期农夫们很快就能将杂草(以及老鼠这样的动物害虫)置于其控制之
下,但几千年来人类的智慧在对付致病微生物上,仍然还停留在摸索阶
段,因此,疾病在作物、畜群和人类当中的滋扰,在整个历史时期的人
类事务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书的目的正是要探讨:在现代医学
弄清疾病传染的某些重要途径之前,人们对疾病一筹莫展时,究竟发生
了什么?
[1]Sherwood Washburn and C. Lancaster,“The Evolution of Hunting”,in
Richard C. Lee and Irven DeVore,Man the Hunter,p.293—303:Kent
V. Flannery,“Origins and Ecological Effects of Early Domestication in
Iran and the Near East”,in Peter Ucko and G.W. Dimbleby,eds.,The
Domestic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
(Chicago,1969),p.77-87.
[2]关于早期中国农业的特殊环境,参阅何炳棣,“The Loess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Agriculture”,American HistoricalReview,75(1969),p.1—36。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的农业情形,参看
R. S.MacNeish,“The Origins of American
Agriculture”,Antiquity,39(1965),p.87—93。
[3]climax,是指动植物因与生长地的气候条件不合而迁移到安定状态
的阶段。
[4]关于过度泛滥以及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参看N. A. Croll,Ecology
of Parasites,p.115以下。新生活方式与疫病
到目前为止,一切还算顺利。但是,当我们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概
括,而提出诸如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些怎样的疾病?流行于哪些地方?
在什么时候?以及对人类生活和文化产生了何种影响?这时,知识的模
糊性使我们很难提供具有说服力的答案。即便不去考虑影响作物和驯养
的动物的疾病,我们仍然缺乏足够的资料来创作一部人类的传染病史。
显而易见,长期或永久性地定居在一个村庄里,就会卷入新的寄生
物侵扰的风险。比如,当人类的粪便在居住地周围堆积时,人们与它接
触的增多有助于肠道寄生物顺利地进行宿主间的转移。相反,一个不停
流动的狩猎群,在任一地点的逗留时间都不长,自然不易受这种循环感
染的威胁。因此,我们应当承认,生活在定居社会里的人们,比起他们
处于同一气候区的狩猎先人或同时代的狩猎族群,更易受寄生物的感
染。有的寄生物通过污染水源在宿主间随意转移,这种情况在经年累月
依靠同一水源生活的定居社会中,自然就更容易出现。
尽管如此,代表原始农业特色的小型村落社会,可能并没有过多地
受累于寄生物的侵扰。近东的刀耕火种者在一生中要屡迁其地;中国的
小米种植者,以及美洲种植玉蜀黍、豆类和马铃薯的印第安人也相当分
散地居住在前文明的小村庄里。各类感染在这些社会中可能是存在的,尽管寄生物的数量因地而异,但在每个小村庄里大家在年幼时都会患上
同类的寄生虫病,至少这是今天原始耕作者的情况。[1]
但这类感染不会
造成非常严重的生物意义上的负担,因为它们未能阻止人口空前规模的增长。仅在几百年内,凡是历史上成功地栽培(domesticated)了有价
值农作物的重要地区,[2]
其人口密度比先前同一地区的狩猎者的人口密
度,要高出10~20倍之多。
在早期农业中依赖灌溉的地区,比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河
流域以及秘鲁沿海地区,与简单的、或多或少封闭的村庄相比,显然需
要更完善的社会控制。运河与沟渠的规划与维修,尤其是灌溉水源在使
用者之间的调配,都需要有权威性的领导者。于是,城市和文明诞生
了,比起乡村生活,它们要求更广泛的合作和生产的专业化。
不过,灌溉农业尤其是相对温暖气候条件下的灌溉农业,在某种程
度上等于重构了有利于病原虫传播的环境,这种环境普遍存在于孕育人
类远祖的热带雨林中。充足的水分(甚至比热带雨林还要充足)加快了
寄生物在宿体间的转移频率,众多潜在的人类宿主在温暖、浅缓的水域
中驻足,为其提供了理想的传播媒介。在这种环境中,寄生体并不需要
胞虫囊一类能够长期抵御干旱的生命形式即可顺利传播。
古代的寄生方式可能与今天稍有不同。但以人类历史的尺度来衡
量,生物的进化是相当缓慢的。5000年前在灌溉农业的特定环境下的寄
生形式,与当今仍困扰着稻田农夫的寄生形式,几乎是一样的。
目前已知的这些寄生物已有不少,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导致血吸虫
病的血吸虫。血吸虫病是一种严重的、令病人虚弱的病症,即便在今
天,它也许还在折磨着上亿的人口。血吸虫的生活史,是软体动物和人
类轮流担任宿主,它以微小的、自由游动的形体,通过水实现宿主间的转移。[3]
一旦感染上它,有时会让钉螺(最一般的软体动物宿主)送
命,但对慢性感染的人来说,它的最严重症状出现在儿童期,其后表现
得持续而相对缓和。像疟疾一样,血吸虫的寄生生活史相当精致。它具
有两种不同的自由游动形式,各自寻找它们的宿主:软体动物或人,以
便一旦侵入宿主即可进行活跃的运动。这种复杂的情形,连同它在人体
内产生的慢性病症的特征表明,在现代血吸虫的行为模式形成之前曾经
过长期的进化。像疟疾一样,其寄生的模式,可能源于非洲或亚洲的雨
林;但这种疾病分布得异常广泛,[4]
以至于我们还不能有把握地指出它
是在何时何地扩散到今天盛行的这些地区的。古代埃及的灌溉者早在公
元前1200年(可能更早)即受此感染;[5]
古苏美尔和巴比伦人是否同样
受此感染还不敢断言,尽管我们不能排除这两大河谷间通过接触而同时
感染的可能性;[6]
同样,在遥远的中国发现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安葬于公
元前2世纪的尸体,尽管死因是心脏病,但同时也携有血吸虫及其虫
卵。[7]
今天,农民需要长时间地浸泡于水田作业的灌溉区,这种病仍能
迅速传播。[8]
就此而言,似乎可以说古代的灌溉技术与血吸虫病很早就
在整个旧大陆紧密联系起来了。
无论古代的血吸虫病以及类似的病症曾如何分布,有一点是肯定
的,即在它们泛滥的地方都容易造成农民出现无力和疲怠的症状,使他
们既不能长时间地在田里劳作和挖掘沟渠,也无力胜任那些对体力的要
求并不亚于劳作的任务,比如抵抗军事进攻或摆脱外来的政治统治与经
济掠夺等。换言之,由血吸虫病和类似感染所造成的倦怠和慢性不
适,[9]
会有助于为人类所惧怕的唯一大型天敌的成功进犯,他们就是自
己的同类,为了战争和征服而武装和组织起来的掠食者。尽管历史学家不习惯于从这样的角度来思考国家、征税和掠夺的问题,但微寄生和巨
寄生之间的相互支持,肯定是正常的生态现象。
农民被寄生物传染这件事,如何加速早期大河文明的建立,其作用
尚难以合理估计。但似乎也有理由怀疑,显现灌溉农业社会特征的专制
政府的存在,除了与经常用来解释这一现象的治水所需技术有关外,也
包括这类令人虚弱的疾病的功劳,多亏它们侵扰了长期光脚在湿漉的田
间劳作的农民。[10]
简言之,埃及的瘟疫与法老的专制统治之间可能存
在着某种形式的关联,而这种关联,不仅古代希伯来人没有想过,现代
历史学家也从未关注过。
只要寄生物小得无法辨认,人类对瘟疫的应对严格说来便是盲目
的。但人类有时的确能摸索出饮食和卫生规则以减少感染机会,最耳熟
能详的例子,便是有的宗教禁食猪肉。这看起来令人费解,除非你意识
到猪是近东村庄的腐食者、喜食人粪和其他“不洁”之物,它们的肉如不
经彻底烹煮便当作美食,就很容易把许多寄生虫吞进肚里,现代的旋毛
虫病(trichinosis)就证明了这一可能性。不过,禁食猪肉的古代习俗与
其说是建立于某种试错法之上,毋宁说是建立于对猪的本能恐惧之上;
至于由遵守禁忌带来的健康上的好处,尚无法从现有史料中看出端倪。
将麻风病人[11]
驱逐于正常社会之外这一做法的背后也隐藏着类似
的情绪。这是另外一条古老的犹太人戒律,想必它减少了通过皮肤接触
而感染的机会。沐浴——无论用水还是沙子,在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仪式
中均有重要地位,这可能也有防止传染的功效。但另外,为庆祝神圣节日,成千上万的朝拜者聚集一处共同沐浴的
仪式,却又为寄生物寻找新宿主提供了绝佳机会。[12]
在印度,很大程
度上霍乱的传播曾是(现在仍然是)宗教朝圣的“职能”。[13]
因此,那些
传统的习俗,即便被宗教和无人记得的仪式奉为神圣,也并不见得总能
有效地阻止疾病的传播;而且,那些实际上扩散疾病的做法也同那些对
健康具有积极意义的仪式一样,可能,也的确被神圣化了。
当然,农业环境中有利于在人类中传播的,并不只是这些多细胞寄
生物。当畜群、作物和人口大量繁殖时,原虫、细菌和病毒的感染的空
间也相应得以拓展,一般来说,其结果并不直接,未曾也无法预见。除
了极特殊的情况,要复原新传染方式赖以形成的环境,是不可能的。
然而,仍有某些例外。譬如,在西非,当农业扩展到雨林环境时,刀耕火种的农作方式显然对旧生态平衡施加了新的压力,一个意想不到
的结果是,疟疾获得了全新的流行强度。事情可能是这样发生的:把森
林夷为平地为喜食人血的冈比亚疟蚊(Anopheles gambiae)扩大了滋生
的地盘。实际上,我们确实可以将疟蚊视为“杂草”类的物种,它们在人
类为农业所开辟的非洲雨林中的空地上恣意繁殖,并随着农业的进展,取代了别的喜食动物血而非人血的蚊子。结果,人—蚊子—疟疾这一循
环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度,切实地影响到每个深入雨林空地的
人。[14]
虽然非洲的劳动者仍能出于农业目的而继续努力征服雨林,但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会伴以基因上的调整,使得制造镰刀形红细胞的基因(异
形合子形式)出现的概率明显增加,这些红细胞对疟原虫,显然不像普通的红细胞那样友好。于是,疟疾令人衰弱的症状在体内含有这类红细
胞的人身上减弱了。
然而,得到这一保护的代价十分高昂。一个人若从父母那里同时继
承了双方的镰刀形红细胞基因,那他(她)往往会在青年时早夭。不
过,那些生来完全没有这种基因的人,更容易受到疟疾的致命感染,这
也使得儿童死亡率进一步攀升。在西非疟疾最猖獗的地区,约有半数的
新生儿携有镰刀形红细胞基因,他们在生理上是很脆弱的。由于农业对
雨林的入侵仍在继续,当前疟疾、疟蚊以及镰刀形红细胞基因的分布情
形,让我们得以重构当年随着旧的生态方式的改变而发生的异常严重的
后果(这种后果目前仍在显现中)。[15]
在19~20世纪的中非和东非,欧洲殖民当局所推行的改变传统畜牧
耕作方式这一错误的做法,也说明了农业向新的地域扩张所带来的令人
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这一活动加剧了嗜睡病在乌干达部分地区、刚果坦
干伊喀、罗得西亚和尼日利亚的流行;最终的结果是,随着殖民政权的
结束,这片大陆更深地受到了采采蝇的感染,而在当局决定更有效地开
发这一片看似优良的农业地区之前,情况并非如此。[16]
显然,在非洲的热带雨林和临近的草原地区——这个地球自然生态
中最严峻和最多样化的地区——人类为缩短食物链所做的尝试仍未能成
功,并依然以持续感染疾患的方式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一点比其他任何
方面都更能说明,为什么非洲与温带地区(或者美洲的热带地区)相
比,在文明的发展上仍显落后。因为在其他地区,主流的生态系统从未
如此精致,因而也不会与人类的简化行为[17]
如此抵触。[1]Ivan V. Polunin,“Health and Disease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in
Don Brothwell A. T.Sandison,eds.,Diseases in Antiquity,p.74,84.
[2]对古代人口的估算完全是推测性的,依据每平方英里人口密度的假
定。下列论著提供了两个全球性的估计:Kent V. Flannery,“Origins
and Ecological Effects of Early Domestication in Iran and the Near
East”,in Peter Ucko G. W. Dimbleby,eds.,The Domestic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Chicago,1969),p.93;D. R.
Brothwell,“Dietary Variation and the Biology of Earlier Human
Populations”,同上书,p.539—540。
[3]详情请参见C. A. Wright,“The Schistosome Life Cycle”,in F. K.
Mostofi,ed.,Bilharziasis (New York,1967),p.3—7。
[4]今天的埃及是血吸虫最著名的滋生地,同时受影响的还有东非、西
非、西亚和东亚的稻田区,以及菲律宾这样的岛国和巴西的一部
分。这里牵涉到三种不同的血肝蛭,各地的血肝蛭因软体动物的不
同经常有所不同,从而在性质上——对人而言则表现为疾病症状
——呈现出非常复杂且至今仍未完全弄清楚的地方性变异。参看
Louis Olivier Nasser Ansari,“The Epidemiology of Bilharziasis”,in F.
K. Mostofi,ed.,Bilharziasis(New York,1967),p.8—14。
[5]M. A. Ruffer,Studies in Paleopathology of Egypt(Chicago,1921),18
页提到在属于第20王朝的两具木乃伊的肾脏里发现了血吸虫卵。他
在被检查的6个肾脏中的两个发现了这种虫卵;而肾脏并不是最容
易受血吸虫感染的器官(它们最经常寄居的膀胱和其他软内脏都被
古代木乃伊的制作者扔掉了),故可知血吸虫病在埃及的古代可能像现代一样多发。
[6]J. V. Kinnier Wilson,“Organic Diseases of Ancient Mesopotamia”,in
Don Brothwell A. T.Sandison,eds.,Diseases in Antiquity,p.191—
208,试图使楔形文字中的术语对应于疾病的现代分类。这是一项
徒劳无益的事业,他所报道的东西没有一点血吸虫病的影子。也请
参照:Georges Contenau,La Médicine en Assyrie et la Babylonie
(Paris,1938)和Robert Biggs,“Medicine in Ancient
Mesopotamia”,History of Science,8(1969),p.94—105。关于美索不
达米亚与埃及的早期接触,参照Helene J. Kantor,“Early Relations of
Egypt with Asia”,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1(1942),p.174—
213。
[7]“A Lady from China’s past”,the National Geographic,145(May
1974),p.663.这具生前安享富贵的尸体,在肺部也留有肺结核的痕
迹。
[8]参考J. N. Lanoix,“Relations Between Irrigation Engineering and
Bilharziasis”,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Bulletin,18(1958),p.1011—
1035。
[9]在现代埃及,钩虫症在弱化人口素质上以前像、现在仍然像血吸虫
病那样重要,或几乎如此。就全球而言,钩虫症的分布比血吸虫病
更广泛,因为它只需湿润的土壤和裸足的人群即可在宿主间传播。
[10]参考Karl A. Wittfogel,Oriental Despot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New Haven,Connecticut,1957)。他是持如下观点的现
代主要学者:存在一种特殊的极权政治与他所谓的水利文明相适
应。[11]《圣经》中的麻风病对应于当今的何种疾病?这一问题争论颇多
且不易解决。参考Vilhelm M?ller-Christensen,“Evidences of Leprosy
in Earlier Peoples”,in Don Brothwell A. T. Sandison,eds.,Diseases in
Antiquity,p.295—306;Olaf K. Skinsnes,“Notes from the History of
Lepros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prosy,41(1973),p.220—237。
[12]Olivier Ansari前引书,第9页。
[13]参看下文第183页。
[14]René Dubos,Man Adapting,p.237;George Macdonald,The
Epidemiology and Control of Malaria(London,1957),p.33 and
passim.
[15]Frank B. Livingstone,“Anthrop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Sickle Cell
Gene Distribution in West Africa”,American
Anthropologist,60(1958),p.533—562.
[16]关于发生在非洲5个不同地区的事件,详情参见John Ford,The Role
of the Trypanosomiases in African Ecology:A Study of the Tsetse Fly
Problem(Oxford,1971)。也可见Charles N. Good,“Salt,Trade and
Disease:Aspects of Development in Africa’s Northern Great Lakes
Reg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5(1972),p.43—86;H. W. Mulligan,ed.,The African
Trypanosomiases(London,1970),p. 632ff。在Mulligan看来,20世
纪非洲昏睡症的暴发直接源于早先被突然打乱的生态关系,而这最
终可归结于19世纪90年代牛瘟在非洲猎物中的灾难性传播。大量畜
群的死亡导致采采蝇活动范围的缩小,同时伴以驯畜数量及其活动
范围的缩小。当野畜和驯畜痊愈并开始扩张活动地域时,相互渗透发生了,在扩张着的农业和畜牧业的边界区,鱼鞭虫传染到人类身
上。和Ford的观点相比,上述观点不太怪罪殖民当局,而更强调其
生态原因,尽管两者在使用的基本材料上是一致的。
[17]即缩短食物链的行为。儿童病与文明社会疾病模式的出现
在历史上首先出现农业社会的重要地区,它们的生态系统不像热带
非洲那样从本质上抵制人类的改造。在温带地区,能随时利用人口增长
所带来好处的潜在寄生物不仅数量少,而且也不那么可怕。但是,因为
自然平衡的突破性改变都发生在5000年到1万年前,所以不可能像对非
洲那样,推理出或观察到特定的农业发明和领地扩张所带来的疾病代
价。
不过,我们仍旧可以推导出所有文明社会或早或迟都会遭遇的接触
疾病方面的某种重要而普遍的变化,那就是,即便无须借助中间宿主,农业社会不断稠密的人口最终也会达到可以无限维持细菌和病毒感染的
程度。这种情况在小型社会通常不会发生,因为与多细胞寄生物不一
样,细菌和病毒的入侵会在人体内引起免疫反应,而免疫反应会要求在
宿主—寄生物的关系上做出择优选择:要么受感染人迅速死亡,要么受
感染人完全恢复而入侵者被驱逐出宿主的身体组织。再次感染需等到有
免疫力的抗体淡出血液循环之后,那么至少需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
不过,像生物领域里的普遍情形那样,事情绝不是一两句话所能表
达清楚的。个人对感染的抵抗不只是形成抗体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有些病原体虽然引发抗体,但仍然可能在病人体内潜伏几年甚至一生。
像著名的“伤寒玛丽”(Typhoid Mary)的携带者可以无限期地携带某种
病原体,并且把可怕的甚至致命的症状传染给别人时,自身却没有明显
的病症;在另外的情况下,一种传染病也可以变成隐性的病原,即潜伏于宿主身体的某些部位,并在那里长期隐藏。
最有名的一种潜伏感染模式可以让水痘病毒退到输出(efferent)神
经组织中,潜伏50年之久,然后等到感染者年老时再重新发作,引发带
状疱疹。这样,病毒就完美地解决了在小型社会中如何保持传染链不中
断的问题:即使每一个接触到的人都感染了水痘,并且产生了免疫力,但几十年以后,当没有抗体的新一代人成长起来时,感染又会重现江
湖,潜伏于该人群年长者体内的病毒就会沿着输出神经蔓延到皮肤上,产生带状疱疹;然而,一旦传染到新的宿主身上,该病毒引发的仍是习
见的儿童症状,即水痘。该病对大部分人来说,症状并不严重,加上它
表现出的显著的潜伏方式,都说明这是人类久已有之的病毒性传染病。
在这方面水痘与现今常见的其他儿童病不同。[1]
缺乏上述生存技巧的病菌,若又遭遇宿主体内的因抗体反应所产生
的激烈取舍后果,其生存便只得依靠潜在宿主的庞大数量,也就是说,如果社会的整体规模足够大,那么总有尚未感染这种疾病而易感的人群
存在。这种寄生物,若按生物进化的时间尺度来衡量,无论怎么说都只
能是晚辈,尽管按人类历史的时间尺度来衡量,它已经古老得无从追溯
了。只有在上千人的社会里,这种疾病才会延续,频繁的交往可以使疾
病不间断地从一人传到另一人,而这类社会就是我们所谓“文明”的社
会:规模巨大、组织复杂、人口密集,而且毫无例外地由城市掌管和控
制。因此,直接在人类之间传播而无须通过中介宿主的细菌和病毒性疫
病,首先是文明社会的疾病(即所谓“文明病”):乃城市和与城市相连
的农村的特殊标识和疫病负担。它们包括麻疹、腮腺炎、百日咳、天花等,几乎是所有现代人都熟悉的常见儿童病。[2]
儿童病花了几千年才扩散到全球,本书将用很大篇幅探讨这一扩散
过程的关键性阶段。我们必须假设这些疾病(或今天已知传染病的始
祖)最初的形成过程本身必定是渐进性的,包含了无数错误的开始和致
命的遭遇,其中人类宿主的死亡、入侵的寄生物被消灭、传染链因此而
中断,使它终未能成为文明社会的生物平衡中正常的、地方性的、或多
或少带有稳定性质的因素。
在多数情况下,文明社会所特有的传染病原本都由动物传给人类。
人类同驯养的动物联系紧密,因此毫不奇怪,人类常见的很多传染病与
家畜(禽)的传染病存在着明显的关联。比如,麻疹可能与牛痘或犬瘟
热有关;天花肯定与牛痘一类动物传染病有关;流感则是人猪共患。[3]
根据标准手册(standard book)的记载,[4]
今天的人类与家畜共有的疾
病计有:
这个统计有很多重叠,某些传染病在感染人的同时还感染不止一类
动物;而且,既然一些传染病很少发作,而另一些则很常见,只是统计种类就不是特别有意义。不过,大量的重叠确实表明我们同家畜(禽)
的疾病联系是多么盘根错节;它还表明,随着人与动物之间亲密度的提
高,共同患病的概率也在提高。
除了源自家畜或与家畜(禽)共有的疾病以外,人类也可能因卷入
野生动物内部的疾病循环圈而得病。横行于穴居啮齿动物的腺鼠疫、蔓
延于猴群之中的黄热病,以及蝙蝠易患的狂犬病,都属于这类较为致命
的传染病。[5]
寄生物寻找新宿主的过程还远没有结束,甚至就在近代,这一过程
还造成了出人意料的严重后果。比如,牛瘟在1891年侵入非洲,杀死大
量家畜以及羚羊一类的野生物种;但因它的肆虐如此严重和突然——死
亡率高达90%,所以并没有在当地扎下根来,[6]
相反,可能因为缺少易
感染的有蹄类动物,它在几年后就消失了。1959年,一种叫作“奥尼
欧”(Onyong nyong fever)的热病出现在乌干达——这一人类新病可能
源自猴子身上的病毒。其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但对人类的影响却比较
温和,而且随着免疫力的产生恢复得很快。结果同非洲羚羊所患的牛瘟
一样,奥尼欧热病也未能作为一种地方病存在下来,而是神秘地消失
了,正如它神秘地出现——可能退回它原来居留的树冠区域。[7]
10年以
后,即1969年,另一种比乌干达的热病更致命的热病出现在尼日利亚,这个所谓“拉沙热”(Lassa fever)的新疫病是以医疗站里初次发现它的
西医的名字而命名的。这种热病最终于1973年被证明源自啮齿动物——
被认为是该病主要的宿主。于是,人们便采取了适当的预防措施来阻止
该病的进一步传播。[8]可以想象,随着新动物的驯养、新植物的种植,以及人口的增长,这类插曲还会不时出现:传染病必定不断地从动物,尤其与人类长期紧
密接触的驯养动物中传到人类身上。这种传染自然可以多向度进行,比
如,有时候人的疾病也会传染给他们的家畜(禽)。同样,传染病可以
在家养和野生的动物之间互换,既可以发生在同类间,也可以跨越物种
界限,这是由接触机会以及潜在宿主的易感程度来决定的。
换言之,当新的生态龛由于人类活动改变了动植物的自然布局而空
出后,致病寄生物在利用新的机会占领新的生态龛方面,和人类一样成
功。人类的成功意味着动植物种类的减少,而每一种类数量的增多,在
这一经过改进的新的饲养环境中,寄生物只要侵入单一的物种,就能够
大量地滋生。几乎所有的病毒和细菌在侵入机体后,只能活跃几天或几
周时间,就会被抗体阻断其在单个宿主体内的发展。
在继续探讨疾病史之前,我想还是有必要先来看看采用传染病方式
的微寄生和采用军事行动的巨寄生之间的相似性。只有当文明社会的财
富和技能积累到一定水平,战争和掠夺才能成为经济上可行的事业。如
果武力掠夺收成导致农业劳动力很快被饿死,这还不是稳定的巨寄生模
式。但这种情形经常发生,甚至可以跟1891年的非洲牛瘟感染相比,后
者也是大量杀死宿主,以致未能建立起稳定持续的传染方式。
在文明历史的早期,成功的掠夺者变成了征服者,他们学会这样掠
夺农民,即从后者那里抢走部分的而不是所有的收成。通过试错法可以
且确实能够建立起某种平衡,生产者通过生产超过自身维生所需的谷物
和其他粮食,在这样的掠夺中生存了下来。这种剩余正可以看作应付人类巨寄生的抗体,成功的政府可以使纳税人对灾难性的掠夺和外敌入侵
产生免疫力,正如轻微的感染可以让它的宿主对致病的疫病产生免疫
力。疾病的免疫力通过刺激抗体形成,以及将其他生理防御能力提高到
更活跃的水平而发生作用;政府则通过刺激食物和原材料的更多生产以
供养掌握数量庞大、武器精良的专业武士,来提升对抗外来巨寄生
的“免疫力”。这两种抗体反应都会构成对宿主族群的负担,不过比起反
复遭受突然而致命的灾难来说,这份负担显然要轻一些。
建立成功政府的结果,就是创建了一个与其他人类社群相比更为强
大且更加可怕的社会。专业的武士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战胜那些成
年累月从事生产或寻找食物的人们。正如我们不久将看到的,一个适度
感染、经地方病的病毒和细菌感染而在易感人群中形成抗体的社会,从
流行病学的观点看,要比更简单、更健康的人类社群更为强大。可见,导致强大的军事和政治组织发展的巨型寄生,几乎可以与形成人体产生
免疫反应的微型寄生相对应;换言之,战争和疫病的联系其实并不仅仅
限于巧饰的修辞和经常伴随或尾随战争的瘟疫。[9]
就像牛瘟和奥尼欧热病在非洲的传播那样,大部分的细菌和病毒等
病原体的感染最初可能是不稳定的。我们可以想象,人类族群的人数曾
多次因某些新的地方性疫病的流行而急剧削减。而人类易感宿主一而再
地被消耗,又必定会不断地把入侵的病原体从早期农夫体内的“牧场”中
驱逐出去。尽管如此,再次感染的基础仍然存在,因为驯化的动物极有
可能已经是病毒及细菌性传染病的慢性携带者,这种传染病能够不断地
骚扰人类。从追溯牛、马、羊这类动物的野生状态中,我们也许就能看出它们
被认为是这些传染病的慢性携带者的理由。在人类狩猎者多得足以影响
它们的生存之前,它们是群栖的,成群游荡在欧亚大陆的草地上。作为
单一物种组成的群体,它们正好提供了使细菌和病毒感染演变成地方病
的条件,因为在足够大的群体里总可以找到易感染的宿主来完成传染
链。畜群和寄生物之间漫长的相互进化足以形成稳定的生物平衡,一些
病毒和细菌性传染病可能盛行于野生的牛、羊、马群,却不会导致严重
的症状。这种传染病想必是畜群中的“儿童病”,只影响敏感的幼兽,但
几乎不造成大的伤害。然而,它一旦传入人体,通常会变得很凶猛,因
为初次感染的人体缺少必要的免疫力,而熟悉它们的老宿主则从一开始
就至少拥有局部的防护能力。[10]
不过,我们必须假设,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各种病毒性和
细菌性寄生物最终仍成功地传给了人类,并同它们的新宿主建立了长期
的关系。在很多的甚或是全部的情况下,迅速的和半灾难性的早期调适
无疑是必需的,宿主和寄生物的大量死亡可能交替发生,直到新宿主发
展出的免疫力和寄生物达到的适应性使传染病地方化。当今似乎已难以
找到发生这一过程的例子,但澳大利亚的野兔受到恶性传染的事例表
明,当病毒感染传到新群体时,它是如何生存下来并成为地方病的。
这个故事颇有戏剧性。英国殖民者在1859年把野兔引入澳大利亚,在缺少天敌的情况下,新物种迅速扩散到整个大陆,数量众多,并且对
人而言已经变成了害虫:它们吃掉本应属于绵羊的草,澳大利亚的羊毛
产量由此减少,无数牧场主的收益也跟着缩水。人类在澳大利亚尝试消灭野兔的努力直到1950年才出现转机,当时多发性黏液瘤(人类天花的
远亲)的病毒被成功地植入澳大利亚的野兔群。最初的效力是爆炸性
的:仅仅在一个季节里,相当于西欧那么大的地区就全被感染了。第一
年,感染这种病毒的野兔的死亡率高达99.8%,第二年降到90%,而7
年以后,死亡率仅为25%。显然,非常有力的和迅速的自然选择分别在
野兔和病毒当中发生了,采自野兔身上的病毒样本,其毒性在逐年降
低。尽管如此,澳大利亚野兔的数量再也没有或许永远也不可能恢复到
它以前的水平——截至1965年,生活在澳大利亚的野兔只有多发性黏液
瘤引进之前的五分之一左右。[11]
1950年以前,在巴西的野兔中多发性黏液瘤是一种常见病,该病毒
只在这里的野兔当中引发轻微的症状,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地方病的发病
模式。因此可能有人会认为,从巴西野兔向澳大利亚野兔的传播过程中
所需要的调适,程度上应不如寄生物从不同类的宿主那儿传播到人类所
需要的调适。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它们共有一个名字,但美洲野兔和
欧洲、澳大利亚野兔并不是同种,因此,1950年在专家眼皮底下发生的
宿主转移,与某疾病突破动物宿主的界限开始感染人类,从而成为人类
重要疾病的可能性方式相似。
无论新疾病开始时是否像多发性黏液瘤那样致命,宿主和寄生物之
间的相互调适过程本质上是一致的。一种稳定的新疾病模式,只有当双
方从最初的接触当中存活下来,并且通过适当的生物的和文化的[12]
调
适达到相互容忍的关系时才算确立。在调适的全过程中,细菌和病毒拥
有产生下一代所需时间比人类短得多的优势,因而有助于病原体产生在宿主间安全传播的基因突变,它要比人类遗传天赋或生理特征的相应改
变快得多。的确,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后来的历史表明,人
类要将其对剧烈新疫病的反应稳定下来,大约需要120~150年的时
间。[13]
通过比较,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的野兔数量的最低点出现在1953年,即多发性黏液瘤首次暴发的3年以后。考虑到野兔代际的短暂——澳大
利亚野兔从出生到生崽只要6~10个月[14]
,按每代人25年计算,野兔的
3年相当于人类的90~150年。换言之,人类和野兔需要大致相当的代际
时间来适应致命性的新疾病。
我们可以把宿主与寄生物之间相互调适的整个过程,设想成生物平
衡形成之前一系列的波浪状动荡。最初的动荡可能非常剧烈,像发生于
1950年的澳大利亚野兔那样,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寄生物向新宿主的转
移太过剧烈而无法长久持续。然而,只要新的传染病能够无限期地生
存,自然会出现动态的平衡:频繁感染期与疫病衰弱甚至几乎消失的时
期交替出现。这些变动往往会形成程度不等的有规律的循环,也就是
说,只要来自外部的重大入侵不改变新兴的宿主和寄生物间的平衡模
式。很多的因素都会参与到这种周期性的平衡中来,比如,温度和湿度
的季节变化往往使春季成为温带地区现代城市中儿童病的多发期。
人口中易感人群的数量,以及他们是群居还是散居,都是基础性的
因素。例如,学校和军营一直是现代社会两个最重要的易感的年轻人的
聚集场所,当代西方社会的父母都能觉察到小学在传播儿童病方面扮演
的重要角色:在普及疫苗接种以前的19世纪,法国军队中的来自农村的士兵容易患病,有时非常严重,而这些传染病在城里的同龄人那里因已
有过接触而具有免疫力。结果,强壮的农民子弟比那些来自城市贫民窟
的营养不良的士兵死亡率更高。[15]
感染一个新宿主所需的剂量,传染病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身
上所需的时间,诸如此类的传染方式,以及影响交互传染机会的习俗,都决定着多少人得病和什么时间得病。通常,只有人类宿主大量聚集在
大都市,传染病才能长久地生存下去。在这里,为维持传染链不中断而
与足够多的易感新宿主接触的机会,显然远多于潜在宿主稀疏分布的广
大农村地区。不过,一旦乡村社会也有了足够多的易感人群,这类传染
病也可能以城市为中心向外扩散,像恐怖的野火在村与村、家与家之间
蔓延燃烧。然而,这类传染病的暴发,来得快,去得也快。随着当地易
感宿主的难以为继,传染病也就消失了,只有它最初出现的城市中心是
例外。在那里,足够多的易感人口仍然存在,使病原体不致消亡,而待
到缺乏免疫力的人口再度聚集于在农村地区,又一回合的疫病暴发便再
一次成为可能。
有时,所有这些复杂的因素却会沉潜下来,成为相对简单的、普遍
的发病模式。对麻疹在现代城市社会中传播方式的详细统计研究表明,某种波浪式向前推进的方式在每隔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达到一次高峰。而
且,最近的研究发现,要维系这种模式,麻疹的持续性要求有至少7000
名易感者。考虑到当今的出生率、城市的生活方式以及送孩子读书的习
惯(在这里麻疹可以在初次接触该病毒的一个班级的孩子当中迅速传
播),这一数字意味着,麻疹若要在现代城市中延续下去,其人口下限大约为50万。另外,通过在农村地区的散布,稍小规模的人群也可以维
持麻疹的传染链不致中断。真正让该病毒难以为继的人数底线为30万~
40万人。这一点,可由麻疹感染在那些人口高于或低于这个底限的海岛
上的表现方式来加以证明。[16]
但在现时流行的疾病当中,再没有别的疾病展示出如此明确的方
式,可能也没有别的疾病需要如此大的人群规模来保证它的生存。对于
别的常见儿童病,哪怕是相对精确的研究也尚未展开,这在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人工的免疫措施在所有现代国家中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传染方式。
不过,最常见的儿童病的毒性和发作频率,无论在最近还是欧洲各国政
府首次开始搜集有关各类传染病发病情况的统计数字的19世纪,都出现
了明显的变化。换言之,病原体和人类宿主之间的相互调适,无论过去
还是现在都一直处于快速的演进之中,以应对人类生活环境的变迁。
那么,当代儿童病的“始祖”是在何时何地开始首次侵害人类的呢?
为此搜寻相关的历史记载可能令人沮丧。首先,古代的医学术语很难适
用于当代的疾病分类。其次,症状的变化之大,甚至已令人无法辨认。
新疾病在开始的时候表现出的症状,在后来宿主逐渐产生抗体后往往就
消失了。
关于以往的这类现象,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梅毒在欧洲最
初暴发出来的症状。在今天,当新疾病第一次侵入到刚打破封闭的社会
时,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情形。实际上,这些变化了的症状确实
可以完全掩饰该疾病的性质,除非专家通过细菌学分析才能判断出来。
例如,当结核病第一次进入加拿大的印第安人部落时,他们的身体器官被病菌攻击,但在白人身上却未见有病理反应。而且与那些早就接触过
结核病的社群所表现的感染情形相比,不仅诸如脑膜炎之类的症状表现
得更为严重,其病情的发展速度也快得多。在病症最初出现的时候,只
有显微镜下的分析才能让医生确认这就是结核病。然而到第三代,随着
宿主与寄生物的相互调适逐渐接近常见的城市发病方式,北美印第安人
的结核病症状也倾向于集中出现在肺部了。[17]
宿主与寄生物的调适过程是如此快速而花样繁多,以至我们必须假
定现今流行的传染方式只是瘟疫当下的表现,历史已深刻地改变了它们
的症状。然而,鉴于已知现代城市保持麻疹流行需要50万人,值得注意
的是,最新有关古代苏美尔——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的
总人口的估算,正好是这个数字。[18]
似乎可以肯定,当时苏美尔诸城
市之间有着足够密切的联系,足以构成一个单独的疾病库:若真的如
此,接近50万的人口规模肯定足够支撑类似现代儿童病这样的传染链。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随着世界其他地方也开始了城市文明,连续的传
染链可能也开始在别的地方出现。首先在这儿,然后在那儿,一种又一
种的病原体可能就这样侵入到随处可见的人类宿主,并在由日渐增加的
人口密度为它所创造出的适宜的生态龛上稳定下来。
[1]参阅R. Edgar Hope-Simpson,“Studies on Shingles:Is the Virus
Ordinary Chicken Pox?”Lancet,2(1954),p.1299—1302;R. Edgar
Hope-Simpson,“The Nature of Herpes Zoster:A LongTerm Study and a
New Hypothesis”,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48(1965),p.8—20。[2]Francis L. Black,“Infectious Diseases in Primitive
Societie ......
[美]威廉·麦克尼尔 著
余新忠 毕会成 译
中信出版集团
书名:瘟疫与人
作者:【美】威廉·麦克尼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5月
ISBN:978-7-5086-7780-4
本书由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译者序
在学术史上,借由精深的研究,就某一具体问题发前人所未发,甚
或提出某些不易之论,这样的成果虽然不易取得,但也不时可以见到;
而那种能从宏观上洞察人类思维的某些疏漏,从而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知
识上都能给人以巨大启发和触动的研究,却总是微乎其微。威廉·H.麦
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的《瘟疫与人》,可以说正是这类微乎其
微的研究中的一种。“原来我们对历史的呈现和解读疏忽了如此之
多!”清楚地记得,数年前,当我集中精力读完这一著作后,感受到的
不仅仅是欣喜和激动,还有一种对学术心灵的震撼。毫无疑问,它已成
为我开展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最初乃至持久的动力之一。
作者麦克尼尔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曾以著作《西方
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而蜚声世界史林,是美国当代最具声名
的历史学家之一。本书在西方早已不是一部新著,最早于1976年出版于
美国,翌年和1979年两次再梓于英国,1994年被“企鹅丛书”收入并再
版。作为一部学术著作,以如此高的频率一版再版,其影响之广泛已不
言而喻。而且,其影响显然并不局限于西方世界,本书出版不久,陈秋
坤就以中文书评做了介绍。[1]
1985年,日译本正式出版。[2]
韩文版也于
1992年出版。而中译繁体字版直到1998年才问世。[3]
本著作无疑是部极具开创性的论著,英国牛津大学的基思·托马斯
(Keith Thomas)教授曾在书评中指出:“他(指麦克尼尔)是第一位把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起来,重新解释人类行为的学者,也是第一位把传
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它应有地位的史学工作者。”[4]
即使时至今日,相信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本书仍会让人耳目一新。他从疫病史的角度对
人们习以为常的众多历史现象所做的解释,往往与以往政治史、经济
史、文化史乃至社会史的分析大异其趣。比如,在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
的历史中,1520年,科尔特斯只带了不到600名随从,就征服了拥有数
百万之众的阿兹特克帝国,个中原因,麦氏认为过去种种解释都不够充
分,最为关键的因素还在于“新大陆”居民遭遇了从未接触过而西班牙人
却习以为常的致命杀手——天花。他指出,就在阿兹特克人把科尔特斯
及手下逐出墨西哥城的那晚,天花正在城中肆虐,连那位率队攻打西班
牙人的阿兹特克人首领也死于那个“悲伤之夜”。正是传染病这一可怕
的“生物武器”,帮助西班牙人消灭了大量印第安人的躯体,还最终摧垮
了他们的意志和信念。又如,过去在人们论述公元前430—前429年雅典
和斯巴达争霸战中雅典的失败时,往往将其归因于政治体制的不同等因
素,然而,麦氏却指出,雅典陆军在这段时间,曾因一场来去无踪的瘟
疫折损近四分之一的官兵,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瘟疫改变了地中
海后续的政治史。同样,在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中,瘟疫也至少部分
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当时,天花使得两万法军失去了作战能力,而普鲁
士军人由于做了预防接种而未受影响。当然,麦氏全新的观察并不只是
为了给某些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插入一些偶然性因素,以增加历史的
不确定性。实际上,作者采取的是一种真正从整体上审视人类文明发展
的大历史观,本书“旨在通过揭示各种疫病循环模式对过去和当代历史
的影响,将疫病史纳入历史诠释的范畴”,“并把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中的
角色还置于更为合理的地位上”。从这一视角出发,作者对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重要现象做出了合理而意味深长的诠释。比如麦氏指出,非
洲热带雨林和邻近大草原温暖湿润的气候和丰富的食物十分有利于人类
最初成长,但同时也孕育了极其复杂多样的致病微生物。在这片生态体
系最严峻而多样化的地区,“人类为缩短食物链所做的尝试仍未臻成
功,依然以不断感染疾息的方式,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一点,比其他任
何方面,都更能说明,为什么非洲与温带地区(或者美洲的热带地区)
相比在文明的发展上仍显落后”。又如,作者认为,在另一个微寄生物
特别复杂多样的地区——印度,由于大量微寄生物耗去了当地农民相当
的能量,使得印度的城市及统治者从他们身上攫取的物质与世界其他地
区相比,总显得相对稀少。正是这种表面富足、实则贫穷的现象,让印
度的国家结构总处在一种脆弱而短暂的状态之中,同时,向往来世的人
生观的形成与践行,也就势在必行了。
以上所举不过是作者众多匠心独具的历史阐释中的寥寥数例。在论
述其他诸如罗马帝国的崩溃、佛教和基督教的兴起、欧洲的扩张、印度
种姓制度的形成,以及大英帝国的崛起等种种历史现象时,麦氏均能通
过一般的因果解释,认识到疫病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这些现象表明,疾病,特别是其中的传染病,乃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
一”。然而,如此重要的内容何以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历史学家的冷落
呢?作者认为,“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同样的疫病在熟悉它并具有免
疫力的人群中流行与在完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中暴发,其后果差别巨
大,以往的历史学家才未能对此给予足够重视”。另外还因为,历史学
家往往会在历史中刻意突出那些可预计、可界定且经常也是可控制的因
素。“然而,当流行病确乎在和平或战争中成为决定性因子时,对它的强调无疑会弱化以往的历史解释力,故而史学家总是低调处理这类重要
的事件。”其实循着麦氏的思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史学研究者
对历史问题的兴趣,基本来自现实生活的体验,即使是受过严格训练的
职业历史学者,往往也会在不经意间就以当今世界的经验来理解历史现
象,特别是对那些自己缺乏深入探讨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一方面,疾
病尽管直接关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但人们习以为常,很难想象它会对
一系列重大事件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现在乃至过去的一些经验,一般会使人把疫病当作一种纯粹自然的现象,因此也就难以引起专注于
人类社会文化行为的历史学者的关注。此外,在史籍中,此类资料零
散、不够丰富,这可能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由于过去相关研究的缺乏,人类疾病史上的众多细节问题必然还不
够清楚。在这种状况下,要完成这样一部从宏观上论述瘟疫与人类历史
关系的大作,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技艺。作者正是凭借他深厚
的世界史功力,借由敏锐机智的观察和推理,娓娓道出了传染病在人类
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通过深入的分析和流畅的笔触,作者把传染病如何在人类历史上影响到整个人类的迁移、民族的盛衰、战争的胜败、社会的荣枯、文化的起落、宗教的兴灭、政体的变革、产
业的转型、文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等,做了完整的论述,堪称经典。
全书除“引言”外,共分六章。第一章“狩猎者”,介绍史前时代人类
在征服自然过程中与传染病的关系及传染病对人类文化形成的影响。第
二章“历史的突破”,探讨了公元前3000—前500年人类所遭受的疫病以
及与疫病逐渐调适的过程。第三章“欧亚疾病的大交融”,论述公元前500—公元1200年的疫病史,提出地中海岸、印度和中国间的贸易,在
公元200年左右已运作稳定。这暗示着在交换物资的同时,传染病也一
并交换。由于天花、麻疹和鼠疫等一些原产于印度或非洲的传染病在东
西方相继出现,使其在公元3世纪前后,出现了疫病的多发和人口的减
损。而后,大约在900年,欧亚大陆发展出了相当稳定的疫病模式,人
口再度增长。第四章“蒙古帝国颠覆旧有的疾病平衡”,阐述了1200—
1500年世界各地遭受的疫病。这一时期,蒙古骑士东征西战,使得鼠疫
杆菌等致病微生物轻易地穿越河川等天然屏障,造成了东西方传染病模
式的再度失衡,新一轮的疫病大流行在欧洲以及中国等地出现,特别是
欧洲的黑死病影响至深,直到1500年前后,新的平衡才在各地陆续达
至。第五章“跨越大洋的交流”,讨论1500—1700年世界疫病状态,主要
探讨了欧洲人在征服美洲过程中,由其引入的传染病在其中所起到的巨
大作用,它在摧垮美洲印第安人的信念和与其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
要远甚于武力等人为因素。在这一时期,世界各地的传染病模式还出现
了均质化倾向,即世界各地的致病微生物与人类共生模式更趋稳定,疫
病主要以儿童病、地方病的形式出现,流行频度增加,杀伤力减弱。以
文明族群的大规模成长和疫病隔离群落的加速崩解为主要特征的“现
代”疾病形式逐渐形成。第六章“近代医学实践的影响”,探讨1700年以
后的人类疾病史。随着天花接种的发明推广、近代医学和公共卫生制度
的出现和发展,人类第一次能够通过科学原理在卫生行政上的运用,彻
底打败因类似的科学原理运用到机械运输上而导致的逾越传统地理疆界
的传染病。但疾病与人类的竞争依然存在,直到今天,而且还将会和人
类长久共存。麦克尼尔从病理学和历史学相结合这一独特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和
阐释了人类历史,纵横捭阖,左右逢源,确实提出了众多独具匠心且发
人深省的认识。如果说,这些具体的认识还有重新探讨,至少是进一步
论证的必要,那么,作者在具体的论说中表明的一些基本原理,不管是
否完全正确,都值得每一个历史研究者重视并认真思考。按照笔者的理
解,这些原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人类大部分的生命处
在一种介于“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之间的危险平衡之
中。“微寄生”泛指各种侵害人体的致病微生物,“巨寄生”为对人类能够
开展战斗、抢劫和收税等活动的天敌,包括各种大型动物和其他族群或
阶级,主要为其他族群或阶级,比如征服者、统治者等。自然的变迁和
人类活动往往会导致其中的一方过度发展,使原有的均衡遭受威胁,而
一旦这种均衡被打破,人类的生命也就面临着难以延续的危机。不过人
体的自然免疫力、人类的理性以及自然的有机调节能力又会形成某种合
力指向修弥和维持这种均衡。所以人类的成长,尽管多有波折,但总体
上保持着发展之态势。其次,微寄生与人类宿主之间,主要依靠生物的
自然调适能力,双方才长期维持一种内涵上不断变化但却不失均衡的关
系。这种自然调适可能是为了避免物种的两败俱伤而形成,因为微寄生
如果过分肆虐,则有可能找不到下一个宿主而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从
而中断传染链。所以,传染病在同具有一定规模的人群接触后,其毒力
和致死力会逐渐减弱,以免与人类同归于尽,从而确保在宿主族群中的
永续寄生;而痊愈的宿主一旦增加,即会提高族群的集体免疫力,促使
传染病从流行病转变为地方病乃至儿童病,比如天花、麻疹、流行性腮
腺炎等。不过,这类疾病的形成,必须以人口聚居规模的扩大为前提,因为,只有在数千人组成的社群中,大伙交往的频繁足以让感染不间断地由某人传到另一个人身上,它们才能存在。所以,目前这种幼儿疾病
遍布全球的现象,是经过好几千年才形成的。第三,虽然人类与微寄生
之间总体上总能维持某种均衡,但具体到不同时段和地区,这种均衡实
在非常脆弱,人类任何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改变、生产能力的提升和
交通的发展等,均有可能导致均衡的破坏。其中又以以下三种变化影响
最大:1.人类舍渔猎而就农业生产;2.人口不断增长与集中,人口密度
的增加以及城居生活方式的出现;3.交通工具与运输能力的改进,引发
洲际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频繁。这些人类本身的行为,一般都会引
起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并最终促使人类与微寄生原有的平衡经受新的
考验甚至崩溃。因此,疾病史研究与自然生态史密不可分。第四,尽管
几乎所有传染病模式的改变,均由人类自身的行为所引起,但在近代医
学和公共卫生制度出现和确立之前,人类与微寄生之间形成的稳定关系
基本是依靠生物自然调适机制完成的。作者认为,传统医学理论大致说
来是经验主义的,并极端地教条化,“经验每每被牵强地套用既有理论
术语来加以解释,而治疗方法因而也歧义互见”,而且“很少有人能付得
起昂贵的医疗费用”。所以,“即便是最出色的医疗也对疾病无能为力,甚至还妨碍康复”。
循着以上思路来考量中国历史,相信会引发我们对许多历史现象的
重新思考。比如,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但现代认为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长江流域却长期处于后进状态,其缘由
是否跟南方的疾病梯度较高关系密切?又如,魏晋时期和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大的分裂时期,而这几个时期恰好是中国历史上疫
病的高发期,同时也是欧亚大陆传染病模式动荡调整时期,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有某种必然的联系?若有联系,究竟是分裂促发的瘟疫,还是瘟
疫阻碍了统一?再如,清代人口的高速增长,除了现有的众多解释外,是否与十六七世纪以来世界性的传染病模式日趋稳定有关,或者还有清
代医药整体水平提高的功劳?以上种种,显然只有等待我们对中国疾病
史做出较为专深的研究后,才有可能获得相对满意的回答。
当然,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东方世界,疾病社会史研究还明显不
够深入细致的情况下,撰写这样一部从宏观上把握疫病与人类历史发展
关系的著作,危险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我们在书中也很容易发
现,作者的论述常夹杂着假设和旁证,有时还包括某些想象的成分。在
不少的细部研究上,尤其是关于中国的部分,还多有误会。比如,由于
作者基本不了解甚至误解中国医学19世纪以前在对付温病[5]
和接种“人
痘”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本书中有关中国传统医学对人口增长作用的
认识显得有过分夸大自然调节作用而无视人为因素之嫌。另外,其赖以
为基础(指中国部分)的疫情年表,也显得过于粗糙。对于细节的错
误,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已通过译注的方式做了辨析。尽管如此,这
些微瑕仍不足以影响本书的重要价值,或许,其价值本不在于呈现出多
少具体的历史真相,而是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独特研究视角。
对于这样一部世界史学界的经典之作,中国史学界特别是大陆史学
界的关注度显然远远不够,尽管中译本本来就姗姗来迟,但就是迟来的
译本,至今在大陆也未能、实际也难以拥有较多的读者。因此,在大陆
出版中译本就显得十分必要。繁体字中译本总体上是较为忠实原文的不
错的译本,译者杨玉龄先生系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对书中有关医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内容有较好的把握,译文也显得颇为精当。但其对历史知
识则相对隔膜,故而以专业历史研究者的眼光视之,译文在历史名词乃
至历史事件的把握方面,仍有不小的改进空间。而利用最新的研究对书
中的相关问题做出辨析这样的工作,自然更是无从谈起了。另外,该译
本在标题方面对原书做了不少调整,虽然比较醒目,但似乎也有不够忠
实原文之处。特别是完全删去原书的注释,颇让人感到美中不足。故
此,我们感到仍有重新翻译的必要。当然,在译完初稿后,我们参考了
这一译本,并借鉴了其中不少精当的译法,特此说明并致以诚挚的谢
意。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始终以忠实原文原意为第一要义,原著行文流
畅而优美,不禁令人深感钦羡,尽管也做了尽可能的努力,但限于时间
和水平,我们的译笔显然仍远无法与原文畅美的笔调相提并论,同时还
可能存在不少不足乃至误译之处,这是需要向读者致歉并敬请读者不吝
赐教的。
本书从开始翻译到现在出版,经历了不少波折,也为我们留下了不
少需要感谢的人物。如果没有中国人民大学夏明方和北京师范大学梅雪
芹两位教授提议和促成,本书的译成和出版,或将是不可能的事。在翻
译的收尾阶段,汪敏(Katherine Robinson)和吾妻惠清楼两位女士在文
字的校订方面做了不少重要的工作。在后来几次修订中,叶慧女士、梅
雪芹教授和孙健先生给予了许多十分有益的指教。另外,第六章的修订
曾得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张瑞和张华的襄助。对于以上师友和同
道的情谊和帮助,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当然,本书翻译中存在的
问题均由译者负责。长江后浪推前浪,人类的知识和对具体问题的认识无疑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不断更新,但凭借知识的累积和个人的敏锐与智慧提出的某些
认识维度和思考方式却似乎可以超越知识更新本身,具有长久的魅力。
二十多年过去了,对书中那些具体的观点,相信不同领域的专家大概都
可能提出异议,不过,书中揭示的研究视角与基本原理,不仅在过去较
深地影响了世界史学的发展,而且也是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者,特别是
医疗社会史和环境史的研究者不应忽视的。在世界范围内,疫病社会史
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二十多年来,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就。不
过就中国史而言,似乎才刚刚兴起。[6]
希望麦克尼尔这部大作的再版,不仅有利于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而且可以促进更多人重新省思认识和
探讨历史的视角与方法。
余新忠
2004年6月初稿于京都大学国际交流会馆
2009年6月修改于南开大学
今年4月下旬的一天,我无意从网上得悉本书的作者麦克尼尔先生
已经于去年7月8日仙逝。一代史学宗师的故去,自然会让如我这般深受
启益的后学晚进感到哀伤。不过,更令我感怀的,似乎还是他再也不可
能知道,由他推动兴起的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影响远播,业已成为中国
学界颇受瞩目的新兴研究,21世纪以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早已不再是
他写作此书时几无成果可资利用的情景了。八年前,麦克尼尔先生为该
书的中文版慷慨赠序,在感动和深受鼓舞之余,也不免对作者对中文学界的相关研究依然缺乏了解感到些许遗憾。想起这些,并不是觉得作者
有什么不妥,而是感到,中国学术虽然近些年取得了不小的发展,但放
眼国际,无疑还远没有可以沾沾自喜的资格。
这本完成于40年前的著作,在国际学术界取得了广泛而深远的影
响,不过其对中文学界的影响可谓姗姗来迟,直到20世纪末,才首次出
版了中文繁体字版,简体字版的正式面世也才不过几年时间。但令人感
到欣慰的是,近些年来,该书在国内学术界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注目。
十余年来,国内已经有三家出版社相继购买译著版权,大概就是很好的
证明。这对于我们译者来说,在感到荣幸和欣喜的同时,也更多了一份
对作者的敬意,以及对进一步推动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向前发展的责任
和期盼。
承蒙中信出版社和马晓玲编辑的见爱,本译文有机会再次出版。为
此,马编辑做了大量工作,敦促我们尽可能全面地修正译文。在译文的
修正中,我的研究生宋娟、朱绍祖和王沛珊给予了重要帮助,谨此说明
并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余新忠
2017年7月19日又记于津门寓所
[1]陈秋坤:《人类造就了瘟疫——介绍麦克尼尔教授新著:〈瘟疫与
人〉》,载陈胜昆:《中国疾病史》《附录》,台北:自然科学文
化事业公司,1980年。
[2]《疫病と世界史》,佐々木昭夫译,东京:新潮社,1985年。[3]《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杨玉龄译,台北:天
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
[4]此处内容见陈秋坤:《人类造就了瘟疫——介绍麦克尼尔教授新
著:〈瘟疫与人〉》,载陈胜昆:《中国疾病史》《附录》,第
251页。
[5]温病是中国传统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是指外感热病,即感
受温热病邪所导致的疾病,包括现在的各种疫病和感冒等。
[6]参阅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
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世纪明清疾
病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中国疾
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年第
4期。中文版前言
在我写的所有著作中,无论在历史学家和医生们那里,还是在普通
民众中,《瘟疫与人》受欢迎的程度都是最高的。当它于1976年首次出
版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别的什么书在讨论传染病在整体上对人类历史的
影响。尽管我常常依靠推论来重构交通的变迁如何导致传染病的跨区域
传播,但要解释这种疾病的发生机制,以及测算出人口伴随幸存者血液
中的抗体的增加而恢复增长所需要的时间,则只能依赖传染病学上的最
新进展。
疫病的历程揭示了人类事务中曾被忽视的一个维度;在本书付梓之
后不久,由于偶然的原因,艾滋病引发了广泛的公众注意力。两相结
合,扩大了《瘟疫与人》的读者群,且至今仍在美国及其以外的读者中
深受欢迎。
中国的读者将会看到,为了尽力发掘中国的瘟疫史料,我只能求助
于他人。我不懂汉语,但知道有两本专业的百科全书和所有的正史都谈
到了(中国)瘟疫暴发的地理区域和严重程度。那时还是一名研究生的
约瑟夫·H.查(Joseph H.Cha)教授热心地查阅了这些中国典籍,并把他
查阅的结果整理成一个详细的附录,时间从公元前243年直到公元1911
年。这些工作无疑表明了瘟疫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并使我有可能结
合黑死病时代及其后亚欧大陆其他地区的情形,对此做出适当的推断。
我希望并且相信这个译本将激发今日中国的一些读者,能比我更为细致地来探讨疾病这一类因素在自然环境中的角色,更正和充实我所写
下的结论,并将对中国历史的科学研究提升到堪与前人比肩的水平做出
贡献。
威廉·H.麦克尼尔
2009年6月19日致谢
本书初稿完成于1974年春夏,于1975年春季校订完稿。此间,书稿
曾分送下列专家以求教正:亚历山大·本尼希森(Alexandre
Bennigsen)、詹姆斯·鲍曼(James Bowman)、弗朗西斯·布莱克
(Francis Black)、约翰·Z.鲍尔斯(John Z.Bowers)、杰尔姆·贝勒比尔
(Jerome Bylebyl)、L.沃里克·科普莱逊(L.Warwick Coppleson)、艾
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Alfred W.Crosby,Jr.)、菲利普·柯廷(Philip
Curtin)、艾伦·德布斯(Allen Debus)、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何炳棣(Ping-ti Ho)、拉弗内·库恩克(Laveme Kuhnke)、查尔斯·莱斯莉(Charles Leslie)、乔治·勒罗伊(George Leroy)、斯图
尔特·拉格兰(Stuart Ragland)、康纳德·德劳利(Donald Rowley)、施
钦仁(Olaf K.Skinsnes)、H.伯尔·斯坦巴克(H.Burr Steinbach)、约翰·
伍兹(John Woods)。本书还受益于美国医学史协会1975年5月召开的
一次小组讨论会,在这次会上,索尔·贾科(Saul Jarcho)、芭芭拉·G.
罗森克兰茨(Barbara G.Rosenkrantz)、约翰·达菲(John Duffy)以及
京特·里斯(Guenter B.Risse)等就他们阅读的部分给予了指教。随后,在1975年秋季,芭芭拉·多德韦尔(Barbara Dodwell)和休·斯科金
(Hugn Scogin)分别校阅了本书的第四章和中文资料部分;他们还共
同修正了本人对有关黑死病传播方式的理解。幸运的是,在本书付梓的
最后时刻,这些修正得以体现于文中。
上述情况表明,本书的很多论断和结论多少带有尝试的性质,有待在疫病方面通过对中文以及其他古代文献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后加以进
一步的完善。诸多建议者的指正使本书在许多细节上得以改进,并使我
避免了许多愚蠢的错误;当然,不用说,全书所有的内容,包括许多遗
留的谬误,均由本人自己负责。
承蒙小约瑟·玛西基金会的慷慨赞助,我方能摆脱一些日常的事务
性工作而专事本书的写作。还应感谢爱德华·特纳(Edward Tenner)博
士帮助查阅有关的西文资料,感谢约瑟夫·查博士帮助查阅有关中文和
日文资料,并汇编了附录部分的中国疫情年表。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
的成稿将费时更多,尤其是书中有关远东的论述将会更为粗疏。感谢马
尔尼·维特(Marnie Veghte)以令人满意的准确性和令人钦佩的速度,将书稿打印了两次。道布尔迪(Doubleday)旗下的安科尔(Anchor)
出版社的查尔斯·普里斯特(Charles Priester)提出了一些非常有针对性
的问题,使我在原稿的基础上做了重要的修改和提高。
对上述诸位,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威廉·H.麦克尼尔
1975年12月15日引言
缘起
将近20年前,为撰写《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The Rise of
the West:A History of Human Community)一书,我开始涉猎西班牙征服
墨西哥的历史,以充实相关史料。众所周知,埃尔南多·科尔特斯
(Hernando Cortez)凭借其区区不足600人的兵力就征服了人口数以百
万计的阿兹特克帝国(Aztec Empire)。如此少的兵力何以能横行异
域?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通常的解释似乎都很难令人信服。如果说蒙特祖玛[0]
和他的同盟者
开始时将西班牙人视作神明,然而一经直接接触,现实情况就自然会让
原有的迷信不攻自破;如果说西班牙人的战马和枪炮在初次交战时令对
手惊慌失措,那么一旦短兵相接,这两种武器的局限性不久也自会暴露
无遗——当时的枪炮其实相当原始;当然,科尔特斯联合其他印第安民
族的“以夷制夷”之术对胜局意义重大,然而除非科尔特斯的那些墨西哥
的印第安人盟友认定他一定取胜,又怎么可能与他结盟?
实际上,征服墨西哥的传奇只不过是更大的谜团中的一部分——不
久,皮萨罗(Pizarro)同样不可思议地征服了南美的印加帝国。相对而
言,越洋抵达新大陆的西班牙人并不多,然而他们却把自己的文化成功
地强加给了人数多得不成比例的美洲印第安人。欧洲文明固有的魅力以
及西班牙人无可否认的技术优势似乎并不足以解释古老的印第安生活方式和信仰的全面崩溃。譬如,为什么墨西哥和秘鲁的古老宗教消失得如
此彻底?村民为何对那些多少年来一直庇佑他们的土地丰收的神祇和祭
典不再虔诚了?或许,在基督教教士们的心目中,基督教的真理性是如
此显而易见,以至他们认为使几百万印第安人成功皈依根本就无须解
释,但事实上,他们的布道以及基督教信条和仪式的内在吸引力似乎并
不足以解释这一切。
不过,在有关科尔特斯征服史的诸多解释中,有一项不经意的说法
(我已记不起具体出处了)令我茅塞顿开,而后通过进一步缜密思考这
一解释及其背后的含义,我的新假说逐渐变得合理而有说服力了。因
为,就在阿兹特克人将科尔特斯的军队逐出墨西哥城,并予以重创的那
天晚上,天花这种传染病正在城内肆虐,那位刚刚率领阿兹特克人对西
班牙人展开进攻的将领和好多人一道死于那个“悲伤之夜”(noche
trista,西班牙人后来以此称呼这场疫病)。这场致命的传染病所造成的
毁灭性后果恰好解释,为什么阿兹特克人没有乘胜追击,而让敌人得以
喘息并获得卷土重来的机会,进而联合其印第安盟友完成对城市的合
围,赢得最后的胜利。
值得关注的,还有这场只杀死印第安人、对西班牙人却毫发无损的
疫病对当时人们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对这种明显的偏袒,当时只能从超
自然的角度加以理解,很明显,在这场战争中哪一方得到了神明的助佑
似乎已不再是问题。在西班牙人的神祇展现了其“超自然的能力”之后,那些以古老的印第安神祇为中心构建的宗教、祭祀制度和生活方式也就
很难维持下去了。难怪印第安人会如此温顺地接受基督教,并向西班牙人俯首称臣。显然,上帝站在西班牙人一边,而且以后每一场来自欧洲
(不久后也来自非洲)的传染病的造访,都在重复这一经验。
可见,传染病一边倒地只对美洲印第安人造成伤害这一史实,为我
们理解西班牙何以能轻易征服美洲(这种征服不仅是军事上的,同时也
是文化上的)提供了一把钥匙。不过,这一假说一经提出,马上就会引
发相关问题:西班牙人何以且何时获得了这种使他们在新大陆如入无人
之境的免疫力?为什么印第安人没有属于自己的本土疫病以对付入侵的
西班牙人?只要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随之而来的就将显现一个尚
未被历史学瞩目的人类历史中的新领域,即人类与传染病的互动史,以
及当传染病逾越原有界域侵入对它完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时,所造成的
深远的影响。
由是观之,世界历史其实已经提供了许多与十六七世纪发生于美洲
的这一幕类似的事例。本书就将描述这些致命性遭遇的梗概。我的结论
可能会使许多读者大感意外,因为在传统史学中很少受到关注的事件却
将在我的叙述中占据核心地位。之所以如此,主要就在于,长期以来那
些学识渊博的学者在皓首穷经于各种遗存的文献时,对于人类疾病模式
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缺乏敏锐的洞察力。
自然,传染病首次袭击某族群的著名案例从来没有被欧洲人遗忘,14世纪的黑死病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其次是19世纪的霍乱大流行,后者
虽然破坏性大为降低,但因更接近于现代而留下了比较完整的记录。尽
管如此,历史学家却从未将其归为重大疫病暴发的普遍模式,因为那些
人类与疫病惨烈遭遇的案例都已湮没于时间隧道中。那时资料残缺不全,以致事件发生的规模与意义都很容易被忽略。
在解读古代文献时,历史学家自然会受到他们自身疫病体验的影
响。经历过各种病史的现代人,已对那些常见的传染病拥有了相当程度
的免疫力,这使他们能很快地终止任何一般性疫病的流行。生活在这样
的背景下,受过严格训练的历史学家只能认为那些疫病造成大规模死亡
的说法未免夸张。事实上,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同样的疫病在熟悉它
并具有免疫力的人群中流行与在完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中暴发,其造成
的后果差别巨大,以往的历史学家才未能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确实,如果现代医药出现之前的传染病均与欧洲的传染病模式并无二致,那么
又有什么必要关注疫病的历史呢?因而,历史学家也往往以一种不经意
的笔调处理这类记载,一如我在那本描述科尔特斯征服史的著作中所读
到的那样。
于是疫病史便成了偏好“掉书袋”的老学究们的专利,他们热衷于就
手头掌握的资料摘录一些实质上并没有什么意义的信息。不过,毕竟还
有黑死病以及其他一些事例,在这些事例中,军营里突发的疫情不仅扭
转了战局,有时甚至决定了战争最终的胜负。这类插曲自然不大可能被
遗漏,但它们的不可预见性却使历史学家深感不自在。我们都希望人类
的历史合乎理性、有章可循,为了迎合这一普遍的愿望,历史学家也往
往会在历史中刻意突出那些可预测、可界定且经常也是可控制的因素。
然而,当流行病确实在和平或战争中成为决定性因素时,对它的强调无
疑会弱化以往的历史解释力,故而史学家总是低调处理这类重要的事
件。不过,还是有诸如细菌学家汉斯·津瑟(Hans Zinsser)这样的圈外
人士,搜集一些表现疾病历史重要性的史料,扮演了抬杠者的角色。他
在那本极具可读性的大作《老鼠、虱子和历史》(Rats,Lice and
History)中,描绘了斑疹伤寒的暴发如何经常打乱国王和将领的如意算
盘。但是,这类著作并未试图将疾病史纳入更宏大的人类历史的背景下
考察,与其他著述一样,它们仍将疫病的偶然暴发视为对历史常态突然
而不可预测的扭曲,本质上已超出史学的诠释范围,因而也就很难吸引
以诠释历史为本业的职业历史学家的视线。
本书旨在通过揭示各种疫病循环模式对过去和当代历史的影响,将
疫病史纳入历史诠释的范畴。我在此提出的许多猜测和推论仍是尝试性
的,对它们的证实与修正还有待有关专家对语言晦涩的古代文献做进一
步地爬梳。这类学术性的作品既需要提出一个正面的主题予以确证,又
需要提出一个反面的靶子以便有的放矢,我在本书所做的推理与猜测应
该符合这一要求。与此同时,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引起读者关注那
些人类历史的传统观念与当下认识之间存在的鸿沟。
除了我必须描述的细节外,想必大家都会同意,更加全面深入地认
识人类在自然平衡中不断变动的地位,理应成为我们诠释历史的组成部
分。而且毋庸置疑,无论过去与现在,传染病都在自然平衡中扮演着至
关重要的角色。
关键概念
在叙述故事之前,对寄生、疾病、疫病以及相关概念的解释或许有
助于避免读者的混淆。对所有的生物来说,疾病和寄生物几乎无所不在。当寄生物从某个
有机体身上成功地搜寻到食物时,对后者(宿主)而言,就是一场恶性
感染或疾病。所有的动物都以别的生物为食,人类也不例外。对于人类
的觅食以及觅食方式变迁的论述充斥于经济史的著述中,相反,避免为
别的生物所食的问题却比较少见,这基本是因为人类自从远古时代起,就不怎么畏惧狮子和狼之类的大型食肉动物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
以认为,人类大多数的生命其实处在一种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
巨寄生构成的脆弱的平衡体系之中,而所谓人类的巨寄生则主要是指同
类中的其他人。
微寄生物(microparasites)是指微小生物体(病毒、细菌或多细胞
生物),它们能在人体组织中找到可供维生的食物源。某些微寄生物会
引发急性疾病,结果,或者很快杀死宿主,或者在宿主体内激发免疫反
应,导致自己被消灭。有时,此类致病生物体不知怎的寄生到某个特殊
的宿主身上,使后者成了带菌者,能够传染给别人,自己却基本不受影
响。而且,还有一些微寄生物往往与人类宿主形成比较稳定的平衡关
系,这种感染无疑会消耗掉宿主一定的体能,但却无碍于宿主正常机能
的发挥。
巨寄生物(macroparasites)也呈现出类似的多样性。有些会迅速致
命,像狮子和狼捕食人或其他动物那样;另一些则容许宿主无限期地生
存下去。
早在远古时期,人类捕猎的技巧和威力就已超越了其他食肉动物。
于是人类攀上了食物链的顶端,也就很少再有被天敌吞食的危险了。不过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同类相食几乎构成人类相邻族群间相互关系
的重要内容,这意味着人类作为成功的狩猎者,几乎与狮、狼处于同等
的水平。
后来,当食物的生产成为某些人类社群的生活方式时,一种较温和
的巨寄生方式才成为可能。征服者从生产者那里攫取并消费食物,由此
成为靠生产者为生的新型寄生者。尤其是那些出现在土地肥沃地区的事
实表明,人类社会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巨寄生模式是完全可能的。事实
上,早期文明就是建立在这一模式之上,胜利者只是从臣服族群那里掠
取部分收成,而留下足够的粮食让被掠夺者年复一年地生存下去。在早
期阶段,这种人类文明的巨寄生基础还相当严峻和明确,后来随着城市
和农村间互惠模式的日趋发展,只是上缴租税所体现的寄生单向性才逐
步消除。尽管如此,在开始阶段,那些饱受压榨的农民,供养着神甫、国王以及跟随这些阶层生活在城里的仆从,除了受到某种不确定的保
护,以避免遭受其他更加残忍和短视的掠夺者的侵扰之外,他们所得到
的回报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食物与寄生物之间的共生共存关系,曾经巩固了人类的文明史,类
似的情形亦可发现于人体之内。白细胞是人体内防御疫病感染的主要元
素,它们能够有力地消解人体的入侵者。它们不能消化的部分就变成了
寄生物,反过来消耗人体内对它们来说有营养的东西。[1]
然而,就入侵特定人体的特定生物来说,这不过是影响其能否顺利
侵入并在其中繁殖的极端复杂的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事实上,尽管
医学在过去百年间成就辉煌,但还是无人能完全说得清它们间的相互关系。在机体组织的各个层次(分子[2]
、细胞、生物体和社会)上,我们
都可以碰到均衡模式。在这种均势中,任何来自外力的变动都会引发整
个系统的补偿性变化,借以最大限度地减缓全面的震荡,当然,如果变
化突破了特定的“临界点”,也会导致原有体系的崩溃。此类灾难,既可
能将原系统分解成更简单、更微小的单元,这些单元又都各自形成自己
的平衡模式;或者相反,将原有相对较小的单元组合成更大或更复杂的
整体。实际上,这两个过程也可能同时共存,就像大家所熟悉的动物消
化过程一样,捕食者把食物中的细胞和蛋白质分解成更小的单元,只是
为了把它们合成为自身体内的新蛋白质和新细胞。
对此类机制的解释,显然简单的因果分析远远不够。既然同时存在
许多变量,它们又不间断地交互作用,而且还以不规则的频率改变它们
的规模,因此,如果我们只是将注意力集中到某个单一的“原因”上,并
尽力将某个特定的“结果”归因于它,结果往往是引人误入歧途。对多过
程的同时态研究或许有助于我们的理解更接近真实,但这样做,无论在
观念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都存在巨大的困难。对大部分组织层次而言,仅仅是对组织模式的确认及观察其存在或崩解,就让人感到有些力所不
逮了,更何况在包括社会在内的某些层次上,连哪种模式值得关注或者
能够被可靠地观测,也都存在深刻的不确定性和争议。不同的术语会引
导人们关注不同的模式,然而,要想找出一个逻辑上富有说服力并能为
各方所接受的试验方案,用以测定一套术语是否优于另一套,通常是不
可能的。
然而,缓慢的进化过程不仅适用于人类的身体,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及其符号体系,因此,当有些问题无法依靠逻辑来确定时,生存定
律终将出面解决。对人类来说,那些能将我们的视线引向所处环境中利
害攸关方面的术语,无疑具有巨大的存在价值。正是基于相互交流和沟
通的能力,人类才得以主宰生物世界。然而没有哪一种术语体系有可能
穷尽或涵盖我们所处情境的每一个方面。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己所能地运
用我们所继承的语言和概念,而不必为寻求一个能在任何时空环境下让
任何人满意的所谓“真理”而枉费心机。
正如语言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一样,疾病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如此。
假如史书中的许多圣人生活在今天的美国,恐怕很难逃脱因“精神不正
常”而被送入精神病院的命运;相反,被狩猎先祖们视为生理残疾的近
视眼和味觉迟钝,在今天却不会被认为与健康理念有冲突。不过,尽管
存在这样的历史性差异,“疾病”概念的核心内容仍是确定而普遍适用
的。一个人若因身体机能紊乱而无法完成预期的任务,这人就将被同类
视为“有病”,而在这类生理机能紊乱中,又有许多源自与寄生物的接
触。
毫无疑问,不同的人体和社群对同样的传染病所表现出的敏感程度
和免疫水平相当不同。这种差别部分缘于遗传,更多则是与以前是否接
触过入侵生物体有关。[3]
不断调整对疾病的抵抗力,并不只在个体进
行,在整个族群内部也同样如此。因此,他们对疾病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也会相应地改变。[4]
正如个人与群体为对付传染病而不断进行机能调整一样,各种致病
微生物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典型的,比如这一环境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虽然不是全部)就是宿主体内的状况。毕竟,对于包括病
原体在内的所有寄生体来说,都必须经常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宿主几
乎都是互不相连的独立个体的情况下,它们如何才能成功地转移?
人类宿主和病原体之间在经历了许多世代,以及数量可观的族群的
长期相互调适后,会产生一种能让双方共容共存的相互适应模式。一个
病原体如果很快杀死其宿主,也会使自己陷入生存危机,因为这样一
来,它就必须非常迅速和频繁地找到新的宿主,才能确保自身的存活与
延续。反过来,如果一个人的抗感染能力足以让寄生物无处藏身,显然
也会对病原体造成另一种生存危机。事实上,正是由于上述这类极端情
形的出现,使得许多与疾病为伴的关系未能延续至今;而一些曾经恶名
昭著的病原体,由于全球范围内普遍的疫苗注射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的
推行,正在濒临灭绝——如果某些踌躇满志的公共卫生官员的言论是可
以信任的话。[5]
对寄生物与宿主来说,较为理想的状态通常(但非必然)是,两者
都能在对方存在的情况下无限期地生存下去,并且互相不会对对方的正
常活动造成重要的损害。这类生物平衡的例子不胜枚举,譬如,人的肠
道下端通常带有大量的细菌,但这并不会引起明显的病征。在我们的口
腔中和皮肤上,也附着了众多通常并不会对我们造成实质性影响的微生
物,其中有些可能有助于消化,另一些则被认为能够防止有害生物在我
们体内的恣意繁殖。不过,一般来说,对于或许可以称之为“人类感染
生态学”的这类论题,我们目前还缺少确凿有力的数据来加以论证。[6]
不过,从生态学的观点看,我们似乎仍可以说,很多最致命的病原体其实还未适应它们作为寄生物的角色。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依然处在
与人类宿主的生物调适进程的早期阶段;当然,我们也不应就此假设,长期的共存必定导致相互间的和谐无害。[7]
譬如,引发疟疾的疟原虫可能是人类(甚至前人类)最古老的寄生
物,[8]
但它至今仍给人类宿主带来严重的使人四肢虚弱的发热病。至少
有四种疟原虫能感染人类,其中又以镰状疟原虫(Plasmodium
falciparum)最具杀伤力。不难想见,由于镰状疟原虫侵入人体血管相
对较晚,所以它们还无法像其他疟原虫那样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人类宿
主。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宿主与寄生物之间的进化调适,还会因宿主
的多样性而更加复杂,而寄生物为完成生命周期又不得不适应宿主体内
的环境。而且,有利于疟原虫长期寄居于人类红细胞中的调适,对其实
现在不同宿主间的成功转移并无助益。
事实上,在通常主导性的转移模式中,人体一旦为疟原虫感染,红
细胞就会成百万地周期性坏死,由此导致宿主怕冷发烧,并让疟原虫得
以在血管中自由运动,直到一两天后,它们重新寄居在新的红细胞里。
这一过程会给宿主带来热病和四肢疲软的症状,但同时也会让疟原虫以
一种独立自由的形式趁着疟蚊饱餐人血时“搭便车”转移到别处繁衍。疟
原虫一旦进入疟蚊胃部,就会展示出不同的行为方式,最终完成有性生
殖(sexual replication)。结果是几天后,新一代的疟原虫就会游移到疟
蚊的唾液腺里,以备在疟蚊下次“就餐”时侵入新的宿主体内。
就目前能够观察到的情况看,疟原虫在被疟蚊以如此巧妙的方式从
一个宿主转移到另一个宿主时,并不会对疟蚊造成伤害。疟原虫生活史的完成有赖于疟蚊体内组织的滋养,但这对疟蚊的寿命及其活力却并无
不利的影响。这样说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疟原虫要被成功地转移
到新的人类宿主身上,携带它的疟蚊必须拥有足以供自己正常飞行的精
力。一个沉疴在身的疟蚊不可能将疟原虫成功运送到新的人类宿主以助
其完成生活史。但是,一个身体虚弱、浑身发烧的病人却丝毫不会妨碍
疟原虫完成其生活周期。因此毫不奇怪的是,这种古老的传染病对疟蚊
毫发无损,却一直维持着对人类的杀伤力。
人类其他一些重要的传染病也像疟疾一样,病原体必须让自己适应
多个宿主。假如人类之外的宿主对这类寄生物更为重要,其适应性行为
的重心将会集中于同非人类宿主达成稳定的生物平衡上,一旦它们侵入
人体,则可能对人类造成剧烈的伤害。腺鼠疫(bubonic plague)就是这
样,引起这种疫病的鼠疫杆菌(Pasteurella pestis)通常只感染啮齿动物
以及它们身上的跳蚤,偶尔才染及人类。在穴居啮齿动物群体当中,这
种感染可以长期延续下去。鉴于同一洞穴中可能混居着不同的啮齿动物
宿主,这类感染及康复的模式必定极端复杂,我们对此至今也未能完全
了解。然而,不管怎样,对生活于“地府”中的某些穴居啮齿动物来说,腺鼠疫就像城市居民习以为常的天花、麻疹一样,乃一种常见“儿童
病”(childhood disease)。换言之,啮齿动物与这种寄生杆菌之间已经
形成相当稳定的适应模式。只有当疾病侵入从未感染过该病菌的啮齿动
物和人群时,才会酿成惨剧,就像历史上曾令我们的祖先倍感惊恐的腺
鼠疫大暴发。
由于血吸虫病(通过钉螺传染)、昏睡病(通过采采蝇传染)、斑疹伤寒(通过跳蚤和虱子传染)以及其他一些疾病的病原体拥有两种甚
或更多的宿主,以致它们与宿主的适应模式极为复杂。因此,这类疾病
对于人类来说,仍然十分可怕。斑疹伤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品系相
同或近似的引发斑疹伤寒的立克次体(rickettsial organisms)能稳定地
寄居于某些种类的壁虱身上,代代延续而且基本相安无事;当老鼠及其
身上的跳蚤被感染后,虽会发病,但可以自行康复,也就是说,它们在
感染后可以通过自我调适将入侵的病原体拒于身外。但是,一旦伤寒寄
生菌转移到人体及人身上的体虱,总会导致体虱毙命,而对人来说,也
常常是致命的。上述模式暗示斑疹伤寒病原体曾存在这样一种渐进式的
转移:从最初与壁虱稳定的共存,再到与老鼠及其身上跳蚤的次稳定调
适,最后到与人及其体虱间的极端不稳定适应。这似乎也意味着该病原
体直到晚近才感染人体及其体虱。[9]
当然,也有一些人类疾病并不需要传播媒介便可直接在人类不同宿
主之间迅速传播。结核病、麻疹、天花、水痘、百日咳、流行性腮腺炎
和流行性感冒等都属于这类疾病。事实上,它们也是现代人极为熟悉的
传染病。除了结核病和流行性感冒,人类只要被这类疾病感染一次,即
可获得长期乃至终身的免疫力。于是,这类疾病通常只感染孩子。这在
那些没有采用疫苗接种或其他人工方法改变天然的疾病传播方式的地
区,依然如此。
这种儿童病一般不会特别严重,通常只要精心护理就可以康复。然
而当其侵入以前从未接触过它们的族群时,则可能导致大面积的发病和
死亡,而且正值盛期的青年人比其他年龄层的人更易感染并导致死亡。换言之,一旦某一“处女”族群初次接触这些传染病,极有可能使整个社
会遭受严重的甚至毁灭性的打击,就像天花和随后的其他疾病对阿兹特
克帝国和印加帝国所造成的影响一样。
毫无疑问,无论是慢性传染病、精神紊乱,还是老年性功能衰退,它们对今天人类造成的痛苦会更多,它们构成了一直存在于人类生活中
的某种“背景杂音”(background noise)。近年来,随着人们的日趋长
寿,这种痛苦变得更加显著。不过,我们祖先所经历的疾病模式与我们
今天熟悉的情况根本不同。在先祖那里,不时暴发的瘟疫不论以何种形
式出现,都会给他们造成恐惧和无时不在的震慑力。尽管我们无法得到
统计和临床资料(即便到19世纪也是零星的),以对19世纪以前瘟疫的
发生情况做出准确说明,比如何种瘟疫在何时何地杀死了多少人,但是
我们仍有可能把握这些疫病流行模式的基本变化轨迹。实际上,这也正
是本书的主旨。
[0]Montezuma,阿兹特克帝国皇帝。——译者注(以下除非特别注
明,均为译者注)
[1]请参阅Thomas W. M. Cameron,Parasites and Parasitism,(London,1956),p. 225;Theobald Smith,Parasitism and
Disease(Princeton,1934),p.70。当白细胞破坏侵入人体的细胞结构
时,并不能产生有助人体细胞生成的能量或物质,因此,这个过程
只相当于消化过程的第一阶段。
[2]请参阅Wladimir A. Engelhardt,“Hierarchies and Integration in
Biological Systems”,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Sciences,Bulletin,27(1974),No. 4,p.11—23。Engelhardt把蛋白质一
类复杂分子自我复制的能力归结于分子间作用力量的弱小;他进一
步提出,这些正在强化的有机体总在消耗可利用的能量。从这一观
点上看,人类刚刚完成的跳跃性发展,即利用取自矿物燃料(fossil
fuels)的可用能量,把成百万人口聚集于工业城市的过程,似乎只
是把成百万原子聚合为较大的有机分子这一过程的最近的和最复杂
的展现。的确,正如我们可以想见的,人类城市,因为比起蛋白质
的出现要晚得多也少得多,其结构的精致程度自然不及较大的有机
分子,更不用说细胞和有机体了。但要说同样的法则也适应于我们
生活和活动其中的所有层次的有机体,至少是可以讨论的。
[3]使一类人区别于另一类人的遗传性差异,就疾病抵抗力而言,可能
缘于其先人与特定病原体长期接触所造成的差异。由此产生的基因
对初期感染的那些个体所表现出的或促进康复或延缓康复的不均衡
性,到时将产生对该病的内在抵抗力。这种“物竞天择”般的演化有
时会非常快速;而且,传染越致命,选择也越快。同样严峻的淘选
过程也自然发生于寄生体一方,它们通过基因和行为的调整以趋向
于形成与宿主间更稳定的适应关系。参阅Arno G.
Motulsky,“Polymorphisms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in Human
Evolution”,Human Biology,32(1960),p.28—62;J. B. S.
Haldane,“Natural Selection in Man”,Acta Genetica et Statistica
Medica,6 (1957),p. 321—332。对特定疾病形成抵抗力的基因也
可能对人类产生各种不利影响,因此一个群体的理想状态是“生物
协调的多形性”,这意味着有些人会有抗病基因,而有的人没有。
携带抗病基因的个体比例,将依据对该病抵抗力的选择上的多样性,以及其他可能对人口施加的选择压力的种类而变化。
[4]现代技术甚至使专业人员能够破解某些个体和群体的传染病记录,办法是通过分析血样以确定该个体是否存在“抗体”。这项技术尤其
适用于封闭的小型社会的疾病史研究。参考Francis L. Black et
al.,“Evidence for Persistence of Infectious Agents in Isolated Human
Populations”,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100(1974),p.230—
250。
[5]参阅T. Aidan Cockburn,The Evolution and Eradica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Baltimore and London,1963),p.150。
[6]参阅Theodor Rosebury,Microorganisms Indigenous to
Man(NewYork,1962)。
[7]参阅Theobald Smith,Parasitism and Disease,p. 44—65;Richard
Fiennes,Man,Nature and Disease(London,1964),p.84—102.。
[8]L. J. Bruce-Chwatt,“Paleogenesis and Paleoepidemiology of Primate
Malari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Bulletin,32(1965),p.363—387.
Plasmodium一词,原指生物特性尚不完全清楚的引发疟疾的有机
体,现已成为标准术语。这种有机体实为原生动物,但其形态在生
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有明显的不同。
[9]Hans Zinsser,Rats,Lice and History(NewYork,Bantam edition,1965;
original publication,1935),p.164—171.第一章
狩猎者在人类各族群完成进化之前,必须假定我们的祖先也像其他动物一
样,处在一种自我调适的、微妙的生态平衡之中。其中最显见的一环就
是食物链,在该食物链中,我们的祖先既猎食某些动物,反过来也为别
的动物所猎食。除了大型动物间的这种无可逃避的关系外,我们还应想
见,那些体型微小、通常肉眼无法看见的寄生物,也在我们祖先的体内
寻找食物,并由此成为平衡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命体系的重要因素。
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重构各种相关细节,事实上,即使是人类进化的进
程,对我们而言也依然模糊不清,因为已被发现(主要在非洲)的各种
前人类或类人猿的骨骼残片并不足以供我们构建出完整的故事。非洲应
不会是人类唯一的发祥地,人类的始祖或许也曾生存于亚洲的热带和亚
热带地区,其进化历程应与曾经生活在奥杜威大峡谷(Olduvai Gorge)
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其他地区的猿人(在这些地区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
的骨骼和工具)大致平行。
然而,人类不具有浓密毛发的事实清楚地表明,他们曾生活在温度
很低但又从不低于冰点的温暖的气候环境中。在重叠视野基础上形成的
准确的深度知觉能力[1]
,有抓握能力的手,以及与至今仍主要栖息于树
上的猿、猴之间明显的亲缘关系,表明人类祖先也曾生活在树上。祖先
特定的齿列显示我们曾是杂食动物,坚果、水果、幼虫或许还有某些植
物的嫩苗都比动物的肉更为重要。但是,疾病和寄生物的情况又是怎样
的呢?
[1]深度知觉指个体对其视野以及视野内的物体在三维空间上的反应能
力。人类与寄生物
今天流行于猴子和树栖猿的传染病可能与伴随远古人类祖先的寄生
物种群相似。尽管一些重要的细节仍不得而知,但至少可知侵扰野生灵
长类的寄生物的种群多得惊人。除了各种恙虫、跳蚤、壁虱、苍蝇和蠕
虫之外,野生猿、猴身上显然还寄居着一大堆原虫、真菌和细菌,更不
必说还有150种以上的所谓的“肢节病毒”(arbo-viruses,即arthropod-
borne viruses的简称。它们往往借助于昆虫或别的节肢动物,在温血宿
主之间转移)了。[1]
在感染野生猿、猴的微生物中,有15~20种[2]
疟原虫,寄生于人类
的疟原虫通常只有4种,但猿类仍可能被人类的疟原虫所感染,同时,人也有可能感染来自猿猴的某些疟原虫。除了各种疟蚊能在热带雨林的
树冠层、树干层和地面层之间形成自己的专属栖息地外,[3]
这类种属差
别,也表明了有关三者之间——灵长类、疟蚊和疟原虫——经历过一段
相当长时期的相互调适。不仅如此,根据当前的疟疾和已知古时疟疾的
地理分布情况来看,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似乎一直是这种寄生形式进化
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中心。[4]
在地球上各类自然环境当中,热带雨林可谓是最富生物多样性的地
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干燥、寒冷地区拥有更多的生物物种。故
而,至少直到近代以前,并没有任何一种动植物能够主宰热带雨林,甚
至包括人类。许多无法耐受冰冻和干燥的微生物在热带雨林地区却十分
繁盛。在这种暖湿的环境中,单细胞寄生物通常在宿主体外也能长期存活,有些具有寄生潜能的生物甚至可以以独立个体的形式无限期地生存
下去。这意味着数量不多的潜在宿主族群也可能经历普遍的感染,即便
因为宿主太少而暂时无法寄居,寄生物也可以等待。就人类而言,这意
味着,即使我们的祖先在自然平衡体系中的地位无足轻重,但作为个体
仍可能在一生中感染所有的寄生物。这种情形至今如此,人类征服雨林
的主要障碍仍在于丰富、多样的寄生物潜伏其中,静待入侵者。[5]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前人类和准人类祖先长期性地处于生病
的状态呢?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大量的热带寄生物发展到致病程度是一
个缓慢的过程,一如其缓慢地消失;换言之,热带雨林支持每个层次上
的微妙的自然平衡:寄生物与宿主之间、竞争的寄生物之间、宿主与食
物之间,都是如此。可以肯定地说,几百万年前,即在人类开始改变热
带雨林的生态环境之前,食者和被食者的平衡从长时段看是稳定的或接
近稳定的。
因此,我们的远祖消费的品类繁多的食物,无疑都对应着五花八门
的与他们分享食物的寄生物,而这些寄生物未必一定会导致我们认为
的“生病”的症状。一般的寄生物可能有时会削弱先人的体力和忍耐力,当严重的伤害或灾难(比如饥馑)扰乱了宿主的生理平衡时,轻微的感
染也可能引发致命的并发症。但如果没有这些,健康状况应该还是不错
的,一如今天森林里的灵长类。
只要人的生物进化同寄生物、食肉动物和猎物的进化保持同步,这
张精密编织的生物网(web of life)就不会出现特别重大的变化。源自
基因变异与选择的进化是相当缓慢的,以致其中一方的任何变化都会相应地伴以另一方的基因或行为方式的改变。然而,当人类开始对另一类
进化做出反应,把习惯性的行为转化为文化传统并纳入象征性的意义体
系时,这些古老的生物平衡便又开始面对新的失衡。文化的进化开始对
古老的生物进化方式施以空前的压力,新近获得的技能使人类逐渐能够
以无法预见的、意义深远的方式改变自然平衡。于是,新兴的人类的患
病方式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第一个明显的巨大变化源于可杀死大型食草动物的武器和技术的发
展,这些食草动物充斥着非洲热带草原(可能还有亚洲的同类地区)。
这一转变的准确时间至今不得而知,但可能早在400万年前就已经开
始。
第一批下到地面的灵长类恐怕只能捕获羚羊一类弱小的动物,为了
从狮子等更有力的食肉动物吃剩的腐肉中分一杯羹,他们不惜与鬣狗和
兀鹫争食。这些前人类成天游荡于集中的食物源——比如非洲热带草原
上的大批食草动物——周围,[6]
任何能够提高狩猎效率的基因变异都意
味着巨大收益。丰厚的回报正在等待着那些能够用身心技能在狩猎中进
行有效合作的群体。通过改进有助于危急时刻互相支持的交流方式,以
及有助于更新弥补肌肉组织、牙齿和爪子之无力的工具和武器,新兴的
人类赢得了由此带来的嘉益。这样,新的更有效的特性通过多方面进展
的生物进化迅速累积着,而任何新的变化都成功地扩大了食物的供应,拓展了生存的机遇。
这类进化中的突变在生物学上称为“直向进化”(orthogenic),通常
意味着进化到新的更有利的生态龛。[7]
尽管不能指望厘清该过程在前人类中引发的所有的基因变异,但当变异特别成功时,一类族群通常被另
一类更厉害的狩猎族群所取代。在冲突中越勇敢、狩猎中越有成效,生
存的机遇也就越大。
在接下来的进化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就是语言的进化。主管大
脑、舌头和喉咙形成的基因的变化,对人类通向发音清晰的语言之路是
必需的;而语言的形成又极大地提高了社群的合作能力。不断地谈论周
围世界,由此不断地规定和重新规定各种角色,能够使人类事先尝试和
完善各种技巧,从而在狩猎和其他合作性活动中达到其他方式难以达到
的准确度。随着语言的产生,把生活技能系统传授给他人成为可能,而
这些技能自身又可以进一步地精致化,因为语言可用来为事物分类、排
序,以及表达对环境适宜的反应。简言之,语言第一次将狩猎者提升为
完全的人,启动全新层次上的社会——文化进化,这一进化不久将对人
类赖以形成的生态平衡产生巨大的、至今仍无可比拟的影响。
在上述相对迅速的进化中,疾病的情形如何呢?显然,任何居所的
变化,比如从树上下到地面,在广阔草原上奔走,都牵涉人类可能遭遇
的疫病的变化。当然,某些传染病可能未受影响,比如,靠身体接触传
播的大部分大肠菌。而另外的,比如需在潮湿环境中才能完成宿体转移
的寄生物,在不适宜其生存的草原环境里就少得多了。然而,随着雨林
型的传染病的日益减少,新的特别是来自与草原兽群接触而引发的寄生
物和疾病,则必定已在影响正在快速进化的人类肌体。
但我们无法准确地说出这些疾病的名字。当今天我们食用食草动物
时,可能不经意地吞食了某些寄生物的胞囊形状的卵,这些附在食草动物身上的寄生虫就这样传到人类身上。古代的情形也大致如此。
今天在非洲许多地区引发昏睡症的锥虫,就是当时遭遇到的一种非
常重要的病原体。它是寄居在羚羊类动物身上的“普通”寄生虫,通过采
采蝇(tsetse fly)传播。它在苍蝇或其他动物宿主身上并不会引发明显
的病症,因此属于较稳定、适应性较强、可能也是非常古老的寄生物。
但一旦它进入人体,就会造成人体的极度虚弱,事实上,某类锥虫甚至
可以在几周内置人于死地。
正是因为昏睡症曾经并且至今仍对人类具有极大的破坏性,非洲草
原上的有蹄类畜群才会生存至今。如果不是借助现代的疾病预防方法,人类根本无法在采采蝇肆虐的地区生活。因此,直到晚近,这些地区的
大量草食动物仍是狮子及其他适应性强的食肉动物的猎物,但与猛兽中
更有破坏性的新来者——人类,除偶然的例外,它们并无过多的接触。
似乎可以肯定,假如在我们的先祖下树之前,导致昏睡症的锥虫已经存
在于有蹄类动物中的话,它肯定会在非洲草地上划出鲜明的界限,人类
只能在界外捕获猎物。同理,在采采蝇活动的区域内,类似前人类时代
的某种生态平衡也延续至今。[8]
顺便说一下,把人类在与其他生命关系中的生态角色视为某种疾
病,这并不荒谬。自从语言的发展使人类的文化进化冲击由来已久的生
物进化以来,人类已经能够颠覆此前的自然平衡,一如疾病颠覆宿主体
内的自然平衡。当人类一次又一次蹂躏别的生命形态到达自然极限时,往往就会出现一种暂时稳定的新关系。然而,或早或晚——而且以生物
进化的尺度衡量还总是在极短的时间以后——人类又掌握了新的手段,把此前无法利用的资源纳入可利用的范畴,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其他生
命形态的摧残。所以从别的生物体的角度看来,人类颇像一种急性传染
病,即使偶尔表现出较少具有“毒性”的行为方式,也不足以建立真正稳
定的慢性病关系。
[1]Richard Fiennes,Zoonoses of Primates:The Epidemiology and Ecology
of Simian Diseases in Relation to Man(Ithaca,NewYork,1967),p.121
—122.
[2]权威的说法各有不同。Fiennes在前引书73页中分别列出5种猿类易
患的疟疾和10种猴类易患的疟疾;L. J. Bruce-Chwatt,“Paleogenesis
and Paloeepidemiology of Primate Malari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Bulletin,32(1965),p.368—369提到20种猿类和猴类易
患的疟疾,并说多达25种疟蚊可以充当疟疾在人类和灵长类中传播
的病媒。
[3]Fiennes前引书,第42页。
[4]Bruce-Chwatt前引书,第370—382页。
[5]参阅F. L. Dunn,“Epidemiological Factors:Health and Disease in
Hunter-Gatherers”,in Richard B.Lee and Irven DeVore,eds.,Man the
Hunter(Chicago,1968),p.226—228;N. A. Croll,Ecology of
Parasite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66),p.68。
[6]F. Boulière,“Observations on the Ecology of Some Large African
Mammals”,in F. Clark Howell and Fran?ois Boulière,eds.,African
Ecology and Human Evolution (New York,1963). [Viking Fund
Publication in Anthropology No. 36],p.43—54.据此书估算,在今天的非洲热带草原上,早期人类能够得到的非洲有蹄类动物和其他猎物
的总量远远超出其他地区;而且,在现代条件下,食肉动物对如此
巨大的食物储存库的争夺并不特别激烈,比如,狮子的实际数目就
远远小于潜在的食物供应能够维持的数目。因此,当人类的祖先第
一次离开树丛,冒险进入草原搜寻更大猎物时——如果远古的情况
与现代相似——则可以说他们正步入一种就生态意义而言的部分的
真空地带,自然收获颇丰。
[7]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长颈鹿伸长了的脖子,使它可以吃到别的动物够
不到的植物。参阅C. D.Darlington,The Evolution of Man and
Society(London,1969),p.22—27。
[8]参阅Frank L. Lambrecht,“Trypanosomiasis in Prehistoric and Later
Human Populations:A Tentative Reconstruction”,in Don Brothwell A.
T. Sandison,Diseases in Antiquity(Spingfield,Illinois,1967),p.132—
151。Lambrecht认为,一种源于鱼鞭虫感染的昏睡病已经向着与人
类宿主相适应的方向进化,产生更温和的慢性疟疾形式;但在有蹄
类宿主大量存在的热带草原,演化压力导向与羚羊而不是与类人猿
的适应,永久性造成某种对于人类致命的疾病形式。因此,与人类
宿主的适应事实上将减少(甚至毁灭)那些温良的畜群,使鱼鞭虫
在生物意义上的全面成功化为泡影。人类狩猎者与环境相对稳定关系的建立
第一批成熟的狩猎人群对非洲大草原(或许还有亚洲类似的地方)
的统治,还只是将来事态的不甚凸显的先兆。无疑,当时突然将这些不
太显眼的灵长类动物推到食物链的顶端,确实够剧烈的。作为技艺高超
又令人生畏的狩猎者,人类几乎很快就不再害怕其他的敌对动物了,我
们最早的完全意义的人类祖先就此摆脱了制约人口增长的基本因素。不
过,当大草原内适宜居住的领地都被人类狩猎者占据后,人类便开始了
自我竞争。至少从这时起,人类的自相残杀又同样具备了制约人口增长
的效果;其他限制人口增长的机制也可能就出现了,比如弃婴。无论如
何,今天的狩猎者和采集者所拥有的传统的保持人口与食物供应平衡的
方法,可能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1]
就在人类的发祥地非洲,人类狩猎者确立了与环境相对稳定的关
系。人类对大动物的猎获在大约50万年前的非洲就开始了,尽管装备着
石制和木制武器的人类的全部潜力迟至公元前10万年时还未能充分显
现。虽然偶有危机,比如在随后几千年间由于一些珍贵猎物的灭绝而引
发的危机[2]
,但是人类继续与其他物种分享这块土地。即便后来的农业
革命的确导致了急剧的人口增长和环境变化,但非洲的许多地区仍然是
一片荒蛮。最近几千年间被驱逐到不适合农耕的边缘地带的狩猎团体,仍继续在部分地区固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甚至直到今天。
换言之,其他生命形式的补偿性调整以如此顽固和复杂的方式包围
着人类社会,以至于即使在人类发展出完善的技能之后,文化进化所产生的新效力仍不足以征服和彻底革新孕育人类自身进化的生态系统。也
许减缓人类对其他生命形式的最初冲击力的最显著因素,正是非洲传染
病(infestations and infections)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丰富性和侵害性
——寄生物的进化亦伴随着人类自身的进化,其对人类的侵害随着人类
数量的增长而日益加剧。[3]
肆虐于非洲的很多寄生蠕虫和原虫并不引起免疫反应,即并不在血
液循环中形成抗体,这有助于确立敏感的和自动性的生态平衡:当人类
数量增加时,受感染的概率也会增加;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大,寄生物获
得新宿主的机会也就增加了。当这种趋势越过关键性门槛,感染就会一
发而不可收,严重地阻碍人类的正常活动。像倦怠、腹部疼痛等慢性病
征,如果普遍蔓延的话,就会严重地妨害进食、怀孕以及抚养孩子,这
反过来又会削减人口,直到当地的人口密度下降到过度感染的门槛以
下。然后,随着病征的消退,人类的精力开始恢复,进食和其他活动也
趋于正常,直到下一次,别的传染病大行其道,或者人口密度再次超越
过度感染的门槛。
上述这些生态紊乱自然会影响到人类的猎物以及人体内的寄生物。
过多的狩猎者越来越难以找到合适的猎物。于是营养不良就与寄生物的
过度滋生一起削减了人类的体力和生育孩子的能力,直到再次确定接近
稳定的平衡。
相互依赖的物种也会同时对气候和物质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干
旱、草原大火、暴雨,以及其他紧急状况都为所有的生命形式设定了生
长的限度;而这种数量的上限通常远远低于其在较有利的情况下增长的可能性。换言之,生态系统维持的是一种松散的、不断变动的平衡,尽
管这种平衡可能偶尔或暂时在时空上有一定的变化,但却能有效地抵制
剧烈的、大的变动。人类狩猎者虽然登上了食物链的顶端,他们以其他
动物为食,又不致为别的大型动物所食,但这并不能实质性地改变这些
恒久的生态关系,人类虽以胜利者的姿态取得新的生态地位,但总体来
说并没有改变生态系统本身。
形成并维持这种变动中平衡的相互作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
极端复杂的。虽已历经了几代人的科学观察,疾病、食物、人口密度、居住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在非洲或别的地方仍未被完全弄清,更不用
说对于致病机制来说,疾病的虫媒与各宿主的数量和分布意义了。而
且,当今非洲的环境也并不能够完全匹配人类社会中全然依赖狩猎和农
业而尚未打破古老的自然平衡的环境中的感染模式。
然而,热带非洲的生物多样性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个大陆的
生物平衡曾顽强抵制了来自温带的农业生产方式的输入,这是有据可查
的。事实上,直到晚近(比如5000年前),在非洲,人类在与其他生命
形态的交往中只扮演着很普通的角色。人类无疑是主要的掠食者,但在
这一自然平衡状态中是相对稀少的,就像与人类争食的狮子和其他大型
食肉动物一样。
其实,不是这样才显得奇怪呢。假设(这很有可能)人类起源于非
洲,那么,当猿人缓慢地进化到人类的同时,周围的生命形式有时间调
节自己以适应人类活动所带来的危险和其他可能性。反之,出现在非洲
的人类寄生物的极端的多样性,也暗示着非洲才是人类的主要摇篮。从未见过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调适达到生物上如此的精妙程度。
除了非洲雨林和草原之外,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如何呢?可能早在
150万年前起,旧大陆的若干地区就已出现这些可怕的类人猿狩猎者。
在中国、爪哇和德国发现的有关遗存表明,这些动物在骨骼上存在极大
差别,但这些少量的发现还不足以把它们与非洲发现的较多的人类和前
人类的遗骸明确联系在一起。在亚洲南部和东南部的某些地区可能存在
着从共同的远古灵长类动物的血统中延伸出来的平行的进化路线,因为
即使没有非洲那种提供大型猎物的环境,增大的大脑、直立行走和使用
工具的手也会带来巨大的嘉惠。
由于证据不足,我们所做的推论可能会产生误导。目前,对有关地
区的考古研究仍然相当粗略,甚至一个新的遗址(比如非洲奥杜威峡
谷)的发现,就可能全盘改变我们已有的认识。尽管如此,已知的不多
的情况似乎仍表明,亚欧大陆上的前人类和准人类族群的出现晚于非洲
全盛期的猿人。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10万~5万年前,完全现代型的人
(fully modern types of human beings)的横空出世,则急剧改变了此前
地球上的生物平衡。
关于智人最早从哪里开始进化的证据仍然太少。一些不能确凿地归
于智人的骨头碎片,可上溯至10万年前的东非,在别的地方,现代的人
类遗存仍要等到公元前5万年才出现,而且当现代人出现的时候,此前
存在的原始人类,像西欧著名的尼安德特人,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4]
在非洲内部,像这样成功的人类族群的出现并没有导致像在别处出现的那种剧烈的变化。但一些大型猎物和敌对的类人猿的消失,若是可
以正确地归因于智人的出现的话,仍然展示了人类高超的狩猎能力。当
人类能够通过把握火种和披戴动物毛皮以预防严寒时,更可观的后果出
现了。
衣服的发明有助于狩猎者进攻北部草地和森林里的动物,其效果就
好比人类祖先第一次从树上下到地面。也就是说,一种新的、更准确地
说是一系列新的生态龛等待新来者去占据;并且随着他们学会利用他们
的技术开发出新的食物来源,一种全球范围的生态关系的快速转型就接
踵而至了。大约公元前4万~前1万年间,狩猎者占据了地球上除南极洲
以外的所有陆地板块。他们在4万~3万年前进入澳大利亚;0.5万~1.5
万年后又越过白令海峡从亚洲进入美洲。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人类扩张
到南北美的所有气候带,在大约公元前8000年前到达火地岛[5]。
此前从来没有一种支配性的大型物种能够散布全球,人类做到了,因为他们学会了如何在极端不同的条件下创造适合于热带生物生存的小
环境。衣服与住房的发明,使人类的生存不致受到极度寒冷天气的威
胁。换言之,文化调适和发明创造降低了面对多样环境时调整生物机能
的必要性,由此,在地球各陆地板块的生态平衡中,引进一个本质上带
有破坏性的且不断处于变化中的因素。
当然,尽管对自然环境的文化调适对于公元前4万~前1万年间人类
的大举扩张具有决定性意义,但也仍然存在另外的重要因素。在走出热
带环境的同时,我们的祖先也远离了很多前人已经适应了的寄生虫和病
原体,健康和活力也相应得到了提升,于是人口的增加也变得规模空前。[6]
人类在温带、寒带的自然生态中的位置与在热带地区的截然不同。
如前所述,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人类继续受到生物上的制约,这种
制约即便在人类的狩猎技术已经颠覆了大型动物之间古老的自然平衡之
后,仍然相当有效。但当人类社会能够在温带条件下生存与发展时,他
们面对的是相对单纯的生物环境:总的来说,较低的环境温度意味着生
存适宜度的降低。结果适宜于温带和北方气温的动植物种类要少于热带
条件下的动植物。因此,当人类狩猎者第一次闯入这里时,迎接他们的
是一个不太复杂的生命之网。温带的生态平衡后来证明更容易被人类的
活动所破坏。这一地区起初缺少或几乎缺少能够寄生于人体的生物,但
这只是一个暂时现象,很快,正如我们不久将要看到的,在生物学和人
口统计学上都有重大意义的疾病也开始在温带人类社会中发展起来。但
生态平衡易受人类摆布的脆弱性仍是热带以外地区的永恒特征。
因此,人类在温带地区的生物统治,从一开始便呈现出一种特殊的
类型。作为温带生态系统的新成员,进入新环境的人类宛若刚被引入澳
大利亚的野兔,既没有天敌,又没有自然的寄生物,再加上至少在开始
的时候食物丰沛,澳大利亚的野兔数量急速增长,不久就开始影响到人
类的牧羊业。当欧洲人首先到达美洲时,也出现了类似的外来的生物,诸如猪、牛、马、鼠以及各种植物大量侵入的情形。但是,这些早期不
受制约的繁殖,不久就开始自我矫正了。[7]
若从一个足够长的时段来看,扩张到温带生态中的人类也是如此。
但就我们所习惯的时间长度来说——如百年或千年(而非十亿年)——物种之间一般的生物调适似乎还不足以制约人口的增长。原因在于,产
生和支撑人类进步的与其说是生物的调适,不如说是文化的调适,于
是,每当一两种关键性资源被耗尽、人类利用自然的既定方式面临困境
时,他们的智力总能帮他们找到新的生活方式,利用新的资源,由此一
次次扩展我们对有生命和无生命大自然的统治权。
猛犸象、巨大的树懒以及其他大型但缺乏经验的动物遍布各地等着
人类去猎杀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实际上,曾有人估计,富有技巧而
又浪费的人类狩猎者只花了一千年的时间就消灭了南北美洲大部分的大
型动物。根据对美洲历史的这种认识,狩猎者成群结队,沿着能够发现
大型猎物的界线向前推进,每到一个地方,只需几年的时间,就清空了
各种兽类,以致他们只能不断向南推进,直至美洲大部分的大型猎物物
种都趋于灭绝。[8]
这样灾难性的结局,当然只会在熟练的狩猎者遇到完
全无相应经验的猎物时才会出现。旧大陆就不曾发生过这种戏剧性的对
抗。在那里,人类的狩猎技术只是逐步应用于北方的大型兽群,这可能
只是因为,随着每一次向北的推进,狩猎者都不得不去适应更严酷的气
候和更困难的冬季。而美洲正好相反,移动的方向是从北向南,从严寒
到温暖,结果新大陆大型猎物的灭绝,远比旧大陆来得突然和广泛。
随后的新技术的发明,使人类得以不断地重演这种轻易地采集和迅
速地耗尽资源的边界现象(frontier phenomenon)。目前中东以外地区
的石油短缺,就是人类这种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的最新例证。不过,作
为石器时代定居温带和亚北极地区的结果,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的共存
关系也进入了一种新的更长久模式——这一模式在以后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人类这种跨不同气候带的分布,造成了在不同社群间产生
出一种可称为“梯度寄生”(parasitic gradient)的现象。毕竟,随着气候
上寒冷与干燥的加剧而呈现的生物多样性的降低,就意味着能够侵入人
体的寄生物的数量和种类的减少。而且,随着温度(和湿度)的降低、日照时间的缩短,寄生物在宿主间的转移也变得更加困难。于是就形成
了如下的感染梯度:居住在暖湿区域内的人口若前往干冷地区,有可能
很少遭遇不熟悉的寄生物,而潜伏于南部暖湿区域内的病原体,则往往
威胁着来自寒冷北方或干燥沙漠地区的入侵者。
反过来,这种梯度或许也可以这样描述:人类越深入寒冷或干燥气
候带,他们的生存就越直接地依赖于他们与大型动植物的生态关系,与
微寄生物系统的平衡在热带如此重要,而在这里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我们由此不难做出重要的引申,几乎所有的微型寄生物都小得用肉
眼看不见,这意味着在显微镜这类提高人类观察力的发明出现以前,没
有人能理解或控制与它们的接触。尽管人类在处理可见的和可实验的对
象上拥有智慧,但同微型寄生物的关系,在19世纪之前很大程度上仍停
留在生物性的层面上,也就是说,人类无法对其有意识地加以控制。
然而,在微型寄生物还不那么普遍和重要的地方,智力仍可以自由
地利用人类生命中诸多重要的参数,只要这群男男女女发现新的食物和
对手,他们就能发展出新的方式来对付它们,这样他们不再是狩猎方式
下数量稀少的掠食者,相反,在原来只能养活几千个狩猎者的地方,现
在狩猎者却能成百万地繁衍。因此,脱离热带生命摇篮,对人类后来在
自然平衡当中扮演的角色具有深远的意义,它赋予了文化创造以更大空间,远比孕育赤身裸体的原始人的紧密的生命网要广阔得多。
当然,地域性的状况也能够扭曲这种普遍性的方式,人口密度、水
源、食物和住所的特征与品质,以及人际交流的频率和范围,所有这些
都会严重地影响疾病的模式。直到近代,即使是坐落在凉爽或干燥气候
条件下的大城市,也总是不卫生的。尽管一般说来这种生态关系的局部
性变异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生物梯度规律,即感染的多样性和频率会随着
温度和湿度的增加而增加。[9]
旧石器时代的狩猎者在温带和亚北极地区的扩张,造就了人类在生
物意义上的空前成功。但是等到所有的可供狩猎之地都被占据之后,古
老地区最适合的猎物便惨遭滥杀,有时甚至被屠戮殆尽。
作为食物源的大型猎物的消耗殆尽,显然会给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地
区的狩猎者带来生存危机。与此同时,这场危机又恰巧遭遇了由最近一
次冰帽(ice cap)退缩引发的气候异动(公元前2万年以来)。这两大
因素的重合为狩猎社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环境挑战,只要惯用方法失
灵,就会促使人们去进一步寻找食物和尝试新的可食之物。比如,对沿
海的勘探,促进了造船和渔业的发展;采集可食的种子使另外一些族群
走上发展农业的道路。
旧石器时代的狩猎者和采集者可能粗略地重新体验了最早的猿人在
热带摇篮时的经历。那就是,一旦新的生态龛位显而易见的可能性被利
用,某种大致的平衡就形成了,各类制衡因素亦接踵而来,制约着人口
的增长。这些都因地、因时、因群体的不同而不同。不过,在人类完成自我进化的热带地区以外,病原体并不特别重要。那些可以通过直接的
身体接触而在宿主间传播的寄生物,像虱子、雅司螺旋体(the
spirochete of yaws),仍可以在温带地区流动的狩猎小群体中生存下
来。只要传染进程缓慢,又不对人类宿主产生突然的重创,这些寄生物
可以随同狩猎群体迁出人类的热带摇篮走向全球。但这些感染与它们在
人类最古老的热带居住地的繁盛景象相比,则已大为衰减了。
结果是这些温带地区的古代狩猎者尽管寿命不长,但却可能是身体
最健康的族群。[10]
这一推论还可从当代澳大利亚和美洲狩猎者的生活
状况中得到印证。除了最近因同外部世界接触而产生的可怕疾病外,这
些人似乎不受传染病和多细胞寄生物的感染。[11]
其他一切都是令人惊
讶的,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让缓慢的生物进化以及从宿主到宿主的转移
模式适应阴凉、干燥的条件,而只有有足够的时间,才能使进入温带和
亚北极气候区的相对孤立的狩猎群体维持热带水平的感染。
在上述调整影响人类生活之前,新的关键性的发明再一次使人类与
环境的关系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食物的生产使得人口数量迅速增长,而
且很快推动了城市和文明的兴起。人口一旦集中到如此大的社群中,就
会为潜在的病原体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其情形一如非洲草原的大型猎
物为我们的远祖提供食物来源那样。在人类的村庄、城市和文明的发展
所创造的新环境中,这回轮到微生物猎食美味了。微生物如何利用人口
聚居所带来的机会,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1]Mary Douglas,“Population Control in Primitive Peoples”,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7(1966),p.263—273;Joseph B. Birdsell,“OnPopulation Structure in Generalized Hunting and Collecting
Populations”,Evolution,12(1958),p.189—205.
[2]参阅Darlington前引书第33页中所列的灭绝物种。这些(以及后来
灭绝于北美的)物种的灭绝与人类活动间的关系尚待澄清,参阅
Paul S. Martin H. E. Wright,eds.,Pleistocene Extinctions,the Search
for a Cause(New Haven,1967)中的讨论。在灭绝的诸物种间,Darlington并没有考虑曾生存于非洲的各种类人猿;但很清楚,类
人猿族系中较为温顺的种类也最为脆弱,结果,到公元前2万年
——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该族系中只有一类,即智人,存活下来。
[3]关于原生动物和蠕虫在撒哈拉以南地区极度泛滥,请参阅
Darlington前引书第662页中的图表。
[4]有关这些说法,系参考以下论著而来:David Pilbeam,The Ascent of
Man: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Evolution(New York,1972);Frank
E. Poirier,Fossil Man:An Evolutionary Journey(St.
Louis,Missouri,1973);以及B. J. Williams,Human Origins,an
Introduction to Physical Anthropology(New York,1973)。
[5]Tierra del Fuego,位于南美洲的南端,今属阿根廷。
[6]Joseph B. Birdsell,“Some Population Problems Involving Pleistocene
Man”,Cold Spring Harbor Symposium on Quantitative
Biology,20(1957),p.47—69,该文估计只需2 200年就足以住满澳
大利亚。也参考Joseph B. Birdsell,“On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Generalized Hunting and Collecting
Population”,Evolution,12(1958),p.189—205;——,“Some
Predictions for the Pleistocene Based on Equilibrium Systems AmongRecent Hunters-Gatherers”,in Richard B. Lee Irven DeVore,eds.,Man
the Hunter,p. 229—240。
[7]关于澳大利亚野兔,可参阅Frank Fenner F. N.
Ratcliffe,Myxomatosis(Cambridge,1965)。关于美洲的情形,可参
阅Alfred W. Crosby,The Columbian Exchange: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Westport,1972)。一般性概况可参阅Charles
S. Elton,The Ecology of lnvasions by Animals and Plants (New
York,1958)。
[8]Paul S. Martin,“The Discovery of
America”,Science,179(1973),p.969—974.
[9]N. A. Croll,Ecology of
Parasite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66),p.98—104. Croll主要探
讨的是多细胞寄生虫,但他的结论也适用于所有的寄生形式,尽管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文明人口中产生最重要传染病的病毒性和
细菌性有机体的分布,主要受制于潜在宿主的密度,因而与受气候
影响的分布方式大大不同。F. L. Dunn,“Epidemiological
Factors:Health and Disease in Hunter-Gatherers”,in Richard B. Lee and
Irven DeVore,eds.,Man the Hunter,p.226—228,关于不同气候下的生
物多样性与人类传染病的关系也有有趣的见解,另可参阅René
Dubos,Man Adapting(New Haven,1965),p. 61。
[10]根据对克罗马农人和尼安德特人骨骸的研究,可以尝试性地确定
死者的年龄。根据Paul A.Janssens,Paleopathology:Diseases and
Injuries of Prehistoric Man(London,1970),p. 60—63中收集的材
料,88. 2%的克罗马农人遗骸在死时不到40岁,61.7%不到30岁。尼安德特人遗骸的相应比例分别是95%和80%。然而这种计算的统
计学基础不能令人满意,推算死者年龄的标准也经常是含糊的。
[11]参阅Saul Jarcho,“Some Observations on Diseases in Prehistoric
America”,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38(1964),p.1—19;T.
D. Stewart,“A Physical Anthropologist’s View of the Peopling of the
New World”,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16 (1960),p.256
—266;Lucille E. St. Hoyme,“On the Origins of New World
Paleopath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21(1969),p.295—302。J. V. Neel et al.,“Studies of
the Xavante Indians of the Brazilian Mato Grosso”,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16(1964),p.110.注意到在他所研究的部落中,男
人“相当健壮”,远离疾病困扰,尽管妇女并非如此。大量游记也强
调原始人在起初与外界接触时的健壮,尽管其可靠性尚可置疑,参
阅Robert Fortuine,“The Health of the Eskimos as Portrayed in the
Earliest Written Accounts”,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45(1971),p. 97—114。另外,在可能作为人类最早发源
地的热带地区,许多种疾病仍肆虐于较大的封闭的族群。参阅Ivan
V. Polunin,“Health and Disease in Contemporary Primitive Societies”,in
Don Brothwell A. T. Sandison,Diseasesin Antiquity,p. 69—97。有观
点认为,在与欧洲人接触之前,澳大利亚土著的身体状况也是良好
的,请参阅B. P. Billington,“The Health and Nutritional Status of the
Aborigines”,in Charles P. Mountford,ed.,Records of the American-
Australian Expedition to Arnhem Land,(Melbourne,1960) I,p. 27—
59。第二章
历史的突破大型猎物的灭绝,开始于5万年前的非洲,继之以2万年前的亚欧大
陆,然后在1.1万年前的美洲达到高潮,这一过程对于以猎杀大型动物
为业的狩猎者来说,肯定是一次严重的打击。[1]
大型动物的先后消失可
能导致各地人口的急剧减少。对一群人来说,在一周或更长的时间内依
靠一只猛犸象为食是一回事,但另外,要每天猎杀足够的小型猎物来供
养同样数量的一群人,就不那么容易了。同时,气候的变化也改变了自
然平衡,像在北方沿着冰川退却的边缘地区,而在亚热带地区,信风的
北移使以前适合狩猎的非洲撒哈拉和西亚邻近地区出现了沙漠化。
[1]种类很多(200种食草动物和相关的食肉动物),包括北美诸如马
和骆驼这些潜在有用的动物。参阅Paul Schultz Martin H. E.
Wright,Pleistocene Extinctions,p.82—95。最近对非洲——这里大型
动物的灭绝比别处要缓慢得多——生物量的估算,表明大型猎物的
消失意味着多么巨大的食物损失。比如,单是大象和河马就构成非
洲草原整个动物界生物量的70%;甚至在斑马和牛头羚作为最大食
草动物的地方,这两类动物也至少构成动物界生物量的50%。请参
阅F. Clark Howell Fran?ois Boulière,African Ecology and Human
Evolution,p.44—48. Vernon L. Smith,“The Primitive Hunter
Culture,Pleistocene Extinctions,and the Rise of Agricultur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3(1975),p.727—756,对过度滥杀导致的灭绝
现象进行了有趣的经济学分析。如果发生在更新世(Pleistocene)
的灭绝现象系与人类狩猎者的行为有关,则古代灾难性的滥杀与现
代工业对化石燃料的滥用非常相似;不同的是,现代人毁灭其生存的能源基础的时间可能少于史前祖先对他们的能源基础的毁灭。农牧业的兴起
在每一个地方,古代的狩猎者都必须不断调整他们的习惯以更充分
地利用正在变化的环境。当大型动物灭绝时,就必须找到可替代的食
物。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的祖先再度成为杂食动物,就如同他们的猿
人祖先,开始食用各种各样的动植物。特别是,海边和海洋的食物资源
第一次被系统地利用,这一点可从被抛弃的软体动物的贝壳和不那么显
眼的鱼骨堆中得到证明。不仅如此,人类还发展出了制作食物的新方
式,比如,某些族群认识到,长时间的浸泡可以除掉齐墩果和木薯中的
有毒成分,从而可以食用;另一些蔬菜通过碾磨、蒸煮和发酵,会变得
更可口或更容易消化。[1]
然而,所有这些补偿性措施与通过畜牧和种植发展起来的食物生产
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地球上不同地区的社群都朝着这一方向前进,不
过产生的结果,则随着各地最初的野生状况中可资利用的动植物的不同
而存在差异。一般说来,新大陆相对缺乏可驯养的动物,但有用的植物
却不少,旧大陆则为人类的创造力提供了大量可驯养的动物和大量令人
印象深刻的可能的粮食作物。
我们对早期驯化的细节仍不清楚。我们必须假设,在人类与可种植
和驯养物种之间存在着相互适应的过程,这包括被种植和被驯养的动植
物会出现快速且有时影响深远的生物特性上的改变,这是因为人类对它
们的某些生物特性做了偶然或有意的选择;反过来,我们也必须假设,人类自身也做出了根本的(即使很少是有意的)选择。比如,那些拒绝从事辛苦的农业劳作的往往难以生存下来,而那些不能或不愿为来年的
耕作备足种子而宁愿吃掉所有余粮的人,也将很快被依靠每个年度的收
成生活的社会所淘汰。
牧人、农夫以及各种各样的驯养和种植的动植物,依其气候、土壤
和人类技能的不同,以不同的方式与动植物的野生背景相适应。而其结
果,在村与村之间、地块与地块之间,甚至同一地块内部都存在着明显
的差异。
不过,仍有一些普遍现象值得注意。首先,当人类以增殖某些动植
物的方式改变自然景观时,另一些别的动植物也就被取代了,其一般性
影响是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和区域内的动植物渐趋单一。与此同时,当人
类的活动降低了其掠食者的角色,而又把越来越多的食物储存起来仅供
人类自己消费时,其食物链也就缩短了。
食物链的缩短将人类拖入了永无休止的劳作当中。保护畜群和庄稼
不受动物掠食者的侵害,对于熟练的猎人来说,虽然要求其始终保持警
惕,但算不上是什么大问题。然而,要防范来自人类自身的侵害就不同
了,防范同类掠夺的努力正是催生政治组织的主要动力,这一进程至今
仍未完成。
但对人类生活更重要的还是除草工作,即试图消灭那些与驯养和种
植的动植物争夺生存空间的敌对物种,这是因为其需要整个族群大部分
人持续不懈的努力。以手除草似乎真的是“农业”的最初形式,但当人类
学会了刈除自然界中最茂盛的植物而为他们喜好的作物拓展生态空间,从而更彻底地重塑自然环境时,人类的力量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有
两种方法证明这些手段有助于达到上述目的:对干燥的土地实施人工灌
溉,以挖掘和犁地的方法机械地改变土壤的表面状况。
灌溉有助于淹死竞争的物种。一段时间内土地淹在水下,而在其他
时间里则放水以晾干土地,当这样安排农时时,杂草就不再是大问题
了。很少有植物能在极湿与极干环境的交替下还能照样生存;而当农夫
只通过开关巧妙设计的水闸,便可以随意调整旱涝以适应作物需要时,此时能存活下来的杂草就更是少之又少。当然,只有在浅水中能长势良
好的作物才能获益于这种方法,水稻就是最好的例子。不过,对别的不
那么有价值的根茎类作物,这一耕作方法也同样适用。
以铲子、锄、锹或犁等机械力量来改变土壤的做法,更为西方人所
熟悉,因为这种农耕方式最早出现在古代近东,随后被传入欧洲。此
外,它也盛行于美洲和非洲的早期农业中心。在更早的刀耕火种的阶
段,人类是用剥掉树皮的方法来毁掉落叶林,这有助于阳光直射森林地
面,在没有杂草竞争的环境下促进谷物的成长。然而,即使可以靠焚烧
枯树来更新土地的肥力,这种耕作方式也不够稳定,风中洒落的种子不
久就会在森林空地繁殖起蓟及类似杂草,只需一两年不受控制的疯长,这些入侵者就会完全鸠占鹊巢。于是,最早的近东人、美洲印第安人和
非洲农夫只有另寻处女地,重新开始新一轮只有第一年没有杂草的种
植,才得以生存下去。
公元前3000年左右,随着犁耕的发明,最早的局限首先在古代近东
取得了突破。犁耕可以年复一年地有效地控制杂草,从而使土地无限期地得到耕种。原因很简单:犁耕用畜力代替人力,这样就能让古老的近
东农夫可以耕种两倍于他们所需的农田,多余的土地则处于休耕状态
(即在生长季节犁耕以毁掉杂草),以便为来年的作物生长预留适宜的
生态龛,而不致被杂草所侵扰。
大部分教科书仍然对休耕是如何让土地通过休息来恢复肥力进行解
释,这种说法证明了人类的泛灵论倾向。任何人只要稍做思索就可以认
识到,在一个季节里地质气候的变化及随后的化学变化,无论过程怎样
都不会对来年的植物生长造成显著的差别。诚然,在“旱播”的情况下,呈裸露状休耕的土壤更容易保有水分,否则水就会通过植物的根系和叶
子从土壤里发散到空中,在由于水分不足而影响作物产量的地方,休耕
一年可以通过积聚底土里的水分以提高肥力。而在别的水分并不对植物
生长构成关键性制约的地方,休耕的巨大好处在于可以用犁耕阻断杂草
的自然生命周期,使其枯死。
翻土(或引水灌溉)自然能达到相似的结果;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单凭人的体能尚不足以翻掘足够的耕地,以允许一家人只靠耕地的一半
收成就可以维生,而让另一半休耕。当然,特殊的土壤和生态环境确实
容许出现某些例外,两个最重要的例外是:第一,在中国北部,肥沃而
易碎的黄土使人们无须借助畜力即可以小米维生;第二,在美洲,玉蜀
黍和马铃薯比旧大陆的小麦、大麦和小米一类作物含有更多的单位热
量,所以,即使这里的土地不像中国的黄土那样容易耕种,仍能达到相
似的结果。[2]
上述的技能的确令人钦佩,人类借助它们在以激进的方式重塑自然的过程中发现并利用了其原有的种种可能性,成倍地提高了食物供应,尽管这也意味着人类从此将不得不持久地接受没完没了的劳作的奴役。
毫无疑问,一旦在犁耕中使用了畜力,那么耕作者的生活就要比东亚的
稻米生产者轻松得多,后者需靠自身的体力来完成水田劳作的大部分内
容,包括引水和犁土。但辛劳——日常性的、没有尽头的、与狩猎经历
所造就的人类天性严重冲突的辛劳,仍然是所有农业人口的命运。只有
如此,农夫们才能成功地改造自然的生态平衡,缩短食物链,提高人类
消费能力,增加人口数量,直到这个在自然平衡中原本相对稀缺的物
种,成为称霸于广大农耕地区的大型物种。
人类同杂草(包括可以称为“杂草”的动物,如象鼻虫、鼠类)的斗
争需借助于工具、智力和经验;尽管其过程还了无尽期,却已经为人类
带来了一系列胜利。然而,农业对生态平衡的破坏,还有另一方面:缩
短食物链,增加驯养和种植的动植物的数量,也为寄生物造就了潜在的
更集中的食物源。更重要的是,由于大部分重要的寄生物都微不可见,长期以来人类仅凭智力无法有效地对付它们的滋扰。
因此,在现代科学和显微镜出现以前,先祖对杂草和敌对的大型掠
食者的胜利,尽管成果辉煌,但也遭遇了劲敌。这种微寄生掠食者在农
夫成功改造的环境中找到了更多的生存机遇。实际上,一种或少数几种
物种引起的超级大侵扰,可谓是生命之网中的自然平衡发生突然的和影
响深远的改变的正常反应。杂草往往就是利用灾患对正常的生态系统所
造成的缝隙而生存,在不受干扰的自然植被中,杂草总是稀少和不显眼
的,但一旦当地的终极群聚期[3]
的植被毁坏,它就能够快速地占领因此而产生的空隙。既然很少有物种能够有效地利用这些机会,结果就使得
仅有的几种杂草在裸露的地表上肆虐开来。然而杂草并不能长久维持这
一强劲的势头,复杂的补偿性调节很快就出现了,在缺乏进一步外部干
扰的情况下,程度不同的稳定而多样化的植被将重新出现,通常仿佛回
到破坏前的样子。
只要人类继续改变自然环境,并使之适合于农业,他们就会阻挠重
新建立自然的终极群聚期的生态系统,因此仍会随时遭受杂草泛滥的困
扰。[4]
如前所述,当对付人们可见和可控的大型生物时,观察和试验让
早期农夫们很快就能将杂草(以及老鼠这样的动物害虫)置于其控制之
下,但几千年来人类的智慧在对付致病微生物上,仍然还停留在摸索阶
段,因此,疾病在作物、畜群和人类当中的滋扰,在整个历史时期的人
类事务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书的目的正是要探讨:在现代医学
弄清疾病传染的某些重要途径之前,人们对疾病一筹莫展时,究竟发生
了什么?
[1]Sherwood Washburn and C. Lancaster,“The Evolution of Hunting”,in
Richard C. Lee and Irven DeVore,Man the Hunter,p.293—303:Kent
V. Flannery,“Origins and Ecological Effects of Early Domestication in
Iran and the Near East”,in Peter Ucko and G.W. Dimbleby,eds.,The
Domestic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
(Chicago,1969),p.77-87.
[2]关于早期中国农业的特殊环境,参阅何炳棣,“The Loess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Agriculture”,American HistoricalReview,75(1969),p.1—36。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的农业情形,参看
R. S.MacNeish,“The Origins of American
Agriculture”,Antiquity,39(1965),p.87—93。
[3]climax,是指动植物因与生长地的气候条件不合而迁移到安定状态
的阶段。
[4]关于过度泛滥以及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参看N. A. Croll,Ecology
of Parasites,p.115以下。新生活方式与疫病
到目前为止,一切还算顺利。但是,当我们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概
括,而提出诸如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些怎样的疾病?流行于哪些地方?
在什么时候?以及对人类生活和文化产生了何种影响?这时,知识的模
糊性使我们很难提供具有说服力的答案。即便不去考虑影响作物和驯养
的动物的疾病,我们仍然缺乏足够的资料来创作一部人类的传染病史。
显而易见,长期或永久性地定居在一个村庄里,就会卷入新的寄生
物侵扰的风险。比如,当人类的粪便在居住地周围堆积时,人们与它接
触的增多有助于肠道寄生物顺利地进行宿主间的转移。相反,一个不停
流动的狩猎群,在任一地点的逗留时间都不长,自然不易受这种循环感
染的威胁。因此,我们应当承认,生活在定居社会里的人们,比起他们
处于同一气候区的狩猎先人或同时代的狩猎族群,更易受寄生物的感
染。有的寄生物通过污染水源在宿主间随意转移,这种情况在经年累月
依靠同一水源生活的定居社会中,自然就更容易出现。
尽管如此,代表原始农业特色的小型村落社会,可能并没有过多地
受累于寄生物的侵扰。近东的刀耕火种者在一生中要屡迁其地;中国的
小米种植者,以及美洲种植玉蜀黍、豆类和马铃薯的印第安人也相当分
散地居住在前文明的小村庄里。各类感染在这些社会中可能是存在的,尽管寄生物的数量因地而异,但在每个小村庄里大家在年幼时都会患上
同类的寄生虫病,至少这是今天原始耕作者的情况。[1]
但这类感染不会
造成非常严重的生物意义上的负担,因为它们未能阻止人口空前规模的增长。仅在几百年内,凡是历史上成功地栽培(domesticated)了有价
值农作物的重要地区,[2]
其人口密度比先前同一地区的狩猎者的人口密
度,要高出10~20倍之多。
在早期农业中依赖灌溉的地区,比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河
流域以及秘鲁沿海地区,与简单的、或多或少封闭的村庄相比,显然需
要更完善的社会控制。运河与沟渠的规划与维修,尤其是灌溉水源在使
用者之间的调配,都需要有权威性的领导者。于是,城市和文明诞生
了,比起乡村生活,它们要求更广泛的合作和生产的专业化。
不过,灌溉农业尤其是相对温暖气候条件下的灌溉农业,在某种程
度上等于重构了有利于病原虫传播的环境,这种环境普遍存在于孕育人
类远祖的热带雨林中。充足的水分(甚至比热带雨林还要充足)加快了
寄生物在宿体间的转移频率,众多潜在的人类宿主在温暖、浅缓的水域
中驻足,为其提供了理想的传播媒介。在这种环境中,寄生体并不需要
胞虫囊一类能够长期抵御干旱的生命形式即可顺利传播。
古代的寄生方式可能与今天稍有不同。但以人类历史的尺度来衡
量,生物的进化是相当缓慢的。5000年前在灌溉农业的特定环境下的寄
生形式,与当今仍困扰着稻田农夫的寄生形式,几乎是一样的。
目前已知的这些寄生物已有不少,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导致血吸虫
病的血吸虫。血吸虫病是一种严重的、令病人虚弱的病症,即便在今
天,它也许还在折磨着上亿的人口。血吸虫的生活史,是软体动物和人
类轮流担任宿主,它以微小的、自由游动的形体,通过水实现宿主间的转移。[3]
一旦感染上它,有时会让钉螺(最一般的软体动物宿主)送
命,但对慢性感染的人来说,它的最严重症状出现在儿童期,其后表现
得持续而相对缓和。像疟疾一样,血吸虫的寄生生活史相当精致。它具
有两种不同的自由游动形式,各自寻找它们的宿主:软体动物或人,以
便一旦侵入宿主即可进行活跃的运动。这种复杂的情形,连同它在人体
内产生的慢性病症的特征表明,在现代血吸虫的行为模式形成之前曾经
过长期的进化。像疟疾一样,其寄生的模式,可能源于非洲或亚洲的雨
林;但这种疾病分布得异常广泛,[4]
以至于我们还不能有把握地指出它
是在何时何地扩散到今天盛行的这些地区的。古代埃及的灌溉者早在公
元前1200年(可能更早)即受此感染;[5]
古苏美尔和巴比伦人是否同样
受此感染还不敢断言,尽管我们不能排除这两大河谷间通过接触而同时
感染的可能性;[6]
同样,在遥远的中国发现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安葬于公
元前2世纪的尸体,尽管死因是心脏病,但同时也携有血吸虫及其虫
卵。[7]
今天,农民需要长时间地浸泡于水田作业的灌溉区,这种病仍能
迅速传播。[8]
就此而言,似乎可以说古代的灌溉技术与血吸虫病很早就
在整个旧大陆紧密联系起来了。
无论古代的血吸虫病以及类似的病症曾如何分布,有一点是肯定
的,即在它们泛滥的地方都容易造成农民出现无力和疲怠的症状,使他
们既不能长时间地在田里劳作和挖掘沟渠,也无力胜任那些对体力的要
求并不亚于劳作的任务,比如抵抗军事进攻或摆脱外来的政治统治与经
济掠夺等。换言之,由血吸虫病和类似感染所造成的倦怠和慢性不
适,[9]
会有助于为人类所惧怕的唯一大型天敌的成功进犯,他们就是自
己的同类,为了战争和征服而武装和组织起来的掠食者。尽管历史学家不习惯于从这样的角度来思考国家、征税和掠夺的问题,但微寄生和巨
寄生之间的相互支持,肯定是正常的生态现象。
农民被寄生物传染这件事,如何加速早期大河文明的建立,其作用
尚难以合理估计。但似乎也有理由怀疑,显现灌溉农业社会特征的专制
政府的存在,除了与经常用来解释这一现象的治水所需技术有关外,也
包括这类令人虚弱的疾病的功劳,多亏它们侵扰了长期光脚在湿漉的田
间劳作的农民。[10]
简言之,埃及的瘟疫与法老的专制统治之间可能存
在着某种形式的关联,而这种关联,不仅古代希伯来人没有想过,现代
历史学家也从未关注过。
只要寄生物小得无法辨认,人类对瘟疫的应对严格说来便是盲目
的。但人类有时的确能摸索出饮食和卫生规则以减少感染机会,最耳熟
能详的例子,便是有的宗教禁食猪肉。这看起来令人费解,除非你意识
到猪是近东村庄的腐食者、喜食人粪和其他“不洁”之物,它们的肉如不
经彻底烹煮便当作美食,就很容易把许多寄生虫吞进肚里,现代的旋毛
虫病(trichinosis)就证明了这一可能性。不过,禁食猪肉的古代习俗与
其说是建立于某种试错法之上,毋宁说是建立于对猪的本能恐惧之上;
至于由遵守禁忌带来的健康上的好处,尚无法从现有史料中看出端倪。
将麻风病人[11]
驱逐于正常社会之外这一做法的背后也隐藏着类似
的情绪。这是另外一条古老的犹太人戒律,想必它减少了通过皮肤接触
而感染的机会。沐浴——无论用水还是沙子,在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仪式
中均有重要地位,这可能也有防止传染的功效。但另外,为庆祝神圣节日,成千上万的朝拜者聚集一处共同沐浴的
仪式,却又为寄生物寻找新宿主提供了绝佳机会。[12]
在印度,很大程
度上霍乱的传播曾是(现在仍然是)宗教朝圣的“职能”。[13]
因此,那些
传统的习俗,即便被宗教和无人记得的仪式奉为神圣,也并不见得总能
有效地阻止疾病的传播;而且,那些实际上扩散疾病的做法也同那些对
健康具有积极意义的仪式一样,可能,也的确被神圣化了。
当然,农业环境中有利于在人类中传播的,并不只是这些多细胞寄
生物。当畜群、作物和人口大量繁殖时,原虫、细菌和病毒的感染的空
间也相应得以拓展,一般来说,其结果并不直接,未曾也无法预见。除
了极特殊的情况,要复原新传染方式赖以形成的环境,是不可能的。
然而,仍有某些例外。譬如,在西非,当农业扩展到雨林环境时,刀耕火种的农作方式显然对旧生态平衡施加了新的压力,一个意想不到
的结果是,疟疾获得了全新的流行强度。事情可能是这样发生的:把森
林夷为平地为喜食人血的冈比亚疟蚊(Anopheles gambiae)扩大了滋生
的地盘。实际上,我们确实可以将疟蚊视为“杂草”类的物种,它们在人
类为农业所开辟的非洲雨林中的空地上恣意繁殖,并随着农业的进展,取代了别的喜食动物血而非人血的蚊子。结果,人—蚊子—疟疾这一循
环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度,切实地影响到每个深入雨林空地的
人。[14]
虽然非洲的劳动者仍能出于农业目的而继续努力征服雨林,但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会伴以基因上的调整,使得制造镰刀形红细胞的基因(异
形合子形式)出现的概率明显增加,这些红细胞对疟原虫,显然不像普通的红细胞那样友好。于是,疟疾令人衰弱的症状在体内含有这类红细
胞的人身上减弱了。
然而,得到这一保护的代价十分高昂。一个人若从父母那里同时继
承了双方的镰刀形红细胞基因,那他(她)往往会在青年时早夭。不
过,那些生来完全没有这种基因的人,更容易受到疟疾的致命感染,这
也使得儿童死亡率进一步攀升。在西非疟疾最猖獗的地区,约有半数的
新生儿携有镰刀形红细胞基因,他们在生理上是很脆弱的。由于农业对
雨林的入侵仍在继续,当前疟疾、疟蚊以及镰刀形红细胞基因的分布情
形,让我们得以重构当年随着旧的生态方式的改变而发生的异常严重的
后果(这种后果目前仍在显现中)。[15]
在19~20世纪的中非和东非,欧洲殖民当局所推行的改变传统畜牧
耕作方式这一错误的做法,也说明了农业向新的地域扩张所带来的令人
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这一活动加剧了嗜睡病在乌干达部分地区、刚果坦
干伊喀、罗得西亚和尼日利亚的流行;最终的结果是,随着殖民政权的
结束,这片大陆更深地受到了采采蝇的感染,而在当局决定更有效地开
发这一片看似优良的农业地区之前,情况并非如此。[16]
显然,在非洲的热带雨林和临近的草原地区——这个地球自然生态
中最严峻和最多样化的地区——人类为缩短食物链所做的尝试仍未能成
功,并依然以持续感染疾患的方式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一点比其他任何
方面都更能说明,为什么非洲与温带地区(或者美洲的热带地区)相
比,在文明的发展上仍显落后。因为在其他地区,主流的生态系统从未
如此精致,因而也不会与人类的简化行为[17]
如此抵触。[1]Ivan V. Polunin,“Health and Disease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in
Don Brothwell A. T.Sandison,eds.,Diseases in Antiquity,p.74,84.
[2]对古代人口的估算完全是推测性的,依据每平方英里人口密度的假
定。下列论著提供了两个全球性的估计:Kent V. Flannery,“Origins
and Ecological Effects of Early Domestication in Iran and the Near
East”,in Peter Ucko G. W. Dimbleby,eds.,The Domestic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Chicago,1969),p.93;D. R.
Brothwell,“Dietary Variation and the Biology of Earlier Human
Populations”,同上书,p.539—540。
[3]详情请参见C. A. Wright,“The Schistosome Life Cycle”,in F. K.
Mostofi,ed.,Bilharziasis (New York,1967),p.3—7。
[4]今天的埃及是血吸虫最著名的滋生地,同时受影响的还有东非、西
非、西亚和东亚的稻田区,以及菲律宾这样的岛国和巴西的一部
分。这里牵涉到三种不同的血肝蛭,各地的血肝蛭因软体动物的不
同经常有所不同,从而在性质上——对人而言则表现为疾病症状
——呈现出非常复杂且至今仍未完全弄清楚的地方性变异。参看
Louis Olivier Nasser Ansari,“The Epidemiology of Bilharziasis”,in F.
K. Mostofi,ed.,Bilharziasis(New York,1967),p.8—14。
[5]M. A. Ruffer,Studies in Paleopathology of Egypt(Chicago,1921),18
页提到在属于第20王朝的两具木乃伊的肾脏里发现了血吸虫卵。他
在被检查的6个肾脏中的两个发现了这种虫卵;而肾脏并不是最容
易受血吸虫感染的器官(它们最经常寄居的膀胱和其他软内脏都被
古代木乃伊的制作者扔掉了),故可知血吸虫病在埃及的古代可能像现代一样多发。
[6]J. V. Kinnier Wilson,“Organic Diseases of Ancient Mesopotamia”,in
Don Brothwell A. T.Sandison,eds.,Diseases in Antiquity,p.191—
208,试图使楔形文字中的术语对应于疾病的现代分类。这是一项
徒劳无益的事业,他所报道的东西没有一点血吸虫病的影子。也请
参照:Georges Contenau,La Médicine en Assyrie et la Babylonie
(Paris,1938)和Robert Biggs,“Medicine in Ancient
Mesopotamia”,History of Science,8(1969),p.94—105。关于美索不
达米亚与埃及的早期接触,参照Helene J. Kantor,“Early Relations of
Egypt with Asia”,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1(1942),p.174—
213。
[7]“A Lady from China’s past”,the National Geographic,145(May
1974),p.663.这具生前安享富贵的尸体,在肺部也留有肺结核的痕
迹。
[8]参考J. N. Lanoix,“Relations Between Irrigation Engineering and
Bilharziasis”,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Bulletin,18(1958),p.1011—
1035。
[9]在现代埃及,钩虫症在弱化人口素质上以前像、现在仍然像血吸虫
病那样重要,或几乎如此。就全球而言,钩虫症的分布比血吸虫病
更广泛,因为它只需湿润的土壤和裸足的人群即可在宿主间传播。
[10]参考Karl A. Wittfogel,Oriental Despot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New Haven,Connecticut,1957)。他是持如下观点的现
代主要学者:存在一种特殊的极权政治与他所谓的水利文明相适
应。[11]《圣经》中的麻风病对应于当今的何种疾病?这一问题争论颇多
且不易解决。参考Vilhelm M?ller-Christensen,“Evidences of Leprosy
in Earlier Peoples”,in Don Brothwell A. T. Sandison,eds.,Diseases in
Antiquity,p.295—306;Olaf K. Skinsnes,“Notes from the History of
Lepros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prosy,41(1973),p.220—237。
[12]Olivier Ansari前引书,第9页。
[13]参看下文第183页。
[14]René Dubos,Man Adapting,p.237;George Macdonald,The
Epidemiology and Control of Malaria(London,1957),p.33 and
passim.
[15]Frank B. Livingstone,“Anthrop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Sickle Cell
Gene Distribution in West Africa”,American
Anthropologist,60(1958),p.533—562.
[16]关于发生在非洲5个不同地区的事件,详情参见John Ford,The Role
of the Trypanosomiases in African Ecology:A Study of the Tsetse Fly
Problem(Oxford,1971)。也可见Charles N. Good,“Salt,Trade and
Disease:Aspects of Development in Africa’s Northern Great Lakes
Reg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5(1972),p.43—86;H. W. Mulligan,ed.,The African
Trypanosomiases(London,1970),p. 632ff。在Mulligan看来,20世
纪非洲昏睡症的暴发直接源于早先被突然打乱的生态关系,而这最
终可归结于19世纪90年代牛瘟在非洲猎物中的灾难性传播。大量畜
群的死亡导致采采蝇活动范围的缩小,同时伴以驯畜数量及其活动
范围的缩小。当野畜和驯畜痊愈并开始扩张活动地域时,相互渗透发生了,在扩张着的农业和畜牧业的边界区,鱼鞭虫传染到人类身
上。和Ford的观点相比,上述观点不太怪罪殖民当局,而更强调其
生态原因,尽管两者在使用的基本材料上是一致的。
[17]即缩短食物链的行为。儿童病与文明社会疾病模式的出现
在历史上首先出现农业社会的重要地区,它们的生态系统不像热带
非洲那样从本质上抵制人类的改造。在温带地区,能随时利用人口增长
所带来好处的潜在寄生物不仅数量少,而且也不那么可怕。但是,因为
自然平衡的突破性改变都发生在5000年到1万年前,所以不可能像对非
洲那样,推理出或观察到特定的农业发明和领地扩张所带来的疾病代
价。
不过,我们仍旧可以推导出所有文明社会或早或迟都会遭遇的接触
疾病方面的某种重要而普遍的变化,那就是,即便无须借助中间宿主,农业社会不断稠密的人口最终也会达到可以无限维持细菌和病毒感染的
程度。这种情况在小型社会通常不会发生,因为与多细胞寄生物不一
样,细菌和病毒的入侵会在人体内引起免疫反应,而免疫反应会要求在
宿主—寄生物的关系上做出择优选择:要么受感染人迅速死亡,要么受
感染人完全恢复而入侵者被驱逐出宿主的身体组织。再次感染需等到有
免疫力的抗体淡出血液循环之后,那么至少需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
不过,像生物领域里的普遍情形那样,事情绝不是一两句话所能表
达清楚的。个人对感染的抵抗不只是形成抗体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有些病原体虽然引发抗体,但仍然可能在病人体内潜伏几年甚至一生。
像著名的“伤寒玛丽”(Typhoid Mary)的携带者可以无限期地携带某种
病原体,并且把可怕的甚至致命的症状传染给别人时,自身却没有明显
的病症;在另外的情况下,一种传染病也可以变成隐性的病原,即潜伏于宿主身体的某些部位,并在那里长期隐藏。
最有名的一种潜伏感染模式可以让水痘病毒退到输出(efferent)神
经组织中,潜伏50年之久,然后等到感染者年老时再重新发作,引发带
状疱疹。这样,病毒就完美地解决了在小型社会中如何保持传染链不中
断的问题:即使每一个接触到的人都感染了水痘,并且产生了免疫力,但几十年以后,当没有抗体的新一代人成长起来时,感染又会重现江
湖,潜伏于该人群年长者体内的病毒就会沿着输出神经蔓延到皮肤上,产生带状疱疹;然而,一旦传染到新的宿主身上,该病毒引发的仍是习
见的儿童症状,即水痘。该病对大部分人来说,症状并不严重,加上它
表现出的显著的潜伏方式,都说明这是人类久已有之的病毒性传染病。
在这方面水痘与现今常见的其他儿童病不同。[1]
缺乏上述生存技巧的病菌,若又遭遇宿主体内的因抗体反应所产生
的激烈取舍后果,其生存便只得依靠潜在宿主的庞大数量,也就是说,如果社会的整体规模足够大,那么总有尚未感染这种疾病而易感的人群
存在。这种寄生物,若按生物进化的时间尺度来衡量,无论怎么说都只
能是晚辈,尽管按人类历史的时间尺度来衡量,它已经古老得无从追溯
了。只有在上千人的社会里,这种疾病才会延续,频繁的交往可以使疾
病不间断地从一人传到另一人,而这类社会就是我们所谓“文明”的社
会:规模巨大、组织复杂、人口密集,而且毫无例外地由城市掌管和控
制。因此,直接在人类之间传播而无须通过中介宿主的细菌和病毒性疫
病,首先是文明社会的疾病(即所谓“文明病”):乃城市和与城市相连
的农村的特殊标识和疫病负担。它们包括麻疹、腮腺炎、百日咳、天花等,几乎是所有现代人都熟悉的常见儿童病。[2]
儿童病花了几千年才扩散到全球,本书将用很大篇幅探讨这一扩散
过程的关键性阶段。我们必须假设这些疾病(或今天已知传染病的始
祖)最初的形成过程本身必定是渐进性的,包含了无数错误的开始和致
命的遭遇,其中人类宿主的死亡、入侵的寄生物被消灭、传染链因此而
中断,使它终未能成为文明社会的生物平衡中正常的、地方性的、或多
或少带有稳定性质的因素。
在多数情况下,文明社会所特有的传染病原本都由动物传给人类。
人类同驯养的动物联系紧密,因此毫不奇怪,人类常见的很多传染病与
家畜(禽)的传染病存在着明显的关联。比如,麻疹可能与牛痘或犬瘟
热有关;天花肯定与牛痘一类动物传染病有关;流感则是人猪共患。[3]
根据标准手册(standard book)的记载,[4]
今天的人类与家畜共有的疾
病计有:
这个统计有很多重叠,某些传染病在感染人的同时还感染不止一类
动物;而且,既然一些传染病很少发作,而另一些则很常见,只是统计种类就不是特别有意义。不过,大量的重叠确实表明我们同家畜(禽)
的疾病联系是多么盘根错节;它还表明,随着人与动物之间亲密度的提
高,共同患病的概率也在提高。
除了源自家畜或与家畜(禽)共有的疾病以外,人类也可能因卷入
野生动物内部的疾病循环圈而得病。横行于穴居啮齿动物的腺鼠疫、蔓
延于猴群之中的黄热病,以及蝙蝠易患的狂犬病,都属于这类较为致命
的传染病。[5]
寄生物寻找新宿主的过程还远没有结束,甚至就在近代,这一过程
还造成了出人意料的严重后果。比如,牛瘟在1891年侵入非洲,杀死大
量家畜以及羚羊一类的野生物种;但因它的肆虐如此严重和突然——死
亡率高达90%,所以并没有在当地扎下根来,[6]
相反,可能因为缺少易
感染的有蹄类动物,它在几年后就消失了。1959年,一种叫作“奥尼
欧”(Onyong nyong fever)的热病出现在乌干达——这一人类新病可能
源自猴子身上的病毒。其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但对人类的影响却比较
温和,而且随着免疫力的产生恢复得很快。结果同非洲羚羊所患的牛瘟
一样,奥尼欧热病也未能作为一种地方病存在下来,而是神秘地消失
了,正如它神秘地出现——可能退回它原来居留的树冠区域。[7]
10年以
后,即1969年,另一种比乌干达的热病更致命的热病出现在尼日利亚,这个所谓“拉沙热”(Lassa fever)的新疫病是以医疗站里初次发现它的
西医的名字而命名的。这种热病最终于1973年被证明源自啮齿动物——
被认为是该病主要的宿主。于是,人们便采取了适当的预防措施来阻止
该病的进一步传播。[8]可以想象,随着新动物的驯养、新植物的种植,以及人口的增长,这类插曲还会不时出现:传染病必定不断地从动物,尤其与人类长期紧
密接触的驯养动物中传到人类身上。这种传染自然可以多向度进行,比
如,有时候人的疾病也会传染给他们的家畜(禽)。同样,传染病可以
在家养和野生的动物之间互换,既可以发生在同类间,也可以跨越物种
界限,这是由接触机会以及潜在宿主的易感程度来决定的。
换言之,当新的生态龛由于人类活动改变了动植物的自然布局而空
出后,致病寄生物在利用新的机会占领新的生态龛方面,和人类一样成
功。人类的成功意味着动植物种类的减少,而每一种类数量的增多,在
这一经过改进的新的饲养环境中,寄生物只要侵入单一的物种,就能够
大量地滋生。几乎所有的病毒和细菌在侵入机体后,只能活跃几天或几
周时间,就会被抗体阻断其在单个宿主体内的发展。
在继续探讨疾病史之前,我想还是有必要先来看看采用传染病方式
的微寄生和采用军事行动的巨寄生之间的相似性。只有当文明社会的财
富和技能积累到一定水平,战争和掠夺才能成为经济上可行的事业。如
果武力掠夺收成导致农业劳动力很快被饿死,这还不是稳定的巨寄生模
式。但这种情形经常发生,甚至可以跟1891年的非洲牛瘟感染相比,后
者也是大量杀死宿主,以致未能建立起稳定持续的传染方式。
在文明历史的早期,成功的掠夺者变成了征服者,他们学会这样掠
夺农民,即从后者那里抢走部分的而不是所有的收成。通过试错法可以
且确实能够建立起某种平衡,生产者通过生产超过自身维生所需的谷物
和其他粮食,在这样的掠夺中生存了下来。这种剩余正可以看作应付人类巨寄生的抗体,成功的政府可以使纳税人对灾难性的掠夺和外敌入侵
产生免疫力,正如轻微的感染可以让它的宿主对致病的疫病产生免疫
力。疾病的免疫力通过刺激抗体形成,以及将其他生理防御能力提高到
更活跃的水平而发生作用;政府则通过刺激食物和原材料的更多生产以
供养掌握数量庞大、武器精良的专业武士,来提升对抗外来巨寄生
的“免疫力”。这两种抗体反应都会构成对宿主族群的负担,不过比起反
复遭受突然而致命的灾难来说,这份负担显然要轻一些。
建立成功政府的结果,就是创建了一个与其他人类社群相比更为强
大且更加可怕的社会。专业的武士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战胜那些成
年累月从事生产或寻找食物的人们。正如我们不久将看到的,一个适度
感染、经地方病的病毒和细菌感染而在易感人群中形成抗体的社会,从
流行病学的观点看,要比更简单、更健康的人类社群更为强大。可见,导致强大的军事和政治组织发展的巨型寄生,几乎可以与形成人体产生
免疫反应的微型寄生相对应;换言之,战争和疫病的联系其实并不仅仅
限于巧饰的修辞和经常伴随或尾随战争的瘟疫。[9]
就像牛瘟和奥尼欧热病在非洲的传播那样,大部分的细菌和病毒等
病原体的感染最初可能是不稳定的。我们可以想象,人类族群的人数曾
多次因某些新的地方性疫病的流行而急剧削减。而人类易感宿主一而再
地被消耗,又必定会不断地把入侵的病原体从早期农夫体内的“牧场”中
驱逐出去。尽管如此,再次感染的基础仍然存在,因为驯化的动物极有
可能已经是病毒及细菌性传染病的慢性携带者,这种传染病能够不断地
骚扰人类。从追溯牛、马、羊这类动物的野生状态中,我们也许就能看出它们
被认为是这些传染病的慢性携带者的理由。在人类狩猎者多得足以影响
它们的生存之前,它们是群栖的,成群游荡在欧亚大陆的草地上。作为
单一物种组成的群体,它们正好提供了使细菌和病毒感染演变成地方病
的条件,因为在足够大的群体里总可以找到易感染的宿主来完成传染
链。畜群和寄生物之间漫长的相互进化足以形成稳定的生物平衡,一些
病毒和细菌性传染病可能盛行于野生的牛、羊、马群,却不会导致严重
的症状。这种传染病想必是畜群中的“儿童病”,只影响敏感的幼兽,但
几乎不造成大的伤害。然而,它一旦传入人体,通常会变得很凶猛,因
为初次感染的人体缺少必要的免疫力,而熟悉它们的老宿主则从一开始
就至少拥有局部的防护能力。[10]
不过,我们必须假设,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各种病毒性和
细菌性寄生物最终仍成功地传给了人类,并同它们的新宿主建立了长期
的关系。在很多的甚或是全部的情况下,迅速的和半灾难性的早期调适
无疑是必需的,宿主和寄生物的大量死亡可能交替发生,直到新宿主发
展出的免疫力和寄生物达到的适应性使传染病地方化。当今似乎已难以
找到发生这一过程的例子,但澳大利亚的野兔受到恶性传染的事例表
明,当病毒感染传到新群体时,它是如何生存下来并成为地方病的。
这个故事颇有戏剧性。英国殖民者在1859年把野兔引入澳大利亚,在缺少天敌的情况下,新物种迅速扩散到整个大陆,数量众多,并且对
人而言已经变成了害虫:它们吃掉本应属于绵羊的草,澳大利亚的羊毛
产量由此减少,无数牧场主的收益也跟着缩水。人类在澳大利亚尝试消灭野兔的努力直到1950年才出现转机,当时多发性黏液瘤(人类天花的
远亲)的病毒被成功地植入澳大利亚的野兔群。最初的效力是爆炸性
的:仅仅在一个季节里,相当于西欧那么大的地区就全被感染了。第一
年,感染这种病毒的野兔的死亡率高达99.8%,第二年降到90%,而7
年以后,死亡率仅为25%。显然,非常有力的和迅速的自然选择分别在
野兔和病毒当中发生了,采自野兔身上的病毒样本,其毒性在逐年降
低。尽管如此,澳大利亚野兔的数量再也没有或许永远也不可能恢复到
它以前的水平——截至1965年,生活在澳大利亚的野兔只有多发性黏液
瘤引进之前的五分之一左右。[11]
1950年以前,在巴西的野兔中多发性黏液瘤是一种常见病,该病毒
只在这里的野兔当中引发轻微的症状,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地方病的发病
模式。因此可能有人会认为,从巴西野兔向澳大利亚野兔的传播过程中
所需要的调适,程度上应不如寄生物从不同类的宿主那儿传播到人类所
需要的调适。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它们共有一个名字,但美洲野兔和
欧洲、澳大利亚野兔并不是同种,因此,1950年在专家眼皮底下发生的
宿主转移,与某疾病突破动物宿主的界限开始感染人类,从而成为人类
重要疾病的可能性方式相似。
无论新疾病开始时是否像多发性黏液瘤那样致命,宿主和寄生物之
间的相互调适过程本质上是一致的。一种稳定的新疾病模式,只有当双
方从最初的接触当中存活下来,并且通过适当的生物的和文化的[12]
调
适达到相互容忍的关系时才算确立。在调适的全过程中,细菌和病毒拥
有产生下一代所需时间比人类短得多的优势,因而有助于病原体产生在宿主间安全传播的基因突变,它要比人类遗传天赋或生理特征的相应改
变快得多。的确,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后来的历史表明,人
类要将其对剧烈新疫病的反应稳定下来,大约需要120~150年的时
间。[13]
通过比较,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的野兔数量的最低点出现在1953年,即多发性黏液瘤首次暴发的3年以后。考虑到野兔代际的短暂——澳大
利亚野兔从出生到生崽只要6~10个月[14]
,按每代人25年计算,野兔的
3年相当于人类的90~150年。换言之,人类和野兔需要大致相当的代际
时间来适应致命性的新疾病。
我们可以把宿主与寄生物之间相互调适的整个过程,设想成生物平
衡形成之前一系列的波浪状动荡。最初的动荡可能非常剧烈,像发生于
1950年的澳大利亚野兔那样,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寄生物向新宿主的转
移太过剧烈而无法长久持续。然而,只要新的传染病能够无限期地生
存,自然会出现动态的平衡:频繁感染期与疫病衰弱甚至几乎消失的时
期交替出现。这些变动往往会形成程度不等的有规律的循环,也就是
说,只要来自外部的重大入侵不改变新兴的宿主和寄生物间的平衡模
式。很多的因素都会参与到这种周期性的平衡中来,比如,温度和湿度
的季节变化往往使春季成为温带地区现代城市中儿童病的多发期。
人口中易感人群的数量,以及他们是群居还是散居,都是基础性的
因素。例如,学校和军营一直是现代社会两个最重要的易感的年轻人的
聚集场所,当代西方社会的父母都能觉察到小学在传播儿童病方面扮演
的重要角色:在普及疫苗接种以前的19世纪,法国军队中的来自农村的士兵容易患病,有时非常严重,而这些传染病在城里的同龄人那里因已
有过接触而具有免疫力。结果,强壮的农民子弟比那些来自城市贫民窟
的营养不良的士兵死亡率更高。[15]
感染一个新宿主所需的剂量,传染病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身
上所需的时间,诸如此类的传染方式,以及影响交互传染机会的习俗,都决定着多少人得病和什么时间得病。通常,只有人类宿主大量聚集在
大都市,传染病才能长久地生存下去。在这里,为维持传染链不中断而
与足够多的易感新宿主接触的机会,显然远多于潜在宿主稀疏分布的广
大农村地区。不过,一旦乡村社会也有了足够多的易感人群,这类传染
病也可能以城市为中心向外扩散,像恐怖的野火在村与村、家与家之间
蔓延燃烧。然而,这类传染病的暴发,来得快,去得也快。随着当地易
感宿主的难以为继,传染病也就消失了,只有它最初出现的城市中心是
例外。在那里,足够多的易感人口仍然存在,使病原体不致消亡,而待
到缺乏免疫力的人口再度聚集于在农村地区,又一回合的疫病暴发便再
一次成为可能。
有时,所有这些复杂的因素却会沉潜下来,成为相对简单的、普遍
的发病模式。对麻疹在现代城市社会中传播方式的详细统计研究表明,某种波浪式向前推进的方式在每隔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达到一次高峰。而
且,最近的研究发现,要维系这种模式,麻疹的持续性要求有至少7000
名易感者。考虑到当今的出生率、城市的生活方式以及送孩子读书的习
惯(在这里麻疹可以在初次接触该病毒的一个班级的孩子当中迅速传
播),这一数字意味着,麻疹若要在现代城市中延续下去,其人口下限大约为50万。另外,通过在农村地区的散布,稍小规模的人群也可以维
持麻疹的传染链不致中断。真正让该病毒难以为继的人数底线为30万~
40万人。这一点,可由麻疹感染在那些人口高于或低于这个底限的海岛
上的表现方式来加以证明。[16]
但在现时流行的疾病当中,再没有别的疾病展示出如此明确的方
式,可能也没有别的疾病需要如此大的人群规模来保证它的生存。对于
别的常见儿童病,哪怕是相对精确的研究也尚未展开,这在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人工的免疫措施在所有现代国家中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传染方式。
不过,最常见的儿童病的毒性和发作频率,无论在最近还是欧洲各国政
府首次开始搜集有关各类传染病发病情况的统计数字的19世纪,都出现
了明显的变化。换言之,病原体和人类宿主之间的相互调适,无论过去
还是现在都一直处于快速的演进之中,以应对人类生活环境的变迁。
那么,当代儿童病的“始祖”是在何时何地开始首次侵害人类的呢?
为此搜寻相关的历史记载可能令人沮丧。首先,古代的医学术语很难适
用于当代的疾病分类。其次,症状的变化之大,甚至已令人无法辨认。
新疾病在开始的时候表现出的症状,在后来宿主逐渐产生抗体后往往就
消失了。
关于以往的这类现象,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梅毒在欧洲最
初暴发出来的症状。在今天,当新疾病第一次侵入到刚打破封闭的社会
时,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情形。实际上,这些变化了的症状确实
可以完全掩饰该疾病的性质,除非专家通过细菌学分析才能判断出来。
例如,当结核病第一次进入加拿大的印第安人部落时,他们的身体器官被病菌攻击,但在白人身上却未见有病理反应。而且与那些早就接触过
结核病的社群所表现的感染情形相比,不仅诸如脑膜炎之类的症状表现
得更为严重,其病情的发展速度也快得多。在病症最初出现的时候,只
有显微镜下的分析才能让医生确认这就是结核病。然而到第三代,随着
宿主与寄生物的相互调适逐渐接近常见的城市发病方式,北美印第安人
的结核病症状也倾向于集中出现在肺部了。[17]
宿主与寄生物的调适过程是如此快速而花样繁多,以至我们必须假
定现今流行的传染方式只是瘟疫当下的表现,历史已深刻地改变了它们
的症状。然而,鉴于已知现代城市保持麻疹流行需要50万人,值得注意
的是,最新有关古代苏美尔——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的
总人口的估算,正好是这个数字。[18]
似乎可以肯定,当时苏美尔诸城
市之间有着足够密切的联系,足以构成一个单独的疾病库:若真的如
此,接近50万的人口规模肯定足够支撑类似现代儿童病这样的传染链。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随着世界其他地方也开始了城市文明,连续的传
染链可能也开始在别的地方出现。首先在这儿,然后在那儿,一种又一
种的病原体可能就这样侵入到随处可见的人类宿主,并在由日渐增加的
人口密度为它所创造出的适宜的生态龛上稳定下来。
[1]参阅R. Edgar Hope-Simpson,“Studies on Shingles:Is the Virus
Ordinary Chicken Pox?”Lancet,2(1954),p.1299—1302;R. Edgar
Hope-Simpson,“The Nature of Herpes Zoster:A LongTerm Study and a
New Hypothesis”,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48(1965),p.8—20。[2]Francis L. Black,“Infectious Diseases in Primitive
Societie ......
您现在查看是摘要介绍页, 详见PDF附件(5362KB,3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