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是孤岛:侯孝贤的电影世界.pdf
http://www.100md.com
2020年4月3日
 |
| 第1页 |
 |
| 第7页 |
 |
| 第13页 |
 |
| 第30页 |
 |
| 第35页 |
 |
| 第72页 |
参见附件(8839KB,279页)。
无人是孤岛是作者詹姆斯乌登写的关于侯孝贤的个人传记,主要讲述了侯孝贤的电影创作生涯,他对电影行业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对他的作品进行的详细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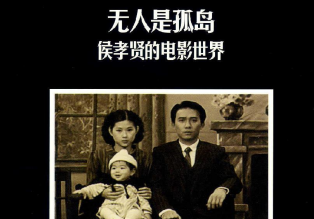
内容介绍
侯孝贤是我国台湾新电影运动的领军人物,也是享誉世界的电影大师,重要作品包括《童年往事》、《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和《海上花》等。本书完整全面地论述了他的创作生涯,阐明了他独一无二的成就与风格的形成及演变。作者认为侯孝贤电影反映了台湾独特的历史与地理状况,并且只可能诞生于那种环境之中。本书也考察了侯孝贤电影对其他亚洲导演的区域性影响。
一部杰出而具开创性的著作。在研究侯孝贤的同类文献中,本书以其覆盖广泛、分析详尽而独树一帜。作者同样观照成就侯孝贤其人其作的宏观的历史与社会框架、对其创作有更直接决定作用的工业与文化因素,以及他的创作生涯所发展的独特的美学策略。本书对侯孝贤作品及其背景所作的精确分析,使之成为英语世界任何研究侯孝贤的学者的重要资源。
作者简介
詹姆斯乌登(James Udden),曾任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现为葛底斯堡学院电影研究副教授。长期研究台湾电影与亚洲电影。为完成本书,赴台居住多年,多次深入采访侯孝贤及其合作伙伴。
黄文杰,复旦大学传播学博士,副编审,曾在《电影艺术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多篇电影论 文。
章节预览
第一章 侯孝贤与台湾经验
1949年前的历史“说法”
侯孝贤与战后台湾经验
侯孝贤与战后政治经验
侯孝贤与战后经济经验
侯孝贤与战后文化的缓慢解冻
台湾电影工业中的侯孝贤
第二章 侯孝贤与台湾新电影
1980年代的台湾
台湾电影文化
危机中的电影工业
《儿子的大玩偶》
《风柜来的人》
《冬冬的假期》
《童年往事》
《恋恋风尘》
《尼罗河女儿》
第三章 还原历史:《悲情城市》与《戏梦人生》
被遮蔽的日本殖民背景
“二二八事件”:台湾身份的沸腾血泊
《悲情城市》:一个空前的文化事件
《悲情城市》的文本现象:先体验,后理解
1989一1993:《戏梦人生》前的长久沉默
《戏梦人生》:浮云连缀的电影
未经修饰或想象的历史?
第四章 再见过往:新的侯孝贤
《好男好女》
《南国再见,南国》
《海上花》
侯孝贤的“中国性”
结论 新千年的侯孝贤
《千禧曼波》
《咖啡时光》
《最好的时光》
《红气球之旅》
侯孝贤:不仅是一座岛
无人是孤岛:侯孝贤的电影世界截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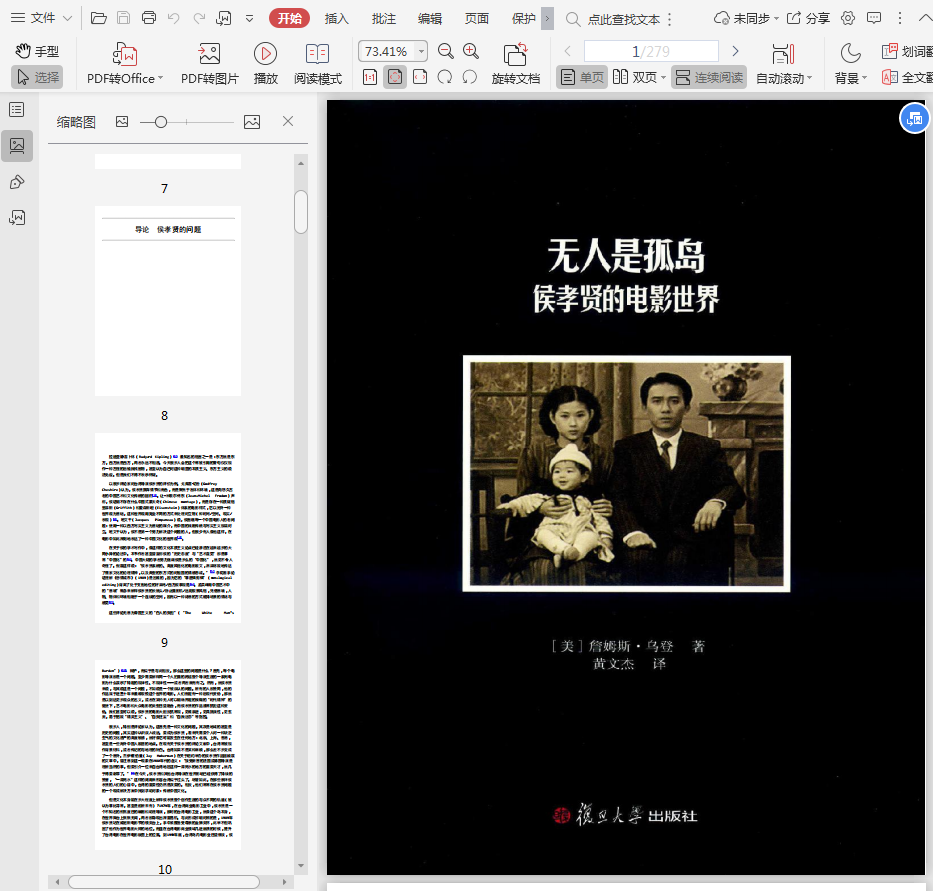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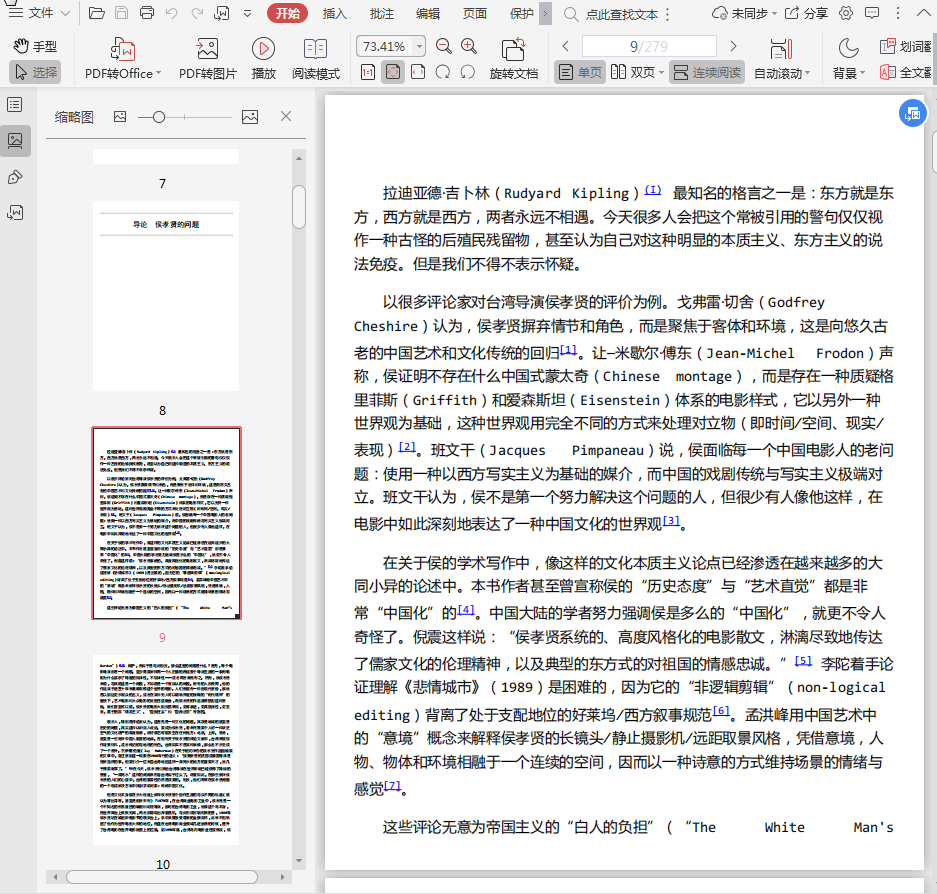
目 录
致谢
导论 侯孝贤的问题
第一章 侯孝贤与台湾经验
1949年前的历史“说法”
侯孝贤与战后台湾经验
侯孝贤与战后政治经验
侯孝贤与战后经济经验
侯孝贤与战后文化的缓慢解冻
台湾电影工业中的侯孝贤
第二章 侯孝贤与台湾新电影
1980年代的台湾
台湾电影文化
危机中的电影工业
《儿子的大玩偶》(1983)
《风柜来的人》(1983)
《冬冬的假期》(1984)《童年往事》(1985)
《恋恋风尘》(1986)
《尼罗河女儿》(1987)
第三章 还原历史:《悲情城市》(1989)与《戏梦人生》(1993)
被遮蔽的日本殖民背景
“二二八事件”:台湾身份的沸腾血泊
《悲情城市》:一个空前的文化事件
《悲情城市》的文本现象:先体验,后理解
1989—1993:《戏梦人生》前的长久沉默
《戏梦人生》:浮云连缀的电影
未经修饰或想象的历史?
第四章 再见过往:新的侯孝贤
《好男好女》(1995)
《南国再见,南国》(1996)
《海上花》(1998)
侯孝贤的“中国性”
结论 新千年的侯孝贤
《千禧曼波》(2001)
《咖啡时光》(2003)《最好的时光》(2005)
《红气球之旅》(2007)
侯孝贤:不仅是一座岛
中英术语对照表
译者后记致谢
这个研究旨在说明没有电影人是单打独斗的,电影人如此,对深入研究他们的
任何人来说,也是如此。和所有从事类似研究项目的人一样,我不仅得到众人的帮
助,也受惠于诸多机构,是他们让这一切成为可能。我要感谢香港大学出版社的支
持,特别是科林·戴(Colin Day)、迈克尔·达克沃斯(Michael Duckworth)和道
恩·刘(Dawn Lau)付出的努力。当然我也要感谢匿名审稿人对原稿提出的详尽意
见,这本书稿能修改得更精炼且质量更高,他或她的建议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虽然书稿付梓在即,但这个项目其实很早就在其他机构和个人的支持下开始
了。我首先要感谢,也是最需要感谢的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传播艺术系,它是这个研究项目的真正诞生地。该系自始至终提供了一个热情周到与大度包容的
环境,培育我脚踏实地,让我不会满足于肤浅的结论或者在学问上抄近道。我无法
点到每一个在早期阶段曾直接或间接影响这个项目的人名,但是有些人一定要提
到。首先我要感谢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他最早指导我的研究。自
从我遇见波德维尔博士那天起,他就对这个项目很热心,为我提供了学界最前沿的
建议和指导,不但包括严格的标准,也包括富有感染力的激情和鼓励。其次要感谢
万斯·开普利(Vance Kepley)和凯利·康韦(Kelley Conway),作为我的论文初
稿审稿人,他们提供了无价的帮助,以及利·雅各布斯和 J·J·墨菲,他们敏锐的洞察
力启发我反思某些问题。我也要感谢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每一个与我共同开
展研究的同事。尽管可能会漏掉许多同样值得特别提到的名字,我还是要感谢丽莎·
东布罗斯基(Lisa Dombrowski)、伊桑·德·塞弗(Ethan de Seife)、帕特里克·
基廷(Patrick Keating)、文斯·博林杰(Vince Bollinger)、崔珍熙
(Jinhee Choi)、汤姆·吉上(Tom Yoshikami)、斯图·法伊夫(Stew Fyfe)、凯瑟琳·斯普林(Katherine Spring)及贝卡·斯文德(Becca Swender)。(如果
我漏了任何人的名字,既然我列了这份名单,无疑我想到了你。)此外,我要多多
感谢尼科尔·黄和爱德华·弗里德曼的批评与宝贵的建议,本书形貌与初稿完全不同,他们对此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如果没有富布赖特–海斯奖学金让我得以开展第一阶段的研究(本研究主要以之
为基础),我无法想象这项工作会成什么样子。我不但要感谢美国国务院在2000年
为我提供这一奖励,也要感谢在台湾地区管理富布赖特奖学金的学术交流基金会。
首先我要感谢吴静吉博士,当我在台北的时候他管理基金会。同样要感谢 Julie
Hu、Amy Pan、Amy Sun 和 Mark Dong。这五位让我们在台北的那一年不但在学
术上成果丰富,而且难以忘怀。我还要感谢2000年至2001年富布赖特社团的同事
们,主要是Sansan Kwan、Kenny Speirs和De-nin Lee。
我还必须感谢台湾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机构——台湾电影资料馆。当然我要感谢
馆长李天礢,主要是因为他在2001年安排了一些关键的访问。然后要感谢黄慧敏,在2000年至2001年间她给予了我持续的支持,还要特别感谢Luo Shu-nan指出了一
些我本来可能错过的相对隐蔽的一手原始资料。我也要感谢资料馆的众多员工,他
们忍受我每天都要出现,特别是那些在前台工作的人们,总是面带微笑为我安排一
天三部片的观赏。资料馆以外,需要感谢的名字多到不可胜数。焦雄屏和黄建业的
支持很重要,他们不厌其烦地帮助我,不仅提供关键的关系,也提供他们自己对侯
孝贤和台湾电影的洞见,他们亲眼见证了这一切。我还要特别感谢陈怀恩、朱天文
和侯孝贤本人,他们每人都在百忙中抽出宝贵时间,分别接受了我长达四个小时的
访问。我同样要感谢黄文英,在我2005年的后续研究之旅中接受了我的访问,她的
谈话发人深省。
我现在的就职单位葛底斯堡学院也值得特别感谢,它无条件地为我提供了教职
和奖学金。我要特别感谢教师发展委员会授予我一项研究与发展基金,让我得以在
2005年夏天重返台湾,真正完成本研究。我也要感谢教务长办公室、杰克·雷恩
(Jack Ryan)、鲍勃·波尔(Bob Bohrer)、玛尔塔·罗伯森(Marta
Robertson)和辛迪·赫尔弗里克(Cindy Helfrich),这里的每一份感谢都有其
原因。我想另外感谢托马斯·居里(Thomas Jurney)、布兰登·库欣–丹尼尔斯
(Brendan Cushing-Daniels)和萨拉·普林奇帕托(Sarah Principato),他们
帮助策划本书的出版。我也要感谢我在葛底斯堡学院的学生们,他们中的许多人没
有意识到我在课堂上对侯孝贤电影(主要是《海上花》)的调查其实是我的研究的一部分。再说一次,我在此不可能点到每一个人的名字,但是我想提一下三个学
生,他们实质上几乎从头至尾是这个漫长历程的一部分:杰克·肯尼迪(Jake
Kennedy)、特里斯坦·门茨(Tristan Mentz)和布朗温·坎宁安(Bronwyn
Cunningham)。他们和其他许多学生让这项研究变得有意义和有价值。
通常最后是更私人地提及那些最亲密的人,他们贡献了恒久的忍耐与支持。但
是我对我的太太Shuchen,要感谢的不止这些。在读研究生之前,差不多二十年
前,我住在台湾并且在那认识了Shuchen。你不但给予了我永恒的爱和一如既往的
支持,还让我看了真正与台湾经验相关的第一手材料。我会永远感激你给予我的一
切,谢谢你和你的家庭接纳我,为我提供真正意义上的第二个家,也让我初步体验
了自身的台湾经验。倘若没有所有这些——主要是如果没有你——一切将毫无意
义。导论 侯孝贤的问题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I) 最知名的格言之一是:东方就是东
方,西方就是西方,两者永远不相遇。今天很多人会把这个常被引用的警句仅仅视
作一种古怪的后殖民残留物,甚至认为自己对这种明显的本质主义、东方主义的说
法免疫。但是我们不得不表示怀疑。
以很多评论家对台湾导演侯孝贤的评价为例。戈弗雷·切舍(Godfrey
Cheshire)认为,侯孝贤摒弃情节和角色,而是聚焦于客体和环境,这是向悠久古
老的中国艺术和文化传统的回归[1]。让–米歇尔·傅东(Jean-Michel Frodon)声
称,侯证明不存在什么中国式蒙太奇(Chinese montage),而是存在一种质疑格
里菲斯(Griffith)和爱森斯坦(Eisenstein)体系的电影样式,它以另外一种
世界观为基础,这种世界观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对立物(即时间空间、现实
表现)[2]。班文干(Jacques Pimpaneau)说,侯面临每一个中国电影人的老问
题:使用一种以西方写实主义为基础的媒介,而中国的戏剧传统与写实主义极端对
立。班文干认为,侯不是第一个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但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在
电影中如此深刻地表达了一种中国文化的世界观[3]。
在关于侯的学术写作中,像这样的文化本质主义论点已经渗透在越来越多的大
同小异的论述中。本书作者甚至曾宣称侯的“历史态度”与“艺术直觉”都是非
常“中国化”的[4]。中国大陆的学者努力强调侯是多么的“中国化”,就更不令人
奇怪了。倪震这样说:“侯孝贤系统的、高度风格化的电影散文,淋漓尽致地传达
了儒家文化的伦理精神,以及典型的东方式的对祖国的情感忠诚。”[5] 李陀着手论
证理解《悲情城市》(1989)是困难的,因为它的“非逻辑剪辑”(non-logical
editing)背离了处于支配地位的好莱坞西方叙事规范[6]。孟洪峰用中国艺术中
的“意境”概念来解释侯孝贤的长镜头静止摄影机远距取景风格,凭借意境,人
物、物体和环境相融于一个连续的空间,因而以一种诗意的方式维持场景的情绪与
感觉[7]。
这些评论无意为帝国主义的“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Burden”)(II) 辩护,而似乎是与此相反,那么这里的问题是什么?首先,每个电
影导演都是一个问题。至少需要解释同一个人拍摄的跨越整个导演生涯的一系列电
影为什么展示了特定的规律性、不规律性——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然而,就侯孝贤
来说,与其说这是一个问题,不如说是一个被误认的问题。所有的人都赞同,他的
作品属于近三十年来最难取悦这个世界的电影。人们假定有一种后现代妥协,那就
是以到达更多观众的名义,或者在某种无人可以明确界定的模糊的“时代精神”的
驱使下,艺术电影和大众电影的类型日益融合,而侯孝贤的作品通常抗拒这种妥
协。我们甚至可以说,侯孝贤的电影大胆反抗常规,更难亲近,更具挑战性,更玄
奥,易于招致“精英主义”、“自负狂妄”和“自我迷恋”等指控。
很多人,特别是评论家认为,这首先是一种文化的问题,其次是地域的甚至是
历史的问题,其实这种认识误入歧途。要成为侯孝贤,看来只需要个人对一种缺乏
生气的文化遗产的高度敏感,就好像它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北京、上海、香港,甚至是一些海外中国人散居的地点。在现有关于侯孝贤的评论文献中,台湾常被视
作背景材料,或者传记的与地理的补白。台湾如果不是某种麻烦,那么差不多变成
了一个意外。杰伊·霍伯曼(Jay Hoberman)在关于纽约举办的侯孝贤作品回顾展
的文章中,曾注意到这一现象在1980年代的含义:“接受新晋的法国或德国导演是
理所当然的事,但要引介一位来自台湾地区这样一潭死水的地方的重要天才,就几
乎得要谢罪了。”[8]在今天,侯孝贤和其他台湾导演在世界影坛已经获得了持续的
赞誉,“一潭死水”这样的词用来形容台湾似乎过头了。尽管如此,在那些崇拜侯
孝贤的人们的心目中,台湾的重要性仍然是次要的。相反,他们常常在侯孝贤问题
的一个现成解决方案中找到求助对象:传统中国文化。
但是文化本身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侯孝贤整个创作生涯的与众不同的轨道(被
认为非比寻常,甚至是前所未有)?1979年,在台湾商业电影工业中,侯孝贤是一
个不知名的煎熬度日的编剧和助理导演,那时的台湾电影工业,就像这个岛本身,在世界舞台上默默无闻,两者都隐现出深重危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89年
侯孝贤站在威尼斯电影节的领奖台上,手中紧握备受尊崇的金狮奖杯,此举不但巩
固了他作为世界电影大师的地位,而且在台湾电影商业领域几近崩溃的时候,提升
了台湾电影在世界电影版图上的位置。到1999年底,台湾岛内电影业日益惨淡,侯孝贤却证明了自己不是昙花一现的现象:一份全球性的电影机构调查结果显示,整
个1990年代全球最佳二十五部电影中,侯孝贤的作品有三部入榜[9];在一次由《村
声》杂志组织的超过五十个评论家参与的评选中,侯孝贤同样被列为90年代最优秀
的导演[10];关于他的书籍也已出版了法文、日文和中文;甚至那些不喜欢他的电影
的批评者也不得不详尽充分地讨论它们。台湾学者叶月瑜(Yeh Yueh-yu)如此概
括侯孝贤的当前地位:“到20世纪末,侯孝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认可和褒奖,任何
一位为西方世界欣赏的当代中国电影人都无法与之相比。”[11]
因为侯孝贤创作生涯中充满转折与转向,我们不得不怀疑传统文化能在多大程
度上解释它:要么这种文化并不是那么没有生命力——考虑到在超过三十年的时间
里有如此戏剧性的变化,要么有其他不得不解释的因素。不过话说回来,也可能是
一种充满活力的、柔韧的文化与许多其他因素相结合,所有这些创造了这个独一无
二的电影整体,唯一没有改变的是这个叫“侯孝贤”的名字,它把这些作品统一了
起来。
文化不但无法单独解释关于侯孝贤的一切,它也提出了几个可能促使我们提防
对类似文化解释过度依赖的深度问题:潜在动机的问题,未经核实的假定的问题,还有最主要的,台湾自身的问题。后者尤其重要,不理解台湾,就无法理解侯孝
贤;没有台湾,就不存在侯孝贤,当然也不可能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侯孝贤。为了
证明这点,让我们逐一分析这些问题,先从隐藏在类似断言背后的动机开始。
有一点得马上指出来,那就是这些观点中的大多数掩饰了潜藏的政治动机,尽
管不是所有的观点都如此。在上述不止一个例子中,我们不得不怀疑,焦点是否实
际上是中国文化,而不顾台湾。也许中国文化就像侯孝贤电影,只不过是达到其他
目的的手段,也就是说为了解构西方电影,特别是好莱坞的霸权。请留意在“东
方”与“西方”之间,一种巨大的对抗如何频繁地被设置:侯孝贤如今代表了一个
勇敢地对抗无处不在的西方体制的东方“他者”形象。这是西方学界关于亚洲电影
研究的老套路:最初研究日本电影,很多人企图将文化议题带至最前沿,其中最著
名的例子是诺埃尔·伯奇(Noel Burch)有时闪现真知灼见,但是常常误入歧途的日
本电影研究:《致远方的观察者:日本电影中的形式与意义》(To the Distant
Observer: Form and Meaning in the Japanese Cinema)。诺埃尔·伯奇的首要目标,他的整个学术研究所显现的,是为了把西方电影中呈现的支配性模式撕
裂。日本电影因而成了这场大的斗争的一个工具,但是它本身不是目的,甚至也不
必然被当成一个值得研究的目的。这种方法和有关第三世界电影的假设可能没有共
同的由头,但有一种近似的主张:反抗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蓄意的,甚至政治
化的、对抗的立场的意图,通过电影手段顽强且自觉地维持自身固有传统的意图,假定另外一种独特的、传统的、源于本土的电影语言要实现的意图[12]。所有这些认
知上的倾向或多或少地被沿用到了关于侯孝贤电影的论述中;有的研究不出意料地
寻找一种能被清晰界定的本土的、“传统的”文化的迹象;这根本就是一种被设置
的用以对抗西方统治地位的“他者”电影。
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学者可能抱有不同的政治动机,它们有意无意地与政府的
官方政策相吻合。中国大陆讨论侯孝贤的学者往往提倡“大中华”的概念,并且常
常显示出民族主义假定。叶月瑜曾回忆一次在北京和一个学者的谈话,这个学者至
少在表面上支持后殖民主义的概念,他曾邀请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和霍米·
巴巴(Homi Bhabha)到北京参加研讨会。当叶问他如何看待台湾与大陆再度统一
的话题时,他礼貌地表示,这是必然而且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13]。因此,当倪震宣称侯孝贤的电影表达了一种儒家“精神”,这种陈述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么单纯,事实上包含了一些政治性的弦外之音。更重
要的是,将侯孝贤简化归纳到传统中国文化上,符合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计划,符
合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的声明。
除了这些主要聚焦于中国文化的不同动机外,还有一些远远超出侯孝贤是否符
合一种现存的文化模式的潜在假定。上述提及的评论家,包括东方和西方的,不但
都假定侯孝贤电影显示了一种独特的“中国风格”,或者说一种独特的“中国世界
观”,也暗中假定一种本质的、统一的、共时的观念——也即非常的“中国”——
是可能的,好像中国文化没有经历毁坏的历史穿越几个时代传承了下来,好像中国
哲学和思想保持了根本的统一并且能被轻易界定——通常是在儒家思想的大标题
下。同样,还有一种假定认为,相比更个性化的和创造性的路径,今天真正的中国
艺术家更重视过去和传统。如果我们希望理解侯,尤其是理解他如何处理他自己的
文化,包括它的传统方面,那么这些假定中的每一种都应该经受检查。即便是对中国文化最草率的评论也认为,相比许多人所认可的中国文化,存在
一种更有活力的、更不易被界定的中国文化。如果一个人对这种文化进行历史分期
——比如,前汉与后汉,佛教引进前后,或者1919年前后——他将发现可以从中挑
选出变化的,甚至自相矛盾的传统。或者认为有其他可行的区分,比如将中国分为
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或者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业余文化和专业文化。这些历史
的、地理的和社会的区分方法都真实存在,中国人长期认可。但是当把侯孝贤定义
为一个本质上的“中国”导演时,上述区分都被忽略了,有时是出于方便。
我们也要考虑下儒家思想自身也改变了很多次。在汉朝(公元前206-公元
220)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以前,它只是一种思想混合体的组成部分,与
之竞争的有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农家,以及因思想过于松
散而得名的杂家[14]。此后,为了维持意识形态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儒家思想一再
自我改造。事实上,在汉朝到隋朝建立之间(220-589)的漫长历史长河中,儒家
遭遇了道教复兴与佛教涌入的围攻,以致很难与强大的后两者竞争[15]。在唐朝
(618-907)——被认为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历史朝代,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也是中
国文明的巅峰——儒家仍然难与佛教相提并论,因为甚至宫廷中也举行佛教仪
式[16]。只有到了宋朝(960-1279),新儒家得以巩固,使得儒家再度获得最高统
治地位,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西方国家的入侵。简而言之,儒家统治了数百年,就
像当年在汉朝时一样。而且,儒家仅仅通过从佛教和道教中增补了许多哲学观点,就做到了这点[17]。换句话说,儒家允许自己不纯粹、自相矛盾,因此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中国的艺术和它的意识形态与宗教思想一样具有历史活力。在传统中国,艺术
家不是一类特别的人群;著名的艺术家文学家通常是儒家系统中享有既得利益,受
过教育的、官僚阶层的精英,至少在年头好的时候是这样。然而,当我们审视在这
种被假定大一统的传统中什么受到保护,甚至赞扬,我们会发现其他传统也在发挥
作用的充足证据[18]。虽然道家思想是一种在根本形式上与儒家思想的等级理想直接
对立的无政府主义者思想,但是没有一种非儒家思想对中国诗人、画家和书法家的
影响超过道家思想。中国历史上一些最受崇敬的艺术家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在中
国,书法可能是最高级的艺术形式,王羲之(303-361)则被认为是最伟大的书法家。他的作品不但代表了当时时尚中的“自发和悠闲淡泊的贵族理想”,而且承载
了深刻的道家根基[19]。竹林七贤是一群成就很高的诗人,他们极不推崇儒家思想,如今被描绘为“个人主义的和特立独行的艺术家”[20]的化身。同样不同寻常的包括
放荡不羁的阮籍(210-263),他可以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女孩之死嚎啕大哭,却胆敢在母亲下葬之日大吃大喝,不流一滴眼泪,这也是冒犯儒家道德的另一种行
径,这些行为令世人目瞪口呆[21]。郭熙(1000年后——约1090年)是中国有着深
远影响的山水画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早春图》描绘了一种道家乐土的景象[22]。总
体而言,山水画在中国画历史上独树一帜,常常描绘出世的隐士,在画面的布局
上,和自然相比,他们微不足道,明显体现了道家思想,虽然后来儒家学者也经常
运用儒家思想来解读山水画。
在盛唐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艺术传统的多样性,特别是两位诗人李白
(701-762)和杜甫(712-770),他们两位拥有的成就就像西方的莫扎特和贝多
芬。然而这两位诗人有着天壤之别[23]。杜甫成为后代在诗歌创作上试图追随的榜样
之一,但是他自身是具有独创性的儒家。与之相反,李白是个信奉道教的叛逆者,一个失败的、嗜酒的官僚。李泽厚形容李白的诗歌是“不可预计的情感抒发,不可
模仿的节奏音调”[24]。
甚至是过去的评论所表达的观念,也包含了一种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文化发展。
关于文学艺术的传统式写作频繁地赞美创造性——而非对传统的模仿——的美德,考虑到它们的儒家信仰,这是令人惊奇的。一个例子是清代学者叶燮(1627-
1703):
诗,末技耳,必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而后为我之诗。若徒以效
颦效步为能事,曰“此法也”,不但诗亡,而法亦且亡矣。余之后法,非废法
也,正所以存法也[25]。
在中国历史上,这实际上不是后来才有的观点。一千多年前,中国最重要的绘
画理论家之一谢赫(活跃于约500-535?)这样评价画家张则:“意思横逸,动笔
新奇。师心独见,鄙于综采。变巧不竭,若环之无端。”[26]苏轼(1037-1101)是中国所谓的学者传统中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他的见解很简单:“诗画本一律,天工
与清新。”[27]跨越多个时代的理论灵活性,具体结果就是中国画是如此的千变万
化,以致最著名的中国艺术研究学者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 Clunas)坚决反对
任何统一的“中国画”概念[28]。
上面我们离题描述了中国思想与艺术的简短历史,目的很简单:只不过为了说
明,说侯孝贤的电影很中国,等于什么也没说。在这种文化多个世纪所展现的成百
上千种层次和面貌中,哪些特别适用于侯孝贤的案例?而且,这个问题因为20世纪
中国历史上的暴力和经常性的残酷扭曲而变得严重。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或
者说时间的)问题,而且是地理的问题。这也就是说,我们不但不能脱离历史,我
们也不能脱离台湾,因为那里正是侯孝贤成长的地方,也仍然是他制作电影的根据
地。如果说中国文化对侯孝贤电影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意义也在于中国文化
在台湾约从1947年(和更早,我们将会在后文分析)到今天是如何过时的。中国文
化在台湾的意义完全不同于它在大陆甚至香港的意义,而且,这种不同是如此之
大,以至于离开台湾,侯孝贤的电影就是不可想象的。
这无疑解释了为什么在台湾批评和学术话语会如此不同。西方人接触台湾人对
于侯孝贤的看法,通常是通过焦雄屏的英文写作,或者是经过翻译的侯孝贤和他的
编剧朱天文的访谈。侯、朱和焦祖籍都在大陆,他们的父母在1949年的大撤退中迁
移来台。然而,无论他们对若隐若现的大陆产生什么样的文化亲和力,他们三人在
台湾长大,这一事实令他们对祖国怀有矛盾的情绪。焦雄屏有时用传统中国文化来
解释侯孝贤[29]。然而焦在台湾有一个不同寻常的身份,作为台湾电影的前辈,由于
她的语言技能和非官方立场,常常肩负提升台湾电影在海外地位的使命。从纯粹的
市场立场考虑,用这样易于消化的文化美味来吊胃口而不是模棱两可,这对她来说
是合情合理的。而且,如果焦雄屏真的信任侯氏风格的“中国性”,那么这充其量
不过是一种偏颇的解释。她也相信侯孝贤是一个现代导演,而且她很聪明地拒绝任
何对侯孝贤的化约式的解释[30]。朱天文似乎使这个议题偏得更远,她宣称,考虑到
中国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和矛盾之处,把侯的风格界定为中国的,是非常困难的[31]。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侯孝贤本人也展现了他的灵活性。在1997年关于他的纪录片
中,奥利维耶·阿萨亚斯(Olivier Assayas)(III)问他到底是一个“中国导演”还是一个“台湾导演”,侯孝贤回答说,人们不能否认他是中国人的文化因素,同时
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个台湾导演[32]。在另一个场合,他还曾解释道,他的目的是创造
一种属于“东方”的含蓄的风格,“东方”并不特指中国大陆、日本或者台湾地区
[33]。表面上看侯孝贤似乎在重提类似前文引述的某种“反转东方主义”(reverse
Orientalism):避免任何单一的或特定的文化标签,他正在为自己创造一种特殊
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故意的暧昧状态,这对一般的台湾人来说是非常典型的。更重
要的是,对台湾的大多数学者和评论家来说,和关于台湾的更直接也常常是历史上
的独特议题(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相比,侯孝贤有多中国成了一个次要议题。对许
多西方和中国大陆的评论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对侯孝贤和他的搭档,以及大多数
关于他的本土文献来说,却是次要的。
无可否认,岛外的一些学者也已开始采用其他的解释路径。这方面的一个重要
人物是台湾出生的学者叶月瑜,她反对任何关于侯孝贤的轻率结论,已经发表了许
多研究侯孝贤的英文论著。英文世界第一个关于侯孝贤的深度资源是一个专门探讨
《悲情城市》的网站,这个网站由叶月瑜与艾贝·马克·诺恩斯(Abe Mark Nornes)
合作运营[34]。这里的关键是他们研究文本与语境能有多深,这对侯孝贤来说是一个
早该存在的项目。当他们分析侯孝贤的风格时,他们总结了各种成见:侯孝贤像任
何亚洲电影人,被想当然地以为吸取了一种含糊的伟大的“东方的文化遗产”。这
种对台湾特性的聚焦在叶月瑜和戴乐为(Darrell Davies)合著的新的突破性著作
《台湾电影导演:一座宝岛》(Taiwan Film Directors: A Treasure
Island)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展。比如说,在侯孝贤早期生涯中,他从一个商业
导演转型为备受电影节追捧的导演,书中描绘了这种转变如何反映了台湾文化脱离
与大陆联系的巨大转型[35]。其他学者也已采用了更鲜明的观点。裴开瑞(Chris
Berry)和玛丽·法夸尔(Mary Farquhar)写道,侯孝贤在《悲情城市》中显现的
历史意识与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直接指导下拍摄的大多数历史片中官方许可的历史编
纂格格不入,是一种次“历史学”,他们论述了这种历史意识是如何完全的不同。
然而他们并不简单描述早于现代国家的某些文化中的差异,而是探索另一种“现代
性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36]。同时,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在他的
近作《聚光灯下》(Figures Traced in Light)中,将侯孝贤纯粹的长镜头风格置于一个基于场面调度的大传统中[37]。波德维尔对侯孝贤的研究就像他早期对日本
导演小津安二郎(Yasujiro Ozu)(IV)的研究一样,他论述了总括性的文化解释通
常是非常肤浅的,它们无法解释我们面前的现象的复杂性。再者,争论焦点不是整
体文化,而是侯孝贤的独特成就以及如何通过特定的方式达到这些成就。中国文
化,主要是传统文化,被发现在解释力方面是不足的。事实证明,这个故事——这
个问题——比探讨文化要有意思多了。
这本专著的目的,不仅是提供一个侯孝贤直至今日的创作生涯的概况,而且试
图解释它为什么会以其特有的方式呈现的大量原因。本书假定侯孝贤有某种能动性
——这是一种电影和文化研究中未必会被接受的观点。然而,本书也承认那是一种
高度受限的能动性,侯孝贤所面对的选择范围常常被每个历史时刻的特殊情况所限
制,由意识形态的、工业的和制度的限制所决定,他一直在这种限制下开展创作。
本研究并不仅仅以传统作者论视角来探究侯孝贤如何反抗这种系统,或者说如何克
服环境局限,更重要的是他如何利用这些环境提供给他的独特的机会。本研究不否
定中国文化的影响,而是试图将这种文化融入现代台湾的背景和历史中来加以考
察。本书甚至不否认这种文化在诸多方面与西方大有不同,但是也认为这种“不
同”并不意味着“他者”,就像任何一种人类文化,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文化,同
样处理生命、死亡、家庭与社会的根本性议题。换句话说,中国文化像任何成功的
文化,是一种集体生存的充满韧性的方式。既然台湾在这里如此重要,那么本书主
要依靠中文的台湾资料,因为岛外几乎不理解关于侯孝贤和台湾电影的本土话语。
然而,最重要的是,本书试图表明在侯孝贤的创作生涯中,台湾是多么的不可或
缺。
本书的结构是简单直接和按照时间顺序安排的:每一章阐述侯孝贤创作生涯中
的每一个独特阶段,有时也论述彻底的和出人意料的断裂。第一章题为“侯孝贤和
台湾经验”,着手解释这个总括性的短语为什么对理解侯孝贤及其电影是关键。当
讨论到1982年,此时在参与台湾新电影之前,侯孝贤导演了他的第三部商业故事
片,本章也概览性回顾了1949年台湾成为国民党最后的和长期的基地之后的发展历
程,继而追溯探讨了几百年来有关台湾(包括中国)的历史争论。(日本殖民统治
时代和紧接的战后时代在第三章中有充分解说。)记住这个大背景,本章还将探讨台湾电影如何与所有这些宏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缠绕在一起。所有这些不但
将为侯孝贤参与台湾新电影后自己精挑细选的主题,也将为他的美学选择,提供揭
示性的背景。
第二章回顾台湾在1980年代发生的戏剧性变化,论述为什么台湾新电影的崛起
不是一个巧合,侯孝贤个人上升至这场运动的巅峰也不是一个巧合。本章介绍了侯
孝贤成长的合作伙伴(包括他的编剧朱天文,她介绍他阅读沈从文的作品)的一
切,他们给他提供了无可估量的帮助,也介绍了他对其他人的帮助,还讲述了他成
功跨越一个总是危机重重的本土电影工业的政治和经济雷区,最后还讲到他通过出
人意料地征服国际电影节领域来克服那种压抑的环境。本章同时概述了他以《儿子
的大玩偶》(1983)为始、以《尼罗河女儿》(1987)为终的新电影作品。《尼罗
河女儿》是部有缺陷的电影,在新电影运动正式结束后不久问世,但是它也为侯孝
贤的下两部突破性作品做好了准备。
第三章在某种意义上论述了侯孝贤创作生涯中的一个“巅峰”,因为主要聚焦
于他的下两部电影《悲情城市》和《戏梦人生》(1993),它们可被认为是侯孝贤
最伟大的杰作。然而,首先,这两部电影提供了一些关键的历史背景,因为它们处
理了台湾历史上两个最关键的时代:日本殖民统治时期(1895-1945)和随后的光
复,它们共同创造了今日台湾的难题。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国民党对台湾
变化无常的统治史上最黑暗的污点。本章还将分析涉及这一著名事件的《悲情城
市》如何成为台湾历史上的文化事件,其影响远远超出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本章还特别关注这部电影本身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它的持续的文化影响。然后
解释相对来说《戏梦人生》却为何几乎没有得到关注,虽然这部作品可能在美学和
历史意识方面都超越了前作。本章最后探讨这两部历史杰作是否代表了一种独特的
历史,它不像任何其他的电影或其他方面的历史,本章以这个问题作结。
第四章涵盖了侯孝贤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他的作品在几个方
面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本章起始于《好男好女》(1995)怎样和为什么代表了侯孝
贤创作生涯中的一个根本性转变,以及下一部影片《南国再见,南国》(1996)怎
样强化了这个转变。不过本章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他1998年的作品《海上花》上,这
是一部视觉密度与复杂性可与沟口健二作品相媲美的影片。而且,因为这部作品是侯孝贤首部场景不在台湾的电影,也因为它的故事发生于19世纪晚期的上海,完全
中国的议题以及侯孝贤的电影如何处理它,就摆在了面前。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
现在变成了,侯孝贤自己的电影风格是否在某种意义上非常“中国化”, 就像很多
人所认为的然而本研究所质疑的那样。
结论部分始于对侯孝贤从《千禧曼波》(2001)到《红气球之旅》(2007)创
作的简短综述,以及这些作品如何加剧了侯孝贤自1995年以来的事业中的无法捉摸
的转变。本章也将尝试把侯孝贤的整体创作生涯放入一个更大的、全球的背景中。
最后的论点是,侯孝贤正如他所变化的那样不可捉摸,但他作为世界上伟大的电影
大师,仍然应该在电影史上获得一席之地,这主要是因为他有幸在一个特定的历史
年代生活在台湾,也因为他在亚洲创造了一种新的电影传统,现在整个亚洲地区有
多个电影人在践行这一传统。
在这里最后需要强调一个词汇,那就是这个问题的独特性。接下来的内容将证
明侯孝贤的电影是独特的,因为他发现他所处的环境是独特的,对任何一个与众不
同的导演来说这点都是成立的。也许这里根本的教训是任何导演的本土因素,不管
他们最终获得了多大的全球性成功。每个导演都是从某处起步;没有导演刚起步就
可以敲开电影节的大门,然后说他或她仅凭一张白纸就可以进入。至于侯孝贤,有
人似乎对他来自台湾困惑不解,但是本研究的目的正是为了解决这个特别的困惑,正是为了彻底地说明,当我们仔细查看最近三十多年来的台湾本身,最重要的是台
湾电影和整个台湾社会走过的旋绕的、连锁的道路时,侯孝贤的创作生涯所经历的
迂回曲折的道路看起来就不奇怪了。这个故事不是一个难解之谜,而是变成了一个
不同历史时刻适时共生的舞蹈,变成了一个充斥着特定的地理政治和环境因素——
它们中的许多纯粹是台湾的——的故事。这最终是一个台湾的故事,一个应该比以
前更严肃对待的故事。
注释
[1]Godfrey Cheshire, “Time Span: The Cinema of Hou Hsiao-hsien,”
Film Comment, vol. 29, no. 6 (NovemberDecember, 1993): 56–62.
[2]Jean-Michel Frodon, “On a Mango Tree in Feng-shan, Perceiving theTime and Space around Him,” in Hou Hsiao-hsien侯孝贤(Chinese Edition of
French Original by Cahiers du Cinema)(Taipei: Chinese Film Archive,2000): 22–25.
[3]Jacques Pimpaneau, “The Light of Motion Pictures,” in
Cahiers(Chinese Edition): 65–68.
[4]James Udden, “Hou Hsiao-hsien and the Poetics of History,”
Cinemascope, 3 (Spring, 2000): 51.
[5]Ni Zhen, “Classical Chinese Painting and Cinematographic
Signification,” Douglas Wilkerson, trans., in Cinematic Landscapes:
Observations on the Visual Arts and Cinema of China and Japan, Linda
Ehrlich, David Desser, ed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75.
[6]Li Tuo, “Narratives of History in the Cinematography of Hou
Xiaoxian,” Positions, 1: 3 (1993): 805–14.
[7]Meng Hongfeng孟洪峰, “A Discussion of Hou Hsiao-hsien's Style,”
in Passionate Detachment: Films of Hou Hsiao-hsien戏恋人生: 侯孝贤电影研
究,Lin Wenchi林文淇,Shen Xiaoyin 沈晓茵,Li Zhenya李振亚,eds.
(Taipei: Maitian, 2000): 48–49.
[8]Jay Hoberman, “The Edge of the World,” Village Voice(July 14,1987): 62.
[9]Peggy Chiao 焦雄屏,“When Will Taiwan Keep Step with Taiwanese
Cinema?” Commonwealth Magazine天下杂志 (January 1, 2000): 123.
[10]“First Annual ‘Village Voice’ Film Critics Poll,” Village
Voice(January 4, 2000): 41.[11]Yeh Yueh-yu,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Hou Hsiao-hsien's
Films,”Post Script, vol. 20, nos. 2 3 (WinterSpring Summer,2001): 68.
[12]这种批评范式的最佳总结仍是罗伊·阿姆斯(Roy Armes)的《第三世界电
影制作与西方》(Third World Film Making and the West,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13]Yeh Yueh-yu叶月瑜,“Taiwanese New Cinema: Nativism's
‘Other’,” Chung-wai Literary Monthly中外文学,27: 8 (January, 1999):
60.
[14]Wilt Idema and Lloyd Haft, A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85.
[15]艾德玛和哈夫特认为“玄学”是一个误导性术语,最好是称呼其为伴随
《庄子》和《易经》的普遍可获得出现的儒家思想的再造。相反,亚瑟·F·赖特在
他的《中国历史中的佛教》中说,随着汉朝灭亡,儒家思想“完全名誉扫地”,从
公元250年开始道教是统治性哲学。参见Wright,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New York: Atheneum,1969): 17–24。无论怎样,为了重申它的意识形
态霸权,儒家不得不彻底调整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这点是很清楚的。
[16]Wright, 67–70.
[17]John Fairbank, Edwin Reischauer and Albert Craig,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8): 149–50.
[18]亚瑟·F·赖特认为,为了这种系统生效,这些学者不只是从孔子作品中发
展出一套广泛的关系——人类和其他事物——系统,形成一个赖以统治的包罗万象
的系统,是势在必行的。
[19]Craig Clunas, Art in China(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136.[20]Patricia Ebrey,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1996): 89.
[21]Ibid., 88.
[22]Clunas, 54–56.
[23]Li Zehou, The Path of Beauty: A Study of Chinese Aesthetics(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54.
[24]同上书,第142页。然而李白遵循的是中国艺术中一种非常长久的传统:对
酒的喜好,甚至根据杜甫的说法,他是“酒中仙”(参见上书,第141页)。应该注
意,侯孝贤也是这种传统的行家里手,尽管他常常添加卡拉OK歌唱的现代感。
[25]Ye Xie, “The Origins of Poetry,” in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Stephen Owen,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511.
[26]Hsieh Ho, in Early Chinese Texts on Painting, Susan Bush, Hsio-
yen Shih, e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30.
[27]Su Shih, in ibid., 224.
[28]Craig Clunas, 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13–16.
[29]Peggy Chiao 焦雄屏,in introduction to Passionate Detachment, 26;
“Great Changes in a Vast Ocean: Neither Tragedy nor Joy,” Performing
Arts Journal, vol. 17, no. 5051 (MaySeptember, 1995): 52.
[30]Peggy Chiao, interview by author, March 10, 2002, Middleton,Wisconsin.
[31]Chu Tian-wen朱天文,interview by author, June 2, 2001, SogoDepartment Store Coffee Shop, Taipei, Taiwan.
[32]Hou Hsiao-hsien, HHH: A Portrait of Hou Hsiao-Hsien, prod. by
Peggy Chiao and Hsu Hsiao-ming, dir. by Olivier Assayas, 96 min., Arc
Light Films, 1997.
[33]Hou Hsiao-hsien 侯孝贤,interview by author, June 20; 2001,Sinomovie Company Office, Taipei, Taiwan.
[34]Abe Mark Nornes and Yeh Yueh-yu, A City of Sadness, website at
http:cinemaspace.berkeley.eduPapersCityOfSadness.
[35]Yeh Yueh-yu and Darrell Davis, Taiwan Film Directors: A Treasure
Island(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3–76.
[36]Chris Berry and Mary Farquhar, China on Scree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29–38.
[37]David Bordwell, Figures Traced in Light: On Cinematic
Staging(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186–237.
(I)拉迪亚德·吉卜林(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1907年获诺贝尔文
学奖。本书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注,所有尾注均为作者注(统一附在各章末尾),以
下不再指出。
(II)拉迪亚德·吉卜林的一首诗名,指西方有责任治理落后的东方,因被解读
为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而备受争议。
(III)阿萨亚斯(1955- ),法国影评人与导演,作品有《清洁》、《夏日时
光》以及纪录片《侯孝贤画像》等。
(IV)小津安二郎(1903-1963),日本电影大师,代表作有《东京物语》、《晚
春》、《秋刀鱼之味》等。第一章 侯孝贤与台湾经验台湾是一个独特的地方,产生了独特的电影,侯孝贤及其作品就是它最无法磨
灭的产物。我们应该提防任何笼统的用以解释这种地缘政治和电影特性的措辞。不
过,这里有一个相近的概念:“台湾经验”。这个术语的起源不可考,但很显然得
到广泛使用是在1980年代,并且在今天的台湾仍然是个习惯的用法。有一些书籍致
力于解释这个术语[1]。陈儒修关于台湾新电影的重要研究有一个揭示性的标题:
《台湾新电影的历史文化经验》[2]。对不知情的人来说,把“历史”、“文
化”和“经验”相提并论可能会感到奇怪。然而,在台湾,“经验”这个词最重
要;在台湾,它是独一无二的经验,以原始的、不定形的然而也不可否认的人类形
态,取代了所有锻造一个固定的地区和种族身份的努力。
在台湾,流动的共同的经验压倒所有固定的经验,这不是理性思维的产物,而
是台湾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事实。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
为,资本主义、印刷技术和教育体制一起创造了一种“民族”凝聚感,因为人们现
在会认同他们至少可以想象的另外的大群体,民族主义由此变得可能[3]。而且大多
数人或多或少相信那些“想象的共同体”的本体论,它们构成了他们分享民族身份
感的基础。然而,在台湾,大多数人并不这样。台湾不断发展变化的环境迫使它的
居民高度警惕任何事物的想象性,任何标签都似乎是幻影。数十年来他们被不断地
重复告知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们是中国人。今天他们更有可能被某些人
告知他们根本不是中国人,而是“台湾人”。这些争论要么基于文化要么基于历
史。然而,鲍梅立(Melissa Brown)在她的台湾身份问题调查研究中发现,这些
并不能从根本上统一一个族群或民族。“不如说,身份以共同的社会经验,包括经
济和政治经验为基础,得以形成并巩固。”[4]作为这些经验的结果,民意调查结果
始终显示,台湾的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致力于避免所有的解决方案,甚至标签——
称他们为中国人和台湾人,而倾向于既不统也不“独”[5]。台湾人摇摆不定,作为
一个整体固执地寻求一种中间状态——只要有可能就永远维持现状——好像他们永
远把牌紧紧攥在胸前,永远不把牌亮给世人看,永远不会被别人操纵。这种共同的
矛盾是一种不断发展的艺术,台湾这座岛屿就是以之为基础。这该归咎于谁?也许和每一个人有关:统治台湾地区超过半个世纪的国民党,明朝和清朝,欧洲人,日本人,美国人,当然还有大陆的共产党,更不用说目前要
求“独立”的本土政客。所有这些因素使得台湾经验本身成为一个变化无常的老
师。台湾无法靠自己生存,这是一个实际上处于夹缝中的岛屿,常常受制于历史偏
见,比如台湾只不过是一个战略的、地理政治的工具,只不过是一些据说更强大的
东西的附属物。冷战实际上创造了一座冰宫,今日的台湾不知何故还没有“融
化”到如它常被预测的那样被遗忘。相反,尽管困难重重,它幸存了下来,甚至更
加繁荣。
侯孝贤在1980年代声誉鹊起不是巧合。他将这种宏大形势转化为不可磨灭的电
影表达方式,它们捕捉、传达,甚至体现那种共同经验难以捉摸的抓不住的外形
——没有固定的身份,没有明晰的修辞,没有确切的东西抚慰人心。起初,侯孝贤
专注于聚焦1950年代后的台湾经验,因为他直接体验了这段历史。然而,那种奇特
的形势的源头得追溯到几百年前。不过,侯孝贤后来的创作与维特根斯坦式的历史
选择和忽视的艺术相违背:他的历史电影不是聚焦于关于台湾的标准的历史说法,而是主要聚焦于那些让这些说法最复杂化的年代。我们将简要地探讨这些“说
法”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台湾形成今天的样子。1949年前的历史“说法”
最早到达台湾的大陆人通常是周期性地、非法地赴台,数量也少。他们的人数
远远少于当时的土著人口。由于受到17世纪荷兰人在岛上建起殖民地的刺激,更多
的大陆人来到台湾永久定居[6]。和20世纪局势惊人相似的是,很快大陆发生的政治
事件波及了台湾。在明朝败亡的时候,明朝将军郑成功(人称“国姓爷”)远道而
来并且赶跑了荷兰人,这一丰功伟绩为其赢得了“台湾之父”的名声。然而郑成功
的眼睛只盯着返归大陆,这一目标也被他的继承人所延续。后来郑成功的儿子(V)抵
抗清王朝失败,台湾于1684年被清政府纳入版图[7]。
此后最后的中国王朝统治了台湾两百余年。在那些年移民台湾也仍然是非法的
或者说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且看上去好像最腐败无能的官员被派驻那里。每个官员
都短时间服务,任期三年,没人把台湾当作自己的家。在清朝统治的两百一十一年
里,当地人——无论大陆移民还是土著居民——抗议清王朝多达七十三次,另外诉
诸暴力的对抗不下于六十次[8]。台湾成为一个不法之徒的地方,吸引来自大陆的拓
荒先锋,他们渴望逃离大陆的环境,主要是为了逃离福建省周边蔓延的穷困和贫瘠
的土地。这些有独立意识的移民反而被那些留在大陆的人们瞧不起。台湾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在整体上已与大陆背道而驰。清政府没有做任何事来缓和这
种局面;事实上,他们的政策只是拓宽了裂缝[9]。
到了19世纪,当清朝统治者发现外国人图谋台湾,他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这个
岛。首先,北京政府取消了所有的移民禁令[10]。1885年,在抗击法国侵略后,清
政府决定在台湾建省,而此前台湾仅仅只是福建省的一部分。台湾第一次有了一个
能干的有远见的治理者,他叫刘铭传,他不仅巩固统治,而且开始建造包括铁路和
电力在内的公共基础设施。然而,1891年刘铭传离开,他的所有现代化计划都莫名
其妙地被废止了。台湾再次被严重忽视[11]。
1895年,清政府输掉了与日本的甲午战争。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将台湾与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1945年,台湾光复。然而,在非常短暂的有序统治之后——事实上在几个月之
后——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却导致事与愿违:一个新的和更持久的台湾身份深深地烙
印在血泊中。这一切随着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爆发达到高潮,我们将在第三章
详细讨论。现在已可说,随着导致数千人死亡的大暴行发生,新的统治者的所作所
为比其日本前任更像殖民者。国民党有失体统的、残酷的行径在大陆被广泛报道。
很快“二二八事件”成为全中国反抗国民党的一个焦点,加速了它仅仅两年后在大
陆的最终失败[1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事件实际上在台湾创造了一个自制的敌
意角落,国民党1949年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将发现这点。
所有这些变幻莫测的历史转折之后,“台湾人”这个术语到底意味着什么?这
要看情况而定。“台湾”和“台湾人”已经变成了反映一定的地理政治现实的便利
术语,但那些曾经统治这个岛屿的人或那些横跨海峡想要有朝一日统治它的人并不
乐意接受。“中国人”和“台湾人”含混的语义学界限,被更进一步的、本土的复
杂情况搞乱了,它很难用英语来澄清。自从1940年代末起,本省人和外省人制造了
分化。外省人是指祖先在大陆但是好几代在台湾生活的人,他们几百年前就扎根在
台湾。由于历史原因,这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包括不可忽视的客家人,他们占
少数,有自己的方言和文化,常常和占多数的鹤佬人发生冲突。鹤佬人主要由福建
移民构成,他们讲台湾方言,近似直接跨越海峡的福建方言。与之对比的是,外省
人是最近的到来者,他们中的一部分是1945年以后来到这里,大部分人是在1949年
国民党把大陆输给共产党后来到这里。大体上来说,本省人今天构成了岛上人口的
百分之八十五,而来自大陆的外省人接近百分之十四。现在人口中剩余的百分之一
大多数是原住民,而且数量日渐减少。
无论如何,1949年后,岛上的外省人和本省人都被切断了和中国大陆的联系,带着从来没有愈合的、暗中化脓的历史创伤,被迫生活在一起。在最初试图为他们
的行为辩护后,在之后接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官方简单地否认1947年的血案曾经发
生。具有尖锐讽刺意味的是,当台湾变成国民党最后的堡垒,国民党当局如果要继
续生存下去,不得不根本调整它的姿态。“二二八事件”后国民党缺乏真正的合法
性,它是国民党最终从事改革的关键要素,它导致了一个复杂多变的档案,就像对先前日本统治的记录。台湾的本省人是改变的首批接受者,改变的后来受益人,也
是改变的最终主人,改变首先在经济阵线显现成果,最终在政治和文化阵线结出果
实。这些创造了我们今天认识的台湾:能量充沛的经济,世界上最民主的地区之
一,还有富有活力的文化,包括一个如今拥有世界声望的非同凡响的电影导演。侯孝贤与战后台湾经验
侯孝贤真正参与这种局势是在1949年。西方人和大陆人对侯孝贤都有错误的看
法,但台湾人也有自己的误解。直到近年,最普遍的本地误解是侯孝贤是一个本省
人。他已经树立了这样一种公众形象:他讲流利的台湾话,讲带浓厚台湾口音
的“国语”。而且,他的电影似乎完全表达身为台湾人——其中的大多数是本省人
——意味着什么。因此当发现侯孝贤是一个1947年出生在大陆的外省人,当他只有
两岁的时候才来到台湾时,很多台湾人很吃惊。侯孝贤的家庭是客家人,客家人是
中国一种特殊的四处迁徙的少数族群,在台湾,1895年前经常受到占多数的其他汉
人的骚扰[13]。不过,侯孝贤在台湾南部长大,主要在本省人中间。在他年少的时
候,父亲去世了,这使得他不必遵循那个年代孩子的行为规范,而可以在外四处游
荡。这些随心所欲的闲荡促使他在年轻的时候每天都讲台湾话,这被证明具有决定
性的影响。
因此,侯孝贤人生的多数时候都将认同本省人,虽然他和那个族群其实没什么
关系。这表明他的实际经验,不是血统,也不是任何固有的文化意识,在多大程度
上决定了他的身份和世界观。同时身为客家人和外省人,只是增加了侯孝贤的敏
感。朱天文,著名作家和侯孝贤的编剧,解释了为什么她那一代人——父母至少有
一方来自大陆,然而成长在台湾——会成为文化领域台湾经验的重要支持者。在台
湾他们只是听说大陆,可是她后来去了那里发现它是想象的。然而,他们亲身体验
的在他们眼前的是台湾,一个完全不同于关于大陆的壁炉边故事的世界。数代台湾
人把身边发生的一切视作理所当然,而那种流散的心理焦虑对他们来说不存在,只
证明是肥沃的艺术土壤[14]。
对于像朱天文这样的作家和像侯孝贤这样的电影人来说,台湾实际上成为一个
无底的题材库。但是侯孝贤见证和经历了什么?简而言之,变化:政治的、经济
的、文化的和电影的变化。当侯孝贤自身在1980年代成为一个导演的时候,所有这
些变化要么正在发生,要么将要发生。侯孝贤与战后政治经验
侯孝贤的父亲是一个低级官僚,来到台湾后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他过早地离
世。缺少证据表明侯孝贤和他的家庭直接受到战后政治的影响。不过,政治在战后
的台湾无处不在,潜伏在日常生活的背景中。也许并不奇怪,这种情形在侯孝贤电
影中同样真实存在,至少那些电影涉及了政治:《童年往事》(1985)、《悲情城
市》和《好男好女》。侯孝贤常常因为他的政治矛盾和逃避而受到批评。甚至很少
有人能够指出侯孝贤在台湾真实的政治光谱中的位置,它不是“右对左”(区别在
台湾意义不大),而是“独立对统一”。大多数台湾百姓对政治和政客都没什么好
感,这是国民党五十年压迫性统治的一个直接结果。大多数本省人甚至有一个共同
的说法:“卷入政治就像吃狗屎。”[15]
尽管国民党当局的基本意识形态前提是作为“中华民国”的政府,声称代表所
有中国人,但是再多的宣传也无法掩盖它仅仅统治台湾和其他一些小岛屿的事实。
事后来看,国民党不可能永远维持这种局面,这是足够清楚的。另一方面,也存在
一些有利于国民党的历史机遇。当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残兵败将1949年撤退到台湾
时,看上去似乎日暮途穷。这个党已经失去了太多的公信力,以致美国也切断了对
其支援。大陆共产党已经草拟了计划,准备很快解放台湾,一劳永逸地消灭国民
党。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所有这些都改变了。朝鲜战争打响后两天,美国派
出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朝鲜冲突同时终结了共产党制定的进攻这个岛屿的计
划[16]。台湾再次经历又一个戏剧性改变:它成为国民党领导下的冷战前沿的堡垒。
紧张的冷战气氛弥漫了1950年代,1958年8月随着大陆在金门与马祖上空的所
谓“炮战”而达到高潮,两地均在福建省的视线之内。蒋介石希望美国直接参与对
大陆方面的攻击,但美国人仅仅间接提供帮助,甚至曾经试图劝说国民党放弃对这
两个岛屿的控制,不过徒劳无功。最终,这两个互不信任的盟友在10月达成了一个
折中方案:台湾不再进攻大陆,以此作为对金门和马祖持续控制的交换。大陆的共
产党表示抗议,但有些人推断毛泽东私下同意国民党控制那两个岛屿。因为它们距离大陆很近,这有助于缓冲任何“台独”的企图[17]。结果就是维持到今天的僵局:
金门和马祖仍然在台湾而非大陆的控制之下。
紧张的、恐慌的冷战气氛非常便于蒋介石寻求控制整个岛屿的绝对权力。国民
党的较小的、地方的部门都是较大的部门不可摆脱的部分,而较大的部门直接通向
由蒋介石亲自控制的中央委员会[18]。这种制度重组与现行法规相吻合,比如1948
年颁行的“动员戡乱法”和“戒严令”,后者于1949年6月(VI)宣布,直到1987年才
被废除。前者极大地增强了蒋介石的“总统”权力,允许他消灭任何形式的异见。
那个1948年的法令,和“戒严令”一起,形成了“白色恐怖”的基础。事实上,台
湾变成了一个以“国防会议”(后来改称“国家安全会议”)为中心的警察军
人“地区”,通过“国防会议”这个机构,蒋介石和他的儿子蒋经国控制了所有的
至关重要的信息和情报搜集[19]。
冷战充当了把世人的注意力从“台独”的可能性转移开来的现成的烟幕。事实
上,国民党的很多政策宣称的意图是对抗共产主义,然而实际的目标包括那些主
张“独立”以及对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兴趣的群体。不过,台湾本土针对国民党的反
抗可以追溯至1947年,特别是在台湾流亡者中间。在台湾本身内部,反抗发展得相
对缓慢。尽管如此,即便在1950年代也有人开始质疑“中华民国”的前提。第一个
标志是《****》杂志,它最初支持国民党,最终却激烈批判国民党,结果被停
刊[20]。当十年过去,在1970年代,第二波反对浪潮兴起并且势头增大。原因非常
清楚:十年消逝了,合法性,本已是让国民党头疼的麻烦,结果却变得更加糟糕。
1972年国民党当局一失去联合国席位,就更加无法遏制反抗。而且,蒋介石自己死
于1975年,那时有效控制权已经移交给了蒋经国。
从表面看,这个儿子似乎和他的父亲是政治同类。1972年之前,蒋经国已经是
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关键角色,事实上他通过大量的关键职位来为他的父亲掌管台
湾,这些职位大多数都在情报搜集部门和军队中。他于1970年代跃居政治一线,也
仍然以有时反复无常的方式利用集权的制度。但是,蒋经国从来没有分享他父
亲“收复”大陆的痴心妄想,这是一个关键的不同。相反,他着重在台湾推行实用
的政策,启动了促进台湾现代化的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最重要的是,蒋经国启动了“本土化”进程,允许本地台湾人进入管理层,也允许他们加入国民党[21]。
从长远来看,这对台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部分原因是它意味着1988年对蒋经国接
班人李登辉的包容,而李是本省人。
在1970年代的新的政治气候下,产生了“党外运动”。这场运动起初包括非国
民党籍的候选人,他们参与地方选举竞逐,尽管国民党的作弊普遍存在,但是他们
有时也会获胜。1978年12月美国撤回对“中华民国”的承认(VII),一年后在南部台
湾运动就达到了最高点。所谓的“美丽岛事件”,有时也被称作“高雄事件”,是
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后首起公开对抗国民党的抗议活动。“没有党名的政
党”的领导者们在1979年12月10日于高雄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人权示威,那天是国
际人权日。大批高雄警察出动,以武力威胁民众,人们没有屈服,甚至冲破了警方
的防线。看到这一切,一个目击者说:“历史有了一个新的开始。”[22]它开启了
1980年代的历史闸门。
侯孝贤完全没有掺和这些事。1970年代,侯孝贤正在台湾电影工业中努力工作
缓慢地往上爬,在此过程中,没有证据表明他站在任何政治一方。那个时期看不出
来他会处理他最终卷入的任务、议题和争论。但是在台湾事情总在发生变化——甚
至在一夜之间发生。侯孝贤与战后经济经验
在海外,“经济奇迹”毫无疑问是最知名的台湾经验,侯孝贤的电影偶尔也间
接提及它。甚至侯孝贤自身的经历也部分地反映了这点。电影似乎是一种错失了经
济奇迹的工业。不过,在冒险从事他自己实质上的作坊式电影制作之前,侯孝贤在
商业电影工业干了超过十年。侯孝贤现在运作一项小范围的事业,主要为出口创造
产品,尽管对他来说那是一个利基市场,而不是一个大规模市场。这在台湾很有代
表性。
人们经常忽视经济奇迹与“二二八事件”之间有怎样的直接联系。1947年的反
抗和随后的血案,主要根源就是经济。只要有可能,国民党就竭力维持它在台湾的
绝对权力,当环境所迫,它也只是缓慢地不情愿地交出权力。但是在经济领域,国
民党几乎从一开始就交出了权力,因为它真的别无选择。对台湾来说这是第二次现
代化,这次现代化远远超过日本人所做的。对国民党来说,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现代
化。他们再也没有拘囿于饱受战争摧残的大陆的、农业的思维。相反,他们很快学
会依靠国际贸易。
近几十年来台湾经济增速惊人,这使得人们容易遗忘1950年代对台湾经济的预
测是贫困的,特别是突然从大陆涌入一百五十万人口。台湾有一个不利的人均占地
比例、极少的资本资源和一个名誉扫地的领导阶层,所有这些导致了台湾在外国经
济学家眼中的“经济瘫痪”的状况[23]。然而,尽管从如此糟糕的起点起步,台湾却
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发展纪录。从1953年到1964年,工业部门每年以百分之十
二点二的增速发展,在那个时期台湾从美国获得了充足的支援。美国援助终止后,台湾经济继续急速前冲。从1965年到1975年,工业部门的年增速高达百分之十六点
一[24]。从1963年到1980年,台湾经济整体,包括相对来说停滞不前的农业部门在
内,每年平均以百分之十的增速发展。等到经济完全发展成熟,从1981年到1995
年,台湾仍然保持了年均百分之七点五的增速[25]。这种发展形势中最重要的是老百
姓在多大程度上受益。1950年台湾人均收入和大陆人均收入一样。到了1980年代,台湾人均收入是大陆人均收入的二十倍[26]。
国民党推行的几项特殊政策也促进了这一巨大发展。彻底的土地改革将土地资
本转变为商业资本,为经济发展打好了基础。岛上的本地土地拥有者没有反抗,因
为“二二八事件”的教训记忆犹新。但是,与此同时,国民党在主要的官方产业中
给予这些失去土地的地主股份,将他们变为资本家,从而有效地结束了封建制度
[27]。台湾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关键是私有化[28]。总的来说,当局控制公有产业,而
允许私有产业兴旺发展。到1959年,私人运营的工业企业比例已经超过了官方运营
的企业[29]。1954年私营企业的工业生产仅占百分之四十三,到了1972年比例跃升
至百分之八十,到了1980年代中期更达到百分之九十,这使得以任何标准来考量台
湾,它都是世界上私有化程度最高的经济实体之一[30]。台湾经济高度分散化,由中
小型企业占支配地位,其分散程度之高在世界上绝无仅有。1981年,百分之四十五
的制造业由中小型企业完成。在台湾经济最成功与最有活力的部分——出口制造业
——中,这一比例跃升至百分之六十八[31]。这个政策的主要受益人是本省人,而
不是那些新近来自大陆的“精英”。尽管制定了严厉的教育、政治和文化政策,但
是外省人没有像1947年所做的那样来阻挠那个对立的多数族群,他们既没有胆量也
没有能力。
国民党当局也引导经济向出口发展。台湾是严重的贸易主导型经济:到1980年
代,进出口额占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五,当你意识到在日本这一数据仅是百分之
三十,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吃惊的数字[32]。回到1950年代,国民党当局利
用了很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通用的所谓“进口替代政策”。这主要指通过贸易
保护措施集中发展岛内市场。这项政策在台湾获得了非比寻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这是一个主要局限于生产资料工业的临时措施。而在消费品、半成品和制造
业领域,总体来说几乎所有的发展都源自满足岛内需求,无一源自进口替代。与之
相对的是,在菲律宾,上述四个领域接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成长归因于进口替
代,仅仅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用于满足国内需求。在菲律宾,这种状况长期存在于脆
弱的工业中[33]。很快,国民党当局就通过鼓励出口超过进口的方式,引导台湾朝向
外向型经济发展。1959年,他们废除了双重汇率制,实行货币贬值,降低关税和制
定法律、规则和税率,所有这些都鼓励出口[34]。也许国民党当局作出的其他决定都没有如此显著地提升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
总而言之,虽然台湾本省人数十年来都否认获得了政治好处,但他们已经获得
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即便是在冷战的高峰期。本省人尽最大可能利用这一经济回旋
余地,甚至到了蔑视通常拙劣地强迫执行的法律界限的地步。结果是,台湾更像是
在地上运转的地下经济实体。国民党当局维持对银行业的严格控制,对一般台湾人
来说贷款是困难的。为了逃避这点,台湾人成立了成千上万的专门的民间信用社团
(标会),来筹集他们自己的资金。这是一种明显具有风险性的投机,如果任何组
织的所有成员都值得信赖的话,它可以赚得盆满钵满[35]。许多企业公开地无证经
营,大多数保存两本账簿,一本是给自己看的,另一个缩减的版本是为税务员准备
的。一般来说人们倾向于向当局瞒报收入,这导致真实的人均收入很难统计。到
1980年代,台湾富得遍地流油,这主要是辛勤工作和无视官方阻挠的结果。国民党
当局注意到总体的民众不服从,明白它的唯一选择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与此
同时,当这个经济奇迹已成既定事实,侯孝贤和1980年代新电影的其他成员,开始
探讨所有这一切对生活在这个岛屿上的人们真正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答案显露出重
重矛盾。侯孝贤与战后文化的缓慢解冻
如果说侯孝贤与战后政治和经济的联系更间接的话,那么对战后文化来说就不
是这么回事了,在战后文化环境中,侯孝贤成了一个中心人物。提及台湾,大多数
人脑海中第一个想到的是经济,接下来可能是政治。相反,台湾的文化通常是人们
事后才回想起来的东西,即使那样,它还常常被遗忘,要么被当作不存在,要么只
不过被当作中国文化的派生物。然而,对最近二十年了解国际电影节情形的人们来
说,情况恰是反过来的:当他们想起台湾,他们很可能首先想到侯孝贤,另外还有
杨德昌和蔡明亮等人。他们常常漏掉的是作为文化现象的侯孝贤与台湾这些大的政
治和经济力量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的密不可分。
自从1949年以来,台湾文化一直处在上述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夹缝之间。台湾的
文化起初是国民党当局严密控制下的一个向心性力量,只是到后来才变成了一个离
心力量,现在扮演着当局做不到的非官方的“外交”角色。除此之外,台湾形势的
不稳定特性使得台湾文化更加富有活力和创造性。侯不是这种现象的唯一证据,但
是最好的之一。
而且,这种文化活力产生于可以想象的一些最恶劣的状况。在1949年到台湾的
流亡者中,有一些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大陆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来到台湾不是因为害
怕共产党,也不是因为效忠国民党。这群人鱼龙混杂,他们为局势所迫,只能在这
个岛上生存并在此抚养自己的孩子,也只能慢慢意识到再也回不去了。然而,很长
一段时间里,国民党严格限制他们可能表达的关于这个陌生的新世界的看法。借助
对文化、教育和媒体的垄断,国民党致力于将中国身份强加在当地人身上,而且严
禁一切将台湾特殊化的东西[36]。与此同时流行一种看法,国民党失去大陆是因为宣
传失败,而不是政策失败。在台湾,国民党不想重蹈覆辙。国民党将文化视作决定
生死的关键要素。
国民党当局垄断控制了所有的文化领域,在年轻人教育问题上尤其严厉。“三
民主义”是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渗透于大学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一个主要的组织是所谓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成立于1952年。这个组织开展针对年轻人的
政治活动和军事训练[37]。它的用意在于紧盯着不过一百英里外的“共匪”,同时也
是一个大野心的一部分,旨在消灭任何将台湾特殊化的东西。这个隐性策略的第一
线还有其他的教育政策:1951年起,所有的课程都必须用“国语”教学,本地的台
湾孩子要是在教室里说了一个台湾方言的字眼,都要受到严厉的处罚[38]。这样的措
施一直施行到1970年代。(侯孝贤自己能讲一口流利的台湾方言,不是习自课堂,而是习自市井。)
当局也直接指导文学和电影创作。1950年,“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包括十个
成员组织(VIII),其中一个用来管理电影。这导致了充斥着“反共”主题,同时颂扬
孙中山“三民主义”优越性的宣传艺术的泛滥[39]。1954年当局进一步强化钳制,那时“中国文艺协会”宣布了一项叫作“文化清洁运动”的政策。这场运动声称是
要清除所有的“赤色的毒”(共产主义)、“黑色的罪”(对社会阴暗面的悲观看
法)、“黄色的害”(纵欲、色情)。这三种不受欢迎的“颜色”反过来又构成此
后所有当局审查的清扫基础,1955年这一切由极其重要的“新闻局”接管[40]。
1960年,这个由“新闻局”传承衣钵的最高文化机构,在其成立十周年纪念日,重
申了反对“赤色”、“黑色”和“黄色”的原则[41]。
不过,这是威权主义的(authoritarian)控制,而不是极权主义的
(totalitarian)控制。裂缝开始在不同的文化领域显现,最终也出现在电影领
域。尽管当局控制严厉,在早年却有与台湾相关议题的现实论战,只要论战不是公
开地支持左派思想或者“台独”。论战在“东方”与“西方”、“本土文
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展开。此类论战的一个共同主题是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关
系,多数探讨现代世界中的儒家思想的意义。很多台湾的知识分子都对他们所谓
的“现代新儒学”颇感兴趣。这些知识分子一致认为儒学将不得不改造以适应现代
社会,需要从其他传统,包括佛学和西方哲学中吸取养料。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
牟宗三,他试图在儒学和康德的道德哲学间发现一种联系[42]。然而,其他的许多人
都想象一种截然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它只为全部的传统提供很小的空间。现代儒家
学者发现他们自己与《****》群体和台湾日渐流行的存在主义(大多数是萨特
的思想)格格不入[43]。1980年代之前,台湾真正的文化先锋毫无疑问是文学,我们可以在两个重要运
动的激烈论战中看到其中最优秀的一些代表,这场论战是现代主义者(现代文学)
与所谓的本土主义者(乡土文学)的论战。当论战局限于哲学家和其他学者圈子,它似乎没有偏离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争议。但是一旦论战渗透到文学领域,其他信息
就开始几乎不知不觉地蔓延,包括一个独特的台湾政治光谱的早期建议,如今已公
开地流行于台湾。
它随着1960年代现代文学运动的来临而开始,和那时萨特的兴起流行直接相
关[44]。台湾的现代文学运动脱离了中国历史上先前所有的文学运动。通过探究心理
和哲学议题,他们避开了现代中国文学在20世纪多数时候的基本主题:民族命运。
现代文学派强调艺术性和精雕细琢,抵制任何流行的政治、道德和美学的传统[45]。
相比西方的现代派,台湾的现代文学派保守得多,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描绘儒家
理想的崩溃,抨击当时的流行文化[46]。1960年代这场运动的中心是《文星》杂
志。起初《文星》聚焦于文学和艺术,但是到1960年代早期,在《****》停刊
之后,它加入了传统和西化现代化之间的论战。《文星》的作者旗帜鲜明地站在后
者阵营,尤其是作家李敖。结果是,这本杂志变得越来越容易遭到保守的统治精英
的攻击[47]。
然而,到了1970年代,现代主义者的主要对手不再是保守精英,而是来自另一
场文学运动,它自1960年代起也已在一些作家——乡土主义者——中扎根。随着乡
土主义者的登场,在传统与现代化和或西化之间的分歧变得更加复杂,甚至混乱,因为乡土主义者既反对现代化,也反对保守的统治精英。乡土主义者甚至看穿了现
代主义者和统治精英在台湾一有危机迹象时就都会争先恐后地移民(至少在乡土主
义者眼里如此),从丢掉了联合国席位开始,在70年代有很多人这么干,由此放弃
了岛上的老百姓。乡土主义者也在美学上做出反应:在与现代主义者的西化赫尔墨
斯主义的正面交锋中,乡土主义者搬出一种新的反映成长于台湾的新生代的族群意
识[48]。典型的乡土主义者的美学策略是社会现实主义,而不是美学实验,他们宣称
目标是传达台湾日常生活的细节,还其本来面目[49]。1977年,在一场多家报刊参
与的激烈论战中,以及一次著名的讨论这场文学运动的会议上,运动背后的潜在表达摆上了前台。它的结果,就是今天众所周知的“乡土文学论战”。
乡土主义者始于一种反西方的前提,似乎加入了东方西方的对抗。起初他们质
疑为什么台湾的科学书籍常常使用英文,而不是中文[50]。他们所认知的台湾是寄生
经济制度的牺牲品,这种经济制度导致台湾依附于人,而非独立自主[51],他们的关
注点聚焦于此。一些作家把这种潜在的冲突描述为中国文化和“日本西方商业文
化”之间的矛盾[52]。1970年代在国际舞台上的大量挫折,促使其他人呼吁台湾人
要依靠自己,不要再依靠西方[53]。事实上他们的话里流露出一种焦虑感和毫不掩饰
的紧迫感。一个作家说:“从来没有什么国际道义;我们必须运用一切最实际的手
段,为自身生存而奋斗。”[54]
但是世上不止一种反西方的立场。当时的反对者要么在文学方面要么以反共理
由攻击乡土文学运动,没有一个人能够阐明这场运动的定义。照字面意义翻
译,“native soil”的意思是“乡土”。但是它是指哪一个“乡土”呢?有个作
家提出如下议题:“我们的乡土是肥沃的;增强我们的乡土感;允许我们认可自己
的乡土;以我们的乡土为豪。这会让我们不易被外来事物所引诱,或被外来文化所
污染。”然而,当被询问这里的“乡土”是中国还是台湾,他永远不会给出非此即
彼的回答[55]。事后看来,那是核心问题。后来很多人宣称乡土主义者采用的最终评
判标准是他们的文学在多大程度上显示了“台湾意识”[56]。然而,在那时,乡土主
义者整体上是回避台湾与中国议题的,也许因为这仍然是一个禁忌的话题:有些乡
土主义者支持“大中国”的概念;其他人则含蓄地赞成以台湾代替中国[57]。不同的
人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的立场并不明确,直到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将台湾
与中国的议题搬到台前。1979年后,当文化和政治气候逐渐开放,许多旧的分歧很
快变得无足轻重,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多数分歧也是如此。台湾议题于是占据了文化
的中心。
然而,所有这些论战都是知识分子的论战,不是民众的论战。这些论战之所以
能被允许大规模发生,是因为在这个岛上,它们几乎没有涉足普通百姓的生活。那
么在普通民众身上发生了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最好的方法是看看在台湾
宗教的发展有多流行。1949年后的第一个二十年中,台湾的基督徒数量稳步增加。侯孝贤的父亲死后,他的母亲变成了基督徒,死后也以基督教丧礼下葬,正如我们
在《童年往事》中看到的。在统治阶层中也有大量的基督徒,国民党当局在1960年
代和1970年代引入享有盛誉的福音传播者,并且在地方电视台播出宗教集会[58]。
不过,基督教会在台湾处于政治光谱的两端。台湾最大的新教徒教派——长老会,以反纳粹的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为榜样挑战国民党,基于
此,在“台独”运动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59]。然而,普通民众并不信任政治,与此相应,台湾基督徒的数量早在1965年就已下降[6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从那时起,佛教徒和道教徒的人数却呈指数级激增。在1960年,台湾的佛教寺庙
刚刚超过八百座;到1989年,超过了四千座。1960年,道观接近三千座;到1989年
接近八千座[61]。(此后没有减缓的趋势:1980年代中期有八十万人声称是佛教
徒,到了2000年,这个数字超过了五百万[62]。)台湾普通百姓的财富不断上涨,本土宗教供养也与日俱增,两者之间似有直接关联:通常两到三年人均收入增加
后,紧跟着就会有大量新的寺庙拔地而起[63]。这又一次和中国大陆对比鲜明——
事实上,当前正好截然相反。以这个宗教标准来衡量,这个被认为更西化的岛屿实
际上比海峡对岸的大陆更“乡土”——甚至更“中国”[64]。不过,普通民众生活
中的这些趋势,和他们快速实现现代化及对诸多西化实践的迅速适应,完全并行不
悖。
台湾文化的另一个方面值得一提。无论是在日本统治之下还是在国民党的高压
之下,台湾始终需要走向世界以求生存。然而,今天,台湾尴尬的政治地位已经导
致“正常的外交”渠道无济于事。这赋予了文化拓展和文化交流——或许更应被称
作“文化外交”——新的意义和紧迫性。就此而言,随着侯孝贤成为台湾最重要的
电影“使者”,台湾电影走到了历史前台。但是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先锋是林怀
民于1973年创立的云门舞集。云门是亚洲第一现代舞团。每年云门都推出一出新的
剧目,包括类似大陆人移民到台湾的独特主题作品(《薪传》,1978),以中国传
统形式呈现的著名作品(《九歌》,2001(IX);《竹梦》,2001),以及存在于纯
粹抽象领域的作品(《水月》,1999)。林怀民从传统(主要是道家和佛家)元素
中汲取精华。此外,云门大胆创新的技巧组合,以及如幽灵般平静的标志性舞蹈动
作,再加上从巴赫到阿尔沃·帕尔特的音乐伴奏,传达出比其东方和西方构成元素的总和要伟大得多的意涵[65]。这样的节目已被证明是可供输出的文化产品,也使得林
怀民成为台湾第一个具有国际声望的艺术家,但他不是最后一个。作为一个本省
人,林怀民在岛内的文化影响力是巨大的。作为一个老师,他培育了许多学生,比
如焦雄屏,焦后来成为台湾影坛的领导性人物之一。焦雄屏声称是林怀民让他们这
一代人(包括像她这样的外省人)思考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个观念渗透到了其
他的文化领域,包括电影[66]。台湾电影工业中的侯孝贤
那么这个时候侯孝贤在哪里?既不在论战中心,也不在论战前线,甚至没有参
与论战。相反,侯孝贤谨慎独处,在很大程度上隔离于这些大的社会潮流。1973
年,台湾当局失去联合国席位仅仅一年后,侯孝贤进入了台湾商业电影工业,在一
部不起眼的电影中开启了起初很不起眼的职业生涯。仅仅十年后,侯孝贤成为台湾
在海外最重要的文化“使者”。只有理解了与台湾全面转型密切相关的电影转型之
后,这点才讲得通。台湾电影并不简单地反映上文讨论的这些历史独特之处;它也
在支持它们的同时扮演了反对的角色。在过去,电影充当了为历史和政治掩盖真相
的工具。然后突然在揭示长期被遮掩的事实方面,跟当局唱起了反调,不仅在台湾
的银幕上,更重要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在这种历史发掘方面,侯孝贤尤其扮演了一
个关键的角色。
然而,侯孝贤1973年加入的电影工业,对完成这样一项历史任务来说,是力不
从心的。在任何地方电影都是一个引人注目和广受欢迎的存在物,一种需要体制高
度支持的艺术媒介,无论这种支持来自个人还是公众,或是两者兼而有之。结果
是,它无法避免社会整体的影响。当然,台湾电影也几无可能避开数十年来造就这
个岛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力量。此外,尽管在侯孝贤的创作生涯中台湾电影发
生了巨大改变,但有一点是持续不变的,那就是台湾统治者,无论是旧的还是新
的,都制定了有利于其他电影——主要是香港和好莱坞——的政策,而本土电影成
了牺牲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将损害侯孝贤的个人利益。
台湾地区真正的商业电影花了很长时间来发展。尽管日本电影是历史上最伟大
的民族电影之一,尽管日本现代化的整个方案曾改变这个岛屿的基础设施、医学、农业和文化,尽管这个岛屿为电影制作提供了广泛的多样化的潜在场景,但是台湾
并没有像1931年后的满洲那样,成为日本电影的生产基地。相反,台湾主要是作为
日本电影的市场。到1935年,四十八家剧院专门放映电影,其中三十一家维持到了
1945年[67]。1945年至1949年间,因为环境动荡,台湾电影没有获得实质性发展。
因此,台湾电影的真正历史始于1949年,那时台湾成为国民党政治经营的最后舞台。然而,它发展得相当缓慢。甚至当国民党试图用一只手扶植电影工业的时候,又会用另一只手扼杀它。
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香港正在发展一种有生命力的并且最终强大的商业电
影,这一事实刺激了台湾电影圈的很多人,他们常说:“如果香港能够做到,为什
么台湾不可以?”毕竟,相比香港这个更小的岛屿,台湾拥有多姿多彩的风景,比
如壮丽的山脉,富饶的森林,美丽的海岸线,甚至在岛屿的西边还有广袤的平原
——所有这些都是电影制作的有利条件。台湾的人口也是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的四
倍。答案是台湾最初的政治和经济条件,甚至直到1960年代中期,都不能有助于发
展一种繁荣兴旺的电影工业[68]。1949年秋天,只有百分之五的上海电影团体迁移
到了台湾,而被更大的自由召唤迁移到香港的,是这个数字的许多倍。而且,那些
1949年来到台湾的人们多数进了农业教育电影公司,这是一家主要制作纪录片和宣
传影片的公营制片厂。这意味着虽然有一定数量的设备和技术人员到了台湾,但是
几乎谈不上有创造性的天才[69]。与国民党没有直接关系的大陆电影导演、制片人或
者明星,要么留在上海,要么投奔香港稳定和自由的环境,这点不难理解。1949
年,台湾看不出有长期稳定的迹象;甚至国民党也仅仅把这个岛屿视作有朝一
日“收复大陆”的临时基地。
在最初的十五年,台湾电影仍然表现得像一场巡回路演,而不是一种真正的电
影工业。台湾当局更关心的是避免重蹈1930年代上海电影界的覆辙——那时左派压
倒右派,取得优势地位。因此,不像香港的殖民政府,国民党偏好严格控制任何电
影“工业”的存在,首先就在1950年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加以监管。国民党当局
直接监管台湾的每一家私人电影公司和电影机构。任何一家与电影相关的机关的头
目都一定是国民党党员。当局情报机关的指令源源不断,均蛮横地强加强烈的反共
立场,另外还有反“赤色”、“黑色”和“黄色”原则。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电影不像其他工业获得足够的重视。电影行业被宣称为一
种“特殊的”工业,尽管它能产出效益,但还是受到压制。台湾其他领域的税率从
来不会超过百分之三十,然而娱乐税高达百分之六十。电影票的印花税比其他任何
工业高出十一倍。更重要的是,进口电影器材,无论是为了制作还是展出,都被视
为“奢侈品”,因而其关税要高出其他行业百分之五十还多[70]。后者对电影行业产生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它强迫台湾的电影制作者在电影胶片上偷工减
料。而且,它甚至影响了主要的制片厂——“中央电影公司”(以下简称“中
影”),它成立于1954年,由当时的农业教育电影制片厂(“农教”)和台湾电影
公司(“台影”,接管自日据时代)合并而成[71]。不用奇怪,“中影”在国民党的
直接控制之下。
当局严密控制的结果是,台湾制作生产了大量的纪录片和宣传短片,但是几乎
没有虚构的故事片。那些拍摄出来的影片主要是为了宣传,而不是为了娱乐,也不
是为了文化教育。1950年代生产的极少数故事片也都是票房灾难。这些电影角色老
套、拙劣,回避官方禁忌,制作粗糙,观众压根不为所动。第一部故事长片《恶梦
初醒》仅仅使用了四万英尺日本过期胶片,这导致影片呈现雾化效果[72]。第二部故
事片是“农教”出品的《永不分离》,通过蓄意描述由共产分子制造的本省人和新
近迁来的大陆人之间的各种矛盾,试图驱散“二二八事件”的幽灵[73]。有时结果令
人哭笑不得。一部1960年代的闽南语电影情节涉及一个邮递员在关键时刻弄丢了一
些信件。这点被当局审查员剪掉了,因为它可能会有损邮递员的形象。然而,这一
删减导致电影几乎无法理解[74]。《飞虎将军》是1959年的一部政宣片,不惜工本
地描绘地方空军学院飞行员的训练。但是军方要求电影情节中不许任何飞机有问题
或出事故,也不许有任何人员伤亡,这导致成片缺乏戏剧张力,也失去了它的宣传
潜能[75]。当局的约束是如此的极端,以致它的政宣电影不被允许表现共产党的旗帜
或徽章,甚至不许出现毛泽东的形象[76]。当局政策也伤害了台湾以外的任何潜在观
众:因为过度反对“共匪”的主题,《恶梦初醒》的发行权没法卖到新加坡、马来
西亚和中国香港。因为这三个地区都要考虑和中国大陆的关系[77]。
本土电影制作陷入瘫痪,台湾影院的增加却总得有其他电影来填充。在每年上
映的六百到七百部电影中,只有两三部是本地制作的“国语片”[78]。在香港,商业
电影工业没有类似的政治和经济的约束,从一开始它的电影就席卷了台湾的银幕。
1950年至1954年间,总共有六百六十二部“国语片”在岛内上映,其中大多数来自
香港,少数是上海老电影,只有十三部是台湾本地摄制的[79]。1953年起,国民党
也将进入台湾市场赚钱的通路作为控制手段,通过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也称“自由总会”(X))对香港电影施加影响。这确保进入台湾市场的香港电影在政治
上都是合口味的[80]。不过香港也反过来能够从国民党那里获取好处。最关键是
1956年,香港“国语片”作为“国片”,可以不受现行配额制度限制,同时免于重
检。所产生的实效是,香港“国语片”不再受限进入台湾市场,它现在被归类为本
土制作的一个部分[81]。正如卢非易总结的:“不管原因是什么、结果如何,可以确
定的是,国民党当局为了说服香港电影工业,允许香港电影不受限制进入台湾市
场。看到这个机遇,香港电影心系台湾市场,最大化地扩大它自身的产量。这对台
湾电影工业本身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82]
其他政策进一步推波助澜。黄卓汉是“自由总会”的核心成员,他跟国民党当
局就不合理的电影生胶片和设备关税进行了协商。自此之后,香港“自由总会”的
会员公司进口电影设备的关税都被新的法规松绑了[83]。“自由总会”的任何会员进
口电影生胶片和设备进入台湾,在六个月内都免征关税。这项措施的目的本是为了
鼓励岛内的香港电影生产,但是制片商可以提交一份两个小时片长的脚本,却只拍
摄一部八十分钟的成片,然后把剩下的生胶片拿到当地的黑市上交易。这种做法是
如此的普遍,以致“新闻局”在1958年终止了电影生胶片进口的免税政策,这项政
策只对电影设备有效[84]。
出乎意料的是,这项政策不仅没有导致台湾制作更多的“国语片”,相反却迎
来闽南语电影摄制的第一波高潮。尽管那时当局希望用“国语”取代闽南语,但
是“国语”主要应用于教育系统,而非电影领域。同时,只要闽南语电影承载了正
确的宣传信息,或者至少不和官方路线背道而驰,国民党也允许它们存在。台湾本
地的电影制作如今可以从香港那边获取电影生胶片,这样就回避了过高的进口关
税。在1955年至1959年间,台湾总共生产了一百七十八部闽南语电影,数量超
过“国语”电影三倍[85]。
然而,我们不应将这种现象理解为一个真正的私营行业的开端。事实上,这些
电影与其说是正规电影厂的制作,不如说是不靠谱的经营者的短期投机和开发。影
片产量之多可能值得称道,但电影本身绝大部分不是这样。考虑到电影生胶片是珍
贵的物品,摄制者总是尽可能地少用。一些人专门在黑市倒卖电影生胶片,电影的实际创作反成了次要的事情[86]。何基明是1956年第一部闽南语电影(XI)的导演,他
绞尽脑汁地设法不让任何胶片被剪掉。他在开拍之前排演多次,使用每卷电影胶片
的七到八英尺引带拍摄成片中的过渡空镜头。最终,他仅使用了九千五百英尺胶
片,几乎没有被剪掉的[87]。辛奇是最著名的闽南语电影导演之一,他拍摄了九十多
部闽南语电影。根据辛奇的说法,电影制作中决定性的因素是生胶片的昂贵和时间
的匮乏:“我们那时拍摄闽南语电影使用的胶片通常进口,或者从黑市买来。一部
电影平均需要八百个镜头。因为胶片昂贵,我们浪费不起。而且,我们拍了那么多
的电影,一年大概一百部,花在每部电影拍摄上的时间非常短,平均两到三天就可
拍完一部电影。”[88]甚至当下一个十年出现相对高档的“国语片”,在摄制中仍然
存在同样的偷工减料现象。
无可否认,1960年代在台湾看到了一个更像样的电影工业的起点。然而,1950
年代为后来的一切奠定了基础,甚至包括1980年代的新电影运动。闽南语电影和制
片体系一样粗劣,却成为后来的工业人才的训练基地,比如李行,他是台湾电影导
演的“教父”。1950年代,台湾本地电影工业中有利可图的玩家只有像“中央电影
公司”和私营的联邦公司这样的发行商。发行商最终决定本地电影工业的长期命
运,甚至在1980年代也是如此。当局政策、香港电影在本地市场的早熟优势、岛内
落后的电影制作、围绕电影生胶片的争议和本地发行商发展迅速的力量——尽管台
湾电影经历的这些变化始于1960年代,但是当侯孝贤和新电影在1980年代早期崛起
的时候,也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先决条件,新电影不可能问
世。
在1963年,因为岛内外一些事情的合力作用,台湾电影的面貌发生了戏剧性变
化。这里的“岛外”,又是指香港。那一年,邵氏兄弟公司发行了《梁山伯与祝英
台》。该片是黄梅调电影类型中的一部“国语片”,当时在台湾获得了巨大的成
功,而且迄今还有人疯狂迷恋。它在台北创造了连续放映一百八十六天的纪录,收
入八百万新台币票房,打破了当时的所有票房纪录。(它的这一成绩直到1983年才
被成龙的《A计划》超越。)因此,香港人开始称呼台北是一座“狂人城”[89]。
《梁山伯与祝英台》对台湾的经济冲击持续久远。它凸显了台湾市场对香港电影的
确切无疑的重要性。它也导致台湾的很多戏院中断和美国电影公司的协议,反而开始放映“国语片”[90]。而且,当这部电影的导演李翰祥突然搬到台湾,带来技术和
艺术人才,外加大制作计划,也启动了一个成熟的私营电影业。李翰祥在那时已经
是邵氏兄弟公司最著名的导演,专攻古装片拍摄。李翰祥为邵氏执导了许多部票房
大卖的影片,但他认为自己没有因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极大成功而获得足够的
奖赏。竞争对手国泰集团看到了这个引诱李翰祥离开的机会。然而,李翰祥仍然要
承担和邵氏兄弟的签约责任,不能毫无法律纠纷地直接为国泰旗下的国际电影懋业
有限公司(简称电懋)拍片。因此,国泰通过在台湾的联邦公司,出资成立一家以
台湾为基地的大的新电影公司,国联公司于是诞生了。公司首脑正是李翰祥本人
[91]。
结果是诞生了一家在台湾规模空前的电影公司。尽管它在五年多内只制作了二
十部电影,但是国联独力将制作水准提升到新的水平,培训人员,创立明星制度,帮助建设更好的海外发行,鼓舞其他公司也装配相似的片厂设备。它也创造了几部
电影经典[92]。事实上,它也可能是一种超过或者至少达到香港电影水平的电影工业
的开始。最重要的财政资助者是马来西亚华人陆运涛,他是国泰集团的老板。陆运
涛在台湾电影业投入了五百万美元,显然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可是他后来死于
空难(XII),这场空难被许多人宣称改变了台湾电影历史的进程。黄卓汉说:“如果
不是这起空难,台湾的国语电影制作可能进入一个黄金年代,提升到国际水准。事
与愿违,香港电影一枝独秀……”[93]
没有了主要赞助人的干预,李翰祥便自作主张,国联公司很快变得像1920年的
联艺公司(XIII),那家公司由缺乏财政管理经验的艺术家掌控。李翰祥1965年拍摄
《西施》是挥霍无度的最好例子,这是一部奢侈的历史古装片,它花费了李翰祥一
年零三个月时间制作,消耗了两千三百万元新台币。有关这部电影的数字是惊人
的:四十二处布景,六千套戏服,三万个道具,八千匹马,十二万个临时演员(军
队提供),三百三十四个工作日,八百辆双轮战车和十二万英尺电影胶片。它是
1965年的本土票房冠军,然而它的首轮放映仅仅收回约五百万新台币,因为票价非
常便宜[94]。国联公司再也没能从这次财政打击中复原过来。然而,所有这一切催生
了“国语片”制作中真正的私营行业。国联的发行公司联邦,也开始自己制作电
影,首作是胡金铨的《龙门客栈》[95]。成功吸引胡金铨来到台湾,他后来在此拍出了1970年代的经典作品《侠女》,它是1980年代之前唯一一部在国际电影节的最高
竞争舞台上获奖的华语片。
但是烦人的问题出现了:这真的是台湾电影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还是仅仅是
香港电影的延伸?事实很简单,台湾私营电影业几乎打一开始就与香港电影纠缠不
清。比如说,黄卓汉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横跨两个地域。1967年他在香港创建了第一
影业机构有限公司,但又在台湾成立制片分部,拍摄武侠片[96]。财政、人才库和政
治方面的联系是如此纠结(甚至当局运营的制片厂也大量从事与香港公司的合作制
片),导致不可能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之间做出明确的区
分。它们一起被归类为“国片”自然于事无补,西方观察家也感到困惑[97]。甚至直
到今天,台湾和香港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台湾的每部电影史都会提
及这一时期在台湾制作的经典影片——《冬暖》(1967)(XIV)、《侠女》
(1970)(XV)和《喜怒哀乐》(1970)(XVI),把它们视作台湾电影来讨论。然而,与此同时,张建德的香港电影史把这些电影归为香港制作,这在香港是普遍的看
法。张建德讨论李翰祥、陆运涛和国联公司,也视之为香港电影史的构成部分[98]。
因为《侠女》在1975年戛纳电影节上获得特别技术大奖,所以此片特别有争议。
为了辨识台湾电影和香港电影的真正区别,我们不得不看看公营制片厂的情
况,它们在同一时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63年,龚弘被“新闻局”挑选出任“中
影”新的总经理。龚弘的任期长达九年半,他表现出的远见出人意料,在这期间,他改进了“中影”的管理结构、摄制设施和影院链。这些改变的结果是,“中
影”成为台湾电影工业的领导者之一。在1963年,龚弘还看了一部私营制作的、低
成本的、半“国语”半闽南语的影片,那就是李行导演的《街头巷尾》。这激发龚
弘聘请李行执导一种新的政策电影类型,它被称为“健康写实”。这股潮流中的电
影在产量上并不突出,但是三部最重要的作品——《蚵女》(1963)、《养鸭人
家》(1965,图1)和《路》(1967)——收获了此前公营制作从未取得的票房成
功[99]。在另一方面,健康写实电影继续为当局的宣传需要服务:它们的立意让人们
更多地联想到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不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这就是龚弘所宣
称的电影模式。这些电影都只用“国语”拍摄。它们也都呈现一个经过高度净化的
台湾现实的版本。最终,这些影片在语调上都充满严重的说教意味,在颂扬当局主导的社会进程的同时维护传统道德价值观。不过,在处理乡村普通百姓及其日常关
注时,健康写实影片与1950年代的宣传电影大相径庭。对健康电影来说也存在一种
更深层的意义。在当局鼓励的影片中,台湾本土的发展现在是一个有价值的主题。
换言之,这是“国语片”首次认可台湾——或者说至少认可一个理想化的台湾版
本。他们不再只是尖声谩骂,高喊“反共”、“收复大陆”的口号了。
图1 《恋恋风尘》(1986)中露天放映电影《养鸭人家》(1965)
在“中影”、国联和联邦的引领下,台湾本土“国语片”的数量在1960年代十
年间增长了二十倍。1960年,台湾只制作了五部“国语片”。1964年,达到二十二
部。到1969年,达到八十九部。1969年也是“国语片”产量超过粗制滥造的闽南语
片的第一年。到1971年,台湾“国语片”数量超过了一百部。
1960年代电影业的发展,成为侯孝贤所接受的非正式教育的一部分,他主要成
长于那十年间。然而,谁也不会预料到,这会培养出一个以拍摄了一些世界上最富
挑战性的剧情片而著称的导演。在学校,侯孝贤不是最勤奋的学生,这主要归因于
他自身兴趣匮乏。但是,他自学了那个时代可接触到的流行文化。侯孝贤自述,他
当时租借、阅读了能找到的每一本武侠小说,而且当他发现再也找不到武侠小说可
读的时候,就读侦探小说、经典小说的通俗改编、翻译的西方小说,当所有这些看
完后他甚至看琼瑶小说[100]。(在《童年往事》中,我们甚至能看见他躲在厕所偷看色情读物。)他早年也对电影如饥似渴,常常偷偷溜进电影院(《风柜来的人》
有所表现),或者在影院门外找到一些旧的、撕裂了的电影票根,粘起来混进去。
他在服兵役期间前所未有地看了大量电影,因为他身为宪兵,执勤特殊,有大把的
空闲时间,有时一天可以看到四部电影[101]。一退役,他就进了“国立艺专”(XVII)
学习电影。他在1960年代末进入艺专,由于学校缺少器材,他只是接受了极为有限
的技术训练。导演课程根本上就是戏剧导演课程,而且再也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可
学[102]。但是至少他看了更多的电影,尽管少于我们所认为的“电影学校”应提供
的数量。
侯孝贤看的大多数电影要么来自好莱坞要么来自香港。他曾提及那时看过的一
部电影,是大概在1967年服兵役期间看过的一部英国片,英语片名不确定[103]。这
部印象模糊的电影让侯孝贤对电影的兴趣更浓厚,但是根据他的说法,它没能帮助
他更好地理解这种媒介[104]。侯孝贤曾回想起,进入艺专后,有一次当一个老师分
析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XVIII)的二流作品《我就爱你》(Arrangement)的
视觉基调时,他感到惊讶[105]。他说,从此他看电影不同以往了,但是仍然不像人
们所预期的那样。他继续沉湎于流行文化,继续无视电影更艺术和更文化的表现。
只有到1970年代末在他自己将要成为一个导演的时候,他终于开始看更多的好莱坞
和香港以外的电影。然而,再一次,这对他影响甚微。当他看安东尼奥尼
(Michelangelo Antonioni)(XIX)作品和其他实验电影时,他无法真正地欣赏其
中任何一部[106]。侯孝贤甚至说过,在他商业导演生涯早期,他曾在看费里尼
(Federico Fellini)(XX)作品时睡着了[107]。
事实上,侯孝贤接受的真正的电影教育不是一种正统教育,而是学徒见习,学
徒身份开启了他进入电影业的日子。到1973年商业电影工业最好的时光已成过去,尽管它不是即刻显现,但是一个缓慢的衰落期已经来临。标志是1970年代初国联公
司偃旗息鼓,联邦很快在1974年结束制片业务,剩下“中影”成为唯一稳定的“国
语”故事片制作者。自1973年始,至1977年,台湾生产的“国语片”数量滑落到每
年四十五部至六十六部,而闽南语电影已经消失无踪。与此同时,香港仍然生产数
量三倍于台湾的故事片[108]。台湾发现它无法和香港在经费、质量和营销上竞争,特别是现在李小龙跃居银幕。火上浇油的是,台湾当局又出台了有利于香港的政
策,在购买和冲洗电影胶片方面,香港公司的花费比本地制作公司要便宜得
多[109]。
电影类型的分类能够解释这一不断扩大的鸿沟。香港比台湾生产了多得多的动
作片(或者说任何一种类型片)。在台湾,这些电影不但被认为制作昂贵,也会被
保守的社会精英批评道德含糊。卢非易曾指出台湾超过三分之一的电影如何在类型
上被改换分类为“文艺”片[110]。“文艺”片曾被翻译为“爱情”或者“文学”电
影,而且有时似乎涵盖了所有片种。因为文艺片制作起来比动作片廉价多了,所以
台湾制作了大量的文艺片,这是值得注意的[111]。没人比多产导演刘家昌更能代表
这股潮流,他在1970年代拍摄了近三十部电影,包括八部为“中影”拍摄的。刘拍
电影总是快速粗糙,人物塑造也很老套。但是他通过为影片配上大量歌曲改造了文
艺类型,使得这些电影甚至可有一点出口[112]。
台湾商业电影的核心是文艺片的一种次类型,也即俗称的“琼瑶片”,因大多
根据作家琼瑶的言情小说改编,故有此名。这股潮流似乎随着1960年代中期李行
为“中影”拍的两部电影的成功而出现[113]。到1983年,共有四十九部电影改编自
琼瑶小说,也有几部改编自琼瑶小说的克隆版。琼瑶甚至在1976年成立了她自己的
制作公司,当然,只拍摄琼瑶片[114]。这些电影容易出口到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这
样的市场,今天很多人认为它们荒诞地逃避现实。健康写实至少尝试处理台湾现实
生活,虽然是失败的;而琼瑶片与现实干脆毫无干系。如果这些电影可信的话,那
么台湾的每一个人都住在阳明山(台北有钱人的度假胜地)上宽敞的休闲山庄里,每个人都流连于西式客厅、餐厅和咖啡厅中打发时间,每个人都向往在基督教堂里
结婚,而且每个人都如此的西化,以至于民族文化的痕迹只剩筷子的偶尔出现,而
这似乎不过是场记的疏忽罢了。林青霞在去香港发展之前是琼瑶片的重要明星,她
直率地说,那些电影之所以影响巨大,确切的原因是它们在一个生活艰难的时代提
供了必要的幻觉。换言之,它们反映的不是台湾的现实,而是每个人都渴望逃往的
另一种世界[115]。
然而,整个1970年代,另一个因素加剧了台湾电影业面临的经济压力。这十年的“外交”受挫让国民党当局再次强调了宣传的重要性。这些政治危机导致了大预
算的政宣片,它们由“中影”这十年间的两任负责人梅长龄和明骥发起拍摄。健康
写实之父龚弘被“中影公司”新的总经理梅长龄所取代。梅长龄立即率领这家党营
制片厂走上了昂贵的电影制作之路[116]。这包括在1972年日本和台湾“断交”之
后,一波反日电影涌现。《梅花》是决定性的作品,1975年发行。这部影片票房收
获排名第一,而且获得台湾的“奥斯卡”金马奖的最佳剧情片奖。它的成功在很大
程度上归因于蒋经国的公开奖掖[117]。(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部片在台湾就相当于
大陆的《红色娘子军》。)台湾当局出于政治目的希望开发利用流行文化,《梅
花》就是一例。它的导演,拍片不辍的刘家昌,以自己的流行气质支援了政治宣
传。这部电影不仅让台湾政宣电影“教父”柯俊雄成为明星,也让非常年轻的张艾
嘉一炮而红。刘家昌创作的电影主题歌《梅花》风靡台湾。这首歌在情节开展的任
何时候都能响起,一个台湾男孩在“二战”期间目睹自己的父亲被日本人残酷虐
待,他唱这首歌效果特别明显。“中国小孩,不要哭。”这个戴着手铐脚镣、被打
得死去活来、鲜血淋漓的爱国父亲警告他的儿子。“我难过。”流泪的孩子回答。
他的父亲于是提议:“难过?唱歌!”这种匪夷所思的胡言乱语,只可能发生在迎
合宣传需要的情况下,台湾人却借此在以完美“国语”演唱的歌声中爆发了,通过
歌唱颂扬“国花”,显示了他们对身为中国人的不朽的热望。
在失去美国的承认和1979年底的“美丽岛事件”之后,这股大制作政宣片的潮
流到达了顶点。大量电影反映了对“台独”的警惕,其中最重要的叫“寻根”三部
曲。《源》是这股潮流在1979年的代表,影片浓墨重彩地描绘台湾19世纪的石油勘
探努力(也有一个丰满有力的得州人妻子的镜头,她帮助男人们干活,但只是作为
点缀)。然而,关键信息是一个最初的闪回,主角还是个小男孩时第一次来到台
湾:当他站在海边,他的父亲提醒他,他们来自大陆,他们来到台湾是为了帮助中
华民族开疆拓土。其他电影很明显看得出台湾当局对失去美国承认的反应。李行也
不甘落伍,在“中影”拍摄了明星云集的《龙的传人》(1980)。片中有一个开放
的纪录片风格的剪辑,表现街头人们对美国人撤退的反应,高潮是一个舞台化的段
落,人们瞪着一个年轻的、卷发的、白肤金发碧眼的男子和两个性感的当地姑娘愉
快地走在一起。那个男子看到人们的表情,掏出一块牌子,上面用中文写着:“我
是澳大利亚人!”这部电影的主题歌《龙的传人》,成为官方倡议的宣传口号,而且跨越海峡,在大陆甚至更流行。不过,这些电影中最声名狼藉的奢侈品是《辛亥
双十》(1981)。这部电影以夸张的英雄主义、数量惊人的临时演员、狄龙耍的一
些功夫,以及高潮那场堪比《乱世佳人》火烧亚特兰特的大火为特色。大多数观众
都是在学校或者俱乐部的公开放映场合看这样的电影;然而,几乎没人想过要买票
观看。结果是,这类电影使得“中影”深陷财政赤字。而且,一些人认为,“反
共”反日电影到此时已经让他们筋疲力尽,他们对这样昂贵的财务开销表示质疑。
从宣传和经济的观点来看,这类电影的产量再度面临锐减[118]。
这就是侯孝贤学习电影制作技艺的环境,如果不是不可能,看上去也是很奇怪
的。更令人吃惊的是,侯孝贤在这块土地上所体验的低成本琼瑶片、甜美的音乐和
夸张浪费的政治宣传,对他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持续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在他最近
的电影中也有迹可循。事实就是这么回事。
长镜头被认为是侯孝贤美学上最决定性的特征。不过,这不是他从早期商业岁
月中学习到的东西;不如说,这是他随着时间推移发展出来的东西。这一时期台湾
电影的平均镜头长度和其他地区不一样,但不明显。1960年代的电影抽样平均每个
镜头长约十秒。若以巴里·索特(Barry Salt)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做的平均镜头长
度的广泛分析作为基准,这一时期台湾电影剪辑通常比美国电影慢,但是非常接近
欧洲电影的平均水平[119]。从1970年至1977年的台湾电影中抽样,平均镜头长度下
降到约八秒,从而和其他地方更快的剪辑潮流取得一致[120]。1978年至1982年,台
湾电影平均镜头长度几乎同样维持在八秒。
这些平均数似乎反映了导演们最初学习技艺的环境。两个著名的移居台湾的香
港导演李翰祥和胡金铨,在台湾拍片的时候,剪辑影片也比他们的台湾同行快。比
如说,李翰祥的《西施》平均镜头长度为七秒,而胡金铨的《侠女》大约为五秒。
李翰祥1967年的经典作品《冬暖》,是一部台湾“健康写实”风格的剧情片,平均
镜头长度不足七秒。台湾最卓越的两个导演,李行和白景瑞,一般来说倾向于使用
较长的镜头。李行两部作品的平均镜头长度为十二秒,七部作品在十秒至十一点五
秒之间,四部在九秒至十秒之间。白景瑞甚至更加始终如一:他的六部抽样作品
中,五部在九秒至十点五秒之间,唯一真正改变的是《皇天后土》,平均镜头长度
为十一点五秒。1970年,上述四位导演联合执导了《喜怒哀乐》,这是为使国联公司复原的最后努力。两位台湾导演的平均镜头长度较长,白景瑞以超过十秒一马当
先,李行达到大约八秒。相反,胡金铨和李翰祥导演的部分平均镜头长度都在六秒
以下。
上述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抽样,揭示了一种以剪辑为基础的商业电影,它
们的剪辑比好莱坞慢一点,但比香港慢太多。台湾商业电影工业在商业制作方面跟
随世界潮流,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总是拖拖拉拉。它不是那种寻求自己风格的
长镜头电影。相反,是一种基于经济合算的更实用的剪辑实践。所以,侯孝贤对于
长镜头的追求,起因于他试图克服这种环境的限制。
当然,侯孝贤后来也在别的方面独树一帜,而这些也受到这种电影工业负面因
素的影响。在布光和镜头构成方面,如果不是指唯美的话,几乎没人可在复杂程度
和密度上与侯孝贤相匹敌。想想侯孝贤出身于台湾如此糟糕的商业电影工业,这更
令人吃惊。在台湾,布光和镜头构成都背弃了明确的低成本制作方法。
在商业电影工业的全盛期,布光很显然是统一的和功能性的,与表现性和艺术
性截然相反。这些电影使用变形宽银幕格式和彩色电影胶片拍摄,所以需要大量光
照,就像十年前很多好莱坞电影的摄制一样。然而,很少有人在用光造型或者使之
柔化方面付出努力。当然,也几乎不在阴影和黑暗方面做出探索,就像同时期《教
父》的摄影师戈登·威利斯(Gordon Willis)所做的工作那样,他被称为“黑暗王
子”。这些电影通常使用平光,演员或无生命物体同样投射出硬边阴影,总之导致
粗糙的光线设计。一个例子是1970年的《葡萄成熟时》。有一场戏是女主角进入她
的卧室,走向一个角落。当她走近墙角,她的身体在两面墙上投射出硬边阴影。不
但这两束来自不同方向的光源没有清晰的动机,轮廓分明的阴影也例证了电影实践
中没有散射的硬光设计。既然布光如此费时,而那些低成本电影又没有多少摄制时
间,所以这也就不足为奇,特别是在香港,这一点也很普遍。图2 《葡萄成熟时》(1970)中的一个画面,两面墙上都有动机不明的硬光
作为补偿,台湾导演求助于一套视觉花招,其中一些显然源自香港。比如快速
变焦镜头的滥用。1980年台湾制作的一部功夫片《乡野人》,有很长一段时间几乎
每个镜头都包含一个快速变焦镜头。变焦镜头在功夫片中不稀奇,但是它同样统治
了台湾的非动作片,不管是林清介导演的所谓“学生电影”(如《学生之爱》,1981),还是军事政宣片(如《黄埔军魂》,1978),或是像《再见阿郎》
(1970,导演白景瑞)这样的戏剧性爱情片。通常这些变焦镜头的目的是为了突出
关键的戏剧性时刻,使得它们不会被观众错过。比如说,在白景瑞的《白屋之恋》
(1974(XXI))中,在表现一个父亲恳请女明星(甄珍)不要再和他的儿子约会的特
别时刻,就使用了一系列的变焦镜头。通常来说,我们很难在那一时期的台湾电影
中找到一部不包含一些快速变焦镜头的电影。甚至是以相对克制著称的李行,也为
了强调感情而使用变焦镜头。在《养鸭人家》中,在养女抓住她的父亲并说她仍然
是他真正的女儿的关键时刻,使用了一个快速的推镜头。在《海韵》(1974)中,一个快速变焦镜头导致一个闪回,强调了一个女人曾经作为舞女的羞耻过去。在
《小城故事》(1979)中,变焦镜头强调了一段萌芽中的恋爱。
然而,另一种视觉花招,似乎把台湾电影和香港电影区别开来。变形宽银幕格式意味着一个浅得多的景深。台湾导演通常通过前景尽头失焦的物体,如灯、灯
光、花瓶、植物或者树枝等,来炫耀这点,而不是避免它。有时候这些模糊不清的
物体甚至会部分地挡住中间地带的演员的视线。这样的例子多到不可胜数。1980年
的电影《台北吾爱》有一场宴会戏,为了突出浪漫的氛围,灯光闪到极致,令人眼
花缭乱。同一年的《美丽与哀愁》包括一段舞蹈戏份,前景尽头的灯光全都处于失
焦状态。琼瑶片特别展示了这一趋势,大部分是在恋爱场景中。比如说,在1977年
的《我是一片云》中,林青霞在一家咖啡店首次宣称她对秦汉的爱,前景是着重突
出的台灯闪耀的铜管,为了浪漫效果全都模糊一片。在《白屋之恋》中,这种做法
变成了“多相变态”(polymorphously perverse)(XXII):片中有大量的物体,包括霓虹灯、铁栅栏、喷泉、蜡烛和吊床等,全都在前景尽头失焦。倒霉的恋人在
小屋里跳舞的场景中,突出了前景尽头的模糊的蜡烛,它占据了比演员还要多的空
间,几乎挡住了观众看他们(图3)。这种实践的广泛运用也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
变形宽银幕格式导致宽画幅需要被填满。相比使用昂贵又费时的高质量布光,或者
更仔细精心的构图和布景,来美化和充实画面,前景中的模糊物体是一种便宜和节
约时间得多的方式。
不过,另一种实践最能诠释在这种行业中工作对一个导演意味着什么,而这点
也特别挫败侯孝贤。李行导演的影片《心有千千结》(1973),让侯孝贤的名字第
一次出现在摄制人员名单中,此片他署名场记。片中有场戏演绎了一种可作为当时
台湾电影工业缩影的分场方法。地点在餐厅。就餐期间,一个住家护士试图说服她
的年老的病人,他的儿子很孝顺,不像他认为的那样叛逆。尽管有二十一个镜头,尽管它们中的很多由正反拍镜头连接,但是在这个场景中,只有七个镜头来自早前
使用的重复的机位设置。无论什么时候拍广角——意味着距离更远且通常展现多个
角色——它通常来自一个相对于之前的广角镜头来说全新的角度,也即餐桌周围的
某个别的地方。图3 《白屋之恋》中故弄玄虚的浅景深
这一点不像好莱坞,在好莱坞拍摄一个场景的主镜头是通例。它必须从一个广
角来拍摄整个场景,捕捉所有的情节。主镜头经常要多拍几遍,以确保有一个好的
可以使用。拍完主镜头,摄影机然后移到其他几个地方拍摄插入镜头、近景镜头、反应镜头、细部特写镜头等,这种做法通常被叫做“涵盖镜头”。关键是,无论最
终使用了什么样的其他镜头,总是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主镜头,它可以用作场景中的
任何一个点的再定位镜头。但是,在台湾,开场从来没有整个场景的主镜头。因
此,无论何时回到广角拍摄,剧组都能在一个新的机位轻易地完成它,就像在最初
的位置一样,因为这两个镜头原本就是独立拍摄的。这也确保了在最终的成片中有
一些视觉的变化。而且,布光是如此的一成不变,乃至从一个机位到下一个机位,布光几乎不做调整,这在好莱坞是很成问题的,因为那里的摄影指导要是不认真对
待每一个独特的位置而“耍诈”的话,会声名狼藉的。实际上,这使得好莱坞导演
较少倾向于使用更多的机位,但是不妨碍台湾导演满足于纯粹实用的、平面的灯光
设计。
这也再次表明了香港电影对台湾电影的影响。在香港,电影人也在镜头之间做
最少的布光调整,而且倾向于把摄影机摆在任何一个场景中任何一个可以想到的位置。大卫·波德维尔称之为“分段拍摄”方法,在香港,场景的拍摄都是从不同的角
度逐个拍摄镜头,然后一起剪辑进一个不必依靠主镜头的单一场景。在好莱坞,在
剪辑中倾向于回到主镜头,结果是香港的机位变化比好莱坞的标准丰富[121]。香港
拍法不同于好莱坞的原因很清楚:在一个劳动密集型的行业,这是创造有活力的动
作场面最有效的方法。然而,在台湾,这种方法也经常用来处理非动作场景。显
然,对电影胶片的节约要求决定了为什么没有主镜头:它太贵了。在台湾,电影人
想方设法地要使片比降至最低。四比一被认为是铺张浪费,三比一到二比一是惯
例。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片比甚至更低。制片人和导演郭清江曾教育侯孝
贤如何做到片比低于二比一。他说他拍摄某部电影(他没有确指是哪一部)时,他
从一万八千英尺琐碎的曝光胶片中挑拣出一万一千英尺剪成影片——片比约是一点
六比一[122]。事实上,这种行业的典范有可能创造一比一的片比。所见即所拍——
没有重来!
这种普遍应用的制作方法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意味着更长的平均镜头长度。
在1980年代初期,郭清江——根据侯孝贤的说法,他是低片比大师——的三部作品
的平均镜头长度在五至七秒之间。然而,考虑到几乎没什么剪辑工作,很容易明白
这些电影大多数在剧情推进方面很不自然,或者粗枝大叶。人们可能会发现偶尔有
部台湾电影的剪辑速度和来自香港的流行电影——比如《鬼马智多星》
(1982(XXIII))和《最佳拍档》(1982),这两部电影的平均镜头长度约为五秒
——一样快。但是我们找不到任何一部台湾电影会像香港电影那样剪得爽快活泼。
原因很简单,既然绝不允许浪费胶片,那么台湾制片商也不会舍得多留任何东西在
剪辑室。正是如此死板的做法导致台湾电影到1980年代初期在香港电影面前不堪一
击。
这种做法对这些电影的意义远不是节奏和速度那么简单。在台湾,表演的最佳
时刻在剪辑时派不上用场,对此演员一点也不在乎。事实上,要是一开始就能将他
们表现最好的某个瞬间记录在胶片上,也够神奇的。侯孝贤对这种做法有丰富的经
验,据他的说法,无论何时拍摄一个人物的近景镜头,演员不是对着另一个演员讲
台词,而是常常对着站在他或她前面的副导演握紧的拳头[123]。他们从来不会用一
个主镜头从头至尾拍摄一个场景;他们只是每次拍摄一个镜头,没有真正的连贯性。理论上说,成片上显现的最好是最初捕捉在胶片上的那个时刻,尽管无法避免
的错误将导致片比高于一比一。停止和开始,情绪中断和对着握紧的拳头极尽夸张
能事地表演,都会冷却表演的激情。甚至李行也很难拍到过目难忘的表演,考虑到
所采用的拍摄方法,这是不足为奇的:一次拍摄一句台词的零碎做法产生了这样一
种感觉,李行的电影不过是用一根敷衍的叙事链条把矫揉造作的通俗剧节段捆在一
起。也许是为了掩饰这一切,李行和其他电影人总是源源不断地提供眼泪。《养鸭
人家》的结尾是一个年轻的阿飞独自在街上哭泣,反省自己走错的人生道路;
《路》的结尾是一个父亲为他孝顺和成功的儿子倍感自豪,而眼中满含泪水。李行
电影的一个典型结尾是放声痛哭的家人们围着濒死的父亲,他要利用临终宝贵的几
口气宣讲必不可少的遗言。动辄轻易地求助泪水,可不是李行一个人这么干。也许
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如此多的电影以痛哭的告别作结。
1973年,侯孝贤开始做场记,很快就变为副导演,最终变为编剧,起初和导演
赖成英写作了三部作品,赖是他7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走得最近的同事。在台湾,导
演很少做实际的导演工作;是副导演在现场真正面对日常的问题,他们掌管使用最
少的胶片。1970年代,侯孝贤至少为十一部电影署名了副导演,这些经验使他彻底
明白了流行电影拍摄方法的局限性。前面所提到的所有做法——实用的剪辑、实用
的布光、构图上玩弄的伎俩、最小的片比、时起时停的表演——侯孝贤有一天会拒
绝,但不是在第一天,甚至也不是在第十天。事实上,侯孝贤有好几年接着这么
干,以此来承担一些个人责任。(这毕竟是他的生计。)正如看起来的那样奇怪,他的这些经验对他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即使在他不再需要依靠这种工业工作
之后。他从这种主要是反面的经验中汲取了大量教训,但有两个宝贵教训最突出:
布光的重要性和表演的重要性,今天这两个领域构成了他自己的美学的基石。
当侯孝贤为李行的《早安台北》创作剧本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重大契机。这部
电影的摄影师是陈坤厚。后来陈和侯组成了一个导演编剧摄影组合。在参与新电
影浪潮前的几年里(1980—1982),这对组合一起完成了七部电影,陈正式导演了
四部,侯孝贤正式导演了三部:《就是溜溜的她》(1980)、《风儿踢踏踩》
(1981)、《在那河畔青草青》(1982)。侯通常是编剧,而陈通常是摄影师,由
于他们的工作关系密不可分,所以当时的评论界把这些影片看成是他们联合执导的
作品。因此,和大多数新电影导演不同,侯和陈在商业电影工业中积累了大量经验。陈和侯共享在台湾电影工业中改革制作实践的理念,他们的想法与众不同,这
给他们带来了声望。他们的一些变革将最终直接影响新电影,首先试验的就是他们
自己合作的作品。他们最早开始解决那些他们认为休戚与共的问题:电影胶片的匮
乏和表演的老套。在他们第一部共同作品陈坤厚导演的《我踏浪而来》(1980)
中,据说他们耗费了三万五千英尺胶片,而那个时候没人敢超过三万英尺[124]。拍
摄侯孝贤导演的《在那河畔青草青》时,他们使用的胶片在四万到五万英尺之间,这被认为是铺张浪费[125]。更高的片比最终在新电影导演中成为一项共同的改革运
动。然而,在新电影出现之前,侯和陈已经对陈规陋习发起了挑战。
甚至是今天已经成为侯孝贤标志的长镜头,也和他早年在工业中的经验有直接
关系。侯孝贤最初并没有把长镜头当作一种有意识的美学策略。它们是他要求更好
的表演无心插柳的产物。作为一个副导演,侯孝贤知道既有的做法需要改变。但
是,他在那个位置上被那些方法所束缚。一旦他自己成为导演,他便开始实践一个
导演应该真正地在现场执导的“新奇”观念。然后他开始不断试验各种调整表演的
方法。陈和侯都没听过什么主镜头系统,但他们发现如果每个镜头都更长些的话,现有的分段拍摄方法中的表演将会更好。有时,更长的镜头对侯孝贤来说似乎是一
种给了他的演员更多表演呼吸空间的实践方法。这就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长镜头
风格大师之一的毫不起眼的起步。
早期的电影证明了这点。以当时的行业标准来看,陈是一个长镜头导演,侯就
更加是了。以1980年至1982年间的二十五部抽样影片来看,平均镜头长度为八点三
秒。然而,陈1982年的《俏如彩蝶飞飞飞》平均镜头长度为十点三秒,侯孝贤的
《就是溜溜的她》为十一点三秒,《风儿踢踏踩》为十二点七秒,《在那河畔青草
青》又是十一点三秒[126]。在同样的三年中,只有李行的《原乡人》和白景瑞的
《皇天后土》的平均镜头长度接近。
这些早期作品的风格揭示了一个新导演在现有条件下仍寻求新美学的不经意的
探索。这三部电影都采用了变形宽银幕格式;都含有大量的变焦镜头。在《风儿踢
踏踩》中,一对爱人(钟镇涛和凤飞飞饰演)外出到田野的情形在一个长达两分钟
的单镜头中展现:首先是远景拍摄,然后拉远至一个更远的镜头展示梯田及其后面
的山岭。与之对照,《就是溜溜的她》中,凤飞飞饰演的角色和她的姑婆在饭店谈话的场景,表明了后来将采用的手法:也长约两分钟,但这一次摄影机纹丝不动。
虽然有这些例子,但是侯尚未有意识地追求长镜头美学。按他自己的说法,他依然
从其他角度拍摄,但是当他发现从一个更宽的视角拍摄的镜头很好很特别时,他明
白再也没有理由使用其他机位的镜头。这逐渐变成了一个习惯[127]。
追求更好的表演不仅影响了侯孝贤拍摄场景的方式,也最终影响了侯孝贤的编
剧方式和结构影片的方式。毕竟,侯在他作为商业导演的早期,仍然面对一个几乎
无法跨越的障碍:明星——或者如侯所形容的,不会表演的流行歌手。这些歌星演
员是如此在意他们的银幕形象,以致侯对他们束手无策。
不过,在他的三部商业电影中,因为一群表演沉着自如的孩子,《在那河畔青
草青》取得了一个大的突破。最值得注意的时刻是在父亲摔死小男孩的宠物猫头鹰
时他表现得很难过。这个五十五秒的镜头构图非常突出,在深度上采用了层次分明
的调度,父亲在前景,小男孩在远处斜对着他,摔掉书包,生气地吼叫(图4)。这
些孩子的表演使得侯孝贤第一次获得评论界的注意。有人形容这部电影“采用一种
平静的诉诸观众情感的方式,温暖柔和地描绘孩子世界,使得影片别开生面,优美
动人,一点也不盲从近期潮流”[128]。侯说他发现指导孩子们拍戏是容易的。当他
们犯错的时候他从不告诉他们,而是总是假装灯光出了问题,或者某个剧组成员犯
了错。(反过来,剧组成员也都明白侯的意图,并且假装内疚。)结果是这些儿童
演员通常在第二次或者第三次拍摄的时候更好。然而,这么做并没让侯孝贤臭名远
扬,反而提炼出了一种运用至今的新的拍摄方法:即兴创作[129]。侯只会告诉这些
孩子们处境,要不然就是让他们即兴创作对话的真正台词,像这些事他是从来不会
让钟镇涛和凤飞飞这样的明星做的[130]。这种导演方法起初只是用来指导《在那河
畔青草青》中的孩子,如今成为侯孝贤指导每个演员的方法:侯通常提供情境、情
绪和一种氛围感,但不提供精确的对话台词或者严格的调度指令[131]。图4 侯在《在那河畔青草青》中运用了复杂的纵深调度
因为侯孝贤和陈坤厚在商业电影中的革新,不难明白为什么他们能够配合默契
地推动新电影萌芽。《在那河畔青草青》是他们开创新局面的敲门砖。詹宏志是侯
孝贤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他说这部电影因其开创性和自由流动的叙事,而成为新
电影的源头之一[132]。黄建业宣称,这部电影的成功鼓舞了“中影公司”以《光阴
的故事》尝试低预算更多艺术自由的拍摄方法[133]。不久,侯和陈被誉为新电影
的“精神领袖”[134]。在这场运动中,侯孝贤发展了一套全新的人际关系,其中一
些人直至今天仍对他至关重要。关于侯孝贤的背景,人们惊奇的是他没有受到外部
影响,这表明他是完全的土生土长。他不像新电影运动中的其他成员,从来没有去
过海外的电影院校求学,而且令人遗憾的是他对诸多世界电影潮流都一无所知,包
括那些被误解认为对他产生影响的潮流。早年常有人拿侯孝贤和小津安二郎作比
较,没什么比这点更清楚:和那些通常推断的相反,侯声称他甚至从来没有看过小
津一部电影,直至他拍了《童年往事》[135]。而且,侯不是那些受过西方训练的电
影人,甚至也不是杨德昌,到头来却成为新电影的真正中心。他的电影定义了这场
运动。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侯有一样东西是别人所不具备的:各个方面的经验。
他不但经历了台湾在他眼前发生的变化,而且拥有在台湾电影工业摸爬滚打的日常
经验。这些共同创造了他的辉煌事业。然而没有大量的运气和帮助,侯孝贤不会有
这样的成就。他需要朋友和制度的支持。幸运的是,他恰好在一个正确的时间成为导演:一切——台湾社会和台湾电影——都在1980年代发生了更剧烈的变化。到这
个十年结束,这个男人和这座岛屿都将脱胎换骨。有时候,时机就是一切。
注释
[1]Song Guangyu宋光宇,ed. The Taiwan Experience台湾经验,2 vols.
(Taipei: Tung Ta,1994).
[2]Chen Ruxiu陈儒修,Taiwanese New Cinema's History,Culture and
Experience台湾新电影的历史文化经验,2nd ed.(Taipei: Wanxiang,1997).
[3]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vised ed.(New York:
Verso,1983,1991).
[4]Melissa J. Brown,Is Taiwan Chines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2.
[5]Ibid.,5;Denny Roy,Taiwan: A Political History(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 242–45.
[6]Li Xiaofeng李筱峰,The Hundred Biggest Incidents of Taiwanese
History台湾史100件大事,vol. 1(Taipei: Yushan,1999): 30–31.
[7]Ibid.,39–45.
[8]Li,57.
[9]Roy,31.
[10]Li,91.
[11]Ibid.,94–96.
[12]George H. Kerr,Formosa Betrayed(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65): 20.[13]更值得注意的是侯和杨德昌同一年出生在广东省的同一个客家聚居地梅
县。
[14]Chu Tian-wen朱天文,interview by author,June 2,2001,Sogo
Department Store Coffee Shop,Taipei,Taiwan.
[15]Li Qiao李乔,“The Significance of 228 in the Taiwanese
Psyche,”228 Studies,403.
[16]Li Xiaofeng,vol. 2,35;Xu Jielin许介鳞,The Post-Wa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aiwan战后台湾史记(Taipei: Wenying Tang,1996),vol. 2,4.
[17]Ibid.,57–59.
[18]Xu,15–16.
[19]Ibid.,25.
[20]Xiong Zijian熊自健,“Post-War Taiwanese Liberalism and the
Thought of Hayek,”in The Taiwan Experience,vol. 2,27–65.
[21]Li Xiaofeng,vol. 2,91–92.
[22]Chen Zhongxin陈忠信,recorded in Violence and Song: The Kaohsiung
Incident and the Formosa Judgment暴力与诗歌:高雄事件与美丽岛大审,Part 3
of the Oral History of the Formosa Incident珍藏美丽岛口述史(Taipei:
Times Publishing,1999): 98.
[23]Copper,115.
[24]Shi Minxiong施敏雄and Li Yongsan李庸三,“The Directions and
Structural Changes of Taiwa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in A Collection
of Treatises on Taiwa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台湾工业发展论文集,Ma Kai
马凯,ed.(hereafter cited 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Taipei:Lianjing,1994): 3.
[25]Yu Tzong-shian,The Story of Taiwan: Economy(Taipei: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1999): 8.
[26]Copper,139.
[27]Li Xiaofeng,vol. 2,31–34;Xu,vol. 2,95–98.
[28]Xu,118.
[29]Shi and Li,22,24.
[30]Copper,122.
[31]Ma Kai,“The Evolution of Taiwan's Industrial Policies,”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97.
[32]Copper,135.
[33]Chen Zhengshun陈正顺,“Import-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Discussion of Conclusions and Research of Taiwan's
Situation,”Industrial Development,84–85.
[34]Copper,126–27.
[35]Ma,147.
[36]Lin Zongguang林宗光,“The Taiwanese Identity Problem and
228,”in 228 Studies,363.
[37]Xu,vol. 2,69–71.
[38]Li Xiaofeng,vol. 2,14–15。当然,当然,当局允许拍摄台湾方言电
影,这可能看起来令人奇怪。事实是,“国语”教育是当局企图压制台湾方言的基石。它并不完全反对出于宣传意图使用台湾话,因为当局知道很多人失学,也学不
好“国语”。只要电影不违反任何政治禁忌,就仍然可以使用台湾话作为主要语
言。
[39]Liu Xiancheng刘现成,Taiwanese Cinema,Society and State(Taipei:
Yangzhi,1997): 34–36.
[40]Ibid.,37;Lu Feiyi卢非易,Taiwanese Cinema: Politics,Economics,Aesthetics(1949–1994)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
1994(Taipei: Yuanliu,1998): 69–71.
[41]Liu,38.
[42]Li Minghui李明辉,“Confucianism and Kant in the Thought of Mou
Zongsan,”in The Taiwan Experience,vol. 2,91–97.
[43]Jiang Nianfeng蒋年丰,“The Existentialist Wave in the Post-War
Taiwan Experience: Sartre at the Center,”in The Taiwan Experience,vol.
2,1.
[44]Ibid.,2.
[45]Chang Sung-sheng,Yvonne,Modernism and the Nativist Resistance: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 12.
[46]Ibid.,100.
[47]Xu,vol. 2,64–65.
[48]Wang Jing,“Taiwan's Hsiang-tu Literature: Perspectives in the
Evolution of a Literary Movement,”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 Critical
Perspectives,Jeannette L. Faurot,ed.(hereafter Fiction from Taiwa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 61-62.[49]Chang Shi-kuo,“Realism in Taiwan Fiction: Two Directions,”in
Fiction from Taiwan,31.
[50]Wu Mingren,“From Worship of the West to a Popular
Consciousness,”A Collection of Discussions about Nativist Literature乡
土文学讨论集,Yu Tianzong尉天骢,ed.(hereafter Nativist Discussions)
(Taipei: Yuanliu Zhangqiao,1978): 3–6.
[51]Wang Fan汪帆,“Speaking of Modern People and Modernization,”in
Nativist Discussions,37.
[52]Jiang Xun蒋勋,“To Irrigate a Cultural Flowering,”in Nativist
Discussions,49.
[53]Chen Yingzhen陈映真,“Literature Both Reflects and Comes from
Society,”in Nativist Discussions,64.
[54]Li Zhuo李拙,“Direc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wentieth Century
Taiwanese Literature,”in Nativist Discussions,126.
[55]Zhang Zhongdong张忠栋,“Native Soil,the People,and
Strengthening Oneself,”in Nativist Discussions,496.
[56]Peng Xiaoyan彭小妍,“The Nativist Debate in 1970's Taiwan,”in
The Taiwan Experience,vol. 2,68–69.
[57]Xiang Yang向阳,“Opening the Map to Consciousness: A Look Back
at Post-War Taiwanese Literary and Broadcast Media Movements,”in
Discussions of Contemporary Taiwanese Political Literature当代台湾政治文
学论,Zheng Mingli郑明娳,ed.(Taipei: Times Publishing,1994): 88.
[58]Song Guangyu宋光宇,“A Discuss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in Taiwan over the Last Forty Years,”in The Taiwan Experience,vol. 2,194.
[59]Ibid.,200.
[60]Ibid.,175.
[61]Ibid.,184.
[62]Hsiao,Hsin-huang Michael,“Coexistence and Synthesis: Cultural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in Many
Globalizations: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Peter
Berger,Samuel Huntington,eds.(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63.
[63]Sung,188–89.
[64]Brown,239.
[65]我没有这些见识,而是采用了富布赖特学者Sansan Kwan的观点,她那时正
在做研究云门的论文,同一年我正在研究侯孝贤。我要多多感谢她为我介绍台湾文
化难题中的关键部分。这里若有任何关于现代舞和云门的幼稚或无知的评述,都完
全是我的责任。
[66]Peggy Chiao焦雄屏,interview by author,March 10,2002,Middleton,Wisconsin.
[67]Li Tianduo李天铎,Taiwanese Cinema,Society and History台湾电影:
社会与历史(Taipei: Yatai,1997): 42–45.
[68]Ibid.,60–61.
[69]Ibid.,106;Lu,35–37.
[70]Huang Ren黄仁,The Film Era of Union联邦电影时代(hereafter cited
as Union)(Taipei: National Film Archives,2001): 35–36.[71]Li Tianduo,109;Lu,64–66.
[72]Lin Zanting林赞庭,Cinematography in Taiwan 1945–1970: History
and Technical Development台湾电影摄影技术发展概述1945—1970(Taipei:
Cultural Development Office,2003): 37.
[73]Peggy Chiao焦雄屏,Generational Reflections时代显影(Taipei:
Yuanliu,1998): 154.
[74]Li Yongquan李泳泉,Taiwanese Cinema: An Illustrated History台湾电
影阅览(Taipei: Yushan,1998): 17.
[75]Huang Ren黄仁,Film and Government Propaganda电影与政治宣传
(hereafter cited as Government Propaganda)(Taipei: Wanxiang,1994):
27.
[76]Ibid.,8.
[77]Ibid.,9.
[78]Lu,155.
[79]Ibid.,163.
[80]Liang Liang梁良,Studies on the Three Chinese Cinemas论两岸三地电
影(Taipei: Maolin,1998): 133–34.
[81]Lu,76;Liang,135.
[82]Lu,206.
[83]Huang Zhuohan黄卓汉,A Life in Cinema: ......
致谢
导论 侯孝贤的问题
第一章 侯孝贤与台湾经验
1949年前的历史“说法”
侯孝贤与战后台湾经验
侯孝贤与战后政治经验
侯孝贤与战后经济经验
侯孝贤与战后文化的缓慢解冻
台湾电影工业中的侯孝贤
第二章 侯孝贤与台湾新电影
1980年代的台湾
台湾电影文化
危机中的电影工业
《儿子的大玩偶》(1983)
《风柜来的人》(1983)
《冬冬的假期》(1984)《童年往事》(1985)
《恋恋风尘》(1986)
《尼罗河女儿》(1987)
第三章 还原历史:《悲情城市》(1989)与《戏梦人生》(1993)
被遮蔽的日本殖民背景
“二二八事件”:台湾身份的沸腾血泊
《悲情城市》:一个空前的文化事件
《悲情城市》的文本现象:先体验,后理解
1989—1993:《戏梦人生》前的长久沉默
《戏梦人生》:浮云连缀的电影
未经修饰或想象的历史?
第四章 再见过往:新的侯孝贤
《好男好女》(1995)
《南国再见,南国》(1996)
《海上花》(1998)
侯孝贤的“中国性”
结论 新千年的侯孝贤
《千禧曼波》(2001)
《咖啡时光》(2003)《最好的时光》(2005)
《红气球之旅》(2007)
侯孝贤:不仅是一座岛
中英术语对照表
译者后记致谢
这个研究旨在说明没有电影人是单打独斗的,电影人如此,对深入研究他们的
任何人来说,也是如此。和所有从事类似研究项目的人一样,我不仅得到众人的帮
助,也受惠于诸多机构,是他们让这一切成为可能。我要感谢香港大学出版社的支
持,特别是科林·戴(Colin Day)、迈克尔·达克沃斯(Michael Duckworth)和道
恩·刘(Dawn Lau)付出的努力。当然我也要感谢匿名审稿人对原稿提出的详尽意
见,这本书稿能修改得更精炼且质量更高,他或她的建议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虽然书稿付梓在即,但这个项目其实很早就在其他机构和个人的支持下开始
了。我首先要感谢,也是最需要感谢的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传播艺术系,它是这个研究项目的真正诞生地。该系自始至终提供了一个热情周到与大度包容的
环境,培育我脚踏实地,让我不会满足于肤浅的结论或者在学问上抄近道。我无法
点到每一个在早期阶段曾直接或间接影响这个项目的人名,但是有些人一定要提
到。首先我要感谢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他最早指导我的研究。自
从我遇见波德维尔博士那天起,他就对这个项目很热心,为我提供了学界最前沿的
建议和指导,不但包括严格的标准,也包括富有感染力的激情和鼓励。其次要感谢
万斯·开普利(Vance Kepley)和凯利·康韦(Kelley Conway),作为我的论文初
稿审稿人,他们提供了无价的帮助,以及利·雅各布斯和 J·J·墨菲,他们敏锐的洞察
力启发我反思某些问题。我也要感谢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每一个与我共同开
展研究的同事。尽管可能会漏掉许多同样值得特别提到的名字,我还是要感谢丽莎·
东布罗斯基(Lisa Dombrowski)、伊桑·德·塞弗(Ethan de Seife)、帕特里克·
基廷(Patrick Keating)、文斯·博林杰(Vince Bollinger)、崔珍熙
(Jinhee Choi)、汤姆·吉上(Tom Yoshikami)、斯图·法伊夫(Stew Fyfe)、凯瑟琳·斯普林(Katherine Spring)及贝卡·斯文德(Becca Swender)。(如果
我漏了任何人的名字,既然我列了这份名单,无疑我想到了你。)此外,我要多多
感谢尼科尔·黄和爱德华·弗里德曼的批评与宝贵的建议,本书形貌与初稿完全不同,他们对此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如果没有富布赖特–海斯奖学金让我得以开展第一阶段的研究(本研究主要以之
为基础),我无法想象这项工作会成什么样子。我不但要感谢美国国务院在2000年
为我提供这一奖励,也要感谢在台湾地区管理富布赖特奖学金的学术交流基金会。
首先我要感谢吴静吉博士,当我在台北的时候他管理基金会。同样要感谢 Julie
Hu、Amy Pan、Amy Sun 和 Mark Dong。这五位让我们在台北的那一年不但在学
术上成果丰富,而且难以忘怀。我还要感谢2000年至2001年富布赖特社团的同事
们,主要是Sansan Kwan、Kenny Speirs和De-nin Lee。
我还必须感谢台湾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机构——台湾电影资料馆。当然我要感谢
馆长李天礢,主要是因为他在2001年安排了一些关键的访问。然后要感谢黄慧敏,在2000年至2001年间她给予了我持续的支持,还要特别感谢Luo Shu-nan指出了一
些我本来可能错过的相对隐蔽的一手原始资料。我也要感谢资料馆的众多员工,他
们忍受我每天都要出现,特别是那些在前台工作的人们,总是面带微笑为我安排一
天三部片的观赏。资料馆以外,需要感谢的名字多到不可胜数。焦雄屏和黄建业的
支持很重要,他们不厌其烦地帮助我,不仅提供关键的关系,也提供他们自己对侯
孝贤和台湾电影的洞见,他们亲眼见证了这一切。我还要特别感谢陈怀恩、朱天文
和侯孝贤本人,他们每人都在百忙中抽出宝贵时间,分别接受了我长达四个小时的
访问。我同样要感谢黄文英,在我2005年的后续研究之旅中接受了我的访问,她的
谈话发人深省。
我现在的就职单位葛底斯堡学院也值得特别感谢,它无条件地为我提供了教职
和奖学金。我要特别感谢教师发展委员会授予我一项研究与发展基金,让我得以在
2005年夏天重返台湾,真正完成本研究。我也要感谢教务长办公室、杰克·雷恩
(Jack Ryan)、鲍勃·波尔(Bob Bohrer)、玛尔塔·罗伯森(Marta
Robertson)和辛迪·赫尔弗里克(Cindy Helfrich),这里的每一份感谢都有其
原因。我想另外感谢托马斯·居里(Thomas Jurney)、布兰登·库欣–丹尼尔斯
(Brendan Cushing-Daniels)和萨拉·普林奇帕托(Sarah Principato),他们
帮助策划本书的出版。我也要感谢我在葛底斯堡学院的学生们,他们中的许多人没
有意识到我在课堂上对侯孝贤电影(主要是《海上花》)的调查其实是我的研究的一部分。再说一次,我在此不可能点到每一个人的名字,但是我想提一下三个学
生,他们实质上几乎从头至尾是这个漫长历程的一部分:杰克·肯尼迪(Jake
Kennedy)、特里斯坦·门茨(Tristan Mentz)和布朗温·坎宁安(Bronwyn
Cunningham)。他们和其他许多学生让这项研究变得有意义和有价值。
通常最后是更私人地提及那些最亲密的人,他们贡献了恒久的忍耐与支持。但
是我对我的太太Shuchen,要感谢的不止这些。在读研究生之前,差不多二十年
前,我住在台湾并且在那认识了Shuchen。你不但给予了我永恒的爱和一如既往的
支持,还让我看了真正与台湾经验相关的第一手材料。我会永远感激你给予我的一
切,谢谢你和你的家庭接纳我,为我提供真正意义上的第二个家,也让我初步体验
了自身的台湾经验。倘若没有所有这些——主要是如果没有你——一切将毫无意
义。导论 侯孝贤的问题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I) 最知名的格言之一是:东方就是东
方,西方就是西方,两者永远不相遇。今天很多人会把这个常被引用的警句仅仅视
作一种古怪的后殖民残留物,甚至认为自己对这种明显的本质主义、东方主义的说
法免疫。但是我们不得不表示怀疑。
以很多评论家对台湾导演侯孝贤的评价为例。戈弗雷·切舍(Godfrey
Cheshire)认为,侯孝贤摒弃情节和角色,而是聚焦于客体和环境,这是向悠久古
老的中国艺术和文化传统的回归[1]。让–米歇尔·傅东(Jean-Michel Frodon)声
称,侯证明不存在什么中国式蒙太奇(Chinese montage),而是存在一种质疑格
里菲斯(Griffith)和爱森斯坦(Eisenstein)体系的电影样式,它以另外一种
世界观为基础,这种世界观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对立物(即时间空间、现实
表现)[2]。班文干(Jacques Pimpaneau)说,侯面临每一个中国电影人的老问
题:使用一种以西方写实主义为基础的媒介,而中国的戏剧传统与写实主义极端对
立。班文干认为,侯不是第一个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但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在
电影中如此深刻地表达了一种中国文化的世界观[3]。
在关于侯的学术写作中,像这样的文化本质主义论点已经渗透在越来越多的大
同小异的论述中。本书作者甚至曾宣称侯的“历史态度”与“艺术直觉”都是非
常“中国化”的[4]。中国大陆的学者努力强调侯是多么的“中国化”,就更不令人
奇怪了。倪震这样说:“侯孝贤系统的、高度风格化的电影散文,淋漓尽致地传达
了儒家文化的伦理精神,以及典型的东方式的对祖国的情感忠诚。”[5] 李陀着手论
证理解《悲情城市》(1989)是困难的,因为它的“非逻辑剪辑”(non-logical
editing)背离了处于支配地位的好莱坞西方叙事规范[6]。孟洪峰用中国艺术中
的“意境”概念来解释侯孝贤的长镜头静止摄影机远距取景风格,凭借意境,人
物、物体和环境相融于一个连续的空间,因而以一种诗意的方式维持场景的情绪与
感觉[7]。
这些评论无意为帝国主义的“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Burden”)(II) 辩护,而似乎是与此相反,那么这里的问题是什么?首先,每个电
影导演都是一个问题。至少需要解释同一个人拍摄的跨越整个导演生涯的一系列电
影为什么展示了特定的规律性、不规律性——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然而,就侯孝贤
来说,与其说这是一个问题,不如说是一个被误认的问题。所有的人都赞同,他的
作品属于近三十年来最难取悦这个世界的电影。人们假定有一种后现代妥协,那就
是以到达更多观众的名义,或者在某种无人可以明确界定的模糊的“时代精神”的
驱使下,艺术电影和大众电影的类型日益融合,而侯孝贤的作品通常抗拒这种妥
协。我们甚至可以说,侯孝贤的电影大胆反抗常规,更难亲近,更具挑战性,更玄
奥,易于招致“精英主义”、“自负狂妄”和“自我迷恋”等指控。
很多人,特别是评论家认为,这首先是一种文化的问题,其次是地域的甚至是
历史的问题,其实这种认识误入歧途。要成为侯孝贤,看来只需要个人对一种缺乏
生气的文化遗产的高度敏感,就好像它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北京、上海、香港,甚至是一些海外中国人散居的地点。在现有关于侯孝贤的评论文献中,台湾常被视
作背景材料,或者传记的与地理的补白。台湾如果不是某种麻烦,那么差不多变成
了一个意外。杰伊·霍伯曼(Jay Hoberman)在关于纽约举办的侯孝贤作品回顾展
的文章中,曾注意到这一现象在1980年代的含义:“接受新晋的法国或德国导演是
理所当然的事,但要引介一位来自台湾地区这样一潭死水的地方的重要天才,就几
乎得要谢罪了。”[8]在今天,侯孝贤和其他台湾导演在世界影坛已经获得了持续的
赞誉,“一潭死水”这样的词用来形容台湾似乎过头了。尽管如此,在那些崇拜侯
孝贤的人们的心目中,台湾的重要性仍然是次要的。相反,他们常常在侯孝贤问题
的一个现成解决方案中找到求助对象:传统中国文化。
但是文化本身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侯孝贤整个创作生涯的与众不同的轨道(被
认为非比寻常,甚至是前所未有)?1979年,在台湾商业电影工业中,侯孝贤是一
个不知名的煎熬度日的编剧和助理导演,那时的台湾电影工业,就像这个岛本身,在世界舞台上默默无闻,两者都隐现出深重危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89年
侯孝贤站在威尼斯电影节的领奖台上,手中紧握备受尊崇的金狮奖杯,此举不但巩
固了他作为世界电影大师的地位,而且在台湾电影商业领域几近崩溃的时候,提升
了台湾电影在世界电影版图上的位置。到1999年底,台湾岛内电影业日益惨淡,侯孝贤却证明了自己不是昙花一现的现象:一份全球性的电影机构调查结果显示,整
个1990年代全球最佳二十五部电影中,侯孝贤的作品有三部入榜[9];在一次由《村
声》杂志组织的超过五十个评论家参与的评选中,侯孝贤同样被列为90年代最优秀
的导演[10];关于他的书籍也已出版了法文、日文和中文;甚至那些不喜欢他的电影
的批评者也不得不详尽充分地讨论它们。台湾学者叶月瑜(Yeh Yueh-yu)如此概
括侯孝贤的当前地位:“到20世纪末,侯孝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认可和褒奖,任何
一位为西方世界欣赏的当代中国电影人都无法与之相比。”[11]
因为侯孝贤创作生涯中充满转折与转向,我们不得不怀疑传统文化能在多大程
度上解释它:要么这种文化并不是那么没有生命力——考虑到在超过三十年的时间
里有如此戏剧性的变化,要么有其他不得不解释的因素。不过话说回来,也可能是
一种充满活力的、柔韧的文化与许多其他因素相结合,所有这些创造了这个独一无
二的电影整体,唯一没有改变的是这个叫“侯孝贤”的名字,它把这些作品统一了
起来。
文化不但无法单独解释关于侯孝贤的一切,它也提出了几个可能促使我们提防
对类似文化解释过度依赖的深度问题:潜在动机的问题,未经核实的假定的问题,还有最主要的,台湾自身的问题。后者尤其重要,不理解台湾,就无法理解侯孝
贤;没有台湾,就不存在侯孝贤,当然也不可能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侯孝贤。为了
证明这点,让我们逐一分析这些问题,先从隐藏在类似断言背后的动机开始。
有一点得马上指出来,那就是这些观点中的大多数掩饰了潜藏的政治动机,尽
管不是所有的观点都如此。在上述不止一个例子中,我们不得不怀疑,焦点是否实
际上是中国文化,而不顾台湾。也许中国文化就像侯孝贤电影,只不过是达到其他
目的的手段,也就是说为了解构西方电影,特别是好莱坞的霸权。请留意在“东
方”与“西方”之间,一种巨大的对抗如何频繁地被设置:侯孝贤如今代表了一个
勇敢地对抗无处不在的西方体制的东方“他者”形象。这是西方学界关于亚洲电影
研究的老套路:最初研究日本电影,很多人企图将文化议题带至最前沿,其中最著
名的例子是诺埃尔·伯奇(Noel Burch)有时闪现真知灼见,但是常常误入歧途的日
本电影研究:《致远方的观察者:日本电影中的形式与意义》(To the Distant
Observer: Form and Meaning in the Japanese Cinema)。诺埃尔·伯奇的首要目标,他的整个学术研究所显现的,是为了把西方电影中呈现的支配性模式撕
裂。日本电影因而成了这场大的斗争的一个工具,但是它本身不是目的,甚至也不
必然被当成一个值得研究的目的。这种方法和有关第三世界电影的假设可能没有共
同的由头,但有一种近似的主张:反抗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蓄意的,甚至政治
化的、对抗的立场的意图,通过电影手段顽强且自觉地维持自身固有传统的意图,假定另外一种独特的、传统的、源于本土的电影语言要实现的意图[12]。所有这些认
知上的倾向或多或少地被沿用到了关于侯孝贤电影的论述中;有的研究不出意料地
寻找一种能被清晰界定的本土的、“传统的”文化的迹象;这根本就是一种被设置
的用以对抗西方统治地位的“他者”电影。
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学者可能抱有不同的政治动机,它们有意无意地与政府的
官方政策相吻合。中国大陆讨论侯孝贤的学者往往提倡“大中华”的概念,并且常
常显示出民族主义假定。叶月瑜曾回忆一次在北京和一个学者的谈话,这个学者至
少在表面上支持后殖民主义的概念,他曾邀请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和霍米·
巴巴(Homi Bhabha)到北京参加研讨会。当叶问他如何看待台湾与大陆再度统一
的话题时,他礼貌地表示,这是必然而且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13]。因此,当倪震宣称侯孝贤的电影表达了一种儒家“精神”,这种陈述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么单纯,事实上包含了一些政治性的弦外之音。更重
要的是,将侯孝贤简化归纳到传统中国文化上,符合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计划,符
合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的声明。
除了这些主要聚焦于中国文化的不同动机外,还有一些远远超出侯孝贤是否符
合一种现存的文化模式的潜在假定。上述提及的评论家,包括东方和西方的,不但
都假定侯孝贤电影显示了一种独特的“中国风格”,或者说一种独特的“中国世界
观”,也暗中假定一种本质的、统一的、共时的观念——也即非常的“中国”——
是可能的,好像中国文化没有经历毁坏的历史穿越几个时代传承了下来,好像中国
哲学和思想保持了根本的统一并且能被轻易界定——通常是在儒家思想的大标题
下。同样,还有一种假定认为,相比更个性化的和创造性的路径,今天真正的中国
艺术家更重视过去和传统。如果我们希望理解侯,尤其是理解他如何处理他自己的
文化,包括它的传统方面,那么这些假定中的每一种都应该经受检查。即便是对中国文化最草率的评论也认为,相比许多人所认可的中国文化,存在
一种更有活力的、更不易被界定的中国文化。如果一个人对这种文化进行历史分期
——比如,前汉与后汉,佛教引进前后,或者1919年前后——他将发现可以从中挑
选出变化的,甚至自相矛盾的传统。或者认为有其他可行的区分,比如将中国分为
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或者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业余文化和专业文化。这些历史
的、地理的和社会的区分方法都真实存在,中国人长期认可。但是当把侯孝贤定义
为一个本质上的“中国”导演时,上述区分都被忽略了,有时是出于方便。
我们也要考虑下儒家思想自身也改变了很多次。在汉朝(公元前206-公元
220)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以前,它只是一种思想混合体的组成部分,与
之竞争的有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农家,以及因思想过于松
散而得名的杂家[14]。此后,为了维持意识形态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儒家思想一再
自我改造。事实上,在汉朝到隋朝建立之间(220-589)的漫长历史长河中,儒家
遭遇了道教复兴与佛教涌入的围攻,以致很难与强大的后两者竞争[15]。在唐朝
(618-907)——被认为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历史朝代,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也是中
国文明的巅峰——儒家仍然难与佛教相提并论,因为甚至宫廷中也举行佛教仪
式[16]。只有到了宋朝(960-1279),新儒家得以巩固,使得儒家再度获得最高统
治地位,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西方国家的入侵。简而言之,儒家统治了数百年,就
像当年在汉朝时一样。而且,儒家仅仅通过从佛教和道教中增补了许多哲学观点,就做到了这点[17]。换句话说,儒家允许自己不纯粹、自相矛盾,因此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中国的艺术和它的意识形态与宗教思想一样具有历史活力。在传统中国,艺术
家不是一类特别的人群;著名的艺术家文学家通常是儒家系统中享有既得利益,受
过教育的、官僚阶层的精英,至少在年头好的时候是这样。然而,当我们审视在这
种被假定大一统的传统中什么受到保护,甚至赞扬,我们会发现其他传统也在发挥
作用的充足证据[18]。虽然道家思想是一种在根本形式上与儒家思想的等级理想直接
对立的无政府主义者思想,但是没有一种非儒家思想对中国诗人、画家和书法家的
影响超过道家思想。中国历史上一些最受崇敬的艺术家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在中
国,书法可能是最高级的艺术形式,王羲之(303-361)则被认为是最伟大的书法家。他的作品不但代表了当时时尚中的“自发和悠闲淡泊的贵族理想”,而且承载
了深刻的道家根基[19]。竹林七贤是一群成就很高的诗人,他们极不推崇儒家思想,如今被描绘为“个人主义的和特立独行的艺术家”[20]的化身。同样不同寻常的包括
放荡不羁的阮籍(210-263),他可以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女孩之死嚎啕大哭,却胆敢在母亲下葬之日大吃大喝,不流一滴眼泪,这也是冒犯儒家道德的另一种行
径,这些行为令世人目瞪口呆[21]。郭熙(1000年后——约1090年)是中国有着深
远影响的山水画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早春图》描绘了一种道家乐土的景象[22]。总
体而言,山水画在中国画历史上独树一帜,常常描绘出世的隐士,在画面的布局
上,和自然相比,他们微不足道,明显体现了道家思想,虽然后来儒家学者也经常
运用儒家思想来解读山水画。
在盛唐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艺术传统的多样性,特别是两位诗人李白
(701-762)和杜甫(712-770),他们两位拥有的成就就像西方的莫扎特和贝多
芬。然而这两位诗人有着天壤之别[23]。杜甫成为后代在诗歌创作上试图追随的榜样
之一,但是他自身是具有独创性的儒家。与之相反,李白是个信奉道教的叛逆者,一个失败的、嗜酒的官僚。李泽厚形容李白的诗歌是“不可预计的情感抒发,不可
模仿的节奏音调”[24]。
甚至是过去的评论所表达的观念,也包含了一种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文化发展。
关于文学艺术的传统式写作频繁地赞美创造性——而非对传统的模仿——的美德,考虑到它们的儒家信仰,这是令人惊奇的。一个例子是清代学者叶燮(1627-
1703):
诗,末技耳,必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而后为我之诗。若徒以效
颦效步为能事,曰“此法也”,不但诗亡,而法亦且亡矣。余之后法,非废法
也,正所以存法也[25]。
在中国历史上,这实际上不是后来才有的观点。一千多年前,中国最重要的绘
画理论家之一谢赫(活跃于约500-535?)这样评价画家张则:“意思横逸,动笔
新奇。师心独见,鄙于综采。变巧不竭,若环之无端。”[26]苏轼(1037-1101)是中国所谓的学者传统中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他的见解很简单:“诗画本一律,天工
与清新。”[27]跨越多个时代的理论灵活性,具体结果就是中国画是如此的千变万
化,以致最著名的中国艺术研究学者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 Clunas)坚决反对
任何统一的“中国画”概念[28]。
上面我们离题描述了中国思想与艺术的简短历史,目的很简单:只不过为了说
明,说侯孝贤的电影很中国,等于什么也没说。在这种文化多个世纪所展现的成百
上千种层次和面貌中,哪些特别适用于侯孝贤的案例?而且,这个问题因为20世纪
中国历史上的暴力和经常性的残酷扭曲而变得严重。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或
者说时间的)问题,而且是地理的问题。这也就是说,我们不但不能脱离历史,我
们也不能脱离台湾,因为那里正是侯孝贤成长的地方,也仍然是他制作电影的根据
地。如果说中国文化对侯孝贤电影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意义也在于中国文化
在台湾约从1947年(和更早,我们将会在后文分析)到今天是如何过时的。中国文
化在台湾的意义完全不同于它在大陆甚至香港的意义,而且,这种不同是如此之
大,以至于离开台湾,侯孝贤的电影就是不可想象的。
这无疑解释了为什么在台湾批评和学术话语会如此不同。西方人接触台湾人对
于侯孝贤的看法,通常是通过焦雄屏的英文写作,或者是经过翻译的侯孝贤和他的
编剧朱天文的访谈。侯、朱和焦祖籍都在大陆,他们的父母在1949年的大撤退中迁
移来台。然而,无论他们对若隐若现的大陆产生什么样的文化亲和力,他们三人在
台湾长大,这一事实令他们对祖国怀有矛盾的情绪。焦雄屏有时用传统中国文化来
解释侯孝贤[29]。然而焦在台湾有一个不同寻常的身份,作为台湾电影的前辈,由于
她的语言技能和非官方立场,常常肩负提升台湾电影在海外地位的使命。从纯粹的
市场立场考虑,用这样易于消化的文化美味来吊胃口而不是模棱两可,这对她来说
是合情合理的。而且,如果焦雄屏真的信任侯氏风格的“中国性”,那么这充其量
不过是一种偏颇的解释。她也相信侯孝贤是一个现代导演,而且她很聪明地拒绝任
何对侯孝贤的化约式的解释[30]。朱天文似乎使这个议题偏得更远,她宣称,考虑到
中国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和矛盾之处,把侯的风格界定为中国的,是非常困难的[31]。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侯孝贤本人也展现了他的灵活性。在1997年关于他的纪录片
中,奥利维耶·阿萨亚斯(Olivier Assayas)(III)问他到底是一个“中国导演”还是一个“台湾导演”,侯孝贤回答说,人们不能否认他是中国人的文化因素,同时
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个台湾导演[32]。在另一个场合,他还曾解释道,他的目的是创造
一种属于“东方”的含蓄的风格,“东方”并不特指中国大陆、日本或者台湾地区
[33]。表面上看侯孝贤似乎在重提类似前文引述的某种“反转东方主义”(reverse
Orientalism):避免任何单一的或特定的文化标签,他正在为自己创造一种特殊
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故意的暧昧状态,这对一般的台湾人来说是非常典型的。更重
要的是,对台湾的大多数学者和评论家来说,和关于台湾的更直接也常常是历史上
的独特议题(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相比,侯孝贤有多中国成了一个次要议题。对许
多西方和中国大陆的评论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对侯孝贤和他的搭档,以及大多数
关于他的本土文献来说,却是次要的。
无可否认,岛外的一些学者也已开始采用其他的解释路径。这方面的一个重要
人物是台湾出生的学者叶月瑜,她反对任何关于侯孝贤的轻率结论,已经发表了许
多研究侯孝贤的英文论著。英文世界第一个关于侯孝贤的深度资源是一个专门探讨
《悲情城市》的网站,这个网站由叶月瑜与艾贝·马克·诺恩斯(Abe Mark Nornes)
合作运营[34]。这里的关键是他们研究文本与语境能有多深,这对侯孝贤来说是一个
早该存在的项目。当他们分析侯孝贤的风格时,他们总结了各种成见:侯孝贤像任
何亚洲电影人,被想当然地以为吸取了一种含糊的伟大的“东方的文化遗产”。这
种对台湾特性的聚焦在叶月瑜和戴乐为(Darrell Davies)合著的新的突破性著作
《台湾电影导演:一座宝岛》(Taiwan Film Directors: A Treasure
Island)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展。比如说,在侯孝贤早期生涯中,他从一个商业
导演转型为备受电影节追捧的导演,书中描绘了这种转变如何反映了台湾文化脱离
与大陆联系的巨大转型[35]。其他学者也已采用了更鲜明的观点。裴开瑞(Chris
Berry)和玛丽·法夸尔(Mary Farquhar)写道,侯孝贤在《悲情城市》中显现的
历史意识与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直接指导下拍摄的大多数历史片中官方许可的历史编
纂格格不入,是一种次“历史学”,他们论述了这种历史意识是如何完全的不同。
然而他们并不简单描述早于现代国家的某些文化中的差异,而是探索另一种“现代
性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36]。同时,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在他的
近作《聚光灯下》(Figures Traced in Light)中,将侯孝贤纯粹的长镜头风格置于一个基于场面调度的大传统中[37]。波德维尔对侯孝贤的研究就像他早期对日本
导演小津安二郎(Yasujiro Ozu)(IV)的研究一样,他论述了总括性的文化解释通
常是非常肤浅的,它们无法解释我们面前的现象的复杂性。再者,争论焦点不是整
体文化,而是侯孝贤的独特成就以及如何通过特定的方式达到这些成就。中国文
化,主要是传统文化,被发现在解释力方面是不足的。事实证明,这个故事——这
个问题——比探讨文化要有意思多了。
这本专著的目的,不仅是提供一个侯孝贤直至今日的创作生涯的概况,而且试
图解释它为什么会以其特有的方式呈现的大量原因。本书假定侯孝贤有某种能动性
——这是一种电影和文化研究中未必会被接受的观点。然而,本书也承认那是一种
高度受限的能动性,侯孝贤所面对的选择范围常常被每个历史时刻的特殊情况所限
制,由意识形态的、工业的和制度的限制所决定,他一直在这种限制下开展创作。
本研究并不仅仅以传统作者论视角来探究侯孝贤如何反抗这种系统,或者说如何克
服环境局限,更重要的是他如何利用这些环境提供给他的独特的机会。本研究不否
定中国文化的影响,而是试图将这种文化融入现代台湾的背景和历史中来加以考
察。本书甚至不否认这种文化在诸多方面与西方大有不同,但是也认为这种“不
同”并不意味着“他者”,就像任何一种人类文化,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文化,同
样处理生命、死亡、家庭与社会的根本性议题。换句话说,中国文化像任何成功的
文化,是一种集体生存的充满韧性的方式。既然台湾在这里如此重要,那么本书主
要依靠中文的台湾资料,因为岛外几乎不理解关于侯孝贤和台湾电影的本土话语。
然而,最重要的是,本书试图表明在侯孝贤的创作生涯中,台湾是多么的不可或
缺。
本书的结构是简单直接和按照时间顺序安排的:每一章阐述侯孝贤创作生涯中
的每一个独特阶段,有时也论述彻底的和出人意料的断裂。第一章题为“侯孝贤和
台湾经验”,着手解释这个总括性的短语为什么对理解侯孝贤及其电影是关键。当
讨论到1982年,此时在参与台湾新电影之前,侯孝贤导演了他的第三部商业故事
片,本章也概览性回顾了1949年台湾成为国民党最后的和长期的基地之后的发展历
程,继而追溯探讨了几百年来有关台湾(包括中国)的历史争论。(日本殖民统治
时代和紧接的战后时代在第三章中有充分解说。)记住这个大背景,本章还将探讨台湾电影如何与所有这些宏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缠绕在一起。所有这些不但
将为侯孝贤参与台湾新电影后自己精挑细选的主题,也将为他的美学选择,提供揭
示性的背景。
第二章回顾台湾在1980年代发生的戏剧性变化,论述为什么台湾新电影的崛起
不是一个巧合,侯孝贤个人上升至这场运动的巅峰也不是一个巧合。本章介绍了侯
孝贤成长的合作伙伴(包括他的编剧朱天文,她介绍他阅读沈从文的作品)的一
切,他们给他提供了无可估量的帮助,也介绍了他对其他人的帮助,还讲述了他成
功跨越一个总是危机重重的本土电影工业的政治和经济雷区,最后还讲到他通过出
人意料地征服国际电影节领域来克服那种压抑的环境。本章同时概述了他以《儿子
的大玩偶》(1983)为始、以《尼罗河女儿》(1987)为终的新电影作品。《尼罗
河女儿》是部有缺陷的电影,在新电影运动正式结束后不久问世,但是它也为侯孝
贤的下两部突破性作品做好了准备。
第三章在某种意义上论述了侯孝贤创作生涯中的一个“巅峰”,因为主要聚焦
于他的下两部电影《悲情城市》和《戏梦人生》(1993),它们可被认为是侯孝贤
最伟大的杰作。然而,首先,这两部电影提供了一些关键的历史背景,因为它们处
理了台湾历史上两个最关键的时代:日本殖民统治时期(1895-1945)和随后的光
复,它们共同创造了今日台湾的难题。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国民党对台湾
变化无常的统治史上最黑暗的污点。本章还将分析涉及这一著名事件的《悲情城
市》如何成为台湾历史上的文化事件,其影响远远超出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本章还特别关注这部电影本身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它的持续的文化影响。然后
解释相对来说《戏梦人生》却为何几乎没有得到关注,虽然这部作品可能在美学和
历史意识方面都超越了前作。本章最后探讨这两部历史杰作是否代表了一种独特的
历史,它不像任何其他的电影或其他方面的历史,本章以这个问题作结。
第四章涵盖了侯孝贤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他的作品在几个方
面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本章起始于《好男好女》(1995)怎样和为什么代表了侯孝
贤创作生涯中的一个根本性转变,以及下一部影片《南国再见,南国》(1996)怎
样强化了这个转变。不过本章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他1998年的作品《海上花》上,这
是一部视觉密度与复杂性可与沟口健二作品相媲美的影片。而且,因为这部作品是侯孝贤首部场景不在台湾的电影,也因为它的故事发生于19世纪晚期的上海,完全
中国的议题以及侯孝贤的电影如何处理它,就摆在了面前。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
现在变成了,侯孝贤自己的电影风格是否在某种意义上非常“中国化”, 就像很多
人所认为的然而本研究所质疑的那样。
结论部分始于对侯孝贤从《千禧曼波》(2001)到《红气球之旅》(2007)创
作的简短综述,以及这些作品如何加剧了侯孝贤自1995年以来的事业中的无法捉摸
的转变。本章也将尝试把侯孝贤的整体创作生涯放入一个更大的、全球的背景中。
最后的论点是,侯孝贤正如他所变化的那样不可捉摸,但他作为世界上伟大的电影
大师,仍然应该在电影史上获得一席之地,这主要是因为他有幸在一个特定的历史
年代生活在台湾,也因为他在亚洲创造了一种新的电影传统,现在整个亚洲地区有
多个电影人在践行这一传统。
在这里最后需要强调一个词汇,那就是这个问题的独特性。接下来的内容将证
明侯孝贤的电影是独特的,因为他发现他所处的环境是独特的,对任何一个与众不
同的导演来说这点都是成立的。也许这里根本的教训是任何导演的本土因素,不管
他们最终获得了多大的全球性成功。每个导演都是从某处起步;没有导演刚起步就
可以敲开电影节的大门,然后说他或她仅凭一张白纸就可以进入。至于侯孝贤,有
人似乎对他来自台湾困惑不解,但是本研究的目的正是为了解决这个特别的困惑,正是为了彻底地说明,当我们仔细查看最近三十多年来的台湾本身,最重要的是台
湾电影和整个台湾社会走过的旋绕的、连锁的道路时,侯孝贤的创作生涯所经历的
迂回曲折的道路看起来就不奇怪了。这个故事不是一个难解之谜,而是变成了一个
不同历史时刻适时共生的舞蹈,变成了一个充斥着特定的地理政治和环境因素——
它们中的许多纯粹是台湾的——的故事。这最终是一个台湾的故事,一个应该比以
前更严肃对待的故事。
注释
[1]Godfrey Cheshire, “Time Span: The Cinema of Hou Hsiao-hsien,”
Film Comment, vol. 29, no. 6 (NovemberDecember, 1993): 56–62.
[2]Jean-Michel Frodon, “On a Mango Tree in Feng-shan, Perceiving theTime and Space around Him,” in Hou Hsiao-hsien侯孝贤(Chinese Edition of
French Original by Cahiers du Cinema)(Taipei: Chinese Film Archive,2000): 22–25.
[3]Jacques Pimpaneau, “The Light of Motion Pictures,” in
Cahiers(Chinese Edition): 65–68.
[4]James Udden, “Hou Hsiao-hsien and the Poetics of History,”
Cinemascope, 3 (Spring, 2000): 51.
[5]Ni Zhen, “Classical Chinese Painting and Cinematographic
Signification,” Douglas Wilkerson, trans., in Cinematic Landscapes:
Observations on the Visual Arts and Cinema of China and Japan, Linda
Ehrlich, David Desser, ed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75.
[6]Li Tuo, “Narratives of History in the Cinematography of Hou
Xiaoxian,” Positions, 1: 3 (1993): 805–14.
[7]Meng Hongfeng孟洪峰, “A Discussion of Hou Hsiao-hsien's Style,”
in Passionate Detachment: Films of Hou Hsiao-hsien戏恋人生: 侯孝贤电影研
究,Lin Wenchi林文淇,Shen Xiaoyin 沈晓茵,Li Zhenya李振亚,eds.
(Taipei: Maitian, 2000): 48–49.
[8]Jay Hoberman, “The Edge of the World,” Village Voice(July 14,1987): 62.
[9]Peggy Chiao 焦雄屏,“When Will Taiwan Keep Step with Taiwanese
Cinema?” Commonwealth Magazine天下杂志 (January 1, 2000): 123.
[10]“First Annual ‘Village Voice’ Film Critics Poll,” Village
Voice(January 4, 2000): 41.[11]Yeh Yueh-yu,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Hou Hsiao-hsien's
Films,”Post Script, vol. 20, nos. 2 3 (WinterSpring Summer,2001): 68.
[12]这种批评范式的最佳总结仍是罗伊·阿姆斯(Roy Armes)的《第三世界电
影制作与西方》(Third World Film Making and the West,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13]Yeh Yueh-yu叶月瑜,“Taiwanese New Cinema: Nativism's
‘Other’,” Chung-wai Literary Monthly中外文学,27: 8 (January, 1999):
60.
[14]Wilt Idema and Lloyd Haft, A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85.
[15]艾德玛和哈夫特认为“玄学”是一个误导性术语,最好是称呼其为伴随
《庄子》和《易经》的普遍可获得出现的儒家思想的再造。相反,亚瑟·F·赖特在
他的《中国历史中的佛教》中说,随着汉朝灭亡,儒家思想“完全名誉扫地”,从
公元250年开始道教是统治性哲学。参见Wright,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New York: Atheneum,1969): 17–24。无论怎样,为了重申它的意识形
态霸权,儒家不得不彻底调整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这点是很清楚的。
[16]Wright, 67–70.
[17]John Fairbank, Edwin Reischauer and Albert Craig,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8): 149–50.
[18]亚瑟·F·赖特认为,为了这种系统生效,这些学者不只是从孔子作品中发
展出一套广泛的关系——人类和其他事物——系统,形成一个赖以统治的包罗万象
的系统,是势在必行的。
[19]Craig Clunas, Art in China(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136.[20]Patricia Ebrey,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1996): 89.
[21]Ibid., 88.
[22]Clunas, 54–56.
[23]Li Zehou, The Path of Beauty: A Study of Chinese Aesthetics(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54.
[24]同上书,第142页。然而李白遵循的是中国艺术中一种非常长久的传统:对
酒的喜好,甚至根据杜甫的说法,他是“酒中仙”(参见上书,第141页)。应该注
意,侯孝贤也是这种传统的行家里手,尽管他常常添加卡拉OK歌唱的现代感。
[25]Ye Xie, “The Origins of Poetry,” in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Stephen Owen,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511.
[26]Hsieh Ho, in Early Chinese Texts on Painting, Susan Bush, Hsio-
yen Shih, e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30.
[27]Su Shih, in ibid., 224.
[28]Craig Clunas, 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13–16.
[29]Peggy Chiao 焦雄屏,in introduction to Passionate Detachment, 26;
“Great Changes in a Vast Ocean: Neither Tragedy nor Joy,” Performing
Arts Journal, vol. 17, no. 5051 (MaySeptember, 1995): 52.
[30]Peggy Chiao, interview by author, March 10, 2002, Middleton,Wisconsin.
[31]Chu Tian-wen朱天文,interview by author, June 2, 2001, SogoDepartment Store Coffee Shop, Taipei, Taiwan.
[32]Hou Hsiao-hsien, HHH: A Portrait of Hou Hsiao-Hsien, prod. by
Peggy Chiao and Hsu Hsiao-ming, dir. by Olivier Assayas, 96 min., Arc
Light Films, 1997.
[33]Hou Hsiao-hsien 侯孝贤,interview by author, June 20; 2001,Sinomovie Company Office, Taipei, Taiwan.
[34]Abe Mark Nornes and Yeh Yueh-yu, A City of Sadness, website at
http:cinemaspace.berkeley.eduPapersCityOfSadness.
[35]Yeh Yueh-yu and Darrell Davis, Taiwan Film Directors: A Treasure
Island(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3–76.
[36]Chris Berry and Mary Farquhar, China on Scree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29–38.
[37]David Bordwell, Figures Traced in Light: On Cinematic
Staging(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186–237.
(I)拉迪亚德·吉卜林(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1907年获诺贝尔文
学奖。本书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注,所有尾注均为作者注(统一附在各章末尾),以
下不再指出。
(II)拉迪亚德·吉卜林的一首诗名,指西方有责任治理落后的东方,因被解读
为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而备受争议。
(III)阿萨亚斯(1955- ),法国影评人与导演,作品有《清洁》、《夏日时
光》以及纪录片《侯孝贤画像》等。
(IV)小津安二郎(1903-1963),日本电影大师,代表作有《东京物语》、《晚
春》、《秋刀鱼之味》等。第一章 侯孝贤与台湾经验台湾是一个独特的地方,产生了独特的电影,侯孝贤及其作品就是它最无法磨
灭的产物。我们应该提防任何笼统的用以解释这种地缘政治和电影特性的措辞。不
过,这里有一个相近的概念:“台湾经验”。这个术语的起源不可考,但很显然得
到广泛使用是在1980年代,并且在今天的台湾仍然是个习惯的用法。有一些书籍致
力于解释这个术语[1]。陈儒修关于台湾新电影的重要研究有一个揭示性的标题:
《台湾新电影的历史文化经验》[2]。对不知情的人来说,把“历史”、“文
化”和“经验”相提并论可能会感到奇怪。然而,在台湾,“经验”这个词最重
要;在台湾,它是独一无二的经验,以原始的、不定形的然而也不可否认的人类形
态,取代了所有锻造一个固定的地区和种族身份的努力。
在台湾,流动的共同的经验压倒所有固定的经验,这不是理性思维的产物,而
是台湾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事实。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
为,资本主义、印刷技术和教育体制一起创造了一种“民族”凝聚感,因为人们现
在会认同他们至少可以想象的另外的大群体,民族主义由此变得可能[3]。而且大多
数人或多或少相信那些“想象的共同体”的本体论,它们构成了他们分享民族身份
感的基础。然而,在台湾,大多数人并不这样。台湾不断发展变化的环境迫使它的
居民高度警惕任何事物的想象性,任何标签都似乎是幻影。数十年来他们被不断地
重复告知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们是中国人。今天他们更有可能被某些人
告知他们根本不是中国人,而是“台湾人”。这些争论要么基于文化要么基于历
史。然而,鲍梅立(Melissa Brown)在她的台湾身份问题调查研究中发现,这些
并不能从根本上统一一个族群或民族。“不如说,身份以共同的社会经验,包括经
济和政治经验为基础,得以形成并巩固。”[4]作为这些经验的结果,民意调查结果
始终显示,台湾的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致力于避免所有的解决方案,甚至标签——
称他们为中国人和台湾人,而倾向于既不统也不“独”[5]。台湾人摇摆不定,作为
一个整体固执地寻求一种中间状态——只要有可能就永远维持现状——好像他们永
远把牌紧紧攥在胸前,永远不把牌亮给世人看,永远不会被别人操纵。这种共同的
矛盾是一种不断发展的艺术,台湾这座岛屿就是以之为基础。这该归咎于谁?也许和每一个人有关:统治台湾地区超过半个世纪的国民党,明朝和清朝,欧洲人,日本人,美国人,当然还有大陆的共产党,更不用说目前要
求“独立”的本土政客。所有这些因素使得台湾经验本身成为一个变化无常的老
师。台湾无法靠自己生存,这是一个实际上处于夹缝中的岛屿,常常受制于历史偏
见,比如台湾只不过是一个战略的、地理政治的工具,只不过是一些据说更强大的
东西的附属物。冷战实际上创造了一座冰宫,今日的台湾不知何故还没有“融
化”到如它常被预测的那样被遗忘。相反,尽管困难重重,它幸存了下来,甚至更
加繁荣。
侯孝贤在1980年代声誉鹊起不是巧合。他将这种宏大形势转化为不可磨灭的电
影表达方式,它们捕捉、传达,甚至体现那种共同经验难以捉摸的抓不住的外形
——没有固定的身份,没有明晰的修辞,没有确切的东西抚慰人心。起初,侯孝贤
专注于聚焦1950年代后的台湾经验,因为他直接体验了这段历史。然而,那种奇特
的形势的源头得追溯到几百年前。不过,侯孝贤后来的创作与维特根斯坦式的历史
选择和忽视的艺术相违背:他的历史电影不是聚焦于关于台湾的标准的历史说法,而是主要聚焦于那些让这些说法最复杂化的年代。我们将简要地探讨这些“说
法”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台湾形成今天的样子。1949年前的历史“说法”
最早到达台湾的大陆人通常是周期性地、非法地赴台,数量也少。他们的人数
远远少于当时的土著人口。由于受到17世纪荷兰人在岛上建起殖民地的刺激,更多
的大陆人来到台湾永久定居[6]。和20世纪局势惊人相似的是,很快大陆发生的政治
事件波及了台湾。在明朝败亡的时候,明朝将军郑成功(人称“国姓爷”)远道而
来并且赶跑了荷兰人,这一丰功伟绩为其赢得了“台湾之父”的名声。然而郑成功
的眼睛只盯着返归大陆,这一目标也被他的继承人所延续。后来郑成功的儿子(V)抵
抗清王朝失败,台湾于1684年被清政府纳入版图[7]。
此后最后的中国王朝统治了台湾两百余年。在那些年移民台湾也仍然是非法的
或者说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且看上去好像最腐败无能的官员被派驻那里。每个官员
都短时间服务,任期三年,没人把台湾当作自己的家。在清朝统治的两百一十一年
里,当地人——无论大陆移民还是土著居民——抗议清王朝多达七十三次,另外诉
诸暴力的对抗不下于六十次[8]。台湾成为一个不法之徒的地方,吸引来自大陆的拓
荒先锋,他们渴望逃离大陆的环境,主要是为了逃离福建省周边蔓延的穷困和贫瘠
的土地。这些有独立意识的移民反而被那些留在大陆的人们瞧不起。台湾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在整体上已与大陆背道而驰。清政府没有做任何事来缓和这
种局面;事实上,他们的政策只是拓宽了裂缝[9]。
到了19世纪,当清朝统治者发现外国人图谋台湾,他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这个
岛。首先,北京政府取消了所有的移民禁令[10]。1885年,在抗击法国侵略后,清
政府决定在台湾建省,而此前台湾仅仅只是福建省的一部分。台湾第一次有了一个
能干的有远见的治理者,他叫刘铭传,他不仅巩固统治,而且开始建造包括铁路和
电力在内的公共基础设施。然而,1891年刘铭传离开,他的所有现代化计划都莫名
其妙地被废止了。台湾再次被严重忽视[11]。
1895年,清政府输掉了与日本的甲午战争。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将台湾与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1945年,台湾光复。然而,在非常短暂的有序统治之后——事实上在几个月之
后——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却导致事与愿违:一个新的和更持久的台湾身份深深地烙
印在血泊中。这一切随着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爆发达到高潮,我们将在第三章
详细讨论。现在已可说,随着导致数千人死亡的大暴行发生,新的统治者的所作所
为比其日本前任更像殖民者。国民党有失体统的、残酷的行径在大陆被广泛报道。
很快“二二八事件”成为全中国反抗国民党的一个焦点,加速了它仅仅两年后在大
陆的最终失败[1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事件实际上在台湾创造了一个自制的敌
意角落,国民党1949年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将发现这点。
所有这些变幻莫测的历史转折之后,“台湾人”这个术语到底意味着什么?这
要看情况而定。“台湾”和“台湾人”已经变成了反映一定的地理政治现实的便利
术语,但那些曾经统治这个岛屿的人或那些横跨海峡想要有朝一日统治它的人并不
乐意接受。“中国人”和“台湾人”含混的语义学界限,被更进一步的、本土的复
杂情况搞乱了,它很难用英语来澄清。自从1940年代末起,本省人和外省人制造了
分化。外省人是指祖先在大陆但是好几代在台湾生活的人,他们几百年前就扎根在
台湾。由于历史原因,这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包括不可忽视的客家人,他们占
少数,有自己的方言和文化,常常和占多数的鹤佬人发生冲突。鹤佬人主要由福建
移民构成,他们讲台湾方言,近似直接跨越海峡的福建方言。与之对比的是,外省
人是最近的到来者,他们中的一部分是1945年以后来到这里,大部分人是在1949年
国民党把大陆输给共产党后来到这里。大体上来说,本省人今天构成了岛上人口的
百分之八十五,而来自大陆的外省人接近百分之十四。现在人口中剩余的百分之一
大多数是原住民,而且数量日渐减少。
无论如何,1949年后,岛上的外省人和本省人都被切断了和中国大陆的联系,带着从来没有愈合的、暗中化脓的历史创伤,被迫生活在一起。在最初试图为他们
的行为辩护后,在之后接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官方简单地否认1947年的血案曾经发
生。具有尖锐讽刺意味的是,当台湾变成国民党最后的堡垒,国民党当局如果要继
续生存下去,不得不根本调整它的姿态。“二二八事件”后国民党缺乏真正的合法
性,它是国民党最终从事改革的关键要素,它导致了一个复杂多变的档案,就像对先前日本统治的记录。台湾的本省人是改变的首批接受者,改变的后来受益人,也
是改变的最终主人,改变首先在经济阵线显现成果,最终在政治和文化阵线结出果
实。这些创造了我们今天认识的台湾:能量充沛的经济,世界上最民主的地区之
一,还有富有活力的文化,包括一个如今拥有世界声望的非同凡响的电影导演。侯孝贤与战后台湾经验
侯孝贤真正参与这种局势是在1949年。西方人和大陆人对侯孝贤都有错误的看
法,但台湾人也有自己的误解。直到近年,最普遍的本地误解是侯孝贤是一个本省
人。他已经树立了这样一种公众形象:他讲流利的台湾话,讲带浓厚台湾口音
的“国语”。而且,他的电影似乎完全表达身为台湾人——其中的大多数是本省人
——意味着什么。因此当发现侯孝贤是一个1947年出生在大陆的外省人,当他只有
两岁的时候才来到台湾时,很多台湾人很吃惊。侯孝贤的家庭是客家人,客家人是
中国一种特殊的四处迁徙的少数族群,在台湾,1895年前经常受到占多数的其他汉
人的骚扰[13]。不过,侯孝贤在台湾南部长大,主要在本省人中间。在他年少的时
候,父亲去世了,这使得他不必遵循那个年代孩子的行为规范,而可以在外四处游
荡。这些随心所欲的闲荡促使他在年轻的时候每天都讲台湾话,这被证明具有决定
性的影响。
因此,侯孝贤人生的多数时候都将认同本省人,虽然他和那个族群其实没什么
关系。这表明他的实际经验,不是血统,也不是任何固有的文化意识,在多大程度
上决定了他的身份和世界观。同时身为客家人和外省人,只是增加了侯孝贤的敏
感。朱天文,著名作家和侯孝贤的编剧,解释了为什么她那一代人——父母至少有
一方来自大陆,然而成长在台湾——会成为文化领域台湾经验的重要支持者。在台
湾他们只是听说大陆,可是她后来去了那里发现它是想象的。然而,他们亲身体验
的在他们眼前的是台湾,一个完全不同于关于大陆的壁炉边故事的世界。数代台湾
人把身边发生的一切视作理所当然,而那种流散的心理焦虑对他们来说不存在,只
证明是肥沃的艺术土壤[14]。
对于像朱天文这样的作家和像侯孝贤这样的电影人来说,台湾实际上成为一个
无底的题材库。但是侯孝贤见证和经历了什么?简而言之,变化:政治的、经济
的、文化的和电影的变化。当侯孝贤自身在1980年代成为一个导演的时候,所有这
些变化要么正在发生,要么将要发生。侯孝贤与战后政治经验
侯孝贤的父亲是一个低级官僚,来到台湾后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他过早地离
世。缺少证据表明侯孝贤和他的家庭直接受到战后政治的影响。不过,政治在战后
的台湾无处不在,潜伏在日常生活的背景中。也许并不奇怪,这种情形在侯孝贤电
影中同样真实存在,至少那些电影涉及了政治:《童年往事》(1985)、《悲情城
市》和《好男好女》。侯孝贤常常因为他的政治矛盾和逃避而受到批评。甚至很少
有人能够指出侯孝贤在台湾真实的政治光谱中的位置,它不是“右对左”(区别在
台湾意义不大),而是“独立对统一”。大多数台湾百姓对政治和政客都没什么好
感,这是国民党五十年压迫性统治的一个直接结果。大多数本省人甚至有一个共同
的说法:“卷入政治就像吃狗屎。”[15]
尽管国民党当局的基本意识形态前提是作为“中华民国”的政府,声称代表所
有中国人,但是再多的宣传也无法掩盖它仅仅统治台湾和其他一些小岛屿的事实。
事后来看,国民党不可能永远维持这种局面,这是足够清楚的。另一方面,也存在
一些有利于国民党的历史机遇。当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残兵败将1949年撤退到台湾
时,看上去似乎日暮途穷。这个党已经失去了太多的公信力,以致美国也切断了对
其支援。大陆共产党已经草拟了计划,准备很快解放台湾,一劳永逸地消灭国民
党。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所有这些都改变了。朝鲜战争打响后两天,美国派
出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朝鲜冲突同时终结了共产党制定的进攻这个岛屿的计
划[16]。台湾再次经历又一个戏剧性改变:它成为国民党领导下的冷战前沿的堡垒。
紧张的冷战气氛弥漫了1950年代,1958年8月随着大陆在金门与马祖上空的所
谓“炮战”而达到高潮,两地均在福建省的视线之内。蒋介石希望美国直接参与对
大陆方面的攻击,但美国人仅仅间接提供帮助,甚至曾经试图劝说国民党放弃对这
两个岛屿的控制,不过徒劳无功。最终,这两个互不信任的盟友在10月达成了一个
折中方案:台湾不再进攻大陆,以此作为对金门和马祖持续控制的交换。大陆的共
产党表示抗议,但有些人推断毛泽东私下同意国民党控制那两个岛屿。因为它们距离大陆很近,这有助于缓冲任何“台独”的企图[17]。结果就是维持到今天的僵局:
金门和马祖仍然在台湾而非大陆的控制之下。
紧张的、恐慌的冷战气氛非常便于蒋介石寻求控制整个岛屿的绝对权力。国民
党的较小的、地方的部门都是较大的部门不可摆脱的部分,而较大的部门直接通向
由蒋介石亲自控制的中央委员会[18]。这种制度重组与现行法规相吻合,比如1948
年颁行的“动员戡乱法”和“戒严令”,后者于1949年6月(VI)宣布,直到1987年才
被废除。前者极大地增强了蒋介石的“总统”权力,允许他消灭任何形式的异见。
那个1948年的法令,和“戒严令”一起,形成了“白色恐怖”的基础。事实上,台
湾变成了一个以“国防会议”(后来改称“国家安全会议”)为中心的警察军
人“地区”,通过“国防会议”这个机构,蒋介石和他的儿子蒋经国控制了所有的
至关重要的信息和情报搜集[19]。
冷战充当了把世人的注意力从“台独”的可能性转移开来的现成的烟幕。事实
上,国民党的很多政策宣称的意图是对抗共产主义,然而实际的目标包括那些主
张“独立”以及对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兴趣的群体。不过,台湾本土针对国民党的反
抗可以追溯至1947年,特别是在台湾流亡者中间。在台湾本身内部,反抗发展得相
对缓慢。尽管如此,即便在1950年代也有人开始质疑“中华民国”的前提。第一个
标志是《****》杂志,它最初支持国民党,最终却激烈批判国民党,结果被停
刊[20]。当十年过去,在1970年代,第二波反对浪潮兴起并且势头增大。原因非常
清楚:十年消逝了,合法性,本已是让国民党头疼的麻烦,结果却变得更加糟糕。
1972年国民党当局一失去联合国席位,就更加无法遏制反抗。而且,蒋介石自己死
于1975年,那时有效控制权已经移交给了蒋经国。
从表面看,这个儿子似乎和他的父亲是政治同类。1972年之前,蒋经国已经是
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关键角色,事实上他通过大量的关键职位来为他的父亲掌管台
湾,这些职位大多数都在情报搜集部门和军队中。他于1970年代跃居政治一线,也
仍然以有时反复无常的方式利用集权的制度。但是,蒋经国从来没有分享他父
亲“收复”大陆的痴心妄想,这是一个关键的不同。相反,他着重在台湾推行实用
的政策,启动了促进台湾现代化的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最重要的是,蒋经国启动了“本土化”进程,允许本地台湾人进入管理层,也允许他们加入国民党[21]。
从长远来看,这对台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部分原因是它意味着1988年对蒋经国接
班人李登辉的包容,而李是本省人。
在1970年代的新的政治气候下,产生了“党外运动”。这场运动起初包括非国
民党籍的候选人,他们参与地方选举竞逐,尽管国民党的作弊普遍存在,但是他们
有时也会获胜。1978年12月美国撤回对“中华民国”的承认(VII),一年后在南部台
湾运动就达到了最高点。所谓的“美丽岛事件”,有时也被称作“高雄事件”,是
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后首起公开对抗国民党的抗议活动。“没有党名的政
党”的领导者们在1979年12月10日于高雄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人权示威,那天是国
际人权日。大批高雄警察出动,以武力威胁民众,人们没有屈服,甚至冲破了警方
的防线。看到这一切,一个目击者说:“历史有了一个新的开始。”[22]它开启了
1980年代的历史闸门。
侯孝贤完全没有掺和这些事。1970年代,侯孝贤正在台湾电影工业中努力工作
缓慢地往上爬,在此过程中,没有证据表明他站在任何政治一方。那个时期看不出
来他会处理他最终卷入的任务、议题和争论。但是在台湾事情总在发生变化——甚
至在一夜之间发生。侯孝贤与战后经济经验
在海外,“经济奇迹”毫无疑问是最知名的台湾经验,侯孝贤的电影偶尔也间
接提及它。甚至侯孝贤自身的经历也部分地反映了这点。电影似乎是一种错失了经
济奇迹的工业。不过,在冒险从事他自己实质上的作坊式电影制作之前,侯孝贤在
商业电影工业干了超过十年。侯孝贤现在运作一项小范围的事业,主要为出口创造
产品,尽管对他来说那是一个利基市场,而不是一个大规模市场。这在台湾很有代
表性。
人们经常忽视经济奇迹与“二二八事件”之间有怎样的直接联系。1947年的反
抗和随后的血案,主要根源就是经济。只要有可能,国民党就竭力维持它在台湾的
绝对权力,当环境所迫,它也只是缓慢地不情愿地交出权力。但是在经济领域,国
民党几乎从一开始就交出了权力,因为它真的别无选择。对台湾来说这是第二次现
代化,这次现代化远远超过日本人所做的。对国民党来说,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现代
化。他们再也没有拘囿于饱受战争摧残的大陆的、农业的思维。相反,他们很快学
会依靠国际贸易。
近几十年来台湾经济增速惊人,这使得人们容易遗忘1950年代对台湾经济的预
测是贫困的,特别是突然从大陆涌入一百五十万人口。台湾有一个不利的人均占地
比例、极少的资本资源和一个名誉扫地的领导阶层,所有这些导致了台湾在外国经
济学家眼中的“经济瘫痪”的状况[23]。然而,尽管从如此糟糕的起点起步,台湾却
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发展纪录。从1953年到1964年,工业部门每年以百分之十
二点二的增速发展,在那个时期台湾从美国获得了充足的支援。美国援助终止后,台湾经济继续急速前冲。从1965年到1975年,工业部门的年增速高达百分之十六点
一[24]。从1963年到1980年,台湾经济整体,包括相对来说停滞不前的农业部门在
内,每年平均以百分之十的增速发展。等到经济完全发展成熟,从1981年到1995
年,台湾仍然保持了年均百分之七点五的增速[25]。这种发展形势中最重要的是老百
姓在多大程度上受益。1950年台湾人均收入和大陆人均收入一样。到了1980年代,台湾人均收入是大陆人均收入的二十倍[26]。
国民党推行的几项特殊政策也促进了这一巨大发展。彻底的土地改革将土地资
本转变为商业资本,为经济发展打好了基础。岛上的本地土地拥有者没有反抗,因
为“二二八事件”的教训记忆犹新。但是,与此同时,国民党在主要的官方产业中
给予这些失去土地的地主股份,将他们变为资本家,从而有效地结束了封建制度
[27]。台湾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关键是私有化[28]。总的来说,当局控制公有产业,而
允许私有产业兴旺发展。到1959年,私人运营的工业企业比例已经超过了官方运营
的企业[29]。1954年私营企业的工业生产仅占百分之四十三,到了1972年比例跃升
至百分之八十,到了1980年代中期更达到百分之九十,这使得以任何标准来考量台
湾,它都是世界上私有化程度最高的经济实体之一[30]。台湾经济高度分散化,由中
小型企业占支配地位,其分散程度之高在世界上绝无仅有。1981年,百分之四十五
的制造业由中小型企业完成。在台湾经济最成功与最有活力的部分——出口制造业
——中,这一比例跃升至百分之六十八[31]。这个政策的主要受益人是本省人,而
不是那些新近来自大陆的“精英”。尽管制定了严厉的教育、政治和文化政策,但
是外省人没有像1947年所做的那样来阻挠那个对立的多数族群,他们既没有胆量也
没有能力。
国民党当局也引导经济向出口发展。台湾是严重的贸易主导型经济:到1980年
代,进出口额占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五,当你意识到在日本这一数据仅是百分之
三十,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吃惊的数字[32]。回到1950年代,国民党当局利
用了很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通用的所谓“进口替代政策”。这主要指通过贸易
保护措施集中发展岛内市场。这项政策在台湾获得了非比寻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这是一个主要局限于生产资料工业的临时措施。而在消费品、半成品和制造
业领域,总体来说几乎所有的发展都源自满足岛内需求,无一源自进口替代。与之
相对的是,在菲律宾,上述四个领域接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成长归因于进口替
代,仅仅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用于满足国内需求。在菲律宾,这种状况长期存在于脆
弱的工业中[33]。很快,国民党当局就通过鼓励出口超过进口的方式,引导台湾朝向
外向型经济发展。1959年,他们废除了双重汇率制,实行货币贬值,降低关税和制
定法律、规则和税率,所有这些都鼓励出口[34]。也许国民党当局作出的其他决定都没有如此显著地提升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
总而言之,虽然台湾本省人数十年来都否认获得了政治好处,但他们已经获得
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即便是在冷战的高峰期。本省人尽最大可能利用这一经济回旋
余地,甚至到了蔑视通常拙劣地强迫执行的法律界限的地步。结果是,台湾更像是
在地上运转的地下经济实体。国民党当局维持对银行业的严格控制,对一般台湾人
来说贷款是困难的。为了逃避这点,台湾人成立了成千上万的专门的民间信用社团
(标会),来筹集他们自己的资金。这是一种明显具有风险性的投机,如果任何组
织的所有成员都值得信赖的话,它可以赚得盆满钵满[35]。许多企业公开地无证经
营,大多数保存两本账簿,一本是给自己看的,另一个缩减的版本是为税务员准备
的。一般来说人们倾向于向当局瞒报收入,这导致真实的人均收入很难统计。到
1980年代,台湾富得遍地流油,这主要是辛勤工作和无视官方阻挠的结果。国民党
当局注意到总体的民众不服从,明白它的唯一选择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与此
同时,当这个经济奇迹已成既定事实,侯孝贤和1980年代新电影的其他成员,开始
探讨所有这一切对生活在这个岛屿上的人们真正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答案显露出重
重矛盾。侯孝贤与战后文化的缓慢解冻
如果说侯孝贤与战后政治和经济的联系更间接的话,那么对战后文化来说就不
是这么回事了,在战后文化环境中,侯孝贤成了一个中心人物。提及台湾,大多数
人脑海中第一个想到的是经济,接下来可能是政治。相反,台湾的文化通常是人们
事后才回想起来的东西,即使那样,它还常常被遗忘,要么被当作不存在,要么只
不过被当作中国文化的派生物。然而,对最近二十年了解国际电影节情形的人们来
说,情况恰是反过来的:当他们想起台湾,他们很可能首先想到侯孝贤,另外还有
杨德昌和蔡明亮等人。他们常常漏掉的是作为文化现象的侯孝贤与台湾这些大的政
治和经济力量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的密不可分。
自从1949年以来,台湾文化一直处在上述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夹缝之间。台湾的
文化起初是国民党当局严密控制下的一个向心性力量,只是到后来才变成了一个离
心力量,现在扮演着当局做不到的非官方的“外交”角色。除此之外,台湾形势的
不稳定特性使得台湾文化更加富有活力和创造性。侯不是这种现象的唯一证据,但
是最好的之一。
而且,这种文化活力产生于可以想象的一些最恶劣的状况。在1949年到台湾的
流亡者中,有一些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大陆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来到台湾不是因为害
怕共产党,也不是因为效忠国民党。这群人鱼龙混杂,他们为局势所迫,只能在这
个岛上生存并在此抚养自己的孩子,也只能慢慢意识到再也回不去了。然而,很长
一段时间里,国民党严格限制他们可能表达的关于这个陌生的新世界的看法。借助
对文化、教育和媒体的垄断,国民党致力于将中国身份强加在当地人身上,而且严
禁一切将台湾特殊化的东西[36]。与此同时流行一种看法,国民党失去大陆是因为宣
传失败,而不是政策失败。在台湾,国民党不想重蹈覆辙。国民党将文化视作决定
生死的关键要素。
国民党当局垄断控制了所有的文化领域,在年轻人教育问题上尤其严厉。“三
民主义”是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渗透于大学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一个主要的组织是所谓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成立于1952年。这个组织开展针对年轻人的
政治活动和军事训练[37]。它的用意在于紧盯着不过一百英里外的“共匪”,同时也
是一个大野心的一部分,旨在消灭任何将台湾特殊化的东西。这个隐性策略的第一
线还有其他的教育政策:1951年起,所有的课程都必须用“国语”教学,本地的台
湾孩子要是在教室里说了一个台湾方言的字眼,都要受到严厉的处罚[38]。这样的措
施一直施行到1970年代。(侯孝贤自己能讲一口流利的台湾方言,不是习自课堂,而是习自市井。)
当局也直接指导文学和电影创作。1950年,“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包括十个
成员组织(VIII),其中一个用来管理电影。这导致了充斥着“反共”主题,同时颂扬
孙中山“三民主义”优越性的宣传艺术的泛滥[39]。1954年当局进一步强化钳制,那时“中国文艺协会”宣布了一项叫作“文化清洁运动”的政策。这场运动声称是
要清除所有的“赤色的毒”(共产主义)、“黑色的罪”(对社会阴暗面的悲观看
法)、“黄色的害”(纵欲、色情)。这三种不受欢迎的“颜色”反过来又构成此
后所有当局审查的清扫基础,1955年这一切由极其重要的“新闻局”接管[40]。
1960年,这个由“新闻局”传承衣钵的最高文化机构,在其成立十周年纪念日,重
申了反对“赤色”、“黑色”和“黄色”的原则[41]。
不过,这是威权主义的(authoritarian)控制,而不是极权主义的
(totalitarian)控制。裂缝开始在不同的文化领域显现,最终也出现在电影领
域。尽管当局控制严厉,在早年却有与台湾相关议题的现实论战,只要论战不是公
开地支持左派思想或者“台独”。论战在“东方”与“西方”、“本土文
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展开。此类论战的一个共同主题是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关
系,多数探讨现代世界中的儒家思想的意义。很多台湾的知识分子都对他们所谓
的“现代新儒学”颇感兴趣。这些知识分子一致认为儒学将不得不改造以适应现代
社会,需要从其他传统,包括佛学和西方哲学中吸取养料。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
牟宗三,他试图在儒学和康德的道德哲学间发现一种联系[42]。然而,其他的许多人
都想象一种截然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它只为全部的传统提供很小的空间。现代儒家
学者发现他们自己与《****》群体和台湾日渐流行的存在主义(大多数是萨特
的思想)格格不入[43]。1980年代之前,台湾真正的文化先锋毫无疑问是文学,我们可以在两个重要运
动的激烈论战中看到其中最优秀的一些代表,这场论战是现代主义者(现代文学)
与所谓的本土主义者(乡土文学)的论战。当论战局限于哲学家和其他学者圈子,它似乎没有偏离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争议。但是一旦论战渗透到文学领域,其他信息
就开始几乎不知不觉地蔓延,包括一个独特的台湾政治光谱的早期建议,如今已公
开地流行于台湾。
它随着1960年代现代文学运动的来临而开始,和那时萨特的兴起流行直接相
关[44]。台湾的现代文学运动脱离了中国历史上先前所有的文学运动。通过探究心理
和哲学议题,他们避开了现代中国文学在20世纪多数时候的基本主题:民族命运。
现代文学派强调艺术性和精雕细琢,抵制任何流行的政治、道德和美学的传统[45]。
相比西方的现代派,台湾的现代文学派保守得多,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描绘儒家
理想的崩溃,抨击当时的流行文化[46]。1960年代这场运动的中心是《文星》杂
志。起初《文星》聚焦于文学和艺术,但是到1960年代早期,在《****》停刊
之后,它加入了传统和西化现代化之间的论战。《文星》的作者旗帜鲜明地站在后
者阵营,尤其是作家李敖。结果是,这本杂志变得越来越容易遭到保守的统治精英
的攻击[47]。
然而,到了1970年代,现代主义者的主要对手不再是保守精英,而是来自另一
场文学运动,它自1960年代起也已在一些作家——乡土主义者——中扎根。随着乡
土主义者的登场,在传统与现代化和或西化之间的分歧变得更加复杂,甚至混乱,因为乡土主义者既反对现代化,也反对保守的统治精英。乡土主义者甚至看穿了现
代主义者和统治精英在台湾一有危机迹象时就都会争先恐后地移民(至少在乡土主
义者眼里如此),从丢掉了联合国席位开始,在70年代有很多人这么干,由此放弃
了岛上的老百姓。乡土主义者也在美学上做出反应:在与现代主义者的西化赫尔墨
斯主义的正面交锋中,乡土主义者搬出一种新的反映成长于台湾的新生代的族群意
识[48]。典型的乡土主义者的美学策略是社会现实主义,而不是美学实验,他们宣称
目标是传达台湾日常生活的细节,还其本来面目[49]。1977年,在一场多家报刊参
与的激烈论战中,以及一次著名的讨论这场文学运动的会议上,运动背后的潜在表达摆上了前台。它的结果,就是今天众所周知的“乡土文学论战”。
乡土主义者始于一种反西方的前提,似乎加入了东方西方的对抗。起初他们质
疑为什么台湾的科学书籍常常使用英文,而不是中文[50]。他们所认知的台湾是寄生
经济制度的牺牲品,这种经济制度导致台湾依附于人,而非独立自主[51],他们的关
注点聚焦于此。一些作家把这种潜在的冲突描述为中国文化和“日本西方商业文
化”之间的矛盾[52]。1970年代在国际舞台上的大量挫折,促使其他人呼吁台湾人
要依靠自己,不要再依靠西方[53]。事实上他们的话里流露出一种焦虑感和毫不掩饰
的紧迫感。一个作家说:“从来没有什么国际道义;我们必须运用一切最实际的手
段,为自身生存而奋斗。”[54]
但是世上不止一种反西方的立场。当时的反对者要么在文学方面要么以反共理
由攻击乡土文学运动,没有一个人能够阐明这场运动的定义。照字面意义翻
译,“native soil”的意思是“乡土”。但是它是指哪一个“乡土”呢?有个作
家提出如下议题:“我们的乡土是肥沃的;增强我们的乡土感;允许我们认可自己
的乡土;以我们的乡土为豪。这会让我们不易被外来事物所引诱,或被外来文化所
污染。”然而,当被询问这里的“乡土”是中国还是台湾,他永远不会给出非此即
彼的回答[55]。事后看来,那是核心问题。后来很多人宣称乡土主义者采用的最终评
判标准是他们的文学在多大程度上显示了“台湾意识”[56]。然而,在那时,乡土主
义者整体上是回避台湾与中国议题的,也许因为这仍然是一个禁忌的话题:有些乡
土主义者支持“大中国”的概念;其他人则含蓄地赞成以台湾代替中国[57]。不同的
人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的立场并不明确,直到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将台湾
与中国的议题搬到台前。1979年后,当文化和政治气候逐渐开放,许多旧的分歧很
快变得无足轻重,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多数分歧也是如此。台湾议题于是占据了文化
的中心。
然而,所有这些论战都是知识分子的论战,不是民众的论战。这些论战之所以
能被允许大规模发生,是因为在这个岛上,它们几乎没有涉足普通百姓的生活。那
么在普通民众身上发生了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最好的方法是看看在台湾
宗教的发展有多流行。1949年后的第一个二十年中,台湾的基督徒数量稳步增加。侯孝贤的父亲死后,他的母亲变成了基督徒,死后也以基督教丧礼下葬,正如我们
在《童年往事》中看到的。在统治阶层中也有大量的基督徒,国民党当局在1960年
代和1970年代引入享有盛誉的福音传播者,并且在地方电视台播出宗教集会[58]。
不过,基督教会在台湾处于政治光谱的两端。台湾最大的新教徒教派——长老会,以反纳粹的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为榜样挑战国民党,基于
此,在“台独”运动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59]。然而,普通民众并不信任政治,与此相应,台湾基督徒的数量早在1965年就已下降[6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从那时起,佛教徒和道教徒的人数却呈指数级激增。在1960年,台湾的佛教寺庙
刚刚超过八百座;到1989年,超过了四千座。1960年,道观接近三千座;到1989年
接近八千座[61]。(此后没有减缓的趋势:1980年代中期有八十万人声称是佛教
徒,到了2000年,这个数字超过了五百万[62]。)台湾普通百姓的财富不断上涨,本土宗教供养也与日俱增,两者之间似有直接关联:通常两到三年人均收入增加
后,紧跟着就会有大量新的寺庙拔地而起[63]。这又一次和中国大陆对比鲜明——
事实上,当前正好截然相反。以这个宗教标准来衡量,这个被认为更西化的岛屿实
际上比海峡对岸的大陆更“乡土”——甚至更“中国”[64]。不过,普通民众生活
中的这些趋势,和他们快速实现现代化及对诸多西化实践的迅速适应,完全并行不
悖。
台湾文化的另一个方面值得一提。无论是在日本统治之下还是在国民党的高压
之下,台湾始终需要走向世界以求生存。然而,今天,台湾尴尬的政治地位已经导
致“正常的外交”渠道无济于事。这赋予了文化拓展和文化交流——或许更应被称
作“文化外交”——新的意义和紧迫性。就此而言,随着侯孝贤成为台湾最重要的
电影“使者”,台湾电影走到了历史前台。但是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先锋是林怀
民于1973年创立的云门舞集。云门是亚洲第一现代舞团。每年云门都推出一出新的
剧目,包括类似大陆人移民到台湾的独特主题作品(《薪传》,1978),以中国传
统形式呈现的著名作品(《九歌》,2001(IX);《竹梦》,2001),以及存在于纯
粹抽象领域的作品(《水月》,1999)。林怀民从传统(主要是道家和佛家)元素
中汲取精华。此外,云门大胆创新的技巧组合,以及如幽灵般平静的标志性舞蹈动
作,再加上从巴赫到阿尔沃·帕尔特的音乐伴奏,传达出比其东方和西方构成元素的总和要伟大得多的意涵[65]。这样的节目已被证明是可供输出的文化产品,也使得林
怀民成为台湾第一个具有国际声望的艺术家,但他不是最后一个。作为一个本省
人,林怀民在岛内的文化影响力是巨大的。作为一个老师,他培育了许多学生,比
如焦雄屏,焦后来成为台湾影坛的领导性人物之一。焦雄屏声称是林怀民让他们这
一代人(包括像她这样的外省人)思考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个观念渗透到了其
他的文化领域,包括电影[66]。台湾电影工业中的侯孝贤
那么这个时候侯孝贤在哪里?既不在论战中心,也不在论战前线,甚至没有参
与论战。相反,侯孝贤谨慎独处,在很大程度上隔离于这些大的社会潮流。1973
年,台湾当局失去联合国席位仅仅一年后,侯孝贤进入了台湾商业电影工业,在一
部不起眼的电影中开启了起初很不起眼的职业生涯。仅仅十年后,侯孝贤成为台湾
在海外最重要的文化“使者”。只有理解了与台湾全面转型密切相关的电影转型之
后,这点才讲得通。台湾电影并不简单地反映上文讨论的这些历史独特之处;它也
在支持它们的同时扮演了反对的角色。在过去,电影充当了为历史和政治掩盖真相
的工具。然后突然在揭示长期被遮掩的事实方面,跟当局唱起了反调,不仅在台湾
的银幕上,更重要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在这种历史发掘方面,侯孝贤尤其扮演了一
个关键的角色。
然而,侯孝贤1973年加入的电影工业,对完成这样一项历史任务来说,是力不
从心的。在任何地方电影都是一个引人注目和广受欢迎的存在物,一种需要体制高
度支持的艺术媒介,无论这种支持来自个人还是公众,或是两者兼而有之。结果
是,它无法避免社会整体的影响。当然,台湾电影也几无可能避开数十年来造就这
个岛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力量。此外,尽管在侯孝贤的创作生涯中台湾电影发
生了巨大改变,但有一点是持续不变的,那就是台湾统治者,无论是旧的还是新
的,都制定了有利于其他电影——主要是香港和好莱坞——的政策,而本土电影成
了牺牲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将损害侯孝贤的个人利益。
台湾地区真正的商业电影花了很长时间来发展。尽管日本电影是历史上最伟大
的民族电影之一,尽管日本现代化的整个方案曾改变这个岛屿的基础设施、医学、农业和文化,尽管这个岛屿为电影制作提供了广泛的多样化的潜在场景,但是台湾
并没有像1931年后的满洲那样,成为日本电影的生产基地。相反,台湾主要是作为
日本电影的市场。到1935年,四十八家剧院专门放映电影,其中三十一家维持到了
1945年[67]。1945年至1949年间,因为环境动荡,台湾电影没有获得实质性发展。
因此,台湾电影的真正历史始于1949年,那时台湾成为国民党政治经营的最后舞台。然而,它发展得相当缓慢。甚至当国民党试图用一只手扶植电影工业的时候,又会用另一只手扼杀它。
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香港正在发展一种有生命力的并且最终强大的商业电
影,这一事实刺激了台湾电影圈的很多人,他们常说:“如果香港能够做到,为什
么台湾不可以?”毕竟,相比香港这个更小的岛屿,台湾拥有多姿多彩的风景,比
如壮丽的山脉,富饶的森林,美丽的海岸线,甚至在岛屿的西边还有广袤的平原
——所有这些都是电影制作的有利条件。台湾的人口也是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的四
倍。答案是台湾最初的政治和经济条件,甚至直到1960年代中期,都不能有助于发
展一种繁荣兴旺的电影工业[68]。1949年秋天,只有百分之五的上海电影团体迁移
到了台湾,而被更大的自由召唤迁移到香港的,是这个数字的许多倍。而且,那些
1949年来到台湾的人们多数进了农业教育电影公司,这是一家主要制作纪录片和宣
传影片的公营制片厂。这意味着虽然有一定数量的设备和技术人员到了台湾,但是
几乎谈不上有创造性的天才[69]。与国民党没有直接关系的大陆电影导演、制片人或
者明星,要么留在上海,要么投奔香港稳定和自由的环境,这点不难理解。1949
年,台湾看不出有长期稳定的迹象;甚至国民党也仅仅把这个岛屿视作有朝一
日“收复大陆”的临时基地。
在最初的十五年,台湾电影仍然表现得像一场巡回路演,而不是一种真正的电
影工业。台湾当局更关心的是避免重蹈1930年代上海电影界的覆辙——那时左派压
倒右派,取得优势地位。因此,不像香港的殖民政府,国民党偏好严格控制任何电
影“工业”的存在,首先就在1950年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加以监管。国民党当局
直接监管台湾的每一家私人电影公司和电影机构。任何一家与电影相关的机关的头
目都一定是国民党党员。当局情报机关的指令源源不断,均蛮横地强加强烈的反共
立场,另外还有反“赤色”、“黑色”和“黄色”原则。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电影不像其他工业获得足够的重视。电影行业被宣称为一
种“特殊的”工业,尽管它能产出效益,但还是受到压制。台湾其他领域的税率从
来不会超过百分之三十,然而娱乐税高达百分之六十。电影票的印花税比其他任何
工业高出十一倍。更重要的是,进口电影器材,无论是为了制作还是展出,都被视
为“奢侈品”,因而其关税要高出其他行业百分之五十还多[70]。后者对电影行业产生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它强迫台湾的电影制作者在电影胶片上偷工减
料。而且,它甚至影响了主要的制片厂——“中央电影公司”(以下简称“中
影”),它成立于1954年,由当时的农业教育电影制片厂(“农教”)和台湾电影
公司(“台影”,接管自日据时代)合并而成[71]。不用奇怪,“中影”在国民党的
直接控制之下。
当局严密控制的结果是,台湾制作生产了大量的纪录片和宣传短片,但是几乎
没有虚构的故事片。那些拍摄出来的影片主要是为了宣传,而不是为了娱乐,也不
是为了文化教育。1950年代生产的极少数故事片也都是票房灾难。这些电影角色老
套、拙劣,回避官方禁忌,制作粗糙,观众压根不为所动。第一部故事长片《恶梦
初醒》仅仅使用了四万英尺日本过期胶片,这导致影片呈现雾化效果[72]。第二部故
事片是“农教”出品的《永不分离》,通过蓄意描述由共产分子制造的本省人和新
近迁来的大陆人之间的各种矛盾,试图驱散“二二八事件”的幽灵[73]。有时结果令
人哭笑不得。一部1960年代的闽南语电影情节涉及一个邮递员在关键时刻弄丢了一
些信件。这点被当局审查员剪掉了,因为它可能会有损邮递员的形象。然而,这一
删减导致电影几乎无法理解[74]。《飞虎将军》是1959年的一部政宣片,不惜工本
地描绘地方空军学院飞行员的训练。但是军方要求电影情节中不许任何飞机有问题
或出事故,也不许有任何人员伤亡,这导致成片缺乏戏剧张力,也失去了它的宣传
潜能[75]。当局的约束是如此的极端,以致它的政宣电影不被允许表现共产党的旗帜
或徽章,甚至不许出现毛泽东的形象[76]。当局政策也伤害了台湾以外的任何潜在观
众:因为过度反对“共匪”的主题,《恶梦初醒》的发行权没法卖到新加坡、马来
西亚和中国香港。因为这三个地区都要考虑和中国大陆的关系[77]。
本土电影制作陷入瘫痪,台湾影院的增加却总得有其他电影来填充。在每年上
映的六百到七百部电影中,只有两三部是本地制作的“国语片”[78]。在香港,商业
电影工业没有类似的政治和经济的约束,从一开始它的电影就席卷了台湾的银幕。
1950年至1954年间,总共有六百六十二部“国语片”在岛内上映,其中大多数来自
香港,少数是上海老电影,只有十三部是台湾本地摄制的[79]。1953年起,国民党
也将进入台湾市场赚钱的通路作为控制手段,通过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也称“自由总会”(X))对香港电影施加影响。这确保进入台湾市场的香港电影在政治
上都是合口味的[80]。不过香港也反过来能够从国民党那里获取好处。最关键是
1956年,香港“国语片”作为“国片”,可以不受现行配额制度限制,同时免于重
检。所产生的实效是,香港“国语片”不再受限进入台湾市场,它现在被归类为本
土制作的一个部分[81]。正如卢非易总结的:“不管原因是什么、结果如何,可以确
定的是,国民党当局为了说服香港电影工业,允许香港电影不受限制进入台湾市
场。看到这个机遇,香港电影心系台湾市场,最大化地扩大它自身的产量。这对台
湾电影工业本身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82]
其他政策进一步推波助澜。黄卓汉是“自由总会”的核心成员,他跟国民党当
局就不合理的电影生胶片和设备关税进行了协商。自此之后,香港“自由总会”的
会员公司进口电影设备的关税都被新的法规松绑了[83]。“自由总会”的任何会员进
口电影生胶片和设备进入台湾,在六个月内都免征关税。这项措施的目的本是为了
鼓励岛内的香港电影生产,但是制片商可以提交一份两个小时片长的脚本,却只拍
摄一部八十分钟的成片,然后把剩下的生胶片拿到当地的黑市上交易。这种做法是
如此的普遍,以致“新闻局”在1958年终止了电影生胶片进口的免税政策,这项政
策只对电影设备有效[84]。
出乎意料的是,这项政策不仅没有导致台湾制作更多的“国语片”,相反却迎
来闽南语电影摄制的第一波高潮。尽管那时当局希望用“国语”取代闽南语,但
是“国语”主要应用于教育系统,而非电影领域。同时,只要闽南语电影承载了正
确的宣传信息,或者至少不和官方路线背道而驰,国民党也允许它们存在。台湾本
地的电影制作如今可以从香港那边获取电影生胶片,这样就回避了过高的进口关
税。在1955年至1959年间,台湾总共生产了一百七十八部闽南语电影,数量超
过“国语”电影三倍[85]。
然而,我们不应将这种现象理解为一个真正的私营行业的开端。事实上,这些
电影与其说是正规电影厂的制作,不如说是不靠谱的经营者的短期投机和开发。影
片产量之多可能值得称道,但电影本身绝大部分不是这样。考虑到电影生胶片是珍
贵的物品,摄制者总是尽可能地少用。一些人专门在黑市倒卖电影生胶片,电影的实际创作反成了次要的事情[86]。何基明是1956年第一部闽南语电影(XI)的导演,他
绞尽脑汁地设法不让任何胶片被剪掉。他在开拍之前排演多次,使用每卷电影胶片
的七到八英尺引带拍摄成片中的过渡空镜头。最终,他仅使用了九千五百英尺胶
片,几乎没有被剪掉的[87]。辛奇是最著名的闽南语电影导演之一,他拍摄了九十多
部闽南语电影。根据辛奇的说法,电影制作中决定性的因素是生胶片的昂贵和时间
的匮乏:“我们那时拍摄闽南语电影使用的胶片通常进口,或者从黑市买来。一部
电影平均需要八百个镜头。因为胶片昂贵,我们浪费不起。而且,我们拍了那么多
的电影,一年大概一百部,花在每部电影拍摄上的时间非常短,平均两到三天就可
拍完一部电影。”[88]甚至当下一个十年出现相对高档的“国语片”,在摄制中仍然
存在同样的偷工减料现象。
无可否认,1960年代在台湾看到了一个更像样的电影工业的起点。然而,1950
年代为后来的一切奠定了基础,甚至包括1980年代的新电影运动。闽南语电影和制
片体系一样粗劣,却成为后来的工业人才的训练基地,比如李行,他是台湾电影导
演的“教父”。1950年代,台湾本地电影工业中有利可图的玩家只有像“中央电影
公司”和私营的联邦公司这样的发行商。发行商最终决定本地电影工业的长期命
运,甚至在1980年代也是如此。当局政策、香港电影在本地市场的早熟优势、岛内
落后的电影制作、围绕电影生胶片的争议和本地发行商发展迅速的力量——尽管台
湾电影经历的这些变化始于1960年代,但是当侯孝贤和新电影在1980年代早期崛起
的时候,也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先决条件,新电影不可能问
世。
在1963年,因为岛内外一些事情的合力作用,台湾电影的面貌发生了戏剧性变
化。这里的“岛外”,又是指香港。那一年,邵氏兄弟公司发行了《梁山伯与祝英
台》。该片是黄梅调电影类型中的一部“国语片”,当时在台湾获得了巨大的成
功,而且迄今还有人疯狂迷恋。它在台北创造了连续放映一百八十六天的纪录,收
入八百万新台币票房,打破了当时的所有票房纪录。(它的这一成绩直到1983年才
被成龙的《A计划》超越。)因此,香港人开始称呼台北是一座“狂人城”[89]。
《梁山伯与祝英台》对台湾的经济冲击持续久远。它凸显了台湾市场对香港电影的
确切无疑的重要性。它也导致台湾的很多戏院中断和美国电影公司的协议,反而开始放映“国语片”[90]。而且,当这部电影的导演李翰祥突然搬到台湾,带来技术和
艺术人才,外加大制作计划,也启动了一个成熟的私营电影业。李翰祥在那时已经
是邵氏兄弟公司最著名的导演,专攻古装片拍摄。李翰祥为邵氏执导了许多部票房
大卖的影片,但他认为自己没有因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极大成功而获得足够的
奖赏。竞争对手国泰集团看到了这个引诱李翰祥离开的机会。然而,李翰祥仍然要
承担和邵氏兄弟的签约责任,不能毫无法律纠纷地直接为国泰旗下的国际电影懋业
有限公司(简称电懋)拍片。因此,国泰通过在台湾的联邦公司,出资成立一家以
台湾为基地的大的新电影公司,国联公司于是诞生了。公司首脑正是李翰祥本人
[91]。
结果是诞生了一家在台湾规模空前的电影公司。尽管它在五年多内只制作了二
十部电影,但是国联独力将制作水准提升到新的水平,培训人员,创立明星制度,帮助建设更好的海外发行,鼓舞其他公司也装配相似的片厂设备。它也创造了几部
电影经典[92]。事实上,它也可能是一种超过或者至少达到香港电影水平的电影工业
的开始。最重要的财政资助者是马来西亚华人陆运涛,他是国泰集团的老板。陆运
涛在台湾电影业投入了五百万美元,显然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可是他后来死于
空难(XII),这场空难被许多人宣称改变了台湾电影历史的进程。黄卓汉说:“如果
不是这起空难,台湾的国语电影制作可能进入一个黄金年代,提升到国际水准。事
与愿违,香港电影一枝独秀……”[93]
没有了主要赞助人的干预,李翰祥便自作主张,国联公司很快变得像1920年的
联艺公司(XIII),那家公司由缺乏财政管理经验的艺术家掌控。李翰祥1965年拍摄
《西施》是挥霍无度的最好例子,这是一部奢侈的历史古装片,它花费了李翰祥一
年零三个月时间制作,消耗了两千三百万元新台币。有关这部电影的数字是惊人
的:四十二处布景,六千套戏服,三万个道具,八千匹马,十二万个临时演员(军
队提供),三百三十四个工作日,八百辆双轮战车和十二万英尺电影胶片。它是
1965年的本土票房冠军,然而它的首轮放映仅仅收回约五百万新台币,因为票价非
常便宜[94]。国联公司再也没能从这次财政打击中复原过来。然而,所有这一切催生
了“国语片”制作中真正的私营行业。国联的发行公司联邦,也开始自己制作电
影,首作是胡金铨的《龙门客栈》[95]。成功吸引胡金铨来到台湾,他后来在此拍出了1970年代的经典作品《侠女》,它是1980年代之前唯一一部在国际电影节的最高
竞争舞台上获奖的华语片。
但是烦人的问题出现了:这真的是台湾电影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还是仅仅是
香港电影的延伸?事实很简单,台湾私营电影业几乎打一开始就与香港电影纠缠不
清。比如说,黄卓汉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横跨两个地域。1967年他在香港创建了第一
影业机构有限公司,但又在台湾成立制片分部,拍摄武侠片[96]。财政、人才库和政
治方面的联系是如此纠结(甚至当局运营的制片厂也大量从事与香港公司的合作制
片),导致不可能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之间做出明确的区
分。它们一起被归类为“国片”自然于事无补,西方观察家也感到困惑[97]。甚至直
到今天,台湾和香港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台湾的每部电影史都会提
及这一时期在台湾制作的经典影片——《冬暖》(1967)(XIV)、《侠女》
(1970)(XV)和《喜怒哀乐》(1970)(XVI),把它们视作台湾电影来讨论。然而,与此同时,张建德的香港电影史把这些电影归为香港制作,这在香港是普遍的看
法。张建德讨论李翰祥、陆运涛和国联公司,也视之为香港电影史的构成部分[98]。
因为《侠女》在1975年戛纳电影节上获得特别技术大奖,所以此片特别有争议。
为了辨识台湾电影和香港电影的真正区别,我们不得不看看公营制片厂的情
况,它们在同一时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63年,龚弘被“新闻局”挑选出任“中
影”新的总经理。龚弘的任期长达九年半,他表现出的远见出人意料,在这期间,他改进了“中影”的管理结构、摄制设施和影院链。这些改变的结果是,“中
影”成为台湾电影工业的领导者之一。在1963年,龚弘还看了一部私营制作的、低
成本的、半“国语”半闽南语的影片,那就是李行导演的《街头巷尾》。这激发龚
弘聘请李行执导一种新的政策电影类型,它被称为“健康写实”。这股潮流中的电
影在产量上并不突出,但是三部最重要的作品——《蚵女》(1963)、《养鸭人
家》(1965,图1)和《路》(1967)——收获了此前公营制作从未取得的票房成
功[99]。在另一方面,健康写实电影继续为当局的宣传需要服务:它们的立意让人们
更多地联想到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不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这就是龚弘所宣
称的电影模式。这些电影都只用“国语”拍摄。它们也都呈现一个经过高度净化的
台湾现实的版本。最终,这些影片在语调上都充满严重的说教意味,在颂扬当局主导的社会进程的同时维护传统道德价值观。不过,在处理乡村普通百姓及其日常关
注时,健康写实影片与1950年代的宣传电影大相径庭。对健康电影来说也存在一种
更深层的意义。在当局鼓励的影片中,台湾本土的发展现在是一个有价值的主题。
换言之,这是“国语片”首次认可台湾——或者说至少认可一个理想化的台湾版
本。他们不再只是尖声谩骂,高喊“反共”、“收复大陆”的口号了。
图1 《恋恋风尘》(1986)中露天放映电影《养鸭人家》(1965)
在“中影”、国联和联邦的引领下,台湾本土“国语片”的数量在1960年代十
年间增长了二十倍。1960年,台湾只制作了五部“国语片”。1964年,达到二十二
部。到1969年,达到八十九部。1969年也是“国语片”产量超过粗制滥造的闽南语
片的第一年。到1971年,台湾“国语片”数量超过了一百部。
1960年代电影业的发展,成为侯孝贤所接受的非正式教育的一部分,他主要成
长于那十年间。然而,谁也不会预料到,这会培养出一个以拍摄了一些世界上最富
挑战性的剧情片而著称的导演。在学校,侯孝贤不是最勤奋的学生,这主要归因于
他自身兴趣匮乏。但是,他自学了那个时代可接触到的流行文化。侯孝贤自述,他
当时租借、阅读了能找到的每一本武侠小说,而且当他发现再也找不到武侠小说可
读的时候,就读侦探小说、经典小说的通俗改编、翻译的西方小说,当所有这些看
完后他甚至看琼瑶小说[100]。(在《童年往事》中,我们甚至能看见他躲在厕所偷看色情读物。)他早年也对电影如饥似渴,常常偷偷溜进电影院(《风柜来的人》
有所表现),或者在影院门外找到一些旧的、撕裂了的电影票根,粘起来混进去。
他在服兵役期间前所未有地看了大量电影,因为他身为宪兵,执勤特殊,有大把的
空闲时间,有时一天可以看到四部电影[101]。一退役,他就进了“国立艺专”(XVII)
学习电影。他在1960年代末进入艺专,由于学校缺少器材,他只是接受了极为有限
的技术训练。导演课程根本上就是戏剧导演课程,而且再也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可
学[102]。但是至少他看了更多的电影,尽管少于我们所认为的“电影学校”应提供
的数量。
侯孝贤看的大多数电影要么来自好莱坞要么来自香港。他曾提及那时看过的一
部电影,是大概在1967年服兵役期间看过的一部英国片,英语片名不确定[103]。这
部印象模糊的电影让侯孝贤对电影的兴趣更浓厚,但是根据他的说法,它没能帮助
他更好地理解这种媒介[104]。侯孝贤曾回想起,进入艺专后,有一次当一个老师分
析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XVIII)的二流作品《我就爱你》(Arrangement)的
视觉基调时,他感到惊讶[105]。他说,从此他看电影不同以往了,但是仍然不像人
们所预期的那样。他继续沉湎于流行文化,继续无视电影更艺术和更文化的表现。
只有到1970年代末在他自己将要成为一个导演的时候,他终于开始看更多的好莱坞
和香港以外的电影。然而,再一次,这对他影响甚微。当他看安东尼奥尼
(Michelangelo Antonioni)(XIX)作品和其他实验电影时,他无法真正地欣赏其
中任何一部[106]。侯孝贤甚至说过,在他商业导演生涯早期,他曾在看费里尼
(Federico Fellini)(XX)作品时睡着了[107]。
事实上,侯孝贤接受的真正的电影教育不是一种正统教育,而是学徒见习,学
徒身份开启了他进入电影业的日子。到1973年商业电影工业最好的时光已成过去,尽管它不是即刻显现,但是一个缓慢的衰落期已经来临。标志是1970年代初国联公
司偃旗息鼓,联邦很快在1974年结束制片业务,剩下“中影”成为唯一稳定的“国
语”故事片制作者。自1973年始,至1977年,台湾生产的“国语片”数量滑落到每
年四十五部至六十六部,而闽南语电影已经消失无踪。与此同时,香港仍然生产数
量三倍于台湾的故事片[108]。台湾发现它无法和香港在经费、质量和营销上竞争,特别是现在李小龙跃居银幕。火上浇油的是,台湾当局又出台了有利于香港的政
策,在购买和冲洗电影胶片方面,香港公司的花费比本地制作公司要便宜得
多[109]。
电影类型的分类能够解释这一不断扩大的鸿沟。香港比台湾生产了多得多的动
作片(或者说任何一种类型片)。在台湾,这些电影不但被认为制作昂贵,也会被
保守的社会精英批评道德含糊。卢非易曾指出台湾超过三分之一的电影如何在类型
上被改换分类为“文艺”片[110]。“文艺”片曾被翻译为“爱情”或者“文学”电
影,而且有时似乎涵盖了所有片种。因为文艺片制作起来比动作片廉价多了,所以
台湾制作了大量的文艺片,这是值得注意的[111]。没人比多产导演刘家昌更能代表
这股潮流,他在1970年代拍摄了近三十部电影,包括八部为“中影”拍摄的。刘拍
电影总是快速粗糙,人物塑造也很老套。但是他通过为影片配上大量歌曲改造了文
艺类型,使得这些电影甚至可有一点出口[112]。
台湾商业电影的核心是文艺片的一种次类型,也即俗称的“琼瑶片”,因大多
根据作家琼瑶的言情小说改编,故有此名。这股潮流似乎随着1960年代中期李行
为“中影”拍的两部电影的成功而出现[113]。到1983年,共有四十九部电影改编自
琼瑶小说,也有几部改编自琼瑶小说的克隆版。琼瑶甚至在1976年成立了她自己的
制作公司,当然,只拍摄琼瑶片[114]。这些电影容易出口到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这
样的市场,今天很多人认为它们荒诞地逃避现实。健康写实至少尝试处理台湾现实
生活,虽然是失败的;而琼瑶片与现实干脆毫无干系。如果这些电影可信的话,那
么台湾的每一个人都住在阳明山(台北有钱人的度假胜地)上宽敞的休闲山庄里,每个人都流连于西式客厅、餐厅和咖啡厅中打发时间,每个人都向往在基督教堂里
结婚,而且每个人都如此的西化,以至于民族文化的痕迹只剩筷子的偶尔出现,而
这似乎不过是场记的疏忽罢了。林青霞在去香港发展之前是琼瑶片的重要明星,她
直率地说,那些电影之所以影响巨大,确切的原因是它们在一个生活艰难的时代提
供了必要的幻觉。换言之,它们反映的不是台湾的现实,而是每个人都渴望逃往的
另一种世界[115]。
然而,整个1970年代,另一个因素加剧了台湾电影业面临的经济压力。这十年的“外交”受挫让国民党当局再次强调了宣传的重要性。这些政治危机导致了大预
算的政宣片,它们由“中影”这十年间的两任负责人梅长龄和明骥发起拍摄。健康
写实之父龚弘被“中影公司”新的总经理梅长龄所取代。梅长龄立即率领这家党营
制片厂走上了昂贵的电影制作之路[116]。这包括在1972年日本和台湾“断交”之
后,一波反日电影涌现。《梅花》是决定性的作品,1975年发行。这部影片票房收
获排名第一,而且获得台湾的“奥斯卡”金马奖的最佳剧情片奖。它的成功在很大
程度上归因于蒋经国的公开奖掖[117]。(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部片在台湾就相当于
大陆的《红色娘子军》。)台湾当局出于政治目的希望开发利用流行文化,《梅
花》就是一例。它的导演,拍片不辍的刘家昌,以自己的流行气质支援了政治宣
传。这部电影不仅让台湾政宣电影“教父”柯俊雄成为明星,也让非常年轻的张艾
嘉一炮而红。刘家昌创作的电影主题歌《梅花》风靡台湾。这首歌在情节开展的任
何时候都能响起,一个台湾男孩在“二战”期间目睹自己的父亲被日本人残酷虐
待,他唱这首歌效果特别明显。“中国小孩,不要哭。”这个戴着手铐脚镣、被打
得死去活来、鲜血淋漓的爱国父亲警告他的儿子。“我难过。”流泪的孩子回答。
他的父亲于是提议:“难过?唱歌!”这种匪夷所思的胡言乱语,只可能发生在迎
合宣传需要的情况下,台湾人却借此在以完美“国语”演唱的歌声中爆发了,通过
歌唱颂扬“国花”,显示了他们对身为中国人的不朽的热望。
在失去美国的承认和1979年底的“美丽岛事件”之后,这股大制作政宣片的潮
流到达了顶点。大量电影反映了对“台独”的警惕,其中最重要的叫“寻根”三部
曲。《源》是这股潮流在1979年的代表,影片浓墨重彩地描绘台湾19世纪的石油勘
探努力(也有一个丰满有力的得州人妻子的镜头,她帮助男人们干活,但只是作为
点缀)。然而,关键信息是一个最初的闪回,主角还是个小男孩时第一次来到台
湾:当他站在海边,他的父亲提醒他,他们来自大陆,他们来到台湾是为了帮助中
华民族开疆拓土。其他电影很明显看得出台湾当局对失去美国承认的反应。李行也
不甘落伍,在“中影”拍摄了明星云集的《龙的传人》(1980)。片中有一个开放
的纪录片风格的剪辑,表现街头人们对美国人撤退的反应,高潮是一个舞台化的段
落,人们瞪着一个年轻的、卷发的、白肤金发碧眼的男子和两个性感的当地姑娘愉
快地走在一起。那个男子看到人们的表情,掏出一块牌子,上面用中文写着:“我
是澳大利亚人!”这部电影的主题歌《龙的传人》,成为官方倡议的宣传口号,而且跨越海峡,在大陆甚至更流行。不过,这些电影中最声名狼藉的奢侈品是《辛亥
双十》(1981)。这部电影以夸张的英雄主义、数量惊人的临时演员、狄龙耍的一
些功夫,以及高潮那场堪比《乱世佳人》火烧亚特兰特的大火为特色。大多数观众
都是在学校或者俱乐部的公开放映场合看这样的电影;然而,几乎没人想过要买票
观看。结果是,这类电影使得“中影”深陷财政赤字。而且,一些人认为,“反
共”反日电影到此时已经让他们筋疲力尽,他们对这样昂贵的财务开销表示质疑。
从宣传和经济的观点来看,这类电影的产量再度面临锐减[118]。
这就是侯孝贤学习电影制作技艺的环境,如果不是不可能,看上去也是很奇怪
的。更令人吃惊的是,侯孝贤在这块土地上所体验的低成本琼瑶片、甜美的音乐和
夸张浪费的政治宣传,对他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持续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在他最近
的电影中也有迹可循。事实就是这么回事。
长镜头被认为是侯孝贤美学上最决定性的特征。不过,这不是他从早期商业岁
月中学习到的东西;不如说,这是他随着时间推移发展出来的东西。这一时期台湾
电影的平均镜头长度和其他地区不一样,但不明显。1960年代的电影抽样平均每个
镜头长约十秒。若以巴里·索特(Barry Salt)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做的平均镜头长
度的广泛分析作为基准,这一时期台湾电影剪辑通常比美国电影慢,但是非常接近
欧洲电影的平均水平[119]。从1970年至1977年的台湾电影中抽样,平均镜头长度下
降到约八秒,从而和其他地方更快的剪辑潮流取得一致[120]。1978年至1982年,台
湾电影平均镜头长度几乎同样维持在八秒。
这些平均数似乎反映了导演们最初学习技艺的环境。两个著名的移居台湾的香
港导演李翰祥和胡金铨,在台湾拍片的时候,剪辑影片也比他们的台湾同行快。比
如说,李翰祥的《西施》平均镜头长度为七秒,而胡金铨的《侠女》大约为五秒。
李翰祥1967年的经典作品《冬暖》,是一部台湾“健康写实”风格的剧情片,平均
镜头长度不足七秒。台湾最卓越的两个导演,李行和白景瑞,一般来说倾向于使用
较长的镜头。李行两部作品的平均镜头长度为十二秒,七部作品在十秒至十一点五
秒之间,四部在九秒至十秒之间。白景瑞甚至更加始终如一:他的六部抽样作品
中,五部在九秒至十点五秒之间,唯一真正改变的是《皇天后土》,平均镜头长度
为十一点五秒。1970年,上述四位导演联合执导了《喜怒哀乐》,这是为使国联公司复原的最后努力。两位台湾导演的平均镜头长度较长,白景瑞以超过十秒一马当
先,李行达到大约八秒。相反,胡金铨和李翰祥导演的部分平均镜头长度都在六秒
以下。
上述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抽样,揭示了一种以剪辑为基础的商业电影,它
们的剪辑比好莱坞慢一点,但比香港慢太多。台湾商业电影工业在商业制作方面跟
随世界潮流,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总是拖拖拉拉。它不是那种寻求自己风格的
长镜头电影。相反,是一种基于经济合算的更实用的剪辑实践。所以,侯孝贤对于
长镜头的追求,起因于他试图克服这种环境的限制。
当然,侯孝贤后来也在别的方面独树一帜,而这些也受到这种电影工业负面因
素的影响。在布光和镜头构成方面,如果不是指唯美的话,几乎没人可在复杂程度
和密度上与侯孝贤相匹敌。想想侯孝贤出身于台湾如此糟糕的商业电影工业,这更
令人吃惊。在台湾,布光和镜头构成都背弃了明确的低成本制作方法。
在商业电影工业的全盛期,布光很显然是统一的和功能性的,与表现性和艺术
性截然相反。这些电影使用变形宽银幕格式和彩色电影胶片拍摄,所以需要大量光
照,就像十年前很多好莱坞电影的摄制一样。然而,很少有人在用光造型或者使之
柔化方面付出努力。当然,也几乎不在阴影和黑暗方面做出探索,就像同时期《教
父》的摄影师戈登·威利斯(Gordon Willis)所做的工作那样,他被称为“黑暗王
子”。这些电影通常使用平光,演员或无生命物体同样投射出硬边阴影,总之导致
粗糙的光线设计。一个例子是1970年的《葡萄成熟时》。有一场戏是女主角进入她
的卧室,走向一个角落。当她走近墙角,她的身体在两面墙上投射出硬边阴影。不
但这两束来自不同方向的光源没有清晰的动机,轮廓分明的阴影也例证了电影实践
中没有散射的硬光设计。既然布光如此费时,而那些低成本电影又没有多少摄制时
间,所以这也就不足为奇,特别是在香港,这一点也很普遍。图2 《葡萄成熟时》(1970)中的一个画面,两面墙上都有动机不明的硬光
作为补偿,台湾导演求助于一套视觉花招,其中一些显然源自香港。比如快速
变焦镜头的滥用。1980年台湾制作的一部功夫片《乡野人》,有很长一段时间几乎
每个镜头都包含一个快速变焦镜头。变焦镜头在功夫片中不稀奇,但是它同样统治
了台湾的非动作片,不管是林清介导演的所谓“学生电影”(如《学生之爱》,1981),还是军事政宣片(如《黄埔军魂》,1978),或是像《再见阿郎》
(1970,导演白景瑞)这样的戏剧性爱情片。通常这些变焦镜头的目的是为了突出
关键的戏剧性时刻,使得它们不会被观众错过。比如说,在白景瑞的《白屋之恋》
(1974(XXI))中,在表现一个父亲恳请女明星(甄珍)不要再和他的儿子约会的特
别时刻,就使用了一系列的变焦镜头。通常来说,我们很难在那一时期的台湾电影
中找到一部不包含一些快速变焦镜头的电影。甚至是以相对克制著称的李行,也为
了强调感情而使用变焦镜头。在《养鸭人家》中,在养女抓住她的父亲并说她仍然
是他真正的女儿的关键时刻,使用了一个快速的推镜头。在《海韵》(1974)中,一个快速变焦镜头导致一个闪回,强调了一个女人曾经作为舞女的羞耻过去。在
《小城故事》(1979)中,变焦镜头强调了一段萌芽中的恋爱。
然而,另一种视觉花招,似乎把台湾电影和香港电影区别开来。变形宽银幕格式意味着一个浅得多的景深。台湾导演通常通过前景尽头失焦的物体,如灯、灯
光、花瓶、植物或者树枝等,来炫耀这点,而不是避免它。有时候这些模糊不清的
物体甚至会部分地挡住中间地带的演员的视线。这样的例子多到不可胜数。1980年
的电影《台北吾爱》有一场宴会戏,为了突出浪漫的氛围,灯光闪到极致,令人眼
花缭乱。同一年的《美丽与哀愁》包括一段舞蹈戏份,前景尽头的灯光全都处于失
焦状态。琼瑶片特别展示了这一趋势,大部分是在恋爱场景中。比如说,在1977年
的《我是一片云》中,林青霞在一家咖啡店首次宣称她对秦汉的爱,前景是着重突
出的台灯闪耀的铜管,为了浪漫效果全都模糊一片。在《白屋之恋》中,这种做法
变成了“多相变态”(polymorphously perverse)(XXII):片中有大量的物体,包括霓虹灯、铁栅栏、喷泉、蜡烛和吊床等,全都在前景尽头失焦。倒霉的恋人在
小屋里跳舞的场景中,突出了前景尽头的模糊的蜡烛,它占据了比演员还要多的空
间,几乎挡住了观众看他们(图3)。这种实践的广泛运用也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
变形宽银幕格式导致宽画幅需要被填满。相比使用昂贵又费时的高质量布光,或者
更仔细精心的构图和布景,来美化和充实画面,前景中的模糊物体是一种便宜和节
约时间得多的方式。
不过,另一种实践最能诠释在这种行业中工作对一个导演意味着什么,而这点
也特别挫败侯孝贤。李行导演的影片《心有千千结》(1973),让侯孝贤的名字第
一次出现在摄制人员名单中,此片他署名场记。片中有场戏演绎了一种可作为当时
台湾电影工业缩影的分场方法。地点在餐厅。就餐期间,一个住家护士试图说服她
的年老的病人,他的儿子很孝顺,不像他认为的那样叛逆。尽管有二十一个镜头,尽管它们中的很多由正反拍镜头连接,但是在这个场景中,只有七个镜头来自早前
使用的重复的机位设置。无论什么时候拍广角——意味着距离更远且通常展现多个
角色——它通常来自一个相对于之前的广角镜头来说全新的角度,也即餐桌周围的
某个别的地方。图3 《白屋之恋》中故弄玄虚的浅景深
这一点不像好莱坞,在好莱坞拍摄一个场景的主镜头是通例。它必须从一个广
角来拍摄整个场景,捕捉所有的情节。主镜头经常要多拍几遍,以确保有一个好的
可以使用。拍完主镜头,摄影机然后移到其他几个地方拍摄插入镜头、近景镜头、反应镜头、细部特写镜头等,这种做法通常被叫做“涵盖镜头”。关键是,无论最
终使用了什么样的其他镜头,总是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主镜头,它可以用作场景中的
任何一个点的再定位镜头。但是,在台湾,开场从来没有整个场景的主镜头。因
此,无论何时回到广角拍摄,剧组都能在一个新的机位轻易地完成它,就像在最初
的位置一样,因为这两个镜头原本就是独立拍摄的。这也确保了在最终的成片中有
一些视觉的变化。而且,布光是如此的一成不变,乃至从一个机位到下一个机位,布光几乎不做调整,这在好莱坞是很成问题的,因为那里的摄影指导要是不认真对
待每一个独特的位置而“耍诈”的话,会声名狼藉的。实际上,这使得好莱坞导演
较少倾向于使用更多的机位,但是不妨碍台湾导演满足于纯粹实用的、平面的灯光
设计。
这也再次表明了香港电影对台湾电影的影响。在香港,电影人也在镜头之间做
最少的布光调整,而且倾向于把摄影机摆在任何一个场景中任何一个可以想到的位置。大卫·波德维尔称之为“分段拍摄”方法,在香港,场景的拍摄都是从不同的角
度逐个拍摄镜头,然后一起剪辑进一个不必依靠主镜头的单一场景。在好莱坞,在
剪辑中倾向于回到主镜头,结果是香港的机位变化比好莱坞的标准丰富[121]。香港
拍法不同于好莱坞的原因很清楚:在一个劳动密集型的行业,这是创造有活力的动
作场面最有效的方法。然而,在台湾,这种方法也经常用来处理非动作场景。显
然,对电影胶片的节约要求决定了为什么没有主镜头:它太贵了。在台湾,电影人
想方设法地要使片比降至最低。四比一被认为是铺张浪费,三比一到二比一是惯
例。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片比甚至更低。制片人和导演郭清江曾教育侯孝
贤如何做到片比低于二比一。他说他拍摄某部电影(他没有确指是哪一部)时,他
从一万八千英尺琐碎的曝光胶片中挑拣出一万一千英尺剪成影片——片比约是一点
六比一[122]。事实上,这种行业的典范有可能创造一比一的片比。所见即所拍——
没有重来!
这种普遍应用的制作方法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意味着更长的平均镜头长度。
在1980年代初期,郭清江——根据侯孝贤的说法,他是低片比大师——的三部作品
的平均镜头长度在五至七秒之间。然而,考虑到几乎没什么剪辑工作,很容易明白
这些电影大多数在剧情推进方面很不自然,或者粗枝大叶。人们可能会发现偶尔有
部台湾电影的剪辑速度和来自香港的流行电影——比如《鬼马智多星》
(1982(XXIII))和《最佳拍档》(1982),这两部电影的平均镜头长度约为五秒
——一样快。但是我们找不到任何一部台湾电影会像香港电影那样剪得爽快活泼。
原因很简单,既然绝不允许浪费胶片,那么台湾制片商也不会舍得多留任何东西在
剪辑室。正是如此死板的做法导致台湾电影到1980年代初期在香港电影面前不堪一
击。
这种做法对这些电影的意义远不是节奏和速度那么简单。在台湾,表演的最佳
时刻在剪辑时派不上用场,对此演员一点也不在乎。事实上,要是一开始就能将他
们表现最好的某个瞬间记录在胶片上,也够神奇的。侯孝贤对这种做法有丰富的经
验,据他的说法,无论何时拍摄一个人物的近景镜头,演员不是对着另一个演员讲
台词,而是常常对着站在他或她前面的副导演握紧的拳头[123]。他们从来不会用一
个主镜头从头至尾拍摄一个场景;他们只是每次拍摄一个镜头,没有真正的连贯性。理论上说,成片上显现的最好是最初捕捉在胶片上的那个时刻,尽管无法避免
的错误将导致片比高于一比一。停止和开始,情绪中断和对着握紧的拳头极尽夸张
能事地表演,都会冷却表演的激情。甚至李行也很难拍到过目难忘的表演,考虑到
所采用的拍摄方法,这是不足为奇的:一次拍摄一句台词的零碎做法产生了这样一
种感觉,李行的电影不过是用一根敷衍的叙事链条把矫揉造作的通俗剧节段捆在一
起。也许是为了掩饰这一切,李行和其他电影人总是源源不断地提供眼泪。《养鸭
人家》的结尾是一个年轻的阿飞独自在街上哭泣,反省自己走错的人生道路;
《路》的结尾是一个父亲为他孝顺和成功的儿子倍感自豪,而眼中满含泪水。李行
电影的一个典型结尾是放声痛哭的家人们围着濒死的父亲,他要利用临终宝贵的几
口气宣讲必不可少的遗言。动辄轻易地求助泪水,可不是李行一个人这么干。也许
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如此多的电影以痛哭的告别作结。
1973年,侯孝贤开始做场记,很快就变为副导演,最终变为编剧,起初和导演
赖成英写作了三部作品,赖是他7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走得最近的同事。在台湾,导
演很少做实际的导演工作;是副导演在现场真正面对日常的问题,他们掌管使用最
少的胶片。1970年代,侯孝贤至少为十一部电影署名了副导演,这些经验使他彻底
明白了流行电影拍摄方法的局限性。前面所提到的所有做法——实用的剪辑、实用
的布光、构图上玩弄的伎俩、最小的片比、时起时停的表演——侯孝贤有一天会拒
绝,但不是在第一天,甚至也不是在第十天。事实上,侯孝贤有好几年接着这么
干,以此来承担一些个人责任。(这毕竟是他的生计。)正如看起来的那样奇怪,他的这些经验对他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即使在他不再需要依靠这种工业工作
之后。他从这种主要是反面的经验中汲取了大量教训,但有两个宝贵教训最突出:
布光的重要性和表演的重要性,今天这两个领域构成了他自己的美学的基石。
当侯孝贤为李行的《早安台北》创作剧本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重大契机。这部
电影的摄影师是陈坤厚。后来陈和侯组成了一个导演编剧摄影组合。在参与新电
影浪潮前的几年里(1980—1982),这对组合一起完成了七部电影,陈正式导演了
四部,侯孝贤正式导演了三部:《就是溜溜的她》(1980)、《风儿踢踏踩》
(1981)、《在那河畔青草青》(1982)。侯通常是编剧,而陈通常是摄影师,由
于他们的工作关系密不可分,所以当时的评论界把这些影片看成是他们联合执导的
作品。因此,和大多数新电影导演不同,侯和陈在商业电影工业中积累了大量经验。陈和侯共享在台湾电影工业中改革制作实践的理念,他们的想法与众不同,这
给他们带来了声望。他们的一些变革将最终直接影响新电影,首先试验的就是他们
自己合作的作品。他们最早开始解决那些他们认为休戚与共的问题:电影胶片的匮
乏和表演的老套。在他们第一部共同作品陈坤厚导演的《我踏浪而来》(1980)
中,据说他们耗费了三万五千英尺胶片,而那个时候没人敢超过三万英尺[124]。拍
摄侯孝贤导演的《在那河畔青草青》时,他们使用的胶片在四万到五万英尺之间,这被认为是铺张浪费[125]。更高的片比最终在新电影导演中成为一项共同的改革运
动。然而,在新电影出现之前,侯和陈已经对陈规陋习发起了挑战。
甚至是今天已经成为侯孝贤标志的长镜头,也和他早年在工业中的经验有直接
关系。侯孝贤最初并没有把长镜头当作一种有意识的美学策略。它们是他要求更好
的表演无心插柳的产物。作为一个副导演,侯孝贤知道既有的做法需要改变。但
是,他在那个位置上被那些方法所束缚。一旦他自己成为导演,他便开始实践一个
导演应该真正地在现场执导的“新奇”观念。然后他开始不断试验各种调整表演的
方法。陈和侯都没听过什么主镜头系统,但他们发现如果每个镜头都更长些的话,现有的分段拍摄方法中的表演将会更好。有时,更长的镜头对侯孝贤来说似乎是一
种给了他的演员更多表演呼吸空间的实践方法。这就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长镜头
风格大师之一的毫不起眼的起步。
早期的电影证明了这点。以当时的行业标准来看,陈是一个长镜头导演,侯就
更加是了。以1980年至1982年间的二十五部抽样影片来看,平均镜头长度为八点三
秒。然而,陈1982年的《俏如彩蝶飞飞飞》平均镜头长度为十点三秒,侯孝贤的
《就是溜溜的她》为十一点三秒,《风儿踢踏踩》为十二点七秒,《在那河畔青草
青》又是十一点三秒[126]。在同样的三年中,只有李行的《原乡人》和白景瑞的
《皇天后土》的平均镜头长度接近。
这些早期作品的风格揭示了一个新导演在现有条件下仍寻求新美学的不经意的
探索。这三部电影都采用了变形宽银幕格式;都含有大量的变焦镜头。在《风儿踢
踏踩》中,一对爱人(钟镇涛和凤飞飞饰演)外出到田野的情形在一个长达两分钟
的单镜头中展现:首先是远景拍摄,然后拉远至一个更远的镜头展示梯田及其后面
的山岭。与之对照,《就是溜溜的她》中,凤飞飞饰演的角色和她的姑婆在饭店谈话的场景,表明了后来将采用的手法:也长约两分钟,但这一次摄影机纹丝不动。
虽然有这些例子,但是侯尚未有意识地追求长镜头美学。按他自己的说法,他依然
从其他角度拍摄,但是当他发现从一个更宽的视角拍摄的镜头很好很特别时,他明
白再也没有理由使用其他机位的镜头。这逐渐变成了一个习惯[127]。
追求更好的表演不仅影响了侯孝贤拍摄场景的方式,也最终影响了侯孝贤的编
剧方式和结构影片的方式。毕竟,侯在他作为商业导演的早期,仍然面对一个几乎
无法跨越的障碍:明星——或者如侯所形容的,不会表演的流行歌手。这些歌星演
员是如此在意他们的银幕形象,以致侯对他们束手无策。
不过,在他的三部商业电影中,因为一群表演沉着自如的孩子,《在那河畔青
草青》取得了一个大的突破。最值得注意的时刻是在父亲摔死小男孩的宠物猫头鹰
时他表现得很难过。这个五十五秒的镜头构图非常突出,在深度上采用了层次分明
的调度,父亲在前景,小男孩在远处斜对着他,摔掉书包,生气地吼叫(图4)。这
些孩子的表演使得侯孝贤第一次获得评论界的注意。有人形容这部电影“采用一种
平静的诉诸观众情感的方式,温暖柔和地描绘孩子世界,使得影片别开生面,优美
动人,一点也不盲从近期潮流”[128]。侯说他发现指导孩子们拍戏是容易的。当他
们犯错的时候他从不告诉他们,而是总是假装灯光出了问题,或者某个剧组成员犯
了错。(反过来,剧组成员也都明白侯的意图,并且假装内疚。)结果是这些儿童
演员通常在第二次或者第三次拍摄的时候更好。然而,这么做并没让侯孝贤臭名远
扬,反而提炼出了一种运用至今的新的拍摄方法:即兴创作[129]。侯只会告诉这些
孩子们处境,要不然就是让他们即兴创作对话的真正台词,像这些事他是从来不会
让钟镇涛和凤飞飞这样的明星做的[130]。这种导演方法起初只是用来指导《在那河
畔青草青》中的孩子,如今成为侯孝贤指导每个演员的方法:侯通常提供情境、情
绪和一种氛围感,但不提供精确的对话台词或者严格的调度指令[131]。图4 侯在《在那河畔青草青》中运用了复杂的纵深调度
因为侯孝贤和陈坤厚在商业电影中的革新,不难明白为什么他们能够配合默契
地推动新电影萌芽。《在那河畔青草青》是他们开创新局面的敲门砖。詹宏志是侯
孝贤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他说这部电影因其开创性和自由流动的叙事,而成为新
电影的源头之一[132]。黄建业宣称,这部电影的成功鼓舞了“中影公司”以《光阴
的故事》尝试低预算更多艺术自由的拍摄方法[133]。不久,侯和陈被誉为新电影
的“精神领袖”[134]。在这场运动中,侯孝贤发展了一套全新的人际关系,其中一
些人直至今天仍对他至关重要。关于侯孝贤的背景,人们惊奇的是他没有受到外部
影响,这表明他是完全的土生土长。他不像新电影运动中的其他成员,从来没有去
过海外的电影院校求学,而且令人遗憾的是他对诸多世界电影潮流都一无所知,包
括那些被误解认为对他产生影响的潮流。早年常有人拿侯孝贤和小津安二郎作比
较,没什么比这点更清楚:和那些通常推断的相反,侯声称他甚至从来没有看过小
津一部电影,直至他拍了《童年往事》[135]。而且,侯不是那些受过西方训练的电
影人,甚至也不是杨德昌,到头来却成为新电影的真正中心。他的电影定义了这场
运动。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侯有一样东西是别人所不具备的:各个方面的经验。
他不但经历了台湾在他眼前发生的变化,而且拥有在台湾电影工业摸爬滚打的日常
经验。这些共同创造了他的辉煌事业。然而没有大量的运气和帮助,侯孝贤不会有
这样的成就。他需要朋友和制度的支持。幸运的是,他恰好在一个正确的时间成为导演:一切——台湾社会和台湾电影——都在1980年代发生了更剧烈的变化。到这
个十年结束,这个男人和这座岛屿都将脱胎换骨。有时候,时机就是一切。
注释
[1]Song Guangyu宋光宇,ed. The Taiwan Experience台湾经验,2 vols.
(Taipei: Tung Ta,1994).
[2]Chen Ruxiu陈儒修,Taiwanese New Cinema's History,Culture and
Experience台湾新电影的历史文化经验,2nd ed.(Taipei: Wanxiang,1997).
[3]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vised ed.(New York:
Verso,1983,1991).
[4]Melissa J. Brown,Is Taiwan Chines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2.
[5]Ibid.,5;Denny Roy,Taiwan: A Political History(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 242–45.
[6]Li Xiaofeng李筱峰,The Hundred Biggest Incidents of Taiwanese
History台湾史100件大事,vol. 1(Taipei: Yushan,1999): 30–31.
[7]Ibid.,39–45.
[8]Li,57.
[9]Roy,31.
[10]Li,91.
[11]Ibid.,94–96.
[12]George H. Kerr,Formosa Betrayed(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65): 20.[13]更值得注意的是侯和杨德昌同一年出生在广东省的同一个客家聚居地梅
县。
[14]Chu Tian-wen朱天文,interview by author,June 2,2001,Sogo
Department Store Coffee Shop,Taipei,Taiwan.
[15]Li Qiao李乔,“The Significance of 228 in the Taiwanese
Psyche,”228 Studies,403.
[16]Li Xiaofeng,vol. 2,35;Xu Jielin许介鳞,The Post-Wa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aiwan战后台湾史记(Taipei: Wenying Tang,1996),vol. 2,4.
[17]Ibid.,57–59.
[18]Xu,15–16.
[19]Ibid.,25.
[20]Xiong Zijian熊自健,“Post-War Taiwanese Liberalism and the
Thought of Hayek,”in The Taiwan Experience,vol. 2,27–65.
[21]Li Xiaofeng,vol. 2,91–92.
[22]Chen Zhongxin陈忠信,recorded in Violence and Song: The Kaohsiung
Incident and the Formosa Judgment暴力与诗歌:高雄事件与美丽岛大审,Part 3
of the Oral History of the Formosa Incident珍藏美丽岛口述史(Taipei:
Times Publishing,1999): 98.
[23]Copper,115.
[24]Shi Minxiong施敏雄and Li Yongsan李庸三,“The Directions and
Structural Changes of Taiwa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in A Collection
of Treatises on Taiwa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台湾工业发展论文集,Ma Kai
马凯,ed.(hereafter cited 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Taipei:Lianjing,1994): 3.
[25]Yu Tzong-shian,The Story of Taiwan: Economy(Taipei: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1999): 8.
[26]Copper,139.
[27]Li Xiaofeng,vol. 2,31–34;Xu,vol. 2,95–98.
[28]Xu,118.
[29]Shi and Li,22,24.
[30]Copper,122.
[31]Ma Kai,“The Evolution of Taiwan's Industrial Policies,”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97.
[32]Copper,135.
[33]Chen Zhengshun陈正顺,“Import-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Discussion of Conclusions and Research of Taiwan's
Situation,”Industrial Development,84–85.
[34]Copper,126–27.
[35]Ma,147.
[36]Lin Zongguang林宗光,“The Taiwanese Identity Problem and
228,”in 228 Studies,363.
[37]Xu,vol. 2,69–71.
[38]Li Xiaofeng,vol. 2,14–15。当然,当然,当局允许拍摄台湾方言电
影,这可能看起来令人奇怪。事实是,“国语”教育是当局企图压制台湾方言的基石。它并不完全反对出于宣传意图使用台湾话,因为当局知道很多人失学,也学不
好“国语”。只要电影不违反任何政治禁忌,就仍然可以使用台湾话作为主要语
言。
[39]Liu Xiancheng刘现成,Taiwanese Cinema,Society and State(Taipei:
Yangzhi,1997): 34–36.
[40]Ibid.,37;Lu Feiyi卢非易,Taiwanese Cinema: Politics,Economics,Aesthetics(1949–1994)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
1994(Taipei: Yuanliu,1998): 69–71.
[41]Liu,38.
[42]Li Minghui李明辉,“Confucianism and Kant in the Thought of Mou
Zongsan,”in The Taiwan Experience,vol. 2,91–97.
[43]Jiang Nianfeng蒋年丰,“The Existentialist Wave in the Post-War
Taiwan Experience: Sartre at the Center,”in The Taiwan Experience,vol.
2,1.
[44]Ibid.,2.
[45]Chang Sung-sheng,Yvonne,Modernism and the Nativist Resistance: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 12.
[46]Ibid.,100.
[47]Xu,vol. 2,64–65.
[48]Wang Jing,“Taiwan's Hsiang-tu Literature: Perspectives in the
Evolution of a Literary Movement,”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 Critical
Perspectives,Jeannette L. Faurot,ed.(hereafter Fiction from Taiwa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 61-62.[49]Chang Shi-kuo,“Realism in Taiwan Fiction: Two Directions,”in
Fiction from Taiwan,31.
[50]Wu Mingren,“From Worship of the West to a Popular
Consciousness,”A Collection of Discussions about Nativist Literature乡
土文学讨论集,Yu Tianzong尉天骢,ed.(hereafter Nativist Discussions)
(Taipei: Yuanliu Zhangqiao,1978): 3–6.
[51]Wang Fan汪帆,“Speaking of Modern People and Modernization,”in
Nativist Discussions,37.
[52]Jiang Xun蒋勋,“To Irrigate a Cultural Flowering,”in Nativist
Discussions,49.
[53]Chen Yingzhen陈映真,“Literature Both Reflects and Comes from
Society,”in Nativist Discussions,64.
[54]Li Zhuo李拙,“Direc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wentieth Century
Taiwanese Literature,”in Nativist Discussions,126.
[55]Zhang Zhongdong张忠栋,“Native Soil,the People,and
Strengthening Oneself,”in Nativist Discussions,496.
[56]Peng Xiaoyan彭小妍,“The Nativist Debate in 1970's Taiwan,”in
The Taiwan Experience,vol. 2,68–69.
[57]Xiang Yang向阳,“Opening the Map to Consciousness: A Look Back
at Post-War Taiwanese Literary and Broadcast Media Movements,”in
Discussions of Contemporary Taiwanese Political Literature当代台湾政治文
学论,Zheng Mingli郑明娳,ed.(Taipei: Times Publishing,1994): 88.
[58]Song Guangyu宋光宇,“A Discuss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in Taiwan over the Last Forty Years,”in The Taiwan Experience,vol. 2,194.
[59]Ibid.,200.
[60]Ibid.,175.
[61]Ibid.,184.
[62]Hsiao,Hsin-huang Michael,“Coexistence and Synthesis: Cultural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in Many
Globalizations: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Peter
Berger,Samuel Huntington,eds.(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63.
[63]Sung,188–89.
[64]Brown,239.
[65]我没有这些见识,而是采用了富布赖特学者Sansan Kwan的观点,她那时正
在做研究云门的论文,同一年我正在研究侯孝贤。我要多多感谢她为我介绍台湾文
化难题中的关键部分。这里若有任何关于现代舞和云门的幼稚或无知的评述,都完
全是我的责任。
[66]Peggy Chiao焦雄屏,interview by author,March 10,2002,Middleton,Wisconsin.
[67]Li Tianduo李天铎,Taiwanese Cinema,Society and History台湾电影:
社会与历史(Taipei: Yatai,1997): 42–45.
[68]Ibid.,60–61.
[69]Ibid.,106;Lu,35–37.
[70]Huang Ren黄仁,The Film Era of Union联邦电影时代(hereafter cited
as Union)(Taipei: National Film Archives,2001): 35–36.[71]Li Tianduo,109;Lu,64–66.
[72]Lin Zanting林赞庭,Cinematography in Taiwan 1945–1970: History
and Technical Development台湾电影摄影技术发展概述1945—1970(Taipei:
Cultural Development Office,2003): 37.
[73]Peggy Chiao焦雄屏,Generational Reflections时代显影(Taipei:
Yuanliu,1998): 154.
[74]Li Yongquan李泳泉,Taiwanese Cinema: An Illustrated History台湾电
影阅览(Taipei: Yushan,1998): 17.
[75]Huang Ren黄仁,Film and Government Propaganda电影与政治宣传
(hereafter cited as Government Propaganda)(Taipei: Wanxiang,1994):
27.
[76]Ibid.,8.
[77]Ibid.,9.
[78]Lu,155.
[79]Ibid.,163.
[80]Liang Liang梁良,Studies on the Three Chinese Cinemas论两岸三地电
影(Taipei: Maolin,1998): 133–34.
[81]Lu,76;Liang,135.
[82]Lu,206.
[83]Huang Zhuohan黄卓汉,A Life in Cinema: ......
您现在查看是摘要介绍页, 详见PDF附件(8839KB,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