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不平等逸史.pdf
http://www.100md.com
2020年4月7日
 |
| 第1页 |
 |
| 第7页 |
 |
| 第20页 |
 |
| 第25页 |
 |
| 第46页 |
 |
| 第101页 |
参见附件(9969KB,231页)。
全球不平等逸史,这是一本妙趣横生的关于研究不平等的佳作,书中为读者以三个章节来分析了不平等,作者所写也是描述社会存在的问题,值得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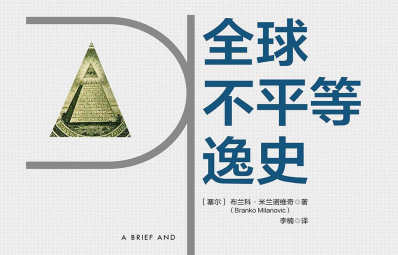
介绍
谁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人?你的出生地会影响你一生所挣财富的多少吗?我们怎样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呢?如果不是出于无所事事时的好奇心,这些问题还会有哪些意义呢?作为研究财富、贫穷和贫富差距的专家之一,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在这本书中回应了上述问题,解释了既往和现今的世界财富缘何分配不均。
作者信息
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卢森堡收入研究中心研究员,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首席客座教授。曾任世界银行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并建立世界银行“All the Ginis”数据库。
书籍目录预览
第一章 散论一 不平等的人们:一国之内个体间的不平等
小品1.1爱情与财富
小品1.2安娜·伏伦斯卡娅?
小品1.3谁是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人?
小品1.4罗马帝国有多不平等?
小品1.5在13世纪和今天,你应该住巴黎的哪个区?
小品1.6谁从财政再分配中获益了?
小品1.7若干国家可存于一体吗?
小品1.8中国的不平等
小品1.9研究不平等的两个学者:帕累托和库兹涅茨
第二章 散论二 不平等的国家:环球诸国间的不平等
小品2.1为什么马克思描述的社会分化后来出现了转折?
小品2.2当今世界的不平等
小品2.3几多富贵前生定?
小品2.4整个世界应由门禁森严的社区组成吗?
小品2.5谁是“哈拉伽”?
小品2.6奥巴马家族的三代
小品2.7去全球化下的世界变得更加不平等了吗?
第三章 散论三 不平等的世界:世界公民间的不平等
小品3.1全球收入分配中,你在哪里?
小品3.2世界范围内的中产阶层存在吗?
小品3.3美国与欧盟有何不同?
小品3.4为何亚洲与拉丁美洲互为镜像?
小品3.5你想在比赛前就知道赢家吗?
小品3.6收入不平等与全球金融危机
小品3.7殖民者随心所欲地剥削吗?
小品3.8为什么罗尔斯对全球不平等问题无动于衷?
小品3.9经济学视角下(或受其启发)的地缘政治
全球不平等逸史截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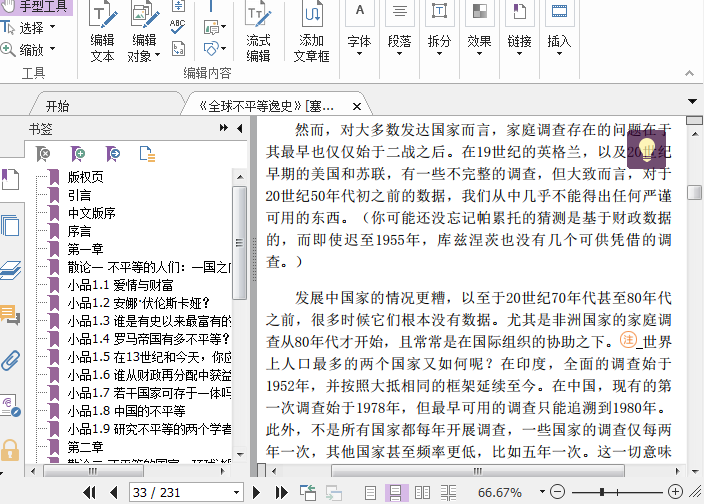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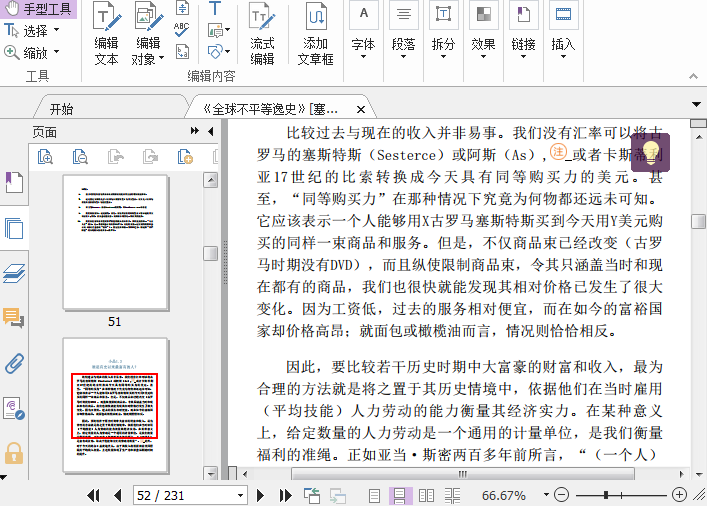
书名:全球不平等逸史
作者:[塞尔]布兰科·米兰诺维奇
译者:李楠
ISBN:9787521708332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是查明规律,以见收入分配是如何
体现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政治经济学原理》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17年)
在对于公平合理的经济学有害的诸趋向之中,最具迷惑性
且……为害尤烈的,是偏注于分配问题。
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
《工业革命:过去与未来》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Past and Future )(2004
年)中文版序
鉴于在国内不平等和全球不平等的演进中,中国异乎寻常
的重要角色,这本针对这两类不平等的书对于中国读者可能尤
为有趣。
让我们先从后者说起。全球收入不平等是普天之下所有个
体间的不平等。我们从国内家庭调查得到相关数据,并根据国
家间的价格差异做出调整,由此,不论收入是来自贫穷国家、中等收入国家还是富裕国家,均以所谓国际元这同一单位表
示。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几乎占了全球人口的15,而且中国发
生的任何事情都将强烈地波及四方,因此中国在这样的计算中
显然至关重要。而结果是,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减少
了全球不平等,但另一方面,其国内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也加剧
了全球不平等。
这就将我们引向了国内不平等。在该问题上,由于过去非
同寻常的三十多年间,中国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15倍,而其由
基尼系数这一最常用的不平等测度表示的收入不平等也翻了一
番,因而中国的经验独一无二。由此,中国的发展不仅于世界
影响巨大,而且也对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人物提出了两
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即使包括最贫困者在内的所有人的收入都增加,就
社会而言,与之相伴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接
受的?鄙意以为,正如中国在1978年所为,若我们从非常低的
收入和不平等开始,则不平等和真实收入的增加显然是可取
的。并非所有人都可以一蹴而就地变富,所以若某些人先起
来,而其他人随后跟进,尤其是若向上流动的前景明朗,则这
样的发展就是受欢迎的。然而,若不平等的上升持续多年,则
在某一点之后社会就面临分崩离析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形下,少数人与大多数人的生活、行为和消费模式产生巨大差异,则
即使经济继续增长,不平等的进一步扩大在政治上都是不可持
续的。换言之,若相信高速增长将最终“弥补”上升的收入和
财富不平等,就太过天真了。问题是,中国是否已经处于这样
的状态?
其次,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间的不平等就是依循西蒙·库
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20世纪50年代揭示的模式在演化,即在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从农村向城市,以及从以国有制
为基础的经济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的转型中,不平等会上
升;然而,当国家“成熟”而变得富裕之后,不平等开始下
降。若中国要跟从库兹涅茨描绘的路径,则其上升的教育水平
应当减少其不同受教育程度工人间的工资差异,其老龄化人口
应当得到更多的退休金和失业救济这样的社会保障,以及甚至
更有效的卫生保健,这些再加上推展到农村人口的惠政,将遏
制不平等的进一步上升,并使其最终减少。基于库兹涅茨的观
点,中国目前可能将开始降低其收入不平等。在中国,有两股力量与库兹涅茨揭示的“无害的”减少不
平等的因素相对抗,即日渐攀升的财富不平等(进而资本利得
不断增加的重要性),以及腐败。在所有国家,资本收入分布
都极为不平等,其上升的部分几乎自动转化为更大的收入不平
等,中国也不例外。而腐败就是第二个负面力量。由于较之于
对穷人,腐败对富人更为有利,因而反腐看起来不仅是维护国
家政治稳定之必需,也是终止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之道。
最后,就中国在全球收入分配中的角色,我们或可多说一
二。20世纪80年代末,一个在中国农村具有平均收入的人比世
界人口中的20%更富裕,而今天,这一比例提高到了36%。至于
城市居民,相关数值则分别是50%和65%。由此,不论是居住在
中国农村还是城市,具有平均收入的人,其收入均超过大约
15%~16%的世界人口,即10亿人。这是巨大的成就。然而,若未
伴以诸如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刚果或埃塞俄比亚此类穷
国类似的高增长率,这也意味着中国未来的高增长率将增大全
球不平等,而不是减少不平等。于世界而言,中国基于其新获
得的财富,将成为不利于平等化的力量。虽然对中国来说,这
一发展确是好事,但这也突显了非洲和亚洲贫困国家的发展对
人类的未来至关重要,并且日渐富裕的中国亦应在减少全球贫
困和不平等问题上充分扮演其国际角色。序言
本书讲述了上下古今的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因为所有的
人类社会都伴随着权力与财富的差别,不平等紧随人类社会的
产生而出现。既然不平等是涉及“关系”的现象(relational
phenomenon,即只有存在别的个体,才能说一个人与之相比是
不平等的),那么从定义上说,不平等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现象
和观念,故而仅存在于社会之中。鲁宾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自己不会有平等的观念,但他和仆人“星期五”在一
起时就有。此外,当社会不是个体的机械汇聚,而是一群共享
着诸如政府、语言、宗教或历史记忆等特征的民众时,谈论不
平等就更为自然不过。
本书以故事铺陈,意在以一种独特而有趣的方式,呈现收
入与财富不平等如何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散
布于茶余饭后案头桌边的谈资或讨论里,而当我们以不同的视
角看待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时它又如何出现。我们的目标在于
揭示收入与财富、富裕与贫穷间的差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
要作用,及其在历史中的非常之处。
本书围绕三种类型的不平等展开。在第一部分,我讨论在
一个单一社群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国
内人际不平等。这种类型最易察知,因为当我们听到“不平
等”这个词时,很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这种不平等。在第二部分,我讨论国家或民族间的收入不平等。对于大多数人,这在
直观上亦非常切近,因为当我们旅行或观看国际新闻时会注意
到这类事情。一些国家大多数人看起来比我们穷,但在另一些
国家大多数人似乎非常富有。而当穷国的工人为了挣更多钱和
享受更高水平的生活移居富国时,这些国家间的不平等也体现
出来。在第三部分,我将话题转向近年来才开始引人注目的问
题上:全球不平等,或者说世界上所有公民间的不平等。这种
不平等是前两种不平等(即国内人际不平等和国家间不平等)
的总和,但却是一个崭新的话题,因为只有伴随着全球化,我
们才开始习惯对照和比较我们自己和世界上其他个体的命运。
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展开,在三种类型中,该类不平等的
重要性可能上升最多。
我以简短的故事(或曰“小品”,vignette)来说明每种类
型的不平等,其中一些小品将我们带回罗马时代,而另一些如
关于巴拉克·奥巴马家族、全球中产阶层或欧洲的马格里布移
民这样的话题,则大抵取自每天的报纸。每篇小品可单独阅
读,且不必按照顺序。然而,有时某些小品的话题互相关联,若依次阅读则更为有趣。但无论如何,它们均独立成篇。
就特定类型的不平等,每部分以散论(essay)开篇,概述
经济学家对此的观点。尽管散论意在能被所有感兴趣的读者理
解,然而与阅读小品相比,确须投入更多精力,因而可能稍具
挑战性。对于小品中讨论的问题,散论将有助于读者在技术上
有更好的理解。对于那些渴望更为深入探究本书问题的读者,散论也是一份文献导引。在该书结尾的“延伸阅读”中,我也列出了以散论和小品为序的精选读物书目,以供想要了解更多
的读者参阅。就每个给定的主题,我认为这些书籍和文章最为
有趣而切当。
对我个人而言,写作本书不仅愉悦,而且颇为轻松。在不
平等问题上研究了超过14世纪后,我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信息
和逸闻趣事,可谓俯拾皆是,故若与读者分享,我认为彼此都
会兴味盎然。动笔之时,我并未多想其内容或架构,而仅是把
我思虑经年且有现成数据的所有东西写下来而已。以个人视角
来看,也许最为重要的是,该书提供了机会,将我对数字和收
入分配的激情与对历史的激情结合起来。
我有三个目标,但正如所有作者一样,我不知道能否达成
其中任何一个。一方面,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故事时能轻松愉
快,并将之与对新事实的了解或者看待事物的新视角结合起
来。另一方面,由于诸多原因[其中一些是“客观”的,而另一
些则可能受制于有钱人(the rich)的利益],不平等问题大多
被置于公众视野之外,以避免使他们“不安”,故而我认为重
要的是第二个目标,即引起公众对财富与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关
注。而第三个目标,则是将财富和贫穷这一问题带入社会讨论
的中心,尤其当危机来临之际,可以激发某些传统的社会行
动。换言之,人们有权开始质疑某些收入的合理性,以及存在
于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内富人与穷人间、世界范围内富国
与穷国间的巨大差距。这是某些主导性的社会舆论制造者试图
弃而不顾的问题,但我认为,他们太草率了。他们认为全部或
几乎全部的不平等都由市场决定,故这类问题不应作为讨论的对象。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不平等取决于相对的政治权力
(全球金融危机就此展示的例子数不胜数),同时也不能通过
引入“市场”就将这类质疑从社会舞台上除去。市场经济是一
种社会构造,它被建立,更确切地说是被发现以服务于人类,因此在每一个社会中提出与其运行方式有关的问题是完全正当
的。
我要以一点技术说明来结束序言。读者阅读所及,会发现
该书包含了大量计算结果,其中所有未明确地以注释标示来源
的部分均为我个人未公开的工作成果。它们基于多种多样的数
据,但大多源于世界银行和“世界收入分配”数据库,其中包
含了来自大多数国家的诸多宏观数据和数百个家庭调查。若对
我计算的每一个数字都逐一列出来源,则过于单调乏味。如果
读者对于某个特定的事实或计算特别感兴趣,我很乐意提供准
确 线 索 , 你 们 可 通 过 电 子 邮 件 与 我 联 系
(bmilanovic@worldbank.org或branko_mi@yahoo.com)。对于
其余的源自其他作者及其出版物中的数据,该书均明确地指出
了资料来源。
我非常高兴在此感谢许多协助和支持我的人。因为该书从
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不平等这个主题超过20年的研究所得,我的
感谢名单不得不非常之长,包括几乎我遇见或受教的每一个
人。但愚钝如我,显然已力有不逮,故只能把范围缩小到那些
直接参与了写作此书的人。在每个小品或散论的开篇之处,我
感谢为之给予了意见、评论和建议的人士。除此之外,我还要
感谢编辑Tim Sullivan和Melissa Veronesi,他们搭建了这本书的结构;感谢Annette Wenda逐字逐句地认真校阅;感谢
Michele Alacevich和Valentina Kalk,我颇为倚重他们对于该
书实质上和审美趣味上的建议;感谢Gouthami Padam,他与我
共事超过7年;感谢陈少华在中国家庭调查上给予了不可估量的
帮助;感谢LeifWenar对政治哲学有关问题提出的建议,尤其是
对我时常参阅的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著作的解释,以
及 对 手 稿 诸 多 部 分 给 出 的 精 彩 评 注 ; 还 有 Slaheddine
Khenissi,感谢他关于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渊博学识。当
然,对该书中表达的观点,我一人承担责任。
布兰科·米兰诺维奇
1. 然而,对该断言须做如下说明:它适用于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即从定
耕农业(sedentary agriculture)出现之后。在人类历史超过90%的史前时
代,在其大多数时间里,据信人们依靠群居生活,而其中的平等几乎是绝对的
(见Ken Binmore,“The Origins of Fair Play,”Keynes Lecture 2006,The
Papers on Economics and Evolution ,No.0614,Jena:Max Planck
Institute,2006)。第一章散论一
不平等的人们:一国之内个体间的不平等
国民收入按职能分配是指总收入如何在社会的大阶级(即
工人和资本家)间分配,许多人认为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所
在。直到20世纪之交,个体收入不平等确实是被纳入这一主题
之下的。 19世纪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通常分为几个截然不
同的阶级:工人出卖劳动而获取工资,相对贫穷;资本家占有
资产并赚取利润,相对富有;地主拥有土地随之收取租金,也
堪殷实。一般认为,这三个阶级间的收入分配对决定社会的未
来至关重要。比如,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这一政治经济
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认为地主的收入份额将会增长,这是因
为随着人口增加,对食物的需求上升,进而会开始耕作那些越
来越不肥沃的土地,并最终使“工资品”(这里指食物)的价
格和地租飞涨。他将最终结果视为一种稳态,即受到同时上涨
的食物价格与地租的挤压,微薄的利润几乎无法激励储蓄和投
资。 又如,在马克思看来,随着工人人均资本增加,机械化
程度加深而资本回报降低,长此以往的趋势是利润率减少并最
终接近于零,从而扼杀投资。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被始于1870年左右的“边际革
命”取代,其焦点由社会各阶级宏大的经济演进转移至个体最
优化,这成为经济学史的关键转折点。随后,古典经济学与边际效用学派这两条研究路线在“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出自
剑桥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名义下融合并确立了其在
主流经济学中的地位。尽管如此,通过社会阶级的棱镜看待收
入分配并未由此改变太多。直到20世纪初,个体间而非阶级间
的收入分配问题才引起执教于瑞士洛桑大学的法国—意大利经
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关注(其贡献见小品1.9)。
大约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国家更加富裕,政府的财
政作用愈发广泛,而个人收入分配数据第一次开始有案可查。
此类信息的出现最初是因为民族国家需要了解收入信息以便征
更多的税,并用于公共教育、工伤以及战争这一最为重要的目
的。此外,意识形态的转变同样重要,即人们转而认识到在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故富人应根据他们更多的财产和收入做出更
大贡献。税收必须更紧密地与收入联系在一起,这就要求对收
入及其家庭分布情况更为了解。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帕累托
用于研究个体间收入分布的数据均来自欧洲19世纪后期的财政
统计。在那时,该书的主题就已经诞生了。
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以三种方式关注不平等。他们提出
的第一类问题包括:是什么决定了一国之内人与人之间的不平
等?随着社会发展,是否存在不平等以某种特定方式表现出来
的规律?不平等会随着经济扩张变得更严重吗?换言之,它是
顺周期性的还是逆周期性的?在这些问题中,不平等是应当得
到解释的因变量。在第二类问题中,不平等是用来解释其他经
济现象的自变量。比如,对于经济增长、更好的治理、吸引外
资或教育普及等,是高还是低的不平等更为有利?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在纯工具意义上审视不平等,即我们感兴趣的是其究
竟促进还是阻碍了某种我们期望的经济结果。不平等进入社会
科学家视野的第三种方式是他们探讨与之相联系的伦理问题。
这时,他们关注的是呈现不同程度不平等的社会制度(social
arrangement)正义与否,比如,是否只有当更严重的不平等增
加了穷人的绝对收入时,前者才可被接受?又如,对源于优越
家庭环境的不平等与源于出色工作和努力的不平等,我们应区
别对待吗?
不平等如何随着社会收入水平变化 ?基于对19世纪末欧洲
国家和城市税收数据少量样本的研究,帕累托坚信“人际不平
等的铁律”,因而即使社会制度有异,但无论是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分配格局均大抵不变。换言
之,社会精英或许不同,他们掌控社会的方式亦可能有别,但
收入分配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平等水平将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如
今,这个规律被普遍称作“二八定律”,即在某些现象中我们
观察到20%的人占有80%的产出;相反,其余80%的人却只占有
20%的产出。比如有人认为,二八定律存在于质量控制(即80%
的问题源于20%的产品)、市场营销和商业应用中,而我们在全
球收入分配问题上甚至也可看到类似规律(见散论三)。至于
国内收入分配,恰恰由于帕累托深信经验已证明其一定是大致
固定的,并无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的法则,故他并未建立
关于其变化的理论,因此称之为“失败”并不完全恰当。在帕
累托看来,唯一的法则就是“收入分配固定”(law of its
fixity)。直到1955年,俄裔美籍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西蒙·库兹涅
茨才提出第一个真正的理论以解释是什么促使收入分配产生变
化(小品1.10是对其和帕累托的传略)。根据比帕累托略为丰
富的数据(虽然数据种类不同:库兹涅茨使用的是家庭调查,而非财政调查),他认为在不同的社会中,人际的不平等并不
相同,且随着社会发展它将以可预见的方式变化。在极度贫穷
的社会,因为大多数人的收入都只在温饱线上下,人与人之间
几乎不存在经济差距,从而不平等程度一定很低。然后,随着
经济发展以及人类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库兹涅茨断
言,相对富裕的产业工人和相对贫穷的农民的平均收入出现差
距。而与农民相比,由于现代工业对工作的要求更为多样化,工人间的收入差距也更大。因此,在这两种不断扩大的收入差
距作用下,收入不平等增加。最终,在更发达的社会,国家开
始扮演再分配的角色(见小品1.6),教育更为普及,不平等亦
随之下降(见小品1.1和小品1.2)。由此,我们得到著名
的“库兹涅茨假说”,其中的倒U形曲线描绘了收入不平等随经
济发展的变化,即不平等一定是先上升,后下降。
然而,这一观点并不是全新的。在库兹涅茨假说问世前约
120年,法国社会科学家、政治家托克维尔已提出类似看法,值
得在此全文引述:
如果仔细观察这个世界自社会出现之后发生了什么,我
们很容易发现,就历史维度而言,平等仅在文明的两极才普
遍存在。野蛮人是平等的,因为他们同样羸弱无知,而非常
文明的人亦可达致平等,因为他们都在其支配范围内用相似的方法得享安康幸福。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境况、财
富和知识的不平等,少数人拥有权力,但其余的人穷困、愚
昧而孱弱。[《济贫法报告》(Memoir on Pauperism
,1835)]
当然,托克维尔并不是库兹涅茨那样的经济学家。除了这
些,他并没有更多的言说,尤其是关于倒U形曲线成立的机制。
库兹涅茨假说自1955年首次发表以来,被经济学家一再检
验。全国性的家庭收入和消费调查本是收入分配信息的关键来
源,随着其日渐唾手可得,关于库兹涅茨假说的实证研究大大
推进了。理论上,当我们研究单一国家内不平等的演变时,随
着其经济经历从农业到工业,并最终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剧变,原则上,该假说应体现得最好。但在此情形下,其表现却模棱
两可,一些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呈现倒U形的发展模式,而其
他国家却没有。
出于对库兹涅茨假说的表现和预测能力不满,人们在其中
加入了新的要素,使它能够更好地解释收入不平等的变化。修
正后的理论被称为“扩展的库兹涅茨假说”。诸如经济体
的“金融深度”、政府支出范围、国有部门就业水平及经济的
开放程度等因素如今也与收入水平一道作为可能的额外变量,用于解释不平等的变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些额外的变量
能够增进我们对不平等变动的理解。例如,这里的基本原理包
括:就金融深度而言,一个更高效而广泛的金融部门将允许穷
人借款支付自己的教育费用,是以教育的大门将向所有人敞
开,而不再仅为富人保留,不平等将随之减少。就政府支出范围和国有部门就业水平而言,作为GDP(国内生产总值)一部分
的政府开支和作为总劳动力一部分的政府就业都应该对不平等
有削弱的作用,因其不仅帮助了穷人,也限制了工资不平等。
就经济的开放程度而言,在贫穷国家,更大程度的开放贸易将
增加对低技术密集型产品(比如纺织品)的需求,而这类产品
恰恰是这些国家擅长的,故相对于熟练工人的工资或资本家的
利润,这将倾向于提高不熟练工人的工资,并最终减少不平
等。在富有国家,因其倾向于出口高科技产品,开放贸易会产
生相反的影响。事实上,这些产品需要高技能的人才(比如计
算机科学家或工程师),是以大学毕业生的工资较之于只有小
学或中学学历的人而言相对增加,故不平等扩大。现在,在收
入之外,经济学家在检验典型的库兹涅茨假说时还包括所有这
些因素,而且可能也常以便宜行事的方式纳入其他一些考量
(比如人口结构或土地所有权的分布)。结果比我们仅使用收
入水平时要好,但也谈不上多么精彩。
最近,在与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安东尼·
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及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等同行合作之下,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
(Thomas Piketty)进行了一系列覆盖十几个国家的实证研
究,否定了库兹涅茨假说及其扩展版本。皮凯蒂的研究表明,在过去14世纪里,西方国家的不平等在经历了长期下降后决然
上升。在他看来,政府会增加或减少对当前收入与遗产的直接
税,而战争会毁灭有形资本,降低资本家收入,这些影响为之
前众所周知的事实提供了某种“政治”解释。由此,这或可视
为收入分配的政治理论,在其中以何谓公正何谓不公正这样的人心归向,以及以选举、政党立场和经济的战争需要等反映的
经济利益,决定了不平等随时间变化的轨迹。
为了解释整个20世纪这样长的时期中推动不平等变化的原
因,皮凯蒂的研究诉诸财政统计这一古老而几乎已被遗弃的数
据来源。这一统计首次为帕累托所用,后来被家庭调查取代,这是因为穷人在大多数国家都不支付直接税,故财政统计只涵
盖了收入分配的高端部分。与之相反,家庭调查则囊括了所有
人。使用财政数据的问题在于,若要从中得出有效的结论,以
下两个假设必须成立:一、应税收入是家庭实际收入的良好近
似(且纳税最多的人也是最富有的人);二、总体不平等的变
动与最高收入群体收入份额的变化相当近似(比如,我们相信
纳税前1%的人亦是家庭财富排在前1%的人)。但是,两个假设
都很难完全站得住脚。就假设一来说,皮凯蒂及其合作者使用
的应税收入是“市场”[或曰“财政前”(pre-fisc)]收入,它排除了税收和政府的转移支付。 然而,我们通常感兴趣的
是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即在完税和收到政府转移支付后的家
庭和个人收入。因此,无论是税收还是转移支付改变,市场收
入的不平等和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都有可能会背道而驰。假设
二的问题在于,原则上,对不平等的统计应包括所有人的收
入,而不仅关注富人。比如,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形,若我们牺
牲中产阶层的份额,就可使最高收入群体和最低收入群体的收
入份额都上升。我们虽会倾向于单纯从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份
额上升得出结论,但在这里却不能说总的不平等增加了。皮凯
蒂等人的研究建立在这些特定假设之上,但这些假设并非放之
四海而皆准,因而对其研究结论的解释也大可存疑。当然,如果有过去足够长时间内的收入和消费调查,我们就不用依靠这
个支离破碎且很不准确的财政数据,问题也随之解决。不幸的
是,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在发达国家,这种调查通常在
二战之后才开始,而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这只是过去二三十
年间的事。
这就是不平等研究的现状。想要在这些不同观点中就哪一
个已经赢得了这场辩论做出结论,是不公平甚至是不可能的。
也许一个都没有。然而,在测量不平等或理解它是如何演变之
外,这一研究的确将我们引向问题的核心,即对于经济增长,不平等是否必要?如果是,它又应该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不平等如何影响经济效率 ?我们关注不平等,或者说我们
最关注不平等,是因为我们相信它影响一些重要的经济现象,尤其是经济增长,即不平等程度更大的国家增长更快还是更
慢?回顾历史,答案的钟摆已经从毫不含糊地认为不平等有利
于经济增长,转向有利于相反主张的更为细致的观点。
为何会有这样的改变?为便于理解,当我们关注经济效率
时,可将不平等视为胆固醇:有“好”与“坏”的不平等,正
如有好与坏的胆固醇。 人们需要“好”的不平等来激励其好
好学习、努力工作或创办有风险的企业项目。没有不平等作为
回报,这些情况都不会发生。但是“坏”的不平等始于一个不
易定义的点,在那之后人们不再有追求卓越的动力,转而靠不
平等提供的手段,维护已有的地位。当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用
来阻碍如农业改革或废除奴隶制这样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治变
革,或只允许富人得到教育,或确保富人占有最好的工作时,这种“坏”的不平等就会显现。所有这些都会削弱经济效率。
如果一个人接受好的教育的能力强烈受制于其父母的财富,这
就等于剥夺了这个社会大部分成员(在这里也就是穷人)的技
能和知识。在这个意义上,基于收入继承造成的歧视与诸如性
别或种族等其他任何歧视并无二致。在所有这些情形中,社会
中某一群人的技能被弃置,故而从经济上看,这样的社会不太
可能成功。因此,在特定的国家和时代,不平等既可是有利
的,亦可是有害的,这取决于居主导地位的是提供激励的“积
极”不平等,还是确保富人垄断地位的“消极”不平等。
当经济学家相信只有富翁才会积蓄,舍此即无投资和财富
创造时,对于经济不平等,占主导地位的是仁慈的眼光,以为
其将激励个人追求卓越。因为人们认为工人(或穷人)倾向于
花光所有,故若每个人拥有相同(相对而言)的低收入,则社
会就没有存蓄,没有投资,也没有经济增长。富人本身不重
要,重要的是其存在,如此他们才会积蓄,才会扩充资本,并
以种种手段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在个人储蓄中,富人被视为
存钱罐,在花费和享乐上不比常人,而超出部分则尽数用于积
攒和投资。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苦行主义是“资本主义精
神”的关键成分:“这种伦理追求的至善,是要尽可能地多挣
钱,同时力避一切本能的生活享乐。其最突出的是完全不掺杂
任何……享乐主义的成分。它被十分单纯地视为目的本身,以
致从个体的幸福或功利角度来看,显得完全……不合常理。”
在高收入被用于投资的前提下,对于此类为收入不平等辩
护的稍显理想化的看法,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1920年的文章中做出了或
许是最好的表达:
(1914年前的欧洲)社会将很大一部分增加的收入交到
了最不可能将其用于消费的阶级手中。19世纪的新贵在其成
长过程中并不习惯纸醉金迷。较之于即期消费的快感,他们
更享受投资带来的权力。事实上,恰恰是财富分配的“不平
等”使购置资产、改良设备这样的巨大积累成为可能,从而
使这个时代与其他时代区分开来。实际上,这正是资本主义
制度存在的最主要理由。若富人将其新财富都用于自我享
乐,则世人早就会无法忍受这样的统治。然而,前者像蜜蜂
一样储蓄和积累财富。此虽出于狭隘的个人目的,却没有减
少其对整个社会的贡献。
这是视资本家为“储蓄机器”和企业家的观点。
但是,世界上还大量存在着另一种资本主义食利者,除了
坐着让钱为其“工作”外,他们大抵是袖手旁观、逍遥自在,而在斯蒂芬·茨威格关于《昨日的世界》(The World of
Yesterday )(即一战前的欧洲)的佳作中,我们能找到对资
本主义食利者的文学描绘。在那个世界里,如茨威格所言,最
珍贵的赞美是“扎扎实实”,而身居高位者看重资产阶级的尊
严,社会的理性与昌明也似乎注定会绵延不绝。对富人来说,生活容易:于有钱人而言,由变利为本的不断累积而使自己富起
来,在那日益繁荣的时代只不过是保守的生财之道罢了,因
为即使是对最富有的人,政府也从未想过对其征收超过百分
之几的税……而国债和工业债券利率很高。
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存钱罐”和可能的投资者这样的角
色,富人看起来不太像是不可或缺的,他们更像是活得有滋有
味的寄生虫,除了撕撕息票,别的几乎什么都不做。然
而,“不平等是有害的”这一在过去几十年间开始占据主导地
位的观点,并非出自伦理道德的考虑。与视不平等为慈惠的力
量一样,它也认为应该有人愿意投资,但奇怪的是,同样的出
发点却导致截然不同的结论。在这种观点看来, 政府支出的
资金来源于税收,而从中获得的好处主要有利于穷人。当富
人、中产阶级和穷人投票决定缴多高的税时,非常不平等的社
会倾向于把票投给高税收,这仅仅是因为有很多人可以从政府
转移支付中获益,却缴很少的税或根本不缴税,故在票数上穷
人总能胜过为数不多的富人(见小品1.7)。然而,高税收减少
了对投资和努力工作的激励,经济增长率也随之降低。这一机
制类似于19世纪时的恐慌,即没有财产的人只要有投票权,就
必然会剥夺富人的财富。现在,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只是剥
夺得稍显温和,换言之,它不是依靠国有化,而是依靠税收。
无论认为经济不平等有利还是有害,最重要的是要有人愿
意投资。但若持第一种观点,富裕的投资者会要求高度的社会
不平等;若持第二种观点,则引入政治上的民主就会破坏高度
的不平等,使其在政治上难以为继。即使富人能设法向穷人承诺他们会将过剩的收入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继而对经济增长
而言他们不可或缺,但该承诺却无法被强制执行,故也是不可
信的。因而,一定得在可持续且不鼓励人们选择敲诈性税率的
税前收入分配之上,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持续运转。为此,人与
人之间的资产须相对均等地分布。在短期或中期内,我们不太
能够影响金融资产的分配,却可以影响教育(经济学家称其
为“人力资本”)的分配,因而重点在于每个人都能更容易地
接受教育。这不仅是因为教育本身是可取的,甚至也不是因为
教育程度高能直接有助于经济增长,还在于人力资本更广泛的
分布将使税前收入分配更为平均,并使相对贫穷的人在把选票
投给高税收之前能够三思。
经济发展会改变我们对不平等的看法吗?很有可能。 在
经济发展早期,物质资本稀缺,故而重要的是富人并不打算把
全部收入用于消费,而是投资,建造更多的机器和道路。随着
经济发展,物质资本不再那么稀缺,与之相比,人力资本(即
教育)的价值上升,于是普及教育变得尤为关键。但如果贫困
家庭有天赋的孩子支付不起教育费用,进而教育普及受到限
制,就将减缓经济增长。因此,即使在没有引入普选权和民主
的情况下,我们也有类似结论,即在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要
想加快经济增长,则必须普及教育,而这无异于减少不平等。
在实证研究中,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毁誉参半,这大
概是不可避免的。在某些国家和时代,不平等会通过其垄断作
用阻碍经济发展,而在另外的情形下则会通过其激励作用而有
助于经济发展。总之,我们关于不平等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积极与否的看法,总是取决于在社会垄断与激励的两难上,我们如
何赋予权重。当我们相信富人运用垄断的权力和财富威胁社会
稳定、经济发展甚至国家存亡时,正如2400年前柏拉图所为,我们将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为社会毒瘤而与之斗争。当被问
到若将节制作为其理想国应该具有的特征,是否会使其面对被
富裕邻国吞并的危险时,据柏拉图描述,苏格拉底是这样应对
的:
“但我们应该怎样称呼别的(不是理想国的)社
会?”他问道。
“我们应该为它们拟一个更堂皇的名字。正如谚语所
云,它们中的每一个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组国家
的集合,因为它总是包含至少两个国家,一个富,一个穷,互相敌视……把它们视为多个国家,将一部分人的财产……
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你的盟友就很多,敌人就很
少。”苏格拉底回答。
相反,收入的均等化意味着人们从成功中得不到胡萝卜,在失败时也可免于大棒。在某些情形中,若收入过分均等,人
们就不会太努力,除非让其更充分地占有自己劳动或投资的成
果。最终,虽然看起来有些让人难以接受,我们就只能转而期
待更大的不平等。
不平等与经济正义 。收入不平等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它
关乎经济效率和经济正义。于大众而言,二者常利害攸关,却时相龃龉。经济效率解决的是社会总产出最大化或其经济增长
率问题,而经济正义解决的是对既定社会制度是否认同和其是
否可持续的问题,对此经济不平等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基于
遗产、种族或性别的不平等,即使无害于经济发展,人们可能
依然认为是不公的,换言之,这一判断超越了不平等纯粹的工
具价值。若大多数人或有影响力的少部分人视某种社会秩序不
公,则该制度是否可持续就大为可疑。
在评价不同社会制度的合意程度时,经济学家常常构
建“社会福利函数”(social welfare function),其在理论
上包括一个社会所有成员的福祉(即效用)。这样做的目的是
要将一个社会制度下所有成员的福祉与另一个社会制度下的比
较,并找出其中较好的。这就是所谓的“福利主义”,而其粗
略的做法就是将个人效用加总。比如,在一个由艾伦、鲍勃和
查理三人组成的社会里,社会总效用就等于艾伦的效用加鲍勃
的效用再加查理的效用。在每个人的效用函数中,一个合理且
被经验证明的假设是,虽然每额外增加1美元收入带来的效用都
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却递减。想想看,在炎炎夏日,第一杯冰
激凌带给你的喜悦会大于第二杯,且定然大于第三杯,此观点
符合收入边际效用递减这一普遍规律。现在,我们更进一步假
设艾伦、鲍勃和查理的效用函数相同,则完全平等的收入分配
是最优的。事实上,较之于鲍勃和查理,若我们给予艾伦更多
的收入,那么因为他们具有递减且相同的边际效用函数,我们
马上看到,这额外的收入带给富有的艾伦的愉悦比带给贫穷的
鲍勃和查理的愉悦少。因此,如果我们将艾伦的额外收入转移
给另外两人,直至三人收入相等,则总效用会增加。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1970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如
何测量不平等的颇有影响力的文章,它也可以让我们对不同社
会制度的合意程度进行排序。就经济学而言,那篇论文是对福
利主义方法的关键贡献,而这一贡献背后正是上述原理。 阿
特金森发明的测度是考虑到相同的社会福利可由更小但完全平
均分配的社会总收入来实现,由此从福利的视角来看,社会不
平等可用总收入中被“浪费”的相对量计算。上述假想的总收
入在某种程度上被称作“平均分配的等价收入”(equally
distributed equivalent income)。形象地说,即使是一张小
饼,若切开的每一块有同样的尺寸,则较之于一张分割不均的
大饼,每人享用一块之后会带来同样的总愉悦。比如,如果古
巴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居民生产的福利总量相等,但多米尼加
的收入总量更高,则从效用的观点看,多米尼加超出的收入是
完全浪费了。换言之,多米尼加人可以不要这笔额外收入,工
作不那么努力,只要重新将更少的收入像古巴人一样更平均地
分配就行。最终,总福利并没有损失。这样看来,有多少收入
被“浪费”了可被视为不平等的一种测度。
显然,如果存在某种方式可以累加不同个体的效用,那么
是古巴人还是多米尼加人的总体状态更好也就显而易见。但问
题是,没有一种严谨的可以被普遍接受的方式可以加总个体效
用。大体上,我们可以认为随着对任意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增
加,所有人都会经历边际效用递减,但因为一个人的效用水平
可能始终高于另一个人,故我们无法比较这些效用的“量”。
换言之,尽管效用函数的形状可能是相似的,即效用随收入增
加而增加,但其大小却因人而异。回到我们的例子,即使鲍勃告诉我们他生活在极乐世界,我们也不能确定他就真的比脾气
暴躁的查理更幸福:他们可能只是使用了不同的效用尺度而
已。
此外,即使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确切效用并继而能在理论上
最大化社会福利,但仍然存在伦理问题。这是因为在使总福利
达到最大的分配方式中,收入被主要给了拥有较高效用函数的
人,他们擅长将给定收入转换为更多的效用,而这正是英国经
济学家弗朗西斯·埃奇沃思(Francis Edgeworth)在19世纪末
用来捍卫不平等的观点。他认为有更“优雅”品味的富人值得
拥有更高的收入,因为他们从诸如美食醇醪一类中获得了更多
乐趣。然而,真的应该将社会中的大多数收入转移给那些最擅
长享受的人吗?最佳的收入分配方式难道是仅靠面包维生的人
去资助少许几个离不开香槟和鱼子酱的奢靡之辈?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的“可行能力方
法”(capability approach),是对福利主义颇有影响力的批
评,而其正是基于这样的困惑。如果仅仅因为残疾人不能与正
常人一样从足球比赛中为自己故而为社会“生产”一样多的效
用,我们就应该给前者愈来愈少和后者愈来愈多的机会吗?以
常理观之,这是一个令人厌恶的结论。与此不同,森认为我们
应该努力让每个人的“可行能力”相等,以使他们得其所哉。
简言之,当以福利作为判断标准对不同的社会制度排序
时,我们面临三种选择。第一,我们将每个人的效用函数视为
相同(虽然知道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那么收入完全均等时总福利达到最大,这就是阿特金森“平均分配的等价收入”背
后的想法。第二,我们可以试图找出更“有效”的效用生产
者,给他们更高的收入。第三,反过来,如森的可行能力方
法,将高收入恰恰给那些更难从给定的产品和服务中享受快乐
的人。这势必减少通过个人效用的某种简单加总得到的总福
利,而我们因此也不再用福利主义作为判断的基础。
一个更为复杂的福利主义方法是构造一个社会福利函数,在其中并无效用总和,包含的仅是每个个体的效用,是对每个
人福利状态的描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至少有一个
人境况变好而没有人境况变糟的“世态”(states of the
world)是更好的。这样的世态转变满足所谓的帕累托准则
(Pareto criterion),故若我们置身其中,可以确信没有人
会抱怨。但问题是,这样的条件不仅极为保守,更严重的是,在现实世界中几无可能实现。想想任何可能满足帕累托准则的
事:对大多数人而言,更好的卫生保健不是皆大欢喜吗?是
的,但一些人不得不付出更多保费,故他们会反对。一个几乎
可谓奇迹的制止消费成瘾性药物的决定不是对很多人堪称良法
吗?是的,但是毒品生产商和贸易商将遭受损失,故他们会反
对,而与其他人一样,他们也是人,我们也得考虑其减少的效
用。难道你不喜欢缴更低的税吗?是的,但是一些人将由此不
能得到社会保障,故他们会否决相关法案。例子不胜枚举。不
管多么努力,我们可能都找不到满足帕累托准则的政策。究其
实质,这一准则开出的药方意味着静止、停滞、无所作为,而
最重要的是让权势维持现状。因此,较之于粗糙的福利主义,精致的福利主义的缺陷也
有很多,两者都无法比较人际效用,以致在对各种社会制度进
行排序之时,其作用极为有限。 实际上,以效用主义或福利
主义为基础构造关于社会制度的正义理论殊非易事。效用主义
之父边沁(Jeremy Bentham)和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
伟大抱负是用“客观的”方式比较业已发现的不同社会,但该
梦想或许已然破灭。
在这样的废墟上,就如何调和经济不平等与正义,美国当
代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着力尤著。在其1971年出版的《正
义 论 》 中 , 他 清 晰 地 阐 明 了 其 著 名 的 “ 差 别 原
则”(difference principle)。罗尔斯认为,除非是为了提
高最贫困的人的绝对收入,任何对平等的背离都是不合理的。
换言之,比较的基准是公民间经济上的完全平等,对此不论何
种违背都需要正当理由。由此,罗尔斯的《正义论》完全摒弃
了效用主义。他毫不含糊地声称:
理性的人不会仅仅因为某种基本社会结构(basic
sturcture)最大限度地增加了其利益的代数和就接受它,而罔顾该结构对其基本权利和利益的长远影响。因此,效用
原则与平等的人之间为了互利而进行社会合作这一思想相矛
盾,看起来也不符合良序(well-ordered)社会这一概念隐
含的互惠观念。
罗尔斯用一句话非常巧妙地将不平等与不公正联系起来。
在他看来,“不公正完全就是不利于所有人的不平等”“尤其是对穷人”。 虽然不平等和不公正由此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
起,又因为许多赋予富人以特权的社会制度并没有使穷人获
得“绝对”利益,故罗尔斯认为运用他的“差别原则”会使收
入分布相对狭窄。然而,在理论上“差别原则”与高高低低的
不平等都是兼容的。若在提高穷人的收入时并不需要增加富人
的收入,则“差别原则”意味着相当严格的平等。但即使富人
不成比例地获得了额外的好处,只要穷人的收入有一点微不足
道的增长,“差别原则”也能容许很高且不断扩大的不平等。
不平等的测量 。与经济不平等相关的另一领域是对其的测
量。虽相当间接,但经济学家对效用主义的迷恋也已影响及
此。对经济不平等的测量始于以公理为基础的简单工作,即设
计一个合理的标尺,再借此将整个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概括为一
个数字。这些关键的公理并不难理解。例如,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若将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则不平等的测度下
降; 又如,若两个人交换位置,则测度不变(此所谓“匿名
原则”);再如,若所有的收入都乘以一个常数,则测度不
变;等等。 因此,与对温度的测量无异,对不平等的测量纯
属技术问题。但在占主导地位的福利主义方法看来,这些测度
表达了某种更深层次的以社会福利为基础的观点。然而,福利
主义的困境显而易见。举例而言,若我们考虑刚才定义的乍看
起来非常合理的匿名原则,为了用福利主义表达这一简单的技
术要求,我们必须接受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主张,即所有个体
的效用函数相同。若他们的效用函数不同,那么从效用产生的
角度看,任意两个人就不可能一样。换言之,如果某人是一台生成效用的高速机器,则其不可能被一个无精打采的“在生成
效用上力不从心”(utility-challenged)的人轻易取代。
从一开始,以公理为基础对不平等的测量与其福利主义阐
释间的矛盾就非常明显。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意大利经济学家
和统计学家科拉多·基尼开发了被普遍接受的对不平等的测度
方法。而早在1921年,他已表达了这一困境:
意大利(反福利主义)学者的方法……不能……与(在
主张福利主义方法中居功至伟的英国经济学家)道尔顿
(Dalton)的方法媲美……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估算经济福
利的不平等,而是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却罔顾这些数量与
经济福利间函数关系的所有假设,或个体经济福利的可加
性。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福利主义方法在经济学家中似乎颇有
市场,但近来却渐渐消隐。这一方面是因为它未能得出有力且
可行的结论,比如回答“什么样的状态更好”,另一方面是因
为作为其根基的效用主义在哲学上站不住脚。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测量不平等。就此,我们
须对家庭进行有代表性的随机抽样调查,参与调查的每个人都
要提供详细收入信息,又因为调查被视为代表着更广泛的群体
(通常是整个国家),故其结果应能外推至全国。我们也会使
用税收数据。但即使是在大多数人都缴纳直接税的非常发达的
国家,因为这些数据遗漏了未缴税的穷人,故也总是给我们不
完整的(或称“截尾”了的)分布信息。我们也不能使用人口普查,因为原则上该普查覆盖整个国家的人口,范围太大,以
至于不能非常深入详尽。事实上,人口普查只收集如年龄、种
族、性别、居住地等基本信息,却不涉及收入或消费。
然而,对大多数发达国家而言,家庭调查存在的问题在于
其最早也仅仅始于二战之后。在19世纪的英格兰,以及20世纪
早期的美国和苏联,有一些不完整的调查,但大致而言,对于
20世纪50年代初之前的数据,我们从中几乎不能得出任何严谨
可用的东西。(你可能还没忘记帕累托的猜测是基于财政数据
的,而即使迟至1955年,库兹涅茨也没有几个可供凭借的调
查。)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更糟,以至于20世纪70年代甚至80年代
之前,很多时候它们根本没有数据。尤其是非洲国家的家庭调
查从80年代才开始,且常常是在国际组织的协助之下。 世界
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又如何呢?在印度,全面的调查始于
1952年,并按照大抵相同的框架延续至今。在中国,现有的第
一次调查始于1978年,但最早可用的调查只能追溯到1980年。
此外,不是所有国家都每年开展调查,一些国家的调查仅每两
年一次,其他国家甚至频率更低,比如五年一次。这一切意味
着什么呢?首先,除了发达富裕的经济体,我们发现很难得到
基于家庭调查的一系列关于不平等的年度统计。其次,对大多
数国家而言,得从20世纪60年代,甚至七八十年代之后,我们
才能多少讨论其不平等问题,而且即便如此,也尚有很大的年
度数据缺口。家庭调查收集很多数据,但我们感兴趣的是其有关收入和
消费的部分。在这类调查中,每个家庭被视为一个收入或消费
单位,而家庭中的所有成员则被视为平均地分享收入或消费。
那该如何确定一个家庭成员的真实收入呢?我们将家庭中每个
成员的年收入加总,得到家庭总的年收入,然后将其除以这一
年居住在这个家庭中的人数,就可以得到家庭人均收入。这是
一个重要概念,因为其大小可以让我们对家庭和个人做出排
名,以决定孰穷孰富。
为什么我们坚持使用“人均”的测度呢?有哲学和实践两
方面的缘由。在哲学上,我们应该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若我们
平等对待每个家庭,那么大家庭中每个成员的价值就远小于小
家庭的成员。若每户的权重(即计算中被赋予的重要性)为1,那么在四口之家中每个个体隐含的权重为14,但在两口之家中
却是12。而在实践中,基于家庭整体而非人均收入的不平等测
度容易产生误导。理由很简单。考虑总收入相同的两个家庭,其中一个有2人,另一个有10人。你认为哪个家庭更富裕呢?答
案显而易见。
即使我们得到的是消费数据,为简化起见,我们通常谈论
的仍是收入分配。然而,收入和消费是不等价的。在一组给定
的家庭中,基于收入的数据几乎总比基于消费的数据呈现更大
的不平等。简单的原因有二。首先,可能有些人年度收入为
零,于是可用过去的储蓄支付目前的消费,这只要想想那些用
工作时攒下来的钱读书的学生就知道。但显然,没有人的年度
消费会为零,故消费分配将会在维持生计所需的最低点被截断。相反,收入分配的底部更长,也由此更加不平等。其次,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分配的另一端。许多高收入的人储蓄一部
分收入,故其收入大于消费,而收入的顶端也将比消费的顶端
更长。最终,当我们用收入而不是消费作为衡量标准时,测得
的不平等就会更大。
一旦有了家庭收入数据,我们该怎样度量不平等呢?这个
问题并不简单。作为对比,让我们先看看国民收入或GDP的测
量。GDP只是将一年之中居住在一国内所有人的收入相加,这包
括全部的工资、利润和利息等。最后,我们得到一个总数,将
之除以这个国家的居民数,就计算出人均GDP。
但收入分配由许多人的收入构成。我们不打算只简单将其
相加,而是得把这些收入相互比较,并进一步将这诸多比较表
达为一个数字,以很好地反映分配差异。这正是困难所在。任
何代表诸如1、5、15、2 009和34 564此类收入差异的单个数字
都有几分武断。比如,我们可以用最大和最小数字之比(34
564除以1)描绘不平等,但这将遗漏在它们中间的所有信息。
事实上,虽有同样的比,但我们难道不觉得例如1、400、620、1 009和34 564这样的分配更平等吗?我们也可以仅考察顶层收
入者所占收入份额来衡量不平等: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将34
564除以所有收入的总和(1+5+15+2 009+34 564或1+400+620+1
009+34 564), 而这正是用最高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衡量不
平等的方法。实际上,可选的方法不可计数。
一个减少备选项的方法是要求对不平等的测度应当利用给
定收入分配中所有人的收入信息,这意味着上例中从1和5直到其最大值34 564的所有信息都应被考虑在内。满足这一要求的
方法之中,到目前为止,以科拉多·基尼命名的基尼系数最为
通行。这位意大利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生活的时代与帕累托有
部分重叠。 在1914年他定义了该系数,即将每个人的收入与
其他所有人的收入逐一相较,而所有双向收入差距的绝对值之
和依次被除以包含在这一计算内的人口总数及该群体的总收
入,最后再除以2,而其最终的结果处于0(表示所有个体的收
入相同,没有不平等)和1(表示群体的所有收入都归一人所
有)之间。 这一特点大可称便。事实上,该系数“有上
界”,而1就是可能的最大不平等。据此,我们有了一个可靠而
确为有用的方式来比较不平等程度。
基尼系数为0或1都不现实: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收入完全平
等,也没有哪个国家是一人占有所有收入而所有其他人皆死于
饥饿。现实生活中,在如北欧诸国、中欧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
伐克这样最平等的国家,基尼系数大抵处于0.25至0.3之间;而
在最不平等的国家,如巴西和南非,该系数可达到0.6。
美国处于什么范围呢?在发达国家中,它是最不平等的。
尽管大多数欧盟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30与0.35之间(但就其整
体水平,可见小品3.3),但美国基尼数却高于0.40。不过,美
国的情况并非一直如此。随着基尼系数在20世纪70年代末滑落
至约0.35,美国的不平等降到了其历史最低点。 从那之后,在奥巴马前的四任总统期间(即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
什),美国的基尼系数持续上升,直至当前水平。增幅之大,每个亲历其间的人都清楚。因为基尼系数是一种变化迟缓的测度,即使一年增加一至两个百分点都非比寻常。如果不平等没
有持续地上升或下降,基尼系数每年上下波动的幅度往往都在
一个百分点之内。
其他国家的情况又如何呢?瑞典的平等众所周知,其基尼
系数在0.30左右;俄罗斯转轨之后又受寡头的困扰,其基尼系
数超过0.40。中国也是如此。与美国相仿,这两个国家的不平
等在过去20年间急剧上升。拉丁美洲很少有国家的基尼系数低
于0.50,非洲亦然。亚洲的不平等虽普遍存在,却不尽一致。
日本、韩国和中国似乎更平等一些,而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基
尼系数与拉丁美洲的水平相当。如果我们按区域内各国间的不
平等程度将各地区排序的话,位列第一的是拉丁美洲,紧接着
是非洲和亚洲,而不平等程度最低的是富裕国家和转轨经济
体,但值得关注的例外是若干不平等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以
及美国和俄罗斯。
然而,从另一个不同角度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欧盟、俄罗斯与中国这四个巨大的经济体都呈现出几乎相同程度的不
平等,即它们的基尼系数都处于0.40附近或者略高,这多少有
些令人讶异。小品3.3将考察前两者的异同,小品1.4和小品1.7
将审视俄罗斯的收入分配,而小品1.8将讨论中国的现状与未
来。
最后,我们可以分解基尼系数,以找出区域内各组成部分
之间(称为“组间”)平均收入差异所致的不平等与该区域各
组成部分内部(即“组内”)个人收入差异所致的不平等。比
如,当观察欧盟与西班牙和法国这样的成员国,美国与缅因和俄勒冈这样的州,又如中国这样的国家与四川、云南和湖南等
这样的省,或更小的国家,如意大利与伦巴第、利古里亚和西
西里岛等这样的行政区时,这样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
解不平等。组间差异的意味很清楚,若其过大,则不平等主要
是因为我们研究的区域由贫穷和富裕的两部分组成。如果组内
差异所占比重较大,则不同部分间地理上的不平等一定较小,但每个部分一定既有穷人也有富人,差异极大。当将此方法运
用于考察全球不平等时,组间差异就是国家间平均收入不同造
成的不平等,而组内差异就是各国内部个人收入的不平等。此
类分解是非常有力的工具,可使经济学者在测量到的不平等背
后一探究竟,故我们将频繁使用(如见小品1.7、小品1.8、小
品3.2和小品3.3)。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两种不平等的政治
意味有很大差别。
1. 感谢Francisco Ferreira对该散论颇有助益的评论。
2. 较之于占有贫瘠的土地(the marginal land),占有更肥沃土地的所有地
主将由此得到更高的租金。
3. 见“Response by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to:‘The Top 1%…of What’by Alan Reynolds”; 可 访 问
http:www.econ.berkeley.edu~saezanswer-WSJreynolds.pdf。
4. 这个比喻由Francisco Ferreira在《类如胆固醇的不平等》(Inequality
as Cholesterol ) 一 文 中 首 先 提 出 , 见 Poverty in Focus
(Brasilia:International Poverty Center,June 2007)。
5. Max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reprint,London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53.6. J.M.Keynes,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1920;reprint,New York:Penguin,1971),第二章第三部分(对“不平
等”的强调乃凯恩斯原文)。
7. Stefan Zweig,The World of Yesterday (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4),7-8.
8. 这 就 是 由 Kevin Roberts ( 见 “Voting over Income Tax
Schedule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1977):329-340)及Allan
Meltzer and Scott Richard ( 见 “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1981):914-927)提出
的“中间选民假说”(median-voter hypothesis)。
9. 甚至可能会出现没有真正的再分配,但对经济增长仍然带来负面影响的情
形。例如,为了避免穷人以政治手段接管财富,富人会联合起来,通过游说来
购买选票和法律,从而防止再分配。然而,游说乃零和博弈,涉及的并非新财
富的创造,而只是财富的再分配,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在这种毫无生产
性的活动上花的功夫纯属浪费,接踵而至的是更低的经济增长。
10. 见 Oded Galor,“Income Distribution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4(2002):706-712,及Oded
Galor and Omer Moav,“From Physical to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1(2004):1001-1026。
11. 在这段对话中,“他”是苏格拉底的哥哥Adeimanus。
12. Plato,The Republic ,translated by Desmond Lee ( New
York:Penguin,1973),pt.IV,sec.3,p.189.
13. “On the Measurement of Inequality,”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1970):244-263.
14. 阿马蒂亚·森于1979年5月22日在斯坦福大学“坦纳讲座:论人的价
值”(Tanner Lecture on Human Values)上做演讲《什么上的平等?》
( Equality of What ? ) , 见
http:www.tannerlectures.utah.edulecturessen80.pdf.亦见其“Social
Justic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in vol.1 of Handbook ofIncome Distribution ,edited by A.B.Atkinson and
F.Bourguignon(Amsterdam:Elsevier,2000)。
15. 准确地说,森的方法就是要求在可行能力空间上人人平等,而不再是效用
空间上。
16.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除了拥有自身的效用尺度,若假设人们也有移情效用
尺度(empathic utility scale),能够“测量”被其他人享有的效用,则我
们就可以做个人效用比较。正如摄氏度和华氏度间的关系一样,他们赋予移情
效用尺度和个体效用尺度的精确值可能不同,但它们是“可传递”的(即若我
们知道其中一个,则也知道另一个)。这一观点可追溯至John Harsanyi
的 “Cardinal Welfare,Individualistic Ethics,and the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 of Utilit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3(1955):309-
321。
17. 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 ,rev.ed. (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13.
18. 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 ,rev.ed. (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第54页。
19. 罗尔斯间接排除了富人和穷人收入绝对提高(故满足其“差别原则”),而中间阶层收入减少这一情形。在其看来,收入分配如同一条相互连接的铁链
那 样 变 动 [ 见 《 正 义 论 》 第 二 章 第 十 三 节 对 “ 紧 密 相 联 ” ( close
knittedness)的定义]。
20.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包含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富人仍然更富有,否则两人可能只是交换了位置。若是那样,认为不平等有所下降是不恰当的。
21. 然而,最后这条公理并不是那么明显或无害的。注意,这意味着即使人与
人之间绝对收入差距增加,不平等的测度仍然不变。我们称满足该公理的不平
等测度为“相对的”,而大多数测量都只采用此类测度。但是,我们不能完全
无视随绝对收入差距上升而上升的绝对测度。
22. Corrado Gini,“Measurement of Inequality of Incomes,”Economic
Journal (March 1921):124.23. 拉丁美洲和东欧的情况要好些。在这两个区域,可靠的调查始于20世纪60
年代。遗憾的是,除了少量总体统计留存下来,许多细节已然遗失,而久远散
佚了的拉丁美洲调查则让我们想起马尔克斯(Márquez)笔下的马贡多
(Macondo),在其中除了一两件文物,这个小镇的过去在雾霭中逐渐模糊直至
成为神话。
24. 除了收入,家庭消费亦可同样处理。这样,我们感兴趣的就是家庭的“福
利”,即他们真正消费了多少,而不是家庭收入,或者说,他们潜在的消费是
多少。
25. 两总和相等。
26. 据Michele Zenga(“Il contributo degli italiani allo studio della
concentrazione:Prima parte:Dal 1895 al 1915,”in La distribuzione
personale del reddito :Problemi diformazione ,di ripartizione e di
misurazione ,edited by M.Zenga[Milan:Vita e Pensiero,1987],307-
328),该集中度最初出现在基尼1914年发表的文章“Sulla misura della
concentrazione e della variabilità dei caratteri,”in Atti del Reale
Istituto Veneto di Scienze ,Lettere ed Arti ( Venice:Premiate
OfficineGrafiche Carlo Ferrari,1914),vol.73,pt.2a,pp.1203-1248中,后
来被称为基尼系数。感谢Andrea Brandolini提供此信息。
27. 原文所谓“The Gini coefficient compares the income of each person
with the incomes of all other people individually,and the sum of all
such bilateral income differences is divided in turn by the number
ofpeople who are included in this calculation and the average income
of the group”表述有误,揣摩其所欲传达的信息得如上译文。这是基尼系数
若干表达之一。——译者注
28. 作者随后写道:“通常情况下,为简便计,基尼系数以百分数的形式呈
现,因此我们会说某国的不平等是43个基尼点(Gini point),而不是0.43。
在该书中,我们依循此例。”故为免混乱计,且循中国学界惯例,在译作中始
终以基尼系数表述,亦由此对原书中某些文字与图表略做调整;不另说明。
——译者注
29. 基于人口普查局的总可支配收入数据,源自Andrea Brandolini和Tim
M.Smeeding,“Inequality Patter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Cross-CountryDifferences and Changes over Time,”in Democracy ,Inequality ,and
Representa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ited by Pablo Beramendi
and Christopher J.Anderson(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8),图2.5.亦请参见由Richard V.Burkhauser等进行的详细研究Estimating Trends
in U .S .Income Inequality Using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The
Importance of Controllingfor Censoring ,Working Paper
14247 ( Cambridge,MA: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August
2008)。小品1.1
爱情与财富
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是一部以“爱”为主题的小
说,这是举世公认的真理,但要说它也是一部关于“金钱”的
小说,就不会有太多人承认了。
故事发生的时间未在书中明确给出,而简·奥斯汀有意为
之的这个具体而微、无始无终的世界也没有让一丝线索能令我
们为其确定一个准确的日期。或许这就是她的目的,以表明谈
情说爱(还有金钱)是如何与人类相始终的。
但是,间接证据表明故事发生于拿破仑战争时期,即大约
1810年至1815年之间。小说的主人公是妩媚的伊丽莎白·班内
特,殷实的班内特一家五个女儿中的次女,而一家之长
(paterfamilias)的名字从未在书里出现过,他的妻子叫他班
内特先生。伊丽莎白和家人过着英国乡绅怡然自得的宜人生
活,不时觥筹交错、轻歌曼舞,间杂以这类聚会催生的闲言碎
语。她美丽、聪慧,当然,也还待字闺中。其家庭年收入约为3
000英镑,由包括五位姐妹和父母在内的七个家庭成员分享,故
人均430英镑(与这里其他例子一样,排除了房屋的估计价值,而 其 定 然 相 当 可 观 ) 。 根 据 罗 伯 特 · 科 洪 ( Robert
Colquhoun)计算的19世纪早期英国社会阶层收入表,这样的收
入水平让班内特一家跻身当时英国收入分配的前1%。伊丽莎白遇到了富有的追求者达西先生,据书中的信息可
知,达西先生年收入约为10 000英镑。 自然,他与他那稍微
不那么富有的朋友宾利先生,都被熟知人情世故(而且并不拐
弯抹角)的班内特夫人视为非常令人满意的东床之选。达西先
生的巨额收入使之处于英国收入分配的至少前1‰水平。须指出
的是,前1%与1‰间,或用小布什的当代措辞,“有产者与富足
者”之间,差异巨大。在19世纪早期的英国,虽然有产者和富
足者在社会上自由融合(显然也通婚),但达西先生的收入却
是伊丽莎白父亲的3倍多;由于达西先生只需照顾自己一个人,以人均计,这一比例则超过了20∶1。
非常明显的是,对于达西先生是否适合自己,伊丽莎白确
有疑虑,而达西先生则明确表达了他对伊丽莎白的“倾
慕”——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婉语在现代作品中会以全然不同
的方式表达。但是,断然回绝达西先生却有婚姻之外不太令人
愉快的意味。根据英国继承法,如果班内特先生去世后没有直
系男性继承人,那么其房舍和运作良好的地产将归于他那令人
讨厌的远房表弟威廉·柯林斯牧师所有。要是那样处置遗产,伊丽莎白就只能自食其力,即基本上依靠其母亲5 000英镑陪嫁
里属于她的份额。根据柯林斯先生令人窘迫的估计,这份自主
的财产有1 000英镑。他假定她将从中获得4%的回报,即每年40
英镑。这是一个少得可怜的数字,大抵等于当时英国人均收入
的2倍,与一个勘测员或商船海员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当。
这便是权衡爱情和财富之所在。让我们从担心女儿幸福的
伊丽莎白母亲的角度考虑。第一种可能是,伊丽莎白可以嫁给达西先生,然后享有每年5 000英镑的收入(我们假设她没在金
钱方面对达西先生做出任何贡献,并且后者将其收入与伊丽莎
白平分)。而在另一种可能中,她会陷入在班内特夫人看来无
疑是永无止境的贫困之中,依靠每年不足50英镑的收入度日。
这两种结局间的收入之比超过100∶1,简直令人咂舌。面对这
样的成本,伊丽莎白选择不结婚,或一直等到理想的爱人在天
边出现,都完全是不可能的。除非真的憎恨达西先生,否则谁
也不可能拒绝他这笔不言而喻的交易!
但是我们可能会问,如今有何不同吗?若要将《傲慢与偏
见》置于当代的英国,我们只需看看眼下的收入分配格局即
可。2004年,税后收入排在前1‰的人平均每年挣40万英镑,前
1%的人平均挣8.1万英镑,而英国的人均收入是11 600英镑。拒
绝今天的达西先生的成本依然不菲,却没有那么不可承受:排
在收入分配前1‰的群体和两倍于人均收入的群体间的收入之比
约为17∶1,而不再是100∶1。
因此,简·奥斯汀不仅展示了爱情与财富之间司空见惯的
权衡,而且还让我们看到,虽然这种权衡本身可能是永恒的,但是其间的利害确实随着时间和所处社会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而变化。社会愈平等,在做出关乎婚姻的决定时,我们预期爱
情愈趋于战胜财富;而在很不平等的社会里,却往往相反。那
么,爱情在非常不平等的社会中就只能存在于婚姻之外吗?我
们接下来讨论这个问题。1. 感谢Michele de Nevers、Carol Leonard和Blanca Sanchez Alonso的评
论。
2. 一位当代评论家就此界定了2 000英镑的收入在简·奥斯汀书中的价
值:“年收入2 000英镑之下[这是《傲慢与偏见》中乡绅班内特先生和《理智
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 )中布兰登上校(Colonel Brandon)的情
形],一家人仍须节约用度,而在《傲慢与偏见》里因有五个女儿需要嫁妆,就
尤其如此。《理智与情感》里詹宁斯夫人(Mrs.Jennings)将布兰登上校的德
拉福德庄园(Delaford)描绘为‘没有债务,没有瑕疵,总之,每件事都称心
如意……哦,这真是个好地方’,其强调的就是2 000英镑下的宁静安怡之
乐”(Edward Copeland,“Money,”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ane
Austen ,edited by Edward Copeland and Juliet
McMast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136)。
3. 他有200 000英镑,而通常的年收益率是4%~5%。
4. 基于Patrick Colquhoun社会阶层收入表得出。小品1.2
安娜·伏伦斯卡娅?
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 但是阿历克赛·亚历山大罗维奇
·卡列宁和安娜真的那么独一无二吗?
诚然,《安娜·卡列尼娜》讲述的是一位有夫之妇爱上了
雅致洒脱、家财万贯的翩翩少年伏伦斯基伯爵的故事。在某种
程度上,这也是对社会规范与伪善的批判,因为要不是那
些“规矩”,安娜不会因为她与伏伦斯基的关系而被社会排
斥,并且会发现离婚更容易(虽然不清楚她是否真的想离婚,因为这么做会让她失去儿子的监护权)。如果他们结婚,我们
不能断言其就不会拥有幸福的婚姻——或者,套用托尔斯泰著
名的开场白, 成就一段美满的姻缘。当然,或也不尽然,因
为托尔斯泰展现的是,阻止安娜和伯爵幸福结合的不仅是社会
和社会规范,也包括他们自身的性格。
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发生在1875年前后的莫斯科、圣彼
得堡和周边的乡村,这与托尔斯泰自己的生活处于同一时代
(该小说1877年出版)。用最简略的话说,这本著作描写了安
娜·卡列尼娜与冷峻以至于常常无动于衷的高级公务员卡列宁
先生的不幸婚姻,以及与伏伦斯基先生的婚外情。这份爱情,始而隐秘,继而公开;始而浸满了兴奋与承诺,继而充斥着冲突、谎言与绝望,它毁掉了伏伦斯基的前途,最终导致两人痛
苦不幸的结局。
乍看之下,《安娜·卡列尼娜》和《傲慢与偏见》之间并
没有什么相同点。如果有人想通过两者的“特质”或“氛
围”比较它们,《傲慢与偏见》的气候应该是英国多变的夏
天,在那里灿烂的阳光与可怖的乌云相互交替。但是乌云和大
雨来去匆匆,读者记忆所及,还是夏日的明艳。相反,《安娜
·卡列尼娜》的开始如同俄国的大陆性夏季,大自然仿佛在人
们的眼前绽放,温暖耀眼,然后慢慢向阴郁的秋日转变,最终
落入漫长、黑暗、萧索而永无止歇的冬天,故而我们从书中感
受到的整体氛围更多的是冬季,而非夏日。这正如在12月中旬
寒冷的日子里,自然难以浮想刚刚过去的悠然自得的6月天。
但是,在收入与地位不平等这一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上,《安娜·卡列尼娜》与《傲慢与偏见》相似。在这两部小说
中,女主人公一开始都生活在十分富有、舒适而体面的家庭,只不过在其中一部里已婚,而在另外一部里待字闺中。然而在
两部作品的后续阶段,就财富而言,她们都凭借恋爱或婚姻扶
摇直上。《安娜·卡列尼娜》中无一字提及卡列宁先生的薪
俸,但是,我们可从他和安娜的哥哥斯特潘·奥布隆斯基的谈
话中了解到,他认为1万卢布是份很高的薪水,而我们从书中别
处可以得知这是银行董事的收入水平。 我们还知道收入高的
政府官员收入有3 000卢布,而同在政府任职但比卡列宁先生位
阶低的斯特潘·奥布隆斯基收入为6 000卢布。 由此,考虑
到卡列宁先生显赫的官场地位,我们可以推断其年收入大概在8000~9 000卢布。那么,富有的伏伦斯基伯爵如何呢?与达西先
生一样,“所有人”也都认定其年收入为10万卢布。但是,我
们可从后面了解到,如果他没有将遗产的一半给弟弟,这本应
是他正常的预期所得,因此伏伦斯基遇见安娜时的真实收入仅
约50万卢布。 后来,当他面临经济问题,重新获得曾经草率
允诺给弟弟的一半遗产时,伏伦斯基的收入大概恢复到10万卢
布的“正常”水平。
现在我们看到,安娜若与伏伦斯基结婚将会带来的财富剧
增,即人均收入从大约3 000卢布(她丈夫的大致收入在夫妇和
儿子之间分配)变为30 000卢布以上(再次假设她像伊丽莎白
·班内特那样对家用的贡献为零,而伏伦斯基先生则像达西先
生那样将自己的收入平分给妻子和女儿)。 由此,从本已富
丽堂皇、仆役成群的卡列宁家,安娜一跃而至像伏伦斯基那样
王侯般的生活,这意味着年收入至少扩大10倍。
对于俄国,我们缺少社会阶层收入表以确定伏伦斯基和卡
列宁先生 在当时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处的位置。但毫无疑问,卡列宁夫妇属于收入阶梯中的极高层(可能是前1%),而由此
伏伦斯基又像达西先生一样,肯定是富豪中的富豪,可能属于
最高的1‰或者更甚。请再次注意这将富裕与极端富裕区分开来
的巨大差距。
但是这对安娜·卡列尼娜的负面影响是什么呢?我们是不
是也能看到这种收入分配中较糟糕的一面呢?对于安娜,黯淡
无光的岁月是其过去的一页。我们知道她来自一个非常不起眼
的家庭, 可能每年仅靠人均几百卢布过活。 从社会地位的角度看,她嫁给卡列宁是占了便宜,致使其生活水平大约提
高了15倍。而另一段与伏伦斯基先生的婚姻,正如我们刚才看
见的,本可以使其收入再增加10倍。凭借这两段婚姻,安娜就
可能从收入分配的均值位置升至极高的位置,将其生活水平提
高约15×10,即150倍。
俄罗斯今天的情况变好了吗?是的。根据2005年的家庭调
查数据,我们发现俄国前1%的家庭人均收入为34万卢布,大约
是平均水平的6.5倍。我们估计在1875年的收入分配中,两个同
样位置(即卡列宁先生的家庭人均收入和全国人均收入)的收
入之比为15∶1,故而俄罗斯的收入差异也在缩小。另一个“安
娜”若要在今天的俄罗斯进入收入分配的高层,将肯定会被带
离其起点很远(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就是证据)。然而,尽管
我们时常瞩目于俄罗斯亿万富翁的财产,在这一过程中隐含的
收入增长将依然小于列夫·托尔斯泰笔下那部名著的时代。
1. Natalia Drozdova Petrova全面的评论令我受益颇多。
2. 这是指该小说的第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
各的不幸。”该小品的第一句话实际上正是借用于此。——译者注
3. Anna Karenina (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2000.Constance
Garnett translation revised by Leonard Kent and Nina Berberova),813.
4. Anna Karenina (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2000.Constance
Garnett translation revised by Leonard Kent and Nina Berberova),第
745页。
5. Anna Karenina (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2000.Constance
Garnett translation revised by Leonard Kent and Nina Berberova),第347页。
6. 基于对伏伦斯基与其弟弟谈话的解读及随后其支出的增加做出推断。
7. 这是假定安娜的儿子(安娜与卡列宁所生)与其父生活,而女儿(安娜与
伏伦斯基伯爵所生)与他们生活。
8. 原文为Messrs.,法语Messieurs的简写,即Gentlemen。——译者注
9. 我们间接察知。这是因为,首先,她与其富有的姑妈生活(想必远较其父
母富有);其次,就社会地位而言,她嫁给卡列宁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10. 我们从托尔斯泰那里对中产阶层的收入所知不多。书中提及的唯一“专业
人才”收入,是一个德国会计每年挣500卢布,而他的工资一定比同等的俄国会
计高(因此才会强调“德国”)。假定他要维持一个四口之家,则这种“中产
阶层”的人均收入仅略多于一百卢布。小品1.3
谁是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人?
比较过去与现在的收入并非易事。我们没有汇率可以将古
罗马的塞斯特斯(Sesterce)或阿斯(As), 或者卡斯蒂利
亚17世纪的比索转换成今天具有同等购买力的美元。甚
至,“同等购买力”在那种情况下究竟为何物都还远未可知。
它应该表示一个人能够用X古罗马塞斯特斯买到今天用Y美元购
买的同样一束商品和服务。但是,不仅商品束已经改变(古罗
马时期没有DVD),而且纵使限制商品束,令其只涵盖当时和现
在都有的商品,我们也很快就能发现其相对价格已发生了很大
变化。因为工资低,过去的服务相对便宜,而在如今的富裕国
家却价格高昂;就面包或橄榄油而言,情况则恰恰相反。
因此,要比较若干历史时期中大富豪的财富和收入,最为
合理的方法就是将之置于其历史情境中,依据他们在当时雇用
(平均技能)人力劳动的能力衡量其经济实力。在某种意义
上,给定数量的人力劳动是一个通用的计量单位,是我们衡量
福利的准绳。正如亚当·斯密两百多年前所言,“(一个人)
是富有或贫穷,取决于他能够支配的劳动力数量”。 此外,对于今天的比尔·盖茨这类人,由于其收入将根据目前美国居
民的平均收入衡量,上述数量体现了生产力和社会福利随时间
的提升。古罗马是一个自然的起点,因为我们拥有其富豪的数据,且其经济也足够“现代化”与货币化,以使我们能够将其与目
前或更晚近的过去做有价值的比较。我们可以考虑古典时代的
三个人。三个执政官之一的马尔库斯·克拉苏(Marcus
Crassus),其财产在公元前50年左右估计约为2亿塞斯特斯,富有得令人难以置信;在公元14年左右,皇帝屋大维·奥古
斯都(Octavian Augustus)的皇室财产估计有2.5亿塞斯特
斯; 最后,尼禄(Nero)治下的自由民马尔库斯·安东尼斯
·帕拉斯(Marcus Antonius Pallas)在公元52年据信拥有富
甲天下的3亿塞斯特斯。
以已与奢靡联系在一起的克拉苏为例(不要将之与希腊国
王克罗伊斯混淆,后者的名字已成为“财富”的代名词)。克
拉苏有2亿塞斯特斯,而年利率是6%(在古罗马的“黄金时
代”,即公元3世纪的通货膨胀前,这被认为是“正常”利
率),故年收入估计可达1 200万塞斯特斯。在公元14年屋大维
过世前后,一般认为罗马公民的年均收入约为380塞斯特斯,并
可假定它与60年前克拉苏在世时相同。 由是观之,克拉苏的
收入相当于32 000个人的年收入,如此庞大的人群大致可以塞
满半个斗兽场。
让我们快进到离今天更近的年代,将相同的逻辑运用到安
德鲁·卡内基、约翰·洛克菲勒和比尔·盖茨这三位美国财富
的化身上。卡内基的财富在1901年其购买美国钢铁公司时达到
顶峰,而他在该公司的股份为2.25亿美元,对此同样采用6%的
回报率,并使用282美元的美国人均GDP(据1901年价格水平计算),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卡内基的收入超过了克拉苏。事实
上,卡内基几乎可用其年收入轻而易举地买下大约48 000人的
劳动力。(注意在所有此类计算中,我们都假设富豪的财产保
持不变,他仅仅使用每年从财产中获得的收益购买劳动力。)
洛克菲勒在1937年以14亿美元达到了其财富的巅峰。 同
样的计算表明,洛克菲勒的收入与1937年大约116 000个美国人
的收入相等。因此,洛克菲勒的财富几乎相当于克拉苏的4倍,也是卡内基的2倍多。他能雇用的人可以轻易地装满帕萨迪纳
(Pasadena)的玫瑰碗球场,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只能留在
门外。
在这样的比较中,比尔·盖茨的表现又如何呢?据《福布
斯》杂志显示,比尔·盖茨2005年的财产为500亿美元,由此可
以估计其收入为每年30亿美元,并且由于该年美国人均GDP约为
40 000美元,那么他可以用其收入支配大约75 000名工人。这
使他跻身于卡内基与洛克菲勒之间的某个位置,却远远高
于“贫穷”的克拉苏。
然而,这种计算仍留下了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俄罗斯的
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和墨西
哥的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他们既是“全球”也
是“一国之内”的亿万富翁,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他们呢?在
霍多尔科夫斯基于2003年成为俄罗斯首富的时候,其资产估计
约为240亿美元。 就全球角度而言,他远不如比尔·盖茨富
有。但是,若我们再次运用之前的假设区域性地评估其财富,以俄罗斯平均价格计算,他能购买超过25万人一年的劳动力。换言之,对比其同胞相对低下的收入水平,霍多尔科夫斯基比
1937年美国的洛克菲勒更富有,可能也更有权力。也许正是后
者,即潜在的政治力量,招致克里姆林宫注意上了他。
如有必要,霍多尔科夫斯基无须动用一分钱的本金,就可
以建立一支25万人的军队。而且就如同一个国家,他既与美国
人也与中国人谈判建设新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这种潜在的势
力难逃克星,倒台和最终的牢狱之灾随之而来。然而,俄罗斯
的历史就是这样,两个政权间的最短路径往往得绕道西伯利
亚,而我们看到的也许并非最后一个霍多尔科夫斯基先生。
墨西哥人卡洛斯·斯利姆做得比他更好。同样根据《福布
斯》显示,他的财富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估计超过530亿美
元。运用与之前相同的计算,我们发现斯利姆在其收入的巅峰
时期可以支配约44万个墨西哥人,比霍多尔科夫斯基更多。由
此,就局部而言,他看起来已经是最富有的人了!甚至包括著
名的阿兹台克体育场在内,在墨西哥没有一个体育场能勉强容
纳斯利姆先生用其年收入可以雇用的所有同胞。
另一个可能的复杂之处是人口的规模。当克拉苏在世并支
配着32 000人的劳动收入时,罗马帝国的人口是这一数量的1
500倍。而与洛克菲勒的年收入对应的116 000个美国人,则占
据总人口中更大的比例,以至于每1 10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因
此,从绝对量和相对比例两方面来说,洛克菲勒都比克拉苏更
富有。那么我们能说谁是他们所有人之中最富有的吗?由于富人
也都倾向于“全球化”发展并将其财富与不同国家的其他富人
比较,考虑到洛克菲勒身处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而在那
里控制着数量最多的劳动力单位,所以魁首可能就是他。但是
当大富豪决定在自己的国家(不一定就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
家,比如俄罗斯和墨西哥)扮演政治角色时,那么他们在那里
的权力甚至可能会超过在全球意义上最富有的人。
1. 塞斯特斯和阿斯均为古罗马硬币。——译者注
2. 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Pelican Books,1970),133.
3. Aldo Schiavone,The End ofthe Past :Ancient Rome and the Modern
West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71.塞斯特斯意为“两
块半”(semithird),指其价值两个半的阿斯(另一种罗马硬币单位)。
4. Raymond Goldsmith在“An Estimate of the Size and Structure of the
National Product of the Early Roman Empire,”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30(September 1984)中估计奥古斯都的年收入为1 500万塞斯特斯;
以通常每年6%的利率计,这意味着其财富是2.5亿塞斯特斯。
5. Tacitus,Annals (New York:Penguin,1996),第十二卷第五十三章。在
塔西佗笔下,帕拉斯附助着尼禄,助纣为虐,直至其也被尼禄下令毒死(第十
四卷第六十五章)。
6. Goldsmith,“Estimate of the Size and Structure.”这是由Branko
Milanovic 、 Peter Lindert 和 Jeffrey Williamson 在 “Preindustrial
Inequality” ( Economic Journal ,forthcoming;previous version
published as Measuring Ancient Inequalit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3550[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October2007])中估计的,等同于1990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出的人均
GDP 633国际元(见散论二)。而Angus Maddison的估计稍低一些,为570国际元(Contours ofthe World Economy ,1-2003 A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chap.1)。
7. 这只是作为一个例子,实际上斗兽场建在克拉苏去世百年之后的罗马帝国
皇帝韦斯巴芗(Vespasian)和提图斯(Titus)治下。
8. 基于《纽约时报》1937年的讣告和维基百科,而Alan Nevins说这个数量并
没有超过9亿美元(Study in Power :John D .Rockefeller ,Industrialist
and Philanthropist ,2 vols.[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53],404-405)。
9. 见《财富》杂志2004年亿万富翁名单。
端的也正是这段时期。
(Gibbon)所言的罗马“衰亡”在学界声名远播,而标志其开
斯·奥利里乌斯(Marcus Aurelius)的儿子康茂德上台。吉本 帝”(five good emperors)统治结束,紧随其后的是马尔库
( 后 来 被 称 作 “ 奥 古 斯 都 ” ) 执 掌 大 权 到 公 元 180 年 “ 五 贤
期横跨了基督纪元的前两个世纪,即大约从公元前31年屋大维 让我们从帝国早期社会结构之大略开始。我们知道这一时
主要特征之一。 (免费书享分更多搜索@.)
的,是的,而且这是区分前现代化时期不平等与现代不平等的
存 。 这 两 种 景 象 是 否 可 以 同 时 成 立 呢 ? 正 如 下 面 我 们 将 看 到
工业社会的另一幅图景,在其中,底层的赤贫与上层的奢靡并
国)的不平等程度应该不高。但与这种观点相反,我们也有前
时,而前工业化社会(甚至包括它们之中最发达的,如罗马帝
形 , 因 此 不 平 等 应 该 只 出 现 在 社 会 进 入 持 续 的 现 代 化 进 程 之
为主变成以工业或“现代”产业为主时,不平等的图像呈倒U
品1.10)。作为不平等经济学的基础,它认为当经济从以农业
的理论,这就是提出于1955年的库兹涅茨假说(见散论一和小
关于前工业化经济中的收入不平等,我们的确有一个隐含
罗马帝国有多不平等?
小品1.4政治上,同时很大程度也在经济上,居于帝国早期顶端的
自然是国王。他,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和他的家族有多富有
呢?据估计,屋大维家族的年收入为1 500万塞斯特斯,约相当
于整个帝国总收入的0.08%(其时人口为5 000万~5 500万)。
换言之,以相对值计算,这大约是19世纪初大不列颠与爱尔
兰联合王国国王乔治三世所占比重的8倍。 (顺带指出,乔
治三世是《傲慢与偏见》故事发生时的国王,见小品1.1。)著
名的罗马史学家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
认为,屋大维去世后从私人和公共基金中捐赠给民众的财富总
和为4 350万塞斯特斯, 约为当时帝国GDP的0.2%。这就大致
好比布什总统在离任时自掏腰包,分发给美国公民大约300亿美
元。
屋大维的慷慨并非独一无二。公元33年,其继承者提贝里
乌斯(Tiberius)拿出大约GDP的0.5%(以当今美国的收入折合
为750亿美元)用于解决银行流动性危机,这和美国财政部2009
年的做法非常类似。塔西佗的记载在今天有了令人惊异的呼
应,唯一不同的是,它是由个人,而非政府支付这笔钱:
这个要求购销土地的法令……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因为
放高利贷者收回放款后便将之囤积起来,以便方便时购买土
地。大量的土地交易降低了其他商品的价格。然而,负债沉
重的债务人却发现难以把货物卖出,于是其中很多人便丧失
了财产,一同失去的还有他们的地位和声誉。这时提贝里乌
斯来拯救他们了。他将1亿塞斯特斯拨给尤为著名的银行,而借款人若能以贷款价值两倍的土地作为抵押的话,就可以得到免息三年的国家贷款。信贷就这样恢复了,而私下放款
的人也逐渐重新出现。
在公元36年,对于罗马遭受巨大火灾的人们,提贝里乌斯
拨了同样多的资金以弥补其损失。 尼禄延续了这一做法。塔
西佗在早期著作《罗马史》一书中,估算尼禄在其统治的14年
中捐赠总额高达23.2亿塞斯特斯,约为全年GDP的10%。这所有
的钱从何而来?是私有的还是公有的?皇帝在这两者间做了严
格的区分吗?或许没有。希腊-罗马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
(Cassius Dio)如此描述屋大维对公共和私人资金的处
理:“名义上公共收入和他自己的财产是分离的,但实际上他
也可以由着性子随支随取。” 正如最著名的罗马史学家之
一、斯坦福大学的沃尔特·谢伊德(Walter Scheidel)所言,皇帝的所作所为与如今的沙特统治者或萨达姆·侯赛因处理私
产和国库资金的方式大抵如出一辙。
毋庸置疑的是,皇帝极其富有,但并非帝国中唯一富有的
人。大量的财富来自对各省的管治和劫掠。用英国著名经济学
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比喻来说,“它是用剑挖掘的,而不
是铁锹”。 我们已由小品1.3了解到罗马帝国历史上最富有
的人可能并非君主。这样一个由富豪统治的社会,其阶层间的
划分以占据世袭爵位和持有大量流通财富这二者的结合为基
础。为了保证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对元老、骑士和市政官这
三个顶层阶层的财富有明确的评估登记。前两个阶层住在罗马
(或意大利其他地方),而第三个阶层,顾名思义,分布在帝
国各地。在帝国早期,对元老的财产要求为100万塞斯特斯,而骑士为25万塞斯特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数字,我们不妨看
看元老。这一阶层的平均财产可能在300万塞斯特斯左右,对此
采用每年6%的通行利率,则有18万塞斯特斯的年收入,而这大
约是估计的当时罗马平均收入的500倍。再以今天美国的情形而
言,这意味着那些元老的年收入(不是财产)约为2 100万美
元, 而如今美国的参议员则相对较穷:他们的年薪少于20万
美元,平均净资产估计约为900万美元。 假定财产有6%的收
益,再加上薪酬,他们的平均收入也大约只有不足70万美元,而这只是其古罗马同行很小的一部分。
然而,古罗马元老不多,也许只有约600位,而骑士则可能
有4万名。另外,由于各地富裕程度不同,对财产的要求在各城
市间有别,故而市政官的数量不那么确定,而且整个帝国所有
市政官的总数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对城市数量、市政议会
(municipal senate)规模等的估计。但若要给出市政官的大
体数目,我们可以认为大约有13万~36万人。无论如何,将这三
个最富有的阶层加在一起,得到的人数在20万~40万人之间。如
果还记得罗马帝国有5 000万~5 500万居民的话,正如我们所
见,金字塔顶端的人数相当少,仅代表着不到1%的总人口。
不足为奇的是,绝大多数人仅靠极低的收入苟延残喘,或
者免于饥饿而已,其间的梯度(即当我们从较为贫穷的收入阶
层向上攀升时收入增长的速度)比现代社会平坦,而在这一大
群人之间以收入比体现的差异很小,因此,该梯度在收入分配
中平缓地上升到很高的点。但随后,当我们接近分配的顶端
时,梯度会陡然上升,其变化之大远超现代社会。因此,不同于以梯度稳定增长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古罗马的中层与底层间
并没有太大差异。即使不是完全阙如,那里仍然缺少可被我们
(用当代术语)称作“中产阶层”的人。
我们先入为主地认为,古人之间既有普遍的平等,又有巨
大的收入差距,现在知道这两者都是正确的:它们只是代表了
收入分配的不同部分而已。当我们着眼于收入分配梯度的大部
分,或者观之以收入不平等的标准测度时,第一个观点(即贫
困中的平等)是成立的。因为这些测度是考虑到社会中所有人
收入的综合性指标,那么既然大部分人之间的收入并无太大差
别,此类不平等统计量也就不会非常高。根据基尼系数(见散
论一)这一我们最偏好的对不平等的测度,罗马帝国早期的基
尼系数估计在0.41~0.42之间。 这一水平与现在的美国和扩
大后的欧盟几乎完全相同(也见小品3.3)。但若着眼于分配中
的极端现象,第二个观点(即处处啼饥号寒之外却有人家财万
贯)也成立。这道横亘在两个极端之间的鸿沟比我们今天观察
到的要大得多。
罗马帝国还存在大范围的空间不平等。在我们考虑的这段
时间里,由单个中心统治的帝国扩张了巨幅领土,西起今天的
摩洛哥和西班牙,东至如今土耳其和亚美尼亚的最东端。沿南
北轴线,从英格兰绵延到波斯湾(尽管只是在图拉真治下的公
元98年到117年之间占有波斯湾,随后便从那里撤离)。其领土
覆盖340万平方公里,大约是美国大陆面积的34。在这片广袤
的土地上居住着5 000万~5 500万人口(由此可知其密度仅约为
当今美国的15),而他们有着不同的发展及收入水平。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估算了各地区收入的范围。 意大利半岛
是最富裕的,较帝国的均值高出约50%。接下来是帝国的粮仓埃
及,也略微比整个帝国的平均水平富裕。再次是希腊、小亚细
亚、非洲的部分地区(利比亚和今天的突尼斯)、西班牙南部
(大抵是现在的安达卢西亚)和法国南部(大致是如今的普罗
旺斯)。那些更加贫穷的地区间差异较小:一些岛屿(西西里
岛、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也许只稍微比高卢好一点,北非(今
天的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紧随其后,而排在最后的是东部
(多瑙河流域)诸省。最富庶和最贫穷地区间的收入之比相对
较低,约为2∶1。
如果看看那些曾属于早期罗马帝国的地区今天的收入,马
上便能发现其间的差距在今天明显大了许多。眼下排在顶端的
是瑞士、奥地利、比利时和法国,其人均GDP皆在35 000国际元
左右。 在另一端,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人均GDP在7 000~8
000国际元之间,而巴尔干半岛诸国只是略微好一些。因此,在
同样的土地上,今天的“省际”贫富之比已经攀升至5∶1,而
且各“省”的排位次序也发生了变化。大体而言,那时的南方
比北方富庶;现在,情况正好相反。然而,西欧相对于东欧的
优势如故。
1. Goldsmith,“An Estimate of the Size and Structureof the National
Product of the Early Roman Empire”。
2. Goldsmith,“An Estimate of the Size and Structureof the National
Product of the Early Roman Empire”,基于Colquhoun的社会阶层收入表与Lee Soltow 的 计 算 , “Long-run changes in British income
inequality,”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9(1968):7-29。
3. 塔西佗,《编年史》第一卷第八章。
4. 塔西佗,《编年史》第一卷第六卷(公元33年),第208页。
5. 数据来自塔西佗《编年史》一书。
6. Cassisu Dio,The Roman History :The Reign of Augustus ( New
York:Penguin Classics,1987),131.
7. 来自私人通信。
8. Alfred Marshall,Principles of Economics ,vol.2:notes,9th
edition(London:Mc Millan,1961),745,Marshall回答William Cunningham之
批评。
9. 这是美国人均GDP(2008年时约为4.2万美元)的500倍。
10. 见 Jessica Holzer,“Meet Senator Millionaire,”Forbes ,November
20,2006 , 可 访 问 http:www.forbes.com20061117senate-politics-
washingtonbiz-wash_cx_jh_1120senate.html。
11. Milanovic,Lindert and Williamson,“Preindustrial Inequality,”附
录。
12. Milanovic,Lindert and Williamson,“Preindustrial Inequality,”,及Walter Scheidel和Steven J.Friesen,“The Size of the Econom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the Roman Empire,”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99(2009):61-91。Milanovic、Lindert和Williamson是对公元14年的估计,而Scheidel和Friesen是对公元150年的估计。
13. Maddison,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30 AD ,53-55。
14. 最富庶的区域(意大利半岛)比均值高50%,而最贫穷的区域(多瑙河诸
省)比均值低25%。
15. 对国际元(PPP US)的定义,见散论二。小品1.5
在13世纪和今天,你应该住巴黎的哪个区?
很多人都被巴黎第十六区吸引,那里有维护良好的建筑、不俗的餐馆、宜人的小公园、鳞次栉比陈列雅致的商铺,以及
无处不在的温软靡丽之气。 的确,2007年法国政府的税收数
据显示,第十六区是巴黎最富足的区之一。连同第六区、第七
区和第八区,其人均应税收入(fiscal income,即报告给税务
机关的收入)是巴黎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 正如图1.1a和图
1.1b所示,深色阴影代表的富裕区覆盖了巴黎西部并横跨塞纳
河。在财富谱系的另一端,第十八区、第十九区和第二十区这
些最为贫穷的区则位于巴黎东北部的边缘,其人均应税收入不
足巴黎平均水平的23。这么几个简单的数字让我们认识到这些
区之间的差别有多大:以2.5除以那个小于23的数可知,顶层
与底层之比约为4∶1。
现在,这幅地图只包含官方所称的巴黎,即在环城大道内
这座城市管辖的20个区,其在几乎两个世纪内没有变化。郊外
既有更加富庶之处,也有穷得多的地方。前者如巴黎西部植被
繁茂的郊区纳伊(Neuilly),而后者则见之于郊外移民(通常
是阿拉伯人和非洲人)聚居区,那里在2005年的暴乱中火光冲
天。因此,如果我们考虑整个大都市区域的1 200万居民,而不是250万生活在市区的居民,则巴黎最富裕地区和最贫困地区间
的差距会大得多。
图1.1a 财富分配:13世纪以“教区”为单位的巴黎图1.1b 收入分配: 21世纪以“区”为单位的巴黎
资料来源: 1292年和2007年的财政数据。
最富有的区也最不平等,而最贫穷的区倒是最平等的。这
里存在着财富和平等相当单调的逆向关系,或者说,一个区愈
富庶,则其不平等愈明显。而这也意味着在最富有的区里也居
住着相对穷困的人群;换言之,就占有的财富多少而论,其间
的人群形形色色。的确,若将所有区的家庭放在一起,分为同
样规模的12个应税收入阶层, 则最低阶层占了第十六区全部
家庭的15,这与生活在贫困区同样阶层所占的比重没有多大区
别。不同之处在于富裕家庭所占的比重。生活在富有区的家庭
中大约15都属于应税收入的最顶层(即第12层),但在贫困区
中这样的富裕家庭几乎不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今天的巴黎,贫穷家庭相当均匀地分布在整个城市,而富裕家庭则集中
于少数的几个区,特别是第十六区,巴黎超过20%的富人住在那
里,而这个比例是平均水平的4倍。
因为年代久远,资料缺失,追寻城市漫长岁月中不断变化
的经济地理殊非易事。但巴黎是个例外。我们有巴黎自13世纪
末、14世纪初以来的税收数据,而近来耶路撒冷大学经济史学
家内森·苏斯曼(Nathan Sussman)已将之数字化并加以利
用。 和2007年的数据一样,这些古老的数据也来源于税收,它们提供了由每个家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每个炉灶
(foyer)]承担的平均财产税。反过来应用估计的税率,我们
就可以估算出总的财产。当然,那时的税收数据远没有现在可
靠。它们遗漏了人口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锦衣玉食却免
于纳税的贵族和牧师,以及身无长物而无从缴税的贫贱之躯。
此外,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财富分配,而不是收入分配。从大
量研究中可知,财富分配较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然而,仔细
比较是可能的,尤其是如果我们使用1292年的税收数据。事实
上,这一年的数据比其他年份的都要完整:在当时巴黎估计超
过100 000的人口中,税收数据涵盖了几乎15 000户家庭,即70
000人左右。
那时的巴黎被分成了24个教区,比现在小得多。第一幅地
图展现出这些教区的相对收入(和如今的行政区一样,越富有
的教区颜色越深)。最富有的[圣雅克(St.Jacques)教区,是
如今第一区的一部分]和最贫穷的教区[圣马塞尔(St.Marcel)
教区,在现在的第五区]间的收入之比约为6∶1,故而顶层与底层的差距似乎远高于现在。但是,我们须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一
结果,因为如下两种偏差或许会(幸运地)相互抵消:一方
面,1292年的数据涉及的是财富,其分配总是比收入分配更加
不平等;另一方面,正如我们看到的,数据遗漏了富有的贵族
和贫穷的游民这收入分配的两极,而该偏差降低了测量到的不
平等。
当时巴黎最富庶的地区是塞纳河右岸和西堤岛,但左岸却
贫穷得多,而今天的第十六区在13世纪时并非巴黎的一部分。
然而,即使粗略对比这两幅地图,我们也可以看出财富和贫穷
在地理上的变化。最富有的地区从巴黎中心和塞纳河右岸向
西“迁移”了很远并跨过塞纳河,因此也“提携”了左岸的部
分地区。那些大体上在左岸且曾经最穷困的区域,如今却处于
巴黎收入分配的中层甚至更高,而今天最窘迫的区则位于巴黎
东北边缘,相对远离市中心,而那里在1292年甚至还不属于这
座城市。
用什么来解释这种地理迁移?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
(CNRS)城市研究学者莫妮克·潘松-夏洛(Monique Pin?on-
Charlot)和米歇尔·潘松(Michel Pin?on)看来,原因在于
巴黎西部在相对较晚的19世纪才并入巴黎并开始城市化。 其
时,拿破仑三世掌权,经济勃兴,而“资产阶级权贵”蒸蒸日
上。他们渴望更多的空间、更舒适的公寓和宅院,而当时相对
落后的巴黎西部满足了他们的需求。较之于在市中心逼仄的住
宅区中花大价钱整修破旧的房屋,他们更倾向于修建自己的房
子。而由于脱离了行会的限制,圣安东尼郊区(FaubourgSaint-Antoine)所在的巴黎东部在传统上一直更为工业化,故
而对富人毫无吸引力,于是这进一步推动了“西迁”。富人由
此慢慢在巴黎西部重新安顿下来,而正如我们刚看到的,他们
现在依然生活在那里。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塞纳河左右两岸之间似乎存在已久的
区别。今天,塞纳河右岸是行政中心,要塞(即通常所说的卢
浮宫)、政府各部、证券交易所和豪华亮丽的商业街分布其
间,而左岸是学生和宗教会众的领地。这的确是13世纪后期税
收调查呈现的图景,也是巴黎的传统形象,即这座城市被塞纳
河分为实现不同功能的两部分:大体上,右岸关乎权力、贸易
和行政,而左岸关乎灵魂和思想。但情况总是如此吗?并不见
得。这样的分划在罗马时代古老的卢泰西亚(Lutetia,巴黎在
当时的罗马名字)是不存在的。其时虽然宫殿和庙宇坐落于西
堤岛(如今的巴黎圣母院就靠近原来一座罗马宫殿的位置),但诸如竞技场、剧院、浴场和广场等其他重要的建筑都在左
岸, 而右岸则没有城市的重要部分。我们可以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子尤利安(Julian)于公元362年对巴黎的描
述中了解这一点。这位曾尝试减缓帝国的基督教化,并且可以
想见也试图回到希腊-罗马式崇拜的皇帝,曾作为恺撒
(Caesar,这是仅次于皇帝的位置)在巴黎待了几年。由于钟
情于这座城市,他这样追忆其在巴黎的时光:
我正好在冬季营地,它就位于我心爱的卢泰西亚
(Lutetia)——凯尔特人 是这么称呼巴黎人的首府
的。这是一叶卧于河中的小岛,城墙紧拥,木桥联通两岸。河水不常涨落,不论冬夏,通常都在同一水位……百姓安居
于此,故不得不主要从河中引水。或许是由于来自海洋的温
暖,其冬季亦是别样温和……甜美可口的葡萄生长左右,甚
至有百姓在冬季借由覆以秸秆之类,设法种出了无花果
树……
的确,在早期,因为左岸不易受洪水之苦,故而是更好的
选择;而右岸则正如著名的区域“玛莱”(Le Marais)这个名
字迄今呈现的那样,有更多沼泽,以至于在12世纪,能够用来
建造房屋之前不得不先排涝。
因此,巴黎财富的地理分布似乎已从罗马时代以塞纳河中
游的岛屿(或许这是开始营造城市的天然所在)和其左岸为中
心,变为中世纪时集中于右岸,再变至当下的格局。今天,如
果你要与富人结邻,首选自然是巴黎西部。
1. 感谢Guillaume Daudin许多极好的建议和评论,其极大地改进了本文,同
时感谢Nathan Sussman提供的13世纪巴黎的数据和地图,以及Thomas Piketty
提供的2007年财政收入数据。
2. 事实上,第十六区是第二富裕的区,仅次于第七区(但是第十六区有更多
居民)。
3. 收入最低的阶层包括年收入低于9 400欧元的家庭[或曰“纳税
户”(foyerfiscal)],而最高的阶层则由年收入97 500欧元及以上的家庭组
成。
4. 对13世纪数据的分析是基于Nathan Sussman的论文“Income Inequality
in Paris in the Heyday of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未刊稿)。5. Income Inequality in Paris in the Heyday of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未刊稿),第3页。
6. 见http:www2.cnrs.frpressethema592.htm。
7. http:www.inshea.frRessource ProductionsSDAD
VTactimage_6ePagesPlanLutece.htm。
8. 凯尔特人是铁器时代和中世纪生活于欧洲的一些共享着某些文化和语言特
质而有亲缘关系的民族的统称。——译者注
9. 尤利安皇帝,The Mispogon 。小品1.6
谁从财政再分配中获益了?
谈及收入分配,我们几乎总是想到经济学中所谓“可支配
收入”的分配。正如字面所示,这是家庭在向政府支付完直接
税并从政府取得了如社会保障和失业救济金之类的现金收益之
后,留给其储蓄或消费的收入。但另一个“收入”概念不时也
是有用的,这就是“市场收入”(market income),即未经财
政参与(也就是说在纳税和接受政府转移支付之前)的来自工
资、利润、利息、租金等的收入。显然,市场收入很低的是那
些不能(或不愿)出售其劳动力,且缺少财产以赚取收入的
人。在发达国家,他们通常是失业者。顺带一提,国家出资的
养老金(如社会保障)或私人养老金被认为等同于工资收入
(只不过是延期的),因此也包含在市场收入内。
有了这些准备,我们就经常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政府以
税收和现金收益体现的再分配中,哪个收入群体受益最多?有
一种理论认为,在民主体制下,民众为再分配政策投票,其主
要受益者应该包括位于(市场)收入分配中间阶层的人。其理
由是:假设这个社会由三个人组成,其市场收入分别为低、中、高——市场收入在这里很重要,因为已经挣得的市场收入
决定你偏好的财政收支政策。穷人会倾向于偏好高税率和大量
的政府支出,因为他可能从中受益。出于完全相反的原因,富人会偏好低税率。那么,关键投票就掌握在中间阶层手中。不
论他支持哪一方,该方就会以2∶1胜出。中间选民(the
median voter),或者我们所称的“中产阶层选民”,由此成
为决定性的投票人。因为税率通常是累进的(也就是说,税率
随着市场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在再分配过程中中产阶层选民
可能不会比穷人获益更多,但在原则上获益是可以肯定的,因
为毕竟是他在选择税率以及随之而来的收益,而这意味着其境
遇在可支配收入下会比在市场收入下更好。
事实果真如此吗?现实并非完全如此,而相关证据也不是
始终一致。 首先,我们发现穷人从再分配中获益最多。就市
场收入而言,他们占的比重通常微乎其微,但在政府再分配之
后却有所增长;最终的份额虽仍然很小,但至少能说得过去。
比如,研究表明1980—2000年的大部分民主国家,最贫穷的十
分位阶层(即总人口的10%)在总的市场收入中的比重非常小,仅占1.2%。在政府再分配之后,相同群体的收入比重上升了;
就各国平均而言,这一比重达到了4.1%。因此,最贫穷阶层获
益将近3个百分点。次贫穷阶层相应的两个数据分别为3.6%和
5%,获益1.4个百分点。对每个紧随的(更富有的)阶层,获益
逐步减少,直到第五和第六阶层开始有了轻微的损失。当然,随后对更高阶层的负面影响愈发严重。图2以美国和德国为例,该图表明,最贫穷阶层在各国的收益也不尽相同。美国的最低
十分位阶层大约获益4个百分点(正如我们之前所见,这个数值
是分析所涉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在德国该受益大约是7个百分
点,显著而一致地高于前者。我们可以立刻得出两个明显的结论。首先,发达国家再分
配过程中的最大受益者“一开始”是最贫穷,即市场收入最低
的人。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令人意外的是我们预期会从再分
配中获益的第五和第六阶层这样的中产阶层,却未能如此,其
所占份额甚至稍有下降。此外,这个结果不仅对发达国家整体
有效,而且对每个单独的国家亦然:中产阶层收入份额的损失
程度因国家而异,因年代不同,但其存在却毋庸置疑。这就引
出了一个我们尚未很好地做出回答的问题:为什么理论上起决
定性作用的中产阶层选民会投票支持某种过程,使其最终只获
得国民收入中较原来更小的一部分?这里有两种可能,对此我
们不能断然肯定或拒绝。第一种可能是,中产阶层视某些再分
配政策为潜在的保险而投票。虽然在我们看到再分配结果的一
刹那,他并没有从中取得任何收益,但其当初的投票“只是以
防万一”。例如,若期望在需要失业救济金时他们能够符合条
件,中产阶层可能会为了积存这些救济金而接受对当前收入征
收更高的税款。这是一个合理假设,但是由于缺少逐年追踪同
一群人而获得的纵向数据(以便我们可以真正确定他们最终是
否从这些转移支付中获益),我们很难证明这种可能是否真
实。此外,即便追踪这些中产阶层家庭一辈子,假如发现他们
在再分配之后仍然遭受损失,我们也可对此做如下解释:就算
从中得不到一分一毫,他们为失业救济金投票似乎仍是有价值
的,因为这是一种保险政策。正如购买车险时,我们并不希望
能从中赚钱;如果我们真的得了钱,情况可能会比没有时更
糟。我们买的就是一个“安心”,同样的道理亦适用于此。图2 美国和德国的最贫穷十分位阶层在分配中的获益
注:当我们从市场收入转为可支配收入时计算获益。
第二种可能是存在主要由中产阶层享有的转移支付,但“可支配收入”这一概念却不能对此有恰当的反映,这对有
社会医疗体系和公共教育的欧洲福利国家来说尤为如此。从这
两者中获得的福利都未列入可支配收入。事实上,可支配收入
只是我们可以支出或储蓄的现金收入。如果我们得到了免费医
疗救助或免费教育,由于它们是以非货币形式获得的福利,因
而就不属于可支配收入。但是,免费医疗救助和免费教育是以
民众的直接税支付的。有可能虽然我们正确估计了中产阶层的
税收,但由于某些福利是以实物形式得到的,总的福利却被低
估了。因此,如果我们能以某种方式说明这些福利的现金价值,就可能发现中产阶层确实从政府再分配政策中获得了净收
益。
两种解释都有可能,但不幸的是我们缺少数据以清楚地证
明其中任何一个。我们还面临另一个有趣的问题。让我们回到
最贫穷的那些人,正如我们所见,他们是政府再分配的最大受
益者。假如现在这一最贫穷群体的境况变得更为悲惨,即他们
已有的非常微薄的市场收入份额进一步减小,这会如何?再分
配过程对其所占份额的下降会产生作用吗?事实证明,答案是
肯定的。在先进的民主国家,政府会通过更具再分配性质的税
收-转移支付政策尽数弥补最贫穷群体市场收入份额的下降。总
的来说,这是令人欣慰的消息,尤其是在危机之中。如果有人
不能出售其劳动力,或者不得不廉价出售,同时也没有任何资
产,因而处在收入最底层的话,那么他将遭受更多损失,税收-
转移支付体系会充分弥补这些损失。
因此,尽管我们看到发达国家在过去25~30年间在可支配收
入上的不平等程度大幅上升,尽管各国税收-转移支付体系存在
差异,但这些制度大致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即帮助那些起步于
最低地位的人中的大多数,并减少最富有群体所占的收入比
重。依然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在决定再分配的程度时扮演关
键角色的中产阶层并没有显示他们从这套体系里明显获益了?
这一结果或许也显示了经济分析的局限性,因为我们的投票行
为受意识形态、原则或价值观的影响,有时这甚至比经济因素
的影响更大。毕竟,我们不只是靠面包活着。1. 其间的依据是,一个人收到的养老金,原则上已由其工作生涯中的工资扣
除支付过了,因此只是工资收入在时间上的“重组”罢了。无须预缴的所谓社
会养老金则是个例外,它支付给诸如从来没有工作过也因此不能获得退休收入
的贫困老人。
2. Branko Milanovic,“The Median Voter Hypothesis,Income
Inequality,and Income Redistribution:An Empirical Test with the
Required Data,”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6,no.3(2000):367-410.
之内,若称人与人之间总的收入不平等为甲,则其可以分解为
收入不平等定然极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在一国
共和国间较高的平均收入差异。这意味着在各共和国内部人际
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整体上较低的人际不平等竟伴随着各
指的是个人之间较低的收入差异。
并不矛盾——前者指的是各共和国之间平均收入的差异,后者
我认为总的收入不平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很低,而这两种观点
当谈到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区域收入差异时,需说明的是,.)
密 联 系 中 寻 找 解 体 的 根 本 原 因 。 ( 免 费 书 享 分 更 多 搜 索 致。我们必须从收入与宗教之间或者收入与种族之间暗合的紧
此外,收入的沟壑与种族的沟壑一致,有时也与宗教的沟壑一
每一个联盟内,我们真正面对的是多个国家及多个发展水平。
所称的“共和国”的收入水平参差不齐,相去甚远。因此,在
实(尽管对捷克斯洛伐克并非如此):构成这两国的州或后来
解释。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对苏联和南斯拉夫成立的一个事
治、宗教等方面的原因,甚至包括纯粹的情境之中前因后果的
解 , 人 们 已 花 了 很 多 笔 墨 详 加 说 明 , 提 出 了 种 族 、 历 史 、 政
就 苏 联 、 南 斯 拉 夫 、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这 些 国 家 联 盟 突 然 瓦
若干国家可存于一体吗?
小品1.7两部分,这就是乙:区域间的不平等,即由区域间平均收入差
异导致的不平等,以及丙:各区域内的人际不平等(见散论
一)。因此,若苏联的甲相对较小而乙相对较大,那么丙必定
非常小。
苏联由15个共和国组成。在1991年解体时,以人均GDP衡
量,最富有的共和国(俄罗斯)与最贫穷的共和国(塔吉克斯
坦)之间的比值大致是6∶1。我们将会看到(见小品3.3),在
美国,最富有和最贫穷的州之间的比值仅为1.5∶1。让我们看
其他几个例子。在以区域不平等臭名昭著的意大利,其最富有
的区域(位于北部的瓦莱达奥斯塔大区,与瑞士接壤)和最贫
穷的区域(位于东南部的卡拉布里亚大区)之间的比值是3∶1;
在区域关系不时紧张的西班牙,其最富有的区域(马德里)和
最贫穷的区域(埃斯特雷马杜拉自治区)之间的比值是1.7∶1;
在法国,这一比值是1.6∶1(即环绕巴黎的法兰西岛大区较之
于北部加来海峡大区);而在德国,则是1.4∶1(柏林较之于
图林根州)。可见,苏联的区域不平等现象比任何这些国家都
要严重得多。
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和俄罗斯,比整个苏联的平均收入要
高出许多,而剩下的11个共和国比平均水平低。 这一差距并
未随着时间减小。尽管要构建各苏维埃共和国一致的数据序列
会面临许多困难,并且在做结论时得相当审慎,但通过1958年
首次可用的数据,我们发现俄罗斯(也是当时最富有的共和
国)和最穷的中亚共和国之间的差距仅为4∶1。因此,共和国之间的差距不仅大,而且在二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一差距
极有可能在不断加大。
解体之时,苏联可视为一个联合体,在其疆域之内容纳着
收入差异巨大的国家,而它们竟如韩国与科特迪瓦一般。 如
果没有大量的再分配来帮助贫穷的成员以巩固国家的团结统
一,这个联合体能存在吗?几乎不可能。但是,那么大范围的
再分配可行吗?那些为这种财富转移掏钱的富裕成员,难道不
会最终因此心生怨怼?这确实在俄罗斯发生了。当叶利钦当选
为其最高领导人时,它仍是苏联的一部分。他支持那些反对进
一步补贴的力量。于是,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和波罗的海诸
国成为苏联最激烈的分裂主义者。富裕的共和国极欲决绝出
去,而贫穷的共和国除了默认,别无他法。
前南斯拉夫的例子更具戏剧性,这不仅因为其瓦解的方
式,更在于虽然它整个领土仅相当于苏联极小的一部分,但其
各共和国间的收入差异却比苏联更大,因而也更令人侧目。人
们或许能够理解苏联内部存在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毕竟它是
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面积约为美国的2.5倍。异乎寻常的是,南
斯拉夫的面积跟密歇根州一般大,但其共和国之间的收入比竟
达到8∶1。 在欧洲,再没有别的国家的区域收入不平等达到
这般水平。南斯拉夫最发达的地区是位于西北的斯洛文尼亚,在1991年解体时,其人均收入水平与西班牙相当。而最不发达
的科索沃省地处东南,其人均收入与洪都拉斯相仿。因此,在
如密歇根州那样大的国家里,中央政府不得不让这两种收入水
平的人都满意。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在南斯拉夫,尽管有由联邦出资的机构进行适度的再分配,但共和国之间的差距却不断
增加。比如,在二战后的南斯拉夫,当其统计数据于1952年首
次可以获得时,以人均GDP计,斯洛文尼亚的富裕程度仅为科索
沃的4倍。40年之后,正如我们看到的,其间的差距业已翻倍。
我们从共产主义联邦政府的瓦解可以看到,解体的一个重
要原因是,尽管它们的政策成功地控制和降低了人际不平等,却不能缩小其各组成部分间由历史遗留的巨大收入差距。再回
到小品标题中提出的问题,它还会困扰其他许多国家。比如中
国的区域收入差距正在迅速加大。欧盟可以不断吸纳更穷的成
员国,却不危害其自身的团结统一和生存发展吗(见小品
3.3)?尼日利亚各州的种族和宗教截然不同,且它们间的人均
收入差异约为4∶1,它又该怎样在其间协调石油收益的分配
呢?
1. 白俄罗斯的位置不清楚。根据某些统计,其收入水平高于苏联平均收入水
平,但据另一些统计则相反。
2. 原文为Ivory Coast(“象牙海岸”),这是科特迪瓦共和国的别称。——
译者注
3. 除了六个共和国,我还使用了两个省(较共和国为低的行政级别)的数
据。小品1.8
中国的不平等
中国目前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中国的不平等不
仅几乎已经翻倍,其基尼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不到0.30
上升至2005年的0.45,而且这一问题还体现在其构成方式上。
为简化计,我们可以把不平等分为两种类型(见小品
3.3):“美国式”不平等是一种较高的不平等,其富人和穷人
较为均等地分布于全国,而没有在地理上集中于特定的州。显
然,富人和穷人的确生活在不同社区,但在第一级行政单位
( 即 “ 州 ” ) 间 并 不 存 在 “ 收 入 隔 离 ” ( income
segregation)现象。究其实质,即“只有”穷人和富人之分,而没有穷州和富州之别。欧盟扩张之后的不平等是另一种类
型,即主要源于其成员国平均收入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产生
的穷人和富人在地理上的集中。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中
国增长的焦点转移到城市地区,其发展逐渐造成了后一种不平
等,即产生了贫穷和富有的省,而这可能更易导致社会的不稳
定(见上一小品)。
中国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沿海省份。不考虑有很高人均GDP的
上海、北京、天津这3个城市, 让我们来看看沿海的另外5个
富裕且发展迅速的省。这些省份从北到南相邻,依次为:山
东,相较于中国的其他部分,其人均GDP从1990年的1左右(意味着它大约等于当时中国的平均水平)增长到2006年的1.3;江
苏,从1.3增长到1.6;浙江,从1.3增长到1.8;福建,从1增长到
1.2;而广东,则从1.5增长到1.6。在过去的15年间,这里的每
个省大致比中国平均增长水平快了20%。据2006—2007年的数
据,这些省份的总人口是3.4亿,大致是整个中国人口的14,然而却创造了其GDP的40%。
如果再加入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这4个直辖市,我们看
到,这5个省和4个直辖市的产出占了中国全部产出的50%以上。
我们可以轻易地把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视为这一现象自然
而然也更极端的扩展。由此,这个“5+6”的省市组合形成
的“集团”,在地理上大致相连,以贸易为导向,相较中国内
陆越来越富足,开始代表一个分离群体。
在另一端,20世纪90年代以来,贵州、甘肃和云南这最贫
穷的三个省的状况都相对下滑。后两个省的人均GDP曾是中国平
均水平的70%,而现在只有50%。最穷的贵州省,最初为中国平
均水平的一半,但现在只有13。富裕的省发展得比平均速度
快,而贫穷的省却比平均速度慢,不出所料,这使最高收入和
最低收入之比急剧增加。1990年大范围的工业改革之初,这个
比例为7∶1,而到2006年已上升到10∶1。而且,以上结果还没
有考虑西藏的收入。鉴于西藏可能是中国最穷的省,这自然会
愈发拉大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间的鸿沟。
这至少为10∶1的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比,较苏联当时的
6∶1(见上一小品)还要高出许多。当然,在别的方面,情况
有所不同。名义上苏联是一个国家联盟,故而在其经济的沟壑之上,是种族、语言以及宗教上的沟壑。但尽管语言存在差
异,中国的汉族可被视为一个民族,而且较之于波罗的海诸国
的民众与俄罗斯人,或者塔吉克人与俄罗斯人,汉族生活于单
个政府之下的历史更长。 然而,至少对广西、内蒙古、宁
夏、新疆和西藏这五个最贫穷的自治区而言,非汉族人口是重
要的少数族裔,甚至还占据多数。以汉族为主的中国(Han
China)的确也曾四分五裂,尤其是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
纪的战国时期,接着是3世纪的三国时期,最近一次是在20世纪
30年代,当时日本在中国北方建立了伪满洲国,而中国的其余
部分则分裂成多个战时政府,在其中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权
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最为声名远播。
因此,就经济和对外部世界的看法而言,繁荣的沿海11省
市和中国其余地区之间渐行渐远。这里潜藏着的危险既难以消
除,也不可忽视。
1. 虽然它们不都是官方定义的“省”(实为23个),为简便讲,我将其均称
为“省”。
2. 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的官方资料,主要是不同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3. 重庆是在1997年之后才成为单独的行政单位,即直辖市。
4. 虽然我们不应忘记,波罗的海诸国并入沙皇俄国始自18世纪(大体而言,对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这是在1721年瑞典—俄国战争之后,而立陶宛是在
1772年波兰解体之后)。小品1.9
研究不平等的两个学者:
帕累托和库兹涅茨
读者可能会惊讶,在个体收入分配的构成及其随时间演变
方面,没有多少理论或理论性的洞见。 考虑到早在1817年,现代经济学开创者之一大卫·李嘉图在其出版的极具影响力的
《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就已将收入分配放在经济学的核心位
置,这就更令人奇怪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至少可从两方面解释。其一,李嘉图关
注的是所谓功能性收入分配,或者说如何分配国民收入以形成
各大阶级的收入:对资本家是利润,对地主是租金,对工人是
工资。而我们这里感兴趣的是人际收入分配,也就是如何在个
体之间分配国民收入,而不论其主要收入是源于财产还是劳
动。现在,只要所有(或大多数)财产拥有者都富有,而所有
(或大多数)劳动者都贫穷,则功能性分配和人际分配看起来
就是相当一致的。我们知道,如果资本家获得了更大部分的收
入,则总的不平等就极有可能上升,而相反的结论对工资亦成
立。因此,对人际收入分配的关注湮没于对功能性收入分配的
关注,或者更准确地说,前者被纳入后者之下。但随着中产阶层的出现,由于其收入主要来自劳动,事情
就发生了变化,不再可能维持收入的功能性分配与人际分配的
一致性。经济学家必须建立理论来解释收入是如何在民众之间
分配的,而不仅仅是研究总收入的多大比例归于资本家,多大
比例归于工人。就是在这里,我们的第一个主人公维尔弗雷多
·帕累托发出了声音。
但在介绍帕累托之前,有必要提一下研究人际不平等不甚
受追捧的第二个原因,这在台面上常常是看不到的。虽然经常
被明智地忽略,但道理其实相当简单:富人不是特别欣赏对不
平等问题的研究。华盛顿某声名赫赫的智库的负责人曾告诉
我,他们的委员会几乎不会资助任何题目中含有“收入不平
等”或“财富不平等”的研究。的确,他们会资助任何消除贫
穷的工作,但不平等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何以如此?因
为“我”对他人贫困的关心将会突显我的古道热肠:我时刻准
备用自己的钱来帮助他们。慈善是好事,因为这会让自尊心膨
胀,而且即便是对穷人极小数额的帮助,也会赚得不少令名。
但是不平等就不同了,事实上一提起它就会引发另外的问题,即我自己的收入是否正当或合法?如果有人认为我拿的是不义
之财,那么我的慈善或许就不会那么讨喜了。因此,对不平等
最好是避而不谈。 类似地,世界银行并没有将其关于此议题
的核心报告冠名以“不平等”,而是更含蓄地称之为关于“平
等”的报告。近来,就对贫穷热切关注与对不平等不闻不问间
的反差,英国历史学家大卫·凯纳斯顿(David Kynaston)做
了极好的总结:“人人都愿意谈论消除贫穷,因为这看起来是对不平等问题可钦可佩、合乎道德的回应,但问题是他们对权
利结构避而不谈。”
不愿谈论不平等并非仅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当我开始对收
入不平等感兴趣时,我生活工作在社会主义社会。当时不平等
被婉称为“敏感”话题,而原因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看似不
同,实则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下,任何关于收入分配的实证研
究都表明其存在收入差异。这使国家统治者感到不安,因为其
在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建立在他们宣传的理念之上,即已开创
了一个没有阶级的平等社会。安全的做法是相信它,而不是对
此深入研究。
让我们把目光回到维尔弗雷多·帕累托身上。他是个充满
矛盾的人。帕累托在欧洲1848年革命时期出生于巴黎一个侯爵
家庭,他的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法国人。帕累托在19世纪
后期的自由环境中长大,精通意大利语和法语,并使用这两种
语言写作和教学(在现代边际学派经济学创始人之一里昂·瓦
尔拉斯退休之后,帕累托接替他在洛桑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
席)。然而,其观念却是贵族一派,强烈地反对社会主义。
他一直是个有争议的学者。正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
所言,在一定程度上,帕累托使老师和学生都感到不舒服。
他鄙视平民,以至于去解释所有的宗教和道德信仰如何在本
质上全是非逻辑的情绪,与作为科学之特征的逻辑-实验方法毫
不相关。然而,他认为又必须保护并传授它们,以使世人有所
信仰,否则他们就只会回到自然的原始状态。他大胆宣称“我
只是在探究现象间的一致性”,而“并不想说服任何人”。之后,他也许是在社会科学史上独一无二地又警告潜在读
者:“怀有其他目的的人很容易找到令其无比满意的作品;这
样的东西有很多,他们大可不必阅读此书。” 就这样,他将
这些潜在读者拒之门外。阿隆解释说,帕累托这种莫名的不安
源自他的某种态度,即就本质而言,教授传授的东西全都是谬
误。但帕累托认为,由于传授真理对任何社会秩序都是致命
的,而平民只能多少听懂那些谎言,因此教授必须在这种错误
中孜孜以求。用他的术语来说,社会均衡需要信奉那些非逻辑
的情绪。
下面是约瑟夫·熊彼特在其不朽之作《经济分析史》中对
帕累托的描述:
他怀有强烈的激情,这种激情实际上使他只能看到政治
问题的一面,或者也因此只能看到文明的一面。他接受的古
典教育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此种性情,并且使他对古老
世界就像对他自己的意大利和法国一样熟悉,而世界上的其
余事物仅仅只为他而存在。
帕累托写了两本颇有影响的经济学著作,也可说是教材,而他在今天的经济学界主要以两项贡献闻名,即“帕累托改
进”(或“帕累托最优”)和帕累托收入分配“铁律”。第一
个术语几乎每天都被经济学家使用,已成为经济学不可或缺的
工具之一。究其实质,帕累托改进指出,对于社会状态的某种
改变,只有每个人的福利都由此增加或至少保持不变,这种改
变才会为社会接受。简言之,必须要有人获益且无人受损。要找到这样的经济政策(或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总有人
会有损失,故而帕累托改进的要求相当严苛。在现实之中,这
无异于维持现状(见散论一)。
帕累托的收入分配“定律”来自对经验的观察。他一开始
学工程,其数学能力出众,最终发现了下面的统计规律。取收
入水平Y,然后找出收入超过Y的人,记其数量为N,然后将收入
水平Y增加比如10%,那么有多少人的收入超过Y(1+10%)呢?
显然,其数量会小于N。帕累托认为他发现了一个规律,或者说
一个定律:收入每增加10%,人数就会减少14%~15%,由此帕累
托常数[或曰“截断常量”(guillotine)]为1.4~1.5。 他
以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十几个欧洲国家和城市的税收数据为样
本,发现使用帕累托常数得到的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当吻合。
就意识形态而言,这个发现给了帕累托极大安慰。在其社
会学论文中,他主张社会的特点就是精英的更迭交替。在《共
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声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
的历史”;似乎是对马克思这一著名论断故意而间接的挑战,帕累托宣称“人类社会的历史……是贵族演替的历史”。 当
然,和马克思不一样,他认为这势必还将继续下去。在帕累托
看来,尽管社会主义式的“均等化”常常是时代聚讼纷纭的政
治话题,但其间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真正上演的,是一部分
官僚或工人领袖代替资本家而已。他们会成为新的精英,然而
也还是精英,不会比在原政权下有更多的平等。经验证明他似
乎是对的:不论选择什么样的国家或城市,收入分配看起来都
极为相似,并且当我们沿着收入分配的阶梯往上爬,几乎同样比例的人便会被淘汰。正如他自己所言,帕累托认为这才揭示
了收入分配的“铁律”。
收入分配研究的第二个使徒西蒙·库兹涅茨与帕累托完全
不同。1901年,库兹涅茨出生于俄罗斯帝国(具体的位置在今
天的白俄罗斯)。1922年,他逃离俄国,移居美国,然后在北
美多所大学读书从教,包括晚年在哈佛大学。他是国民经济研
究局(NBER,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该机构致力于对经济周期
的研究)的发起者之一。库兹涅茨筛查其时相当稀少的证据,以不同方式展示并分析研究数据,总之,其工作是相当经验性
的。在经济学家中,他是少有的一类。相对而言,他的文笔生
动有趣,即使时光流逝,在今天看来也常常充满洞见。然而若
想要引述他的话,却十分困难。在他的行文中,随处可见谨慎
的提示,又包含大量从句和省略句,这使人们基本上无法引用
原文或轻易得其精要。若想要从库兹涅茨的文字中得到简短透
彻的陈述,我们就得将其内容删掉23。在帕累托鞭辟入里、确
信无疑地——有时是存心言辞犀利、无所顾忌——写作的内容
上,库兹涅茨却会小心翼翼地避免错误;当帕累托宣称根据少
量数据已经发现了规律,库兹涅茨却对每一个数字满腹狐疑;
前者以贵族式特立独行的学者形象示人,后者却是一位典型的
教授。
根据上述稀疏的材料,库兹涅茨于1955年提出了现代收入
分配理论的主要框架,其地位至今依旧。这一假说认为,社会
在其发展早期以农业为主,因为大多数农民大抵仅能果腹,故
不平等程度很低。然后,随着工业的发展,人们开始往城市迁移。在那儿,一方面非农业领域的生产力水平和收入水平更
高,另一方面是其中有更多职业,而技能也更多元化,故而城
市里有更大的收入差别,不平等现象也就愈发严重。最后,随
着社会进一步发展,增加的财富使更多人可以接受教育,这减
少了过去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获得的额外好处。新增的财富
也使诸如社会保障、失业救济等阶级间的再分配成为可能。简
而言之,库兹涅茨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不平等呈现为
大的倒U形曲线,即从平等变为不平等,再从不平等回到平等。
这与帕累托收入分配的铁律截然不同。在帕累托看来,不
论社会发展与否,也无论是社会主义抑或资本主义,全无不
同。变化的只是不同的精英阶层,但分配格局如故。而在库兹
涅茨看来,不同发展阶段对应着不同的不平等水平。
谁的理论是正确的?帕累托的有一点点,库兹涅茨的稍微
更多一些。前者的方法中有价值的是,最高收入水平和相应的
人数的确表现出和帕累托“定律”相似的规律。这一数值可能
不会总是1.4或1.5,但是收入的“截断”效应相当清晰,屡试
不爽。然而,这仅适用于最富有的1%或至多2%。在其他情况
下,帕累托定律根本不存在。同时,显而易见的是,不平等与
国家和社会制度有关,且会随着时间改变。帕累托深信的一成
不变的收入分配并不存在。
那么,库兹涅茨的倒U形曲线又如何呢?关于它已有成百上
千的文章,支持和反对者几乎持平。在某一时点上,当绘出不
同收入水平国家对应的基尼系数值后,我们发现它看起来像某
种倒U形。但的确,只有竭力端详它才会如此,因为一眼望去它根本就是没有形状的散点图。尽管如此,仍然有人认为,这个
模糊的倒U形曲线是据拉丁美洲国家数据有意为之的产物,这些
国家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其严重的不平等更多是因为殖民历史
而不是出于库兹涅茨理论解释的原因。就是它们“制造”了驼 ......
作者:[塞尔]布兰科·米兰诺维奇
译者:李楠
ISBN:9787521708332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是查明规律,以见收入分配是如何
体现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政治经济学原理》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17年)
在对于公平合理的经济学有害的诸趋向之中,最具迷惑性
且……为害尤烈的,是偏注于分配问题。
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
《工业革命:过去与未来》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Past and Future )(2004
年)中文版序
鉴于在国内不平等和全球不平等的演进中,中国异乎寻常
的重要角色,这本针对这两类不平等的书对于中国读者可能尤
为有趣。
让我们先从后者说起。全球收入不平等是普天之下所有个
体间的不平等。我们从国内家庭调查得到相关数据,并根据国
家间的价格差异做出调整,由此,不论收入是来自贫穷国家、中等收入国家还是富裕国家,均以所谓国际元这同一单位表
示。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几乎占了全球人口的15,而且中国发
生的任何事情都将强烈地波及四方,因此中国在这样的计算中
显然至关重要。而结果是,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减少
了全球不平等,但另一方面,其国内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也加剧
了全球不平等。
这就将我们引向了国内不平等。在该问题上,由于过去非
同寻常的三十多年间,中国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15倍,而其由
基尼系数这一最常用的不平等测度表示的收入不平等也翻了一
番,因而中国的经验独一无二。由此,中国的发展不仅于世界
影响巨大,而且也对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人物提出了两
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即使包括最贫困者在内的所有人的收入都增加,就
社会而言,与之相伴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接
受的?鄙意以为,正如中国在1978年所为,若我们从非常低的
收入和不平等开始,则不平等和真实收入的增加显然是可取
的。并非所有人都可以一蹴而就地变富,所以若某些人先起
来,而其他人随后跟进,尤其是若向上流动的前景明朗,则这
样的发展就是受欢迎的。然而,若不平等的上升持续多年,则
在某一点之后社会就面临分崩离析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形下,少数人与大多数人的生活、行为和消费模式产生巨大差异,则
即使经济继续增长,不平等的进一步扩大在政治上都是不可持
续的。换言之,若相信高速增长将最终“弥补”上升的收入和
财富不平等,就太过天真了。问题是,中国是否已经处于这样
的状态?
其次,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间的不平等就是依循西蒙·库
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20世纪50年代揭示的模式在演化,即在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从农村向城市,以及从以国有制
为基础的经济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的转型中,不平等会上
升;然而,当国家“成熟”而变得富裕之后,不平等开始下
降。若中国要跟从库兹涅茨描绘的路径,则其上升的教育水平
应当减少其不同受教育程度工人间的工资差异,其老龄化人口
应当得到更多的退休金和失业救济这样的社会保障,以及甚至
更有效的卫生保健,这些再加上推展到农村人口的惠政,将遏
制不平等的进一步上升,并使其最终减少。基于库兹涅茨的观
点,中国目前可能将开始降低其收入不平等。在中国,有两股力量与库兹涅茨揭示的“无害的”减少不
平等的因素相对抗,即日渐攀升的财富不平等(进而资本利得
不断增加的重要性),以及腐败。在所有国家,资本收入分布
都极为不平等,其上升的部分几乎自动转化为更大的收入不平
等,中国也不例外。而腐败就是第二个负面力量。由于较之于
对穷人,腐败对富人更为有利,因而反腐看起来不仅是维护国
家政治稳定之必需,也是终止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之道。
最后,就中国在全球收入分配中的角色,我们或可多说一
二。20世纪80年代末,一个在中国农村具有平均收入的人比世
界人口中的20%更富裕,而今天,这一比例提高到了36%。至于
城市居民,相关数值则分别是50%和65%。由此,不论是居住在
中国农村还是城市,具有平均收入的人,其收入均超过大约
15%~16%的世界人口,即10亿人。这是巨大的成就。然而,若未
伴以诸如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刚果或埃塞俄比亚此类穷
国类似的高增长率,这也意味着中国未来的高增长率将增大全
球不平等,而不是减少不平等。于世界而言,中国基于其新获
得的财富,将成为不利于平等化的力量。虽然对中国来说,这
一发展确是好事,但这也突显了非洲和亚洲贫困国家的发展对
人类的未来至关重要,并且日渐富裕的中国亦应在减少全球贫
困和不平等问题上充分扮演其国际角色。序言
本书讲述了上下古今的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因为所有的
人类社会都伴随着权力与财富的差别,不平等紧随人类社会的
产生而出现。既然不平等是涉及“关系”的现象(relational
phenomenon,即只有存在别的个体,才能说一个人与之相比是
不平等的),那么从定义上说,不平等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现象
和观念,故而仅存在于社会之中。鲁宾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自己不会有平等的观念,但他和仆人“星期五”在一
起时就有。此外,当社会不是个体的机械汇聚,而是一群共享
着诸如政府、语言、宗教或历史记忆等特征的民众时,谈论不
平等就更为自然不过。
本书以故事铺陈,意在以一种独特而有趣的方式,呈现收
入与财富不平等如何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散
布于茶余饭后案头桌边的谈资或讨论里,而当我们以不同的视
角看待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时它又如何出现。我们的目标在于
揭示收入与财富、富裕与贫穷间的差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
要作用,及其在历史中的非常之处。
本书围绕三种类型的不平等展开。在第一部分,我讨论在
一个单一社群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国
内人际不平等。这种类型最易察知,因为当我们听到“不平
等”这个词时,很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这种不平等。在第二部分,我讨论国家或民族间的收入不平等。对于大多数人,这在
直观上亦非常切近,因为当我们旅行或观看国际新闻时会注意
到这类事情。一些国家大多数人看起来比我们穷,但在另一些
国家大多数人似乎非常富有。而当穷国的工人为了挣更多钱和
享受更高水平的生活移居富国时,这些国家间的不平等也体现
出来。在第三部分,我将话题转向近年来才开始引人注目的问
题上:全球不平等,或者说世界上所有公民间的不平等。这种
不平等是前两种不平等(即国内人际不平等和国家间不平等)
的总和,但却是一个崭新的话题,因为只有伴随着全球化,我
们才开始习惯对照和比较我们自己和世界上其他个体的命运。
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展开,在三种类型中,该类不平等的
重要性可能上升最多。
我以简短的故事(或曰“小品”,vignette)来说明每种类
型的不平等,其中一些小品将我们带回罗马时代,而另一些如
关于巴拉克·奥巴马家族、全球中产阶层或欧洲的马格里布移
民这样的话题,则大抵取自每天的报纸。每篇小品可单独阅
读,且不必按照顺序。然而,有时某些小品的话题互相关联,若依次阅读则更为有趣。但无论如何,它们均独立成篇。
就特定类型的不平等,每部分以散论(essay)开篇,概述
经济学家对此的观点。尽管散论意在能被所有感兴趣的读者理
解,然而与阅读小品相比,确须投入更多精力,因而可能稍具
挑战性。对于小品中讨论的问题,散论将有助于读者在技术上
有更好的理解。对于那些渴望更为深入探究本书问题的读者,散论也是一份文献导引。在该书结尾的“延伸阅读”中,我也列出了以散论和小品为序的精选读物书目,以供想要了解更多
的读者参阅。就每个给定的主题,我认为这些书籍和文章最为
有趣而切当。
对我个人而言,写作本书不仅愉悦,而且颇为轻松。在不
平等问题上研究了超过14世纪后,我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信息
和逸闻趣事,可谓俯拾皆是,故若与读者分享,我认为彼此都
会兴味盎然。动笔之时,我并未多想其内容或架构,而仅是把
我思虑经年且有现成数据的所有东西写下来而已。以个人视角
来看,也许最为重要的是,该书提供了机会,将我对数字和收
入分配的激情与对历史的激情结合起来。
我有三个目标,但正如所有作者一样,我不知道能否达成
其中任何一个。一方面,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故事时能轻松愉
快,并将之与对新事实的了解或者看待事物的新视角结合起
来。另一方面,由于诸多原因[其中一些是“客观”的,而另一
些则可能受制于有钱人(the rich)的利益],不平等问题大多
被置于公众视野之外,以避免使他们“不安”,故而我认为重
要的是第二个目标,即引起公众对财富与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关
注。而第三个目标,则是将财富和贫穷这一问题带入社会讨论
的中心,尤其当危机来临之际,可以激发某些传统的社会行
动。换言之,人们有权开始质疑某些收入的合理性,以及存在
于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内富人与穷人间、世界范围内富国
与穷国间的巨大差距。这是某些主导性的社会舆论制造者试图
弃而不顾的问题,但我认为,他们太草率了。他们认为全部或
几乎全部的不平等都由市场决定,故这类问题不应作为讨论的对象。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不平等取决于相对的政治权力
(全球金融危机就此展示的例子数不胜数),同时也不能通过
引入“市场”就将这类质疑从社会舞台上除去。市场经济是一
种社会构造,它被建立,更确切地说是被发现以服务于人类,因此在每一个社会中提出与其运行方式有关的问题是完全正当
的。
我要以一点技术说明来结束序言。读者阅读所及,会发现
该书包含了大量计算结果,其中所有未明确地以注释标示来源
的部分均为我个人未公开的工作成果。它们基于多种多样的数
据,但大多源于世界银行和“世界收入分配”数据库,其中包
含了来自大多数国家的诸多宏观数据和数百个家庭调查。若对
我计算的每一个数字都逐一列出来源,则过于单调乏味。如果
读者对于某个特定的事实或计算特别感兴趣,我很乐意提供准
确 线 索 , 你 们 可 通 过 电 子 邮 件 与 我 联 系
(bmilanovic@worldbank.org或branko_mi@yahoo.com)。对于
其余的源自其他作者及其出版物中的数据,该书均明确地指出
了资料来源。
我非常高兴在此感谢许多协助和支持我的人。因为该书从
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不平等这个主题超过20年的研究所得,我的
感谢名单不得不非常之长,包括几乎我遇见或受教的每一个
人。但愚钝如我,显然已力有不逮,故只能把范围缩小到那些
直接参与了写作此书的人。在每个小品或散论的开篇之处,我
感谢为之给予了意见、评论和建议的人士。除此之外,我还要
感谢编辑Tim Sullivan和Melissa Veronesi,他们搭建了这本书的结构;感谢Annette Wenda逐字逐句地认真校阅;感谢
Michele Alacevich和Valentina Kalk,我颇为倚重他们对于该
书实质上和审美趣味上的建议;感谢Gouthami Padam,他与我
共事超过7年;感谢陈少华在中国家庭调查上给予了不可估量的
帮助;感谢LeifWenar对政治哲学有关问题提出的建议,尤其是
对我时常参阅的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著作的解释,以
及 对 手 稿 诸 多 部 分 给 出 的 精 彩 评 注 ; 还 有 Slaheddine
Khenissi,感谢他关于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渊博学识。当
然,对该书中表达的观点,我一人承担责任。
布兰科·米兰诺维奇
1. 然而,对该断言须做如下说明:它适用于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即从定
耕农业(sedentary agriculture)出现之后。在人类历史超过90%的史前时
代,在其大多数时间里,据信人们依靠群居生活,而其中的平等几乎是绝对的
(见Ken Binmore,“The Origins of Fair Play,”Keynes Lecture 2006,The
Papers on Economics and Evolution ,No.0614,Jena:Max Planck
Institute,2006)。第一章散论一
不平等的人们:一国之内个体间的不平等
国民收入按职能分配是指总收入如何在社会的大阶级(即
工人和资本家)间分配,许多人认为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所
在。直到20世纪之交,个体收入不平等确实是被纳入这一主题
之下的。 19世纪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通常分为几个截然不
同的阶级:工人出卖劳动而获取工资,相对贫穷;资本家占有
资产并赚取利润,相对富有;地主拥有土地随之收取租金,也
堪殷实。一般认为,这三个阶级间的收入分配对决定社会的未
来至关重要。比如,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这一政治经济
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认为地主的收入份额将会增长,这是因
为随着人口增加,对食物的需求上升,进而会开始耕作那些越
来越不肥沃的土地,并最终使“工资品”(这里指食物)的价
格和地租飞涨。他将最终结果视为一种稳态,即受到同时上涨
的食物价格与地租的挤压,微薄的利润几乎无法激励储蓄和投
资。 又如,在马克思看来,随着工人人均资本增加,机械化
程度加深而资本回报降低,长此以往的趋势是利润率减少并最
终接近于零,从而扼杀投资。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被始于1870年左右的“边际革
命”取代,其焦点由社会各阶级宏大的经济演进转移至个体最
优化,这成为经济学史的关键转折点。随后,古典经济学与边际效用学派这两条研究路线在“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出自
剑桥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名义下融合并确立了其在
主流经济学中的地位。尽管如此,通过社会阶级的棱镜看待收
入分配并未由此改变太多。直到20世纪初,个体间而非阶级间
的收入分配问题才引起执教于瑞士洛桑大学的法国—意大利经
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关注(其贡献见小品1.9)。
大约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国家更加富裕,政府的财
政作用愈发广泛,而个人收入分配数据第一次开始有案可查。
此类信息的出现最初是因为民族国家需要了解收入信息以便征
更多的税,并用于公共教育、工伤以及战争这一最为重要的目
的。此外,意识形态的转变同样重要,即人们转而认识到在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故富人应根据他们更多的财产和收入做出更
大贡献。税收必须更紧密地与收入联系在一起,这就要求对收
入及其家庭分布情况更为了解。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帕累托
用于研究个体间收入分布的数据均来自欧洲19世纪后期的财政
统计。在那时,该书的主题就已经诞生了。
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以三种方式关注不平等。他们提出
的第一类问题包括:是什么决定了一国之内人与人之间的不平
等?随着社会发展,是否存在不平等以某种特定方式表现出来
的规律?不平等会随着经济扩张变得更严重吗?换言之,它是
顺周期性的还是逆周期性的?在这些问题中,不平等是应当得
到解释的因变量。在第二类问题中,不平等是用来解释其他经
济现象的自变量。比如,对于经济增长、更好的治理、吸引外
资或教育普及等,是高还是低的不平等更为有利?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在纯工具意义上审视不平等,即我们感兴趣的是其究
竟促进还是阻碍了某种我们期望的经济结果。不平等进入社会
科学家视野的第三种方式是他们探讨与之相联系的伦理问题。
这时,他们关注的是呈现不同程度不平等的社会制度(social
arrangement)正义与否,比如,是否只有当更严重的不平等增
加了穷人的绝对收入时,前者才可被接受?又如,对源于优越
家庭环境的不平等与源于出色工作和努力的不平等,我们应区
别对待吗?
不平等如何随着社会收入水平变化 ?基于对19世纪末欧洲
国家和城市税收数据少量样本的研究,帕累托坚信“人际不平
等的铁律”,因而即使社会制度有异,但无论是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分配格局均大抵不变。换言
之,社会精英或许不同,他们掌控社会的方式亦可能有别,但
收入分配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平等水平将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如
今,这个规律被普遍称作“二八定律”,即在某些现象中我们
观察到20%的人占有80%的产出;相反,其余80%的人却只占有
20%的产出。比如有人认为,二八定律存在于质量控制(即80%
的问题源于20%的产品)、市场营销和商业应用中,而我们在全
球收入分配问题上甚至也可看到类似规律(见散论三)。至于
国内收入分配,恰恰由于帕累托深信经验已证明其一定是大致
固定的,并无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的法则,故他并未建立
关于其变化的理论,因此称之为“失败”并不完全恰当。在帕
累托看来,唯一的法则就是“收入分配固定”(law of its
fixity)。直到1955年,俄裔美籍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西蒙·库兹涅
茨才提出第一个真正的理论以解释是什么促使收入分配产生变
化(小品1.10是对其和帕累托的传略)。根据比帕累托略为丰
富的数据(虽然数据种类不同:库兹涅茨使用的是家庭调查,而非财政调查),他认为在不同的社会中,人际的不平等并不
相同,且随着社会发展它将以可预见的方式变化。在极度贫穷
的社会,因为大多数人的收入都只在温饱线上下,人与人之间
几乎不存在经济差距,从而不平等程度一定很低。然后,随着
经济发展以及人类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库兹涅茨断
言,相对富裕的产业工人和相对贫穷的农民的平均收入出现差
距。而与农民相比,由于现代工业对工作的要求更为多样化,工人间的收入差距也更大。因此,在这两种不断扩大的收入差
距作用下,收入不平等增加。最终,在更发达的社会,国家开
始扮演再分配的角色(见小品1.6),教育更为普及,不平等亦
随之下降(见小品1.1和小品1.2)。由此,我们得到著名
的“库兹涅茨假说”,其中的倒U形曲线描绘了收入不平等随经
济发展的变化,即不平等一定是先上升,后下降。
然而,这一观点并不是全新的。在库兹涅茨假说问世前约
120年,法国社会科学家、政治家托克维尔已提出类似看法,值
得在此全文引述:
如果仔细观察这个世界自社会出现之后发生了什么,我
们很容易发现,就历史维度而言,平等仅在文明的两极才普
遍存在。野蛮人是平等的,因为他们同样羸弱无知,而非常
文明的人亦可达致平等,因为他们都在其支配范围内用相似的方法得享安康幸福。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境况、财
富和知识的不平等,少数人拥有权力,但其余的人穷困、愚
昧而孱弱。[《济贫法报告》(Memoir on Pauperism
,1835)]
当然,托克维尔并不是库兹涅茨那样的经济学家。除了这
些,他并没有更多的言说,尤其是关于倒U形曲线成立的机制。
库兹涅茨假说自1955年首次发表以来,被经济学家一再检
验。全国性的家庭收入和消费调查本是收入分配信息的关键来
源,随着其日渐唾手可得,关于库兹涅茨假说的实证研究大大
推进了。理论上,当我们研究单一国家内不平等的演变时,随
着其经济经历从农业到工业,并最终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剧变,原则上,该假说应体现得最好。但在此情形下,其表现却模棱
两可,一些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呈现倒U形的发展模式,而其
他国家却没有。
出于对库兹涅茨假说的表现和预测能力不满,人们在其中
加入了新的要素,使它能够更好地解释收入不平等的变化。修
正后的理论被称为“扩展的库兹涅茨假说”。诸如经济体
的“金融深度”、政府支出范围、国有部门就业水平及经济的
开放程度等因素如今也与收入水平一道作为可能的额外变量,用于解释不平等的变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些额外的变量
能够增进我们对不平等变动的理解。例如,这里的基本原理包
括:就金融深度而言,一个更高效而广泛的金融部门将允许穷
人借款支付自己的教育费用,是以教育的大门将向所有人敞
开,而不再仅为富人保留,不平等将随之减少。就政府支出范围和国有部门就业水平而言,作为GDP(国内生产总值)一部分
的政府开支和作为总劳动力一部分的政府就业都应该对不平等
有削弱的作用,因其不仅帮助了穷人,也限制了工资不平等。
就经济的开放程度而言,在贫穷国家,更大程度的开放贸易将
增加对低技术密集型产品(比如纺织品)的需求,而这类产品
恰恰是这些国家擅长的,故相对于熟练工人的工资或资本家的
利润,这将倾向于提高不熟练工人的工资,并最终减少不平
等。在富有国家,因其倾向于出口高科技产品,开放贸易会产
生相反的影响。事实上,这些产品需要高技能的人才(比如计
算机科学家或工程师),是以大学毕业生的工资较之于只有小
学或中学学历的人而言相对增加,故不平等扩大。现在,在收
入之外,经济学家在检验典型的库兹涅茨假说时还包括所有这
些因素,而且可能也常以便宜行事的方式纳入其他一些考量
(比如人口结构或土地所有权的分布)。结果比我们仅使用收
入水平时要好,但也谈不上多么精彩。
最近,在与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安东尼·
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及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等同行合作之下,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
(Thomas Piketty)进行了一系列覆盖十几个国家的实证研
究,否定了库兹涅茨假说及其扩展版本。皮凯蒂的研究表明,在过去14世纪里,西方国家的不平等在经历了长期下降后决然
上升。在他看来,政府会增加或减少对当前收入与遗产的直接
税,而战争会毁灭有形资本,降低资本家收入,这些影响为之
前众所周知的事实提供了某种“政治”解释。由此,这或可视
为收入分配的政治理论,在其中以何谓公正何谓不公正这样的人心归向,以及以选举、政党立场和经济的战争需要等反映的
经济利益,决定了不平等随时间变化的轨迹。
为了解释整个20世纪这样长的时期中推动不平等变化的原
因,皮凯蒂的研究诉诸财政统计这一古老而几乎已被遗弃的数
据来源。这一统计首次为帕累托所用,后来被家庭调查取代,这是因为穷人在大多数国家都不支付直接税,故财政统计只涵
盖了收入分配的高端部分。与之相反,家庭调查则囊括了所有
人。使用财政数据的问题在于,若要从中得出有效的结论,以
下两个假设必须成立:一、应税收入是家庭实际收入的良好近
似(且纳税最多的人也是最富有的人);二、总体不平等的变
动与最高收入群体收入份额的变化相当近似(比如,我们相信
纳税前1%的人亦是家庭财富排在前1%的人)。但是,两个假设
都很难完全站得住脚。就假设一来说,皮凯蒂及其合作者使用
的应税收入是“市场”[或曰“财政前”(pre-fisc)]收入,它排除了税收和政府的转移支付。 然而,我们通常感兴趣的
是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即在完税和收到政府转移支付后的家
庭和个人收入。因此,无论是税收还是转移支付改变,市场收
入的不平等和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都有可能会背道而驰。假设
二的问题在于,原则上,对不平等的统计应包括所有人的收
入,而不仅关注富人。比如,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形,若我们牺
牲中产阶层的份额,就可使最高收入群体和最低收入群体的收
入份额都上升。我们虽会倾向于单纯从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份
额上升得出结论,但在这里却不能说总的不平等增加了。皮凯
蒂等人的研究建立在这些特定假设之上,但这些假设并非放之
四海而皆准,因而对其研究结论的解释也大可存疑。当然,如果有过去足够长时间内的收入和消费调查,我们就不用依靠这
个支离破碎且很不准确的财政数据,问题也随之解决。不幸的
是,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在发达国家,这种调查通常在
二战之后才开始,而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这只是过去二三十
年间的事。
这就是不平等研究的现状。想要在这些不同观点中就哪一
个已经赢得了这场辩论做出结论,是不公平甚至是不可能的。
也许一个都没有。然而,在测量不平等或理解它是如何演变之
外,这一研究的确将我们引向问题的核心,即对于经济增长,不平等是否必要?如果是,它又应该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不平等如何影响经济效率 ?我们关注不平等,或者说我们
最关注不平等,是因为我们相信它影响一些重要的经济现象,尤其是经济增长,即不平等程度更大的国家增长更快还是更
慢?回顾历史,答案的钟摆已经从毫不含糊地认为不平等有利
于经济增长,转向有利于相反主张的更为细致的观点。
为何会有这样的改变?为便于理解,当我们关注经济效率
时,可将不平等视为胆固醇:有“好”与“坏”的不平等,正
如有好与坏的胆固醇。 人们需要“好”的不平等来激励其好
好学习、努力工作或创办有风险的企业项目。没有不平等作为
回报,这些情况都不会发生。但是“坏”的不平等始于一个不
易定义的点,在那之后人们不再有追求卓越的动力,转而靠不
平等提供的手段,维护已有的地位。当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用
来阻碍如农业改革或废除奴隶制这样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治变
革,或只允许富人得到教育,或确保富人占有最好的工作时,这种“坏”的不平等就会显现。所有这些都会削弱经济效率。
如果一个人接受好的教育的能力强烈受制于其父母的财富,这
就等于剥夺了这个社会大部分成员(在这里也就是穷人)的技
能和知识。在这个意义上,基于收入继承造成的歧视与诸如性
别或种族等其他任何歧视并无二致。在所有这些情形中,社会
中某一群人的技能被弃置,故而从经济上看,这样的社会不太
可能成功。因此,在特定的国家和时代,不平等既可是有利
的,亦可是有害的,这取决于居主导地位的是提供激励的“积
极”不平等,还是确保富人垄断地位的“消极”不平等。
当经济学家相信只有富翁才会积蓄,舍此即无投资和财富
创造时,对于经济不平等,占主导地位的是仁慈的眼光,以为
其将激励个人追求卓越。因为人们认为工人(或穷人)倾向于
花光所有,故若每个人拥有相同(相对而言)的低收入,则社
会就没有存蓄,没有投资,也没有经济增长。富人本身不重
要,重要的是其存在,如此他们才会积蓄,才会扩充资本,并
以种种手段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在个人储蓄中,富人被视为
存钱罐,在花费和享乐上不比常人,而超出部分则尽数用于积
攒和投资。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苦行主义是“资本主义精
神”的关键成分:“这种伦理追求的至善,是要尽可能地多挣
钱,同时力避一切本能的生活享乐。其最突出的是完全不掺杂
任何……享乐主义的成分。它被十分单纯地视为目的本身,以
致从个体的幸福或功利角度来看,显得完全……不合常理。”
在高收入被用于投资的前提下,对于此类为收入不平等辩
护的稍显理想化的看法,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1920年的文章中做出了或
许是最好的表达:
(1914年前的欧洲)社会将很大一部分增加的收入交到
了最不可能将其用于消费的阶级手中。19世纪的新贵在其成
长过程中并不习惯纸醉金迷。较之于即期消费的快感,他们
更享受投资带来的权力。事实上,恰恰是财富分配的“不平
等”使购置资产、改良设备这样的巨大积累成为可能,从而
使这个时代与其他时代区分开来。实际上,这正是资本主义
制度存在的最主要理由。若富人将其新财富都用于自我享
乐,则世人早就会无法忍受这样的统治。然而,前者像蜜蜂
一样储蓄和积累财富。此虽出于狭隘的个人目的,却没有减
少其对整个社会的贡献。
这是视资本家为“储蓄机器”和企业家的观点。
但是,世界上还大量存在着另一种资本主义食利者,除了
坐着让钱为其“工作”外,他们大抵是袖手旁观、逍遥自在,而在斯蒂芬·茨威格关于《昨日的世界》(The World of
Yesterday )(即一战前的欧洲)的佳作中,我们能找到对资
本主义食利者的文学描绘。在那个世界里,如茨威格所言,最
珍贵的赞美是“扎扎实实”,而身居高位者看重资产阶级的尊
严,社会的理性与昌明也似乎注定会绵延不绝。对富人来说,生活容易:于有钱人而言,由变利为本的不断累积而使自己富起
来,在那日益繁荣的时代只不过是保守的生财之道罢了,因
为即使是对最富有的人,政府也从未想过对其征收超过百分
之几的税……而国债和工业债券利率很高。
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存钱罐”和可能的投资者这样的角
色,富人看起来不太像是不可或缺的,他们更像是活得有滋有
味的寄生虫,除了撕撕息票,别的几乎什么都不做。然
而,“不平等是有害的”这一在过去几十年间开始占据主导地
位的观点,并非出自伦理道德的考虑。与视不平等为慈惠的力
量一样,它也认为应该有人愿意投资,但奇怪的是,同样的出
发点却导致截然不同的结论。在这种观点看来, 政府支出的
资金来源于税收,而从中获得的好处主要有利于穷人。当富
人、中产阶级和穷人投票决定缴多高的税时,非常不平等的社
会倾向于把票投给高税收,这仅仅是因为有很多人可以从政府
转移支付中获益,却缴很少的税或根本不缴税,故在票数上穷
人总能胜过为数不多的富人(见小品1.7)。然而,高税收减少
了对投资和努力工作的激励,经济增长率也随之降低。这一机
制类似于19世纪时的恐慌,即没有财产的人只要有投票权,就
必然会剥夺富人的财富。现在,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只是剥
夺得稍显温和,换言之,它不是依靠国有化,而是依靠税收。
无论认为经济不平等有利还是有害,最重要的是要有人愿
意投资。但若持第一种观点,富裕的投资者会要求高度的社会
不平等;若持第二种观点,则引入政治上的民主就会破坏高度
的不平等,使其在政治上难以为继。即使富人能设法向穷人承诺他们会将过剩的收入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继而对经济增长
而言他们不可或缺,但该承诺却无法被强制执行,故也是不可
信的。因而,一定得在可持续且不鼓励人们选择敲诈性税率的
税前收入分配之上,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持续运转。为此,人与
人之间的资产须相对均等地分布。在短期或中期内,我们不太
能够影响金融资产的分配,却可以影响教育(经济学家称其
为“人力资本”)的分配,因而重点在于每个人都能更容易地
接受教育。这不仅是因为教育本身是可取的,甚至也不是因为
教育程度高能直接有助于经济增长,还在于人力资本更广泛的
分布将使税前收入分配更为平均,并使相对贫穷的人在把选票
投给高税收之前能够三思。
经济发展会改变我们对不平等的看法吗?很有可能。 在
经济发展早期,物质资本稀缺,故而重要的是富人并不打算把
全部收入用于消费,而是投资,建造更多的机器和道路。随着
经济发展,物质资本不再那么稀缺,与之相比,人力资本(即
教育)的价值上升,于是普及教育变得尤为关键。但如果贫困
家庭有天赋的孩子支付不起教育费用,进而教育普及受到限
制,就将减缓经济增长。因此,即使在没有引入普选权和民主
的情况下,我们也有类似结论,即在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要
想加快经济增长,则必须普及教育,而这无异于减少不平等。
在实证研究中,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毁誉参半,这大
概是不可避免的。在某些国家和时代,不平等会通过其垄断作
用阻碍经济发展,而在另外的情形下则会通过其激励作用而有
助于经济发展。总之,我们关于不平等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积极与否的看法,总是取决于在社会垄断与激励的两难上,我们如
何赋予权重。当我们相信富人运用垄断的权力和财富威胁社会
稳定、经济发展甚至国家存亡时,正如2400年前柏拉图所为,我们将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为社会毒瘤而与之斗争。当被问
到若将节制作为其理想国应该具有的特征,是否会使其面对被
富裕邻国吞并的危险时,据柏拉图描述,苏格拉底是这样应对
的:
“但我们应该怎样称呼别的(不是理想国的)社
会?”他问道。
“我们应该为它们拟一个更堂皇的名字。正如谚语所
云,它们中的每一个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组国家
的集合,因为它总是包含至少两个国家,一个富,一个穷,互相敌视……把它们视为多个国家,将一部分人的财产……
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你的盟友就很多,敌人就很
少。”苏格拉底回答。
相反,收入的均等化意味着人们从成功中得不到胡萝卜,在失败时也可免于大棒。在某些情形中,若收入过分均等,人
们就不会太努力,除非让其更充分地占有自己劳动或投资的成
果。最终,虽然看起来有些让人难以接受,我们就只能转而期
待更大的不平等。
不平等与经济正义 。收入不平等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它
关乎经济效率和经济正义。于大众而言,二者常利害攸关,却时相龃龉。经济效率解决的是社会总产出最大化或其经济增长
率问题,而经济正义解决的是对既定社会制度是否认同和其是
否可持续的问题,对此经济不平等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基于
遗产、种族或性别的不平等,即使无害于经济发展,人们可能
依然认为是不公的,换言之,这一判断超越了不平等纯粹的工
具价值。若大多数人或有影响力的少部分人视某种社会秩序不
公,则该制度是否可持续就大为可疑。
在评价不同社会制度的合意程度时,经济学家常常构
建“社会福利函数”(social welfare function),其在理论
上包括一个社会所有成员的福祉(即效用)。这样做的目的是
要将一个社会制度下所有成员的福祉与另一个社会制度下的比
较,并找出其中较好的。这就是所谓的“福利主义”,而其粗
略的做法就是将个人效用加总。比如,在一个由艾伦、鲍勃和
查理三人组成的社会里,社会总效用就等于艾伦的效用加鲍勃
的效用再加查理的效用。在每个人的效用函数中,一个合理且
被经验证明的假设是,虽然每额外增加1美元收入带来的效用都
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却递减。想想看,在炎炎夏日,第一杯冰
激凌带给你的喜悦会大于第二杯,且定然大于第三杯,此观点
符合收入边际效用递减这一普遍规律。现在,我们更进一步假
设艾伦、鲍勃和查理的效用函数相同,则完全平等的收入分配
是最优的。事实上,较之于鲍勃和查理,若我们给予艾伦更多
的收入,那么因为他们具有递减且相同的边际效用函数,我们
马上看到,这额外的收入带给富有的艾伦的愉悦比带给贫穷的
鲍勃和查理的愉悦少。因此,如果我们将艾伦的额外收入转移
给另外两人,直至三人收入相等,则总效用会增加。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1970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如
何测量不平等的颇有影响力的文章,它也可以让我们对不同社
会制度的合意程度进行排序。就经济学而言,那篇论文是对福
利主义方法的关键贡献,而这一贡献背后正是上述原理。 阿
特金森发明的测度是考虑到相同的社会福利可由更小但完全平
均分配的社会总收入来实现,由此从福利的视角来看,社会不
平等可用总收入中被“浪费”的相对量计算。上述假想的总收
入在某种程度上被称作“平均分配的等价收入”(equally
distributed equivalent income)。形象地说,即使是一张小
饼,若切开的每一块有同样的尺寸,则较之于一张分割不均的
大饼,每人享用一块之后会带来同样的总愉悦。比如,如果古
巴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居民生产的福利总量相等,但多米尼加
的收入总量更高,则从效用的观点看,多米尼加超出的收入是
完全浪费了。换言之,多米尼加人可以不要这笔额外收入,工
作不那么努力,只要重新将更少的收入像古巴人一样更平均地
分配就行。最终,总福利并没有损失。这样看来,有多少收入
被“浪费”了可被视为不平等的一种测度。
显然,如果存在某种方式可以累加不同个体的效用,那么
是古巴人还是多米尼加人的总体状态更好也就显而易见。但问
题是,没有一种严谨的可以被普遍接受的方式可以加总个体效
用。大体上,我们可以认为随着对任意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增
加,所有人都会经历边际效用递减,但因为一个人的效用水平
可能始终高于另一个人,故我们无法比较这些效用的“量”。
换言之,尽管效用函数的形状可能是相似的,即效用随收入增
加而增加,但其大小却因人而异。回到我们的例子,即使鲍勃告诉我们他生活在极乐世界,我们也不能确定他就真的比脾气
暴躁的查理更幸福:他们可能只是使用了不同的效用尺度而
已。
此外,即使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确切效用并继而能在理论上
最大化社会福利,但仍然存在伦理问题。这是因为在使总福利
达到最大的分配方式中,收入被主要给了拥有较高效用函数的
人,他们擅长将给定收入转换为更多的效用,而这正是英国经
济学家弗朗西斯·埃奇沃思(Francis Edgeworth)在19世纪末
用来捍卫不平等的观点。他认为有更“优雅”品味的富人值得
拥有更高的收入,因为他们从诸如美食醇醪一类中获得了更多
乐趣。然而,真的应该将社会中的大多数收入转移给那些最擅
长享受的人吗?最佳的收入分配方式难道是仅靠面包维生的人
去资助少许几个离不开香槟和鱼子酱的奢靡之辈?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的“可行能力方
法”(capability approach),是对福利主义颇有影响力的批
评,而其正是基于这样的困惑。如果仅仅因为残疾人不能与正
常人一样从足球比赛中为自己故而为社会“生产”一样多的效
用,我们就应该给前者愈来愈少和后者愈来愈多的机会吗?以
常理观之,这是一个令人厌恶的结论。与此不同,森认为我们
应该努力让每个人的“可行能力”相等,以使他们得其所哉。
简言之,当以福利作为判断标准对不同的社会制度排序
时,我们面临三种选择。第一,我们将每个人的效用函数视为
相同(虽然知道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那么收入完全均等时总福利达到最大,这就是阿特金森“平均分配的等价收入”背
后的想法。第二,我们可以试图找出更“有效”的效用生产
者,给他们更高的收入。第三,反过来,如森的可行能力方
法,将高收入恰恰给那些更难从给定的产品和服务中享受快乐
的人。这势必减少通过个人效用的某种简单加总得到的总福
利,而我们因此也不再用福利主义作为判断的基础。
一个更为复杂的福利主义方法是构造一个社会福利函数,在其中并无效用总和,包含的仅是每个个体的效用,是对每个
人福利状态的描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至少有一个
人境况变好而没有人境况变糟的“世态”(states of the
world)是更好的。这样的世态转变满足所谓的帕累托准则
(Pareto criterion),故若我们置身其中,可以确信没有人
会抱怨。但问题是,这样的条件不仅极为保守,更严重的是,在现实世界中几无可能实现。想想任何可能满足帕累托准则的
事:对大多数人而言,更好的卫生保健不是皆大欢喜吗?是
的,但一些人不得不付出更多保费,故他们会反对。一个几乎
可谓奇迹的制止消费成瘾性药物的决定不是对很多人堪称良法
吗?是的,但是毒品生产商和贸易商将遭受损失,故他们会反
对,而与其他人一样,他们也是人,我们也得考虑其减少的效
用。难道你不喜欢缴更低的税吗?是的,但是一些人将由此不
能得到社会保障,故他们会否决相关法案。例子不胜枚举。不
管多么努力,我们可能都找不到满足帕累托准则的政策。究其
实质,这一准则开出的药方意味着静止、停滞、无所作为,而
最重要的是让权势维持现状。因此,较之于粗糙的福利主义,精致的福利主义的缺陷也
有很多,两者都无法比较人际效用,以致在对各种社会制度进
行排序之时,其作用极为有限。 实际上,以效用主义或福利
主义为基础构造关于社会制度的正义理论殊非易事。效用主义
之父边沁(Jeremy Bentham)和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
伟大抱负是用“客观的”方式比较业已发现的不同社会,但该
梦想或许已然破灭。
在这样的废墟上,就如何调和经济不平等与正义,美国当
代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着力尤著。在其1971年出版的《正
义 论 》 中 , 他 清 晰 地 阐 明 了 其 著 名 的 “ 差 别 原
则”(difference principle)。罗尔斯认为,除非是为了提
高最贫困的人的绝对收入,任何对平等的背离都是不合理的。
换言之,比较的基准是公民间经济上的完全平等,对此不论何
种违背都需要正当理由。由此,罗尔斯的《正义论》完全摒弃
了效用主义。他毫不含糊地声称:
理性的人不会仅仅因为某种基本社会结构(basic
sturcture)最大限度地增加了其利益的代数和就接受它,而罔顾该结构对其基本权利和利益的长远影响。因此,效用
原则与平等的人之间为了互利而进行社会合作这一思想相矛
盾,看起来也不符合良序(well-ordered)社会这一概念隐
含的互惠观念。
罗尔斯用一句话非常巧妙地将不平等与不公正联系起来。
在他看来,“不公正完全就是不利于所有人的不平等”“尤其是对穷人”。 虽然不平等和不公正由此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
起,又因为许多赋予富人以特权的社会制度并没有使穷人获
得“绝对”利益,故罗尔斯认为运用他的“差别原则”会使收
入分布相对狭窄。然而,在理论上“差别原则”与高高低低的
不平等都是兼容的。若在提高穷人的收入时并不需要增加富人
的收入,则“差别原则”意味着相当严格的平等。但即使富人
不成比例地获得了额外的好处,只要穷人的收入有一点微不足
道的增长,“差别原则”也能容许很高且不断扩大的不平等。
不平等的测量 。与经济不平等相关的另一领域是对其的测
量。虽相当间接,但经济学家对效用主义的迷恋也已影响及
此。对经济不平等的测量始于以公理为基础的简单工作,即设
计一个合理的标尺,再借此将整个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概括为一
个数字。这些关键的公理并不难理解。例如,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若将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则不平等的测度下
降; 又如,若两个人交换位置,则测度不变(此所谓“匿名
原则”);再如,若所有的收入都乘以一个常数,则测度不
变;等等。 因此,与对温度的测量无异,对不平等的测量纯
属技术问题。但在占主导地位的福利主义方法看来,这些测度
表达了某种更深层次的以社会福利为基础的观点。然而,福利
主义的困境显而易见。举例而言,若我们考虑刚才定义的乍看
起来非常合理的匿名原则,为了用福利主义表达这一简单的技
术要求,我们必须接受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主张,即所有个体
的效用函数相同。若他们的效用函数不同,那么从效用产生的
角度看,任意两个人就不可能一样。换言之,如果某人是一台生成效用的高速机器,则其不可能被一个无精打采的“在生成
效用上力不从心”(utility-challenged)的人轻易取代。
从一开始,以公理为基础对不平等的测量与其福利主义阐
释间的矛盾就非常明显。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意大利经济学家
和统计学家科拉多·基尼开发了被普遍接受的对不平等的测度
方法。而早在1921年,他已表达了这一困境:
意大利(反福利主义)学者的方法……不能……与(在
主张福利主义方法中居功至伟的英国经济学家)道尔顿
(Dalton)的方法媲美……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估算经济福
利的不平等,而是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却罔顾这些数量与
经济福利间函数关系的所有假设,或个体经济福利的可加
性。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福利主义方法在经济学家中似乎颇有
市场,但近来却渐渐消隐。这一方面是因为它未能得出有力且
可行的结论,比如回答“什么样的状态更好”,另一方面是因
为作为其根基的效用主义在哲学上站不住脚。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测量不平等。就此,我们
须对家庭进行有代表性的随机抽样调查,参与调查的每个人都
要提供详细收入信息,又因为调查被视为代表着更广泛的群体
(通常是整个国家),故其结果应能外推至全国。我们也会使
用税收数据。但即使是在大多数人都缴纳直接税的非常发达的
国家,因为这些数据遗漏了未缴税的穷人,故也总是给我们不
完整的(或称“截尾”了的)分布信息。我们也不能使用人口普查,因为原则上该普查覆盖整个国家的人口,范围太大,以
至于不能非常深入详尽。事实上,人口普查只收集如年龄、种
族、性别、居住地等基本信息,却不涉及收入或消费。
然而,对大多数发达国家而言,家庭调查存在的问题在于
其最早也仅仅始于二战之后。在19世纪的英格兰,以及20世纪
早期的美国和苏联,有一些不完整的调查,但大致而言,对于
20世纪50年代初之前的数据,我们从中几乎不能得出任何严谨
可用的东西。(你可能还没忘记帕累托的猜测是基于财政数据
的,而即使迟至1955年,库兹涅茨也没有几个可供凭借的调
查。)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更糟,以至于20世纪70年代甚至80年代
之前,很多时候它们根本没有数据。尤其是非洲国家的家庭调
查从80年代才开始,且常常是在国际组织的协助之下。 世界
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又如何呢?在印度,全面的调查始于
1952年,并按照大抵相同的框架延续至今。在中国,现有的第
一次调查始于1978年,但最早可用的调查只能追溯到1980年。
此外,不是所有国家都每年开展调查,一些国家的调查仅每两
年一次,其他国家甚至频率更低,比如五年一次。这一切意味
着什么呢?首先,除了发达富裕的经济体,我们发现很难得到
基于家庭调查的一系列关于不平等的年度统计。其次,对大多
数国家而言,得从20世纪60年代,甚至七八十年代之后,我们
才能多少讨论其不平等问题,而且即便如此,也尚有很大的年
度数据缺口。家庭调查收集很多数据,但我们感兴趣的是其有关收入和
消费的部分。在这类调查中,每个家庭被视为一个收入或消费
单位,而家庭中的所有成员则被视为平均地分享收入或消费。
那该如何确定一个家庭成员的真实收入呢?我们将家庭中每个
成员的年收入加总,得到家庭总的年收入,然后将其除以这一
年居住在这个家庭中的人数,就可以得到家庭人均收入。这是
一个重要概念,因为其大小可以让我们对家庭和个人做出排
名,以决定孰穷孰富。
为什么我们坚持使用“人均”的测度呢?有哲学和实践两
方面的缘由。在哲学上,我们应该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若我们
平等对待每个家庭,那么大家庭中每个成员的价值就远小于小
家庭的成员。若每户的权重(即计算中被赋予的重要性)为1,那么在四口之家中每个个体隐含的权重为14,但在两口之家中
却是12。而在实践中,基于家庭整体而非人均收入的不平等测
度容易产生误导。理由很简单。考虑总收入相同的两个家庭,其中一个有2人,另一个有10人。你认为哪个家庭更富裕呢?答
案显而易见。
即使我们得到的是消费数据,为简化起见,我们通常谈论
的仍是收入分配。然而,收入和消费是不等价的。在一组给定
的家庭中,基于收入的数据几乎总比基于消费的数据呈现更大
的不平等。简单的原因有二。首先,可能有些人年度收入为
零,于是可用过去的储蓄支付目前的消费,这只要想想那些用
工作时攒下来的钱读书的学生就知道。但显然,没有人的年度
消费会为零,故消费分配将会在维持生计所需的最低点被截断。相反,收入分配的底部更长,也由此更加不平等。其次,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分配的另一端。许多高收入的人储蓄一部
分收入,故其收入大于消费,而收入的顶端也将比消费的顶端
更长。最终,当我们用收入而不是消费作为衡量标准时,测得
的不平等就会更大。
一旦有了家庭收入数据,我们该怎样度量不平等呢?这个
问题并不简单。作为对比,让我们先看看国民收入或GDP的测
量。GDP只是将一年之中居住在一国内所有人的收入相加,这包
括全部的工资、利润和利息等。最后,我们得到一个总数,将
之除以这个国家的居民数,就计算出人均GDP。
但收入分配由许多人的收入构成。我们不打算只简单将其
相加,而是得把这些收入相互比较,并进一步将这诸多比较表
达为一个数字,以很好地反映分配差异。这正是困难所在。任
何代表诸如1、5、15、2 009和34 564此类收入差异的单个数字
都有几分武断。比如,我们可以用最大和最小数字之比(34
564除以1)描绘不平等,但这将遗漏在它们中间的所有信息。
事实上,虽有同样的比,但我们难道不觉得例如1、400、620、1 009和34 564这样的分配更平等吗?我们也可以仅考察顶层收
入者所占收入份额来衡量不平等: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将34
564除以所有收入的总和(1+5+15+2 009+34 564或1+400+620+1
009+34 564), 而这正是用最高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衡量不
平等的方法。实际上,可选的方法不可计数。
一个减少备选项的方法是要求对不平等的测度应当利用给
定收入分配中所有人的收入信息,这意味着上例中从1和5直到其最大值34 564的所有信息都应被考虑在内。满足这一要求的
方法之中,到目前为止,以科拉多·基尼命名的基尼系数最为
通行。这位意大利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生活的时代与帕累托有
部分重叠。 在1914年他定义了该系数,即将每个人的收入与
其他所有人的收入逐一相较,而所有双向收入差距的绝对值之
和依次被除以包含在这一计算内的人口总数及该群体的总收
入,最后再除以2,而其最终的结果处于0(表示所有个体的收
入相同,没有不平等)和1(表示群体的所有收入都归一人所
有)之间。 这一特点大可称便。事实上,该系数“有上
界”,而1就是可能的最大不平等。据此,我们有了一个可靠而
确为有用的方式来比较不平等程度。
基尼系数为0或1都不现实: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收入完全平
等,也没有哪个国家是一人占有所有收入而所有其他人皆死于
饥饿。现实生活中,在如北欧诸国、中欧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
伐克这样最平等的国家,基尼系数大抵处于0.25至0.3之间;而
在最不平等的国家,如巴西和南非,该系数可达到0.6。
美国处于什么范围呢?在发达国家中,它是最不平等的。
尽管大多数欧盟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30与0.35之间(但就其整
体水平,可见小品3.3),但美国基尼数却高于0.40。不过,美
国的情况并非一直如此。随着基尼系数在20世纪70年代末滑落
至约0.35,美国的不平等降到了其历史最低点。 从那之后,在奥巴马前的四任总统期间(即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
什),美国的基尼系数持续上升,直至当前水平。增幅之大,每个亲历其间的人都清楚。因为基尼系数是一种变化迟缓的测度,即使一年增加一至两个百分点都非比寻常。如果不平等没
有持续地上升或下降,基尼系数每年上下波动的幅度往往都在
一个百分点之内。
其他国家的情况又如何呢?瑞典的平等众所周知,其基尼
系数在0.30左右;俄罗斯转轨之后又受寡头的困扰,其基尼系
数超过0.40。中国也是如此。与美国相仿,这两个国家的不平
等在过去20年间急剧上升。拉丁美洲很少有国家的基尼系数低
于0.50,非洲亦然。亚洲的不平等虽普遍存在,却不尽一致。
日本、韩国和中国似乎更平等一些,而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基
尼系数与拉丁美洲的水平相当。如果我们按区域内各国间的不
平等程度将各地区排序的话,位列第一的是拉丁美洲,紧接着
是非洲和亚洲,而不平等程度最低的是富裕国家和转轨经济
体,但值得关注的例外是若干不平等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以
及美国和俄罗斯。
然而,从另一个不同角度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欧盟、俄罗斯与中国这四个巨大的经济体都呈现出几乎相同程度的不
平等,即它们的基尼系数都处于0.40附近或者略高,这多少有
些令人讶异。小品3.3将考察前两者的异同,小品1.4和小品1.7
将审视俄罗斯的收入分配,而小品1.8将讨论中国的现状与未
来。
最后,我们可以分解基尼系数,以找出区域内各组成部分
之间(称为“组间”)平均收入差异所致的不平等与该区域各
组成部分内部(即“组内”)个人收入差异所致的不平等。比
如,当观察欧盟与西班牙和法国这样的成员国,美国与缅因和俄勒冈这样的州,又如中国这样的国家与四川、云南和湖南等
这样的省,或更小的国家,如意大利与伦巴第、利古里亚和西
西里岛等这样的行政区时,这样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
解不平等。组间差异的意味很清楚,若其过大,则不平等主要
是因为我们研究的区域由贫穷和富裕的两部分组成。如果组内
差异所占比重较大,则不同部分间地理上的不平等一定较小,但每个部分一定既有穷人也有富人,差异极大。当将此方法运
用于考察全球不平等时,组间差异就是国家间平均收入不同造
成的不平等,而组内差异就是各国内部个人收入的不平等。此
类分解是非常有力的工具,可使经济学者在测量到的不平等背
后一探究竟,故我们将频繁使用(如见小品1.7、小品1.8、小
品3.2和小品3.3)。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两种不平等的政治
意味有很大差别。
1. 感谢Francisco Ferreira对该散论颇有助益的评论。
2. 较之于占有贫瘠的土地(the marginal land),占有更肥沃土地的所有地
主将由此得到更高的租金。
3. 见“Response by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to:‘The Top 1%…of What’by Alan Reynolds”; 可 访 问
http:www.econ.berkeley.edu~saezanswer-WSJreynolds.pdf。
4. 这个比喻由Francisco Ferreira在《类如胆固醇的不平等》(Inequality
as Cholesterol ) 一 文 中 首 先 提 出 , 见 Poverty in Focus
(Brasilia:International Poverty Center,June 2007)。
5. Max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reprint,London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53.6. J.M.Keynes,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1920;reprint,New York:Penguin,1971),第二章第三部分(对“不平
等”的强调乃凯恩斯原文)。
7. Stefan Zweig,The World of Yesterday (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4),7-8.
8. 这 就 是 由 Kevin Roberts ( 见 “Voting over Income Tax
Schedule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1977):329-340)及Allan
Meltzer and Scott Richard ( 见 “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1981):914-927)提出
的“中间选民假说”(median-voter hypothesis)。
9. 甚至可能会出现没有真正的再分配,但对经济增长仍然带来负面影响的情
形。例如,为了避免穷人以政治手段接管财富,富人会联合起来,通过游说来
购买选票和法律,从而防止再分配。然而,游说乃零和博弈,涉及的并非新财
富的创造,而只是财富的再分配,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在这种毫无生产
性的活动上花的功夫纯属浪费,接踵而至的是更低的经济增长。
10. 见 Oded Galor,“Income Distribution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4(2002):706-712,及Oded
Galor and Omer Moav,“From Physical to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1(2004):1001-1026。
11. 在这段对话中,“他”是苏格拉底的哥哥Adeimanus。
12. Plato,The Republic ,translated by Desmond Lee ( New
York:Penguin,1973),pt.IV,sec.3,p.189.
13. “On the Measurement of Inequality,”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1970):244-263.
14. 阿马蒂亚·森于1979年5月22日在斯坦福大学“坦纳讲座:论人的价
值”(Tanner Lecture on Human Values)上做演讲《什么上的平等?》
( Equality of What ? ) , 见
http:www.tannerlectures.utah.edulecturessen80.pdf.亦见其“Social
Justic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in vol.1 of Handbook ofIncome Distribution ,edited by A.B.Atkinson and
F.Bourguignon(Amsterdam:Elsevier,2000)。
15. 准确地说,森的方法就是要求在可行能力空间上人人平等,而不再是效用
空间上。
16.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除了拥有自身的效用尺度,若假设人们也有移情效用
尺度(empathic utility scale),能够“测量”被其他人享有的效用,则我
们就可以做个人效用比较。正如摄氏度和华氏度间的关系一样,他们赋予移情
效用尺度和个体效用尺度的精确值可能不同,但它们是“可传递”的(即若我
们知道其中一个,则也知道另一个)。这一观点可追溯至John Harsanyi
的 “Cardinal Welfare,Individualistic Ethics,and the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 of Utilit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3(1955):309-
321。
17. 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 ,rev.ed. (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13.
18. 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 ,rev.ed. (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第54页。
19. 罗尔斯间接排除了富人和穷人收入绝对提高(故满足其“差别原则”),而中间阶层收入减少这一情形。在其看来,收入分配如同一条相互连接的铁链
那 样 变 动 [ 见 《 正 义 论 》 第 二 章 第 十 三 节 对 “ 紧 密 相 联 ” ( close
knittedness)的定义]。
20.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包含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富人仍然更富有,否则两人可能只是交换了位置。若是那样,认为不平等有所下降是不恰当的。
21. 然而,最后这条公理并不是那么明显或无害的。注意,这意味着即使人与
人之间绝对收入差距增加,不平等的测度仍然不变。我们称满足该公理的不平
等测度为“相对的”,而大多数测量都只采用此类测度。但是,我们不能完全
无视随绝对收入差距上升而上升的绝对测度。
22. Corrado Gini,“Measurement of Inequality of Incomes,”Economic
Journal (March 1921):124.23. 拉丁美洲和东欧的情况要好些。在这两个区域,可靠的调查始于20世纪60
年代。遗憾的是,除了少量总体统计留存下来,许多细节已然遗失,而久远散
佚了的拉丁美洲调查则让我们想起马尔克斯(Márquez)笔下的马贡多
(Macondo),在其中除了一两件文物,这个小镇的过去在雾霭中逐渐模糊直至
成为神话。
24. 除了收入,家庭消费亦可同样处理。这样,我们感兴趣的就是家庭的“福
利”,即他们真正消费了多少,而不是家庭收入,或者说,他们潜在的消费是
多少。
25. 两总和相等。
26. 据Michele Zenga(“Il contributo degli italiani allo studio della
concentrazione:Prima parte:Dal 1895 al 1915,”in La distribuzione
personale del reddito :Problemi diformazione ,di ripartizione e di
misurazione ,edited by M.Zenga[Milan:Vita e Pensiero,1987],307-
328),该集中度最初出现在基尼1914年发表的文章“Sulla misura della
concentrazione e della variabilità dei caratteri,”in Atti del Reale
Istituto Veneto di Scienze ,Lettere ed Arti ( Venice:Premiate
OfficineGrafiche Carlo Ferrari,1914),vol.73,pt.2a,pp.1203-1248中,后
来被称为基尼系数。感谢Andrea Brandolini提供此信息。
27. 原文所谓“The Gini coefficient compares the income of each person
with the incomes of all other people individually,and the sum of all
such bilateral income differences is divided in turn by the number
ofpeople who are included in this calculation and the average income
of the group”表述有误,揣摩其所欲传达的信息得如上译文。这是基尼系数
若干表达之一。——译者注
28. 作者随后写道:“通常情况下,为简便计,基尼系数以百分数的形式呈
现,因此我们会说某国的不平等是43个基尼点(Gini point),而不是0.43。
在该书中,我们依循此例。”故为免混乱计,且循中国学界惯例,在译作中始
终以基尼系数表述,亦由此对原书中某些文字与图表略做调整;不另说明。
——译者注
29. 基于人口普查局的总可支配收入数据,源自Andrea Brandolini和Tim
M.Smeeding,“Inequality Patter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Cross-CountryDifferences and Changes over Time,”in Democracy ,Inequality ,and
Representa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ited by Pablo Beramendi
and Christopher J.Anderson(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8),图2.5.亦请参见由Richard V.Burkhauser等进行的详细研究Estimating Trends
in U .S .Income Inequality Using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The
Importance of Controllingfor Censoring ,Working Paper
14247 ( Cambridge,MA: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August
2008)。小品1.1
爱情与财富
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是一部以“爱”为主题的小
说,这是举世公认的真理,但要说它也是一部关于“金钱”的
小说,就不会有太多人承认了。
故事发生的时间未在书中明确给出,而简·奥斯汀有意为
之的这个具体而微、无始无终的世界也没有让一丝线索能令我
们为其确定一个准确的日期。或许这就是她的目的,以表明谈
情说爱(还有金钱)是如何与人类相始终的。
但是,间接证据表明故事发生于拿破仑战争时期,即大约
1810年至1815年之间。小说的主人公是妩媚的伊丽莎白·班内
特,殷实的班内特一家五个女儿中的次女,而一家之长
(paterfamilias)的名字从未在书里出现过,他的妻子叫他班
内特先生。伊丽莎白和家人过着英国乡绅怡然自得的宜人生
活,不时觥筹交错、轻歌曼舞,间杂以这类聚会催生的闲言碎
语。她美丽、聪慧,当然,也还待字闺中。其家庭年收入约为3
000英镑,由包括五位姐妹和父母在内的七个家庭成员分享,故
人均430英镑(与这里其他例子一样,排除了房屋的估计价值,而 其 定 然 相 当 可 观 ) 。 根 据 罗 伯 特 · 科 洪 ( Robert
Colquhoun)计算的19世纪早期英国社会阶层收入表,这样的收
入水平让班内特一家跻身当时英国收入分配的前1%。伊丽莎白遇到了富有的追求者达西先生,据书中的信息可
知,达西先生年收入约为10 000英镑。 自然,他与他那稍微
不那么富有的朋友宾利先生,都被熟知人情世故(而且并不拐
弯抹角)的班内特夫人视为非常令人满意的东床之选。达西先
生的巨额收入使之处于英国收入分配的至少前1‰水平。须指出
的是,前1%与1‰间,或用小布什的当代措辞,“有产者与富足
者”之间,差异巨大。在19世纪早期的英国,虽然有产者和富
足者在社会上自由融合(显然也通婚),但达西先生的收入却
是伊丽莎白父亲的3倍多;由于达西先生只需照顾自己一个人,以人均计,这一比例则超过了20∶1。
非常明显的是,对于达西先生是否适合自己,伊丽莎白确
有疑虑,而达西先生则明确表达了他对伊丽莎白的“倾
慕”——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婉语在现代作品中会以全然不同
的方式表达。但是,断然回绝达西先生却有婚姻之外不太令人
愉快的意味。根据英国继承法,如果班内特先生去世后没有直
系男性继承人,那么其房舍和运作良好的地产将归于他那令人
讨厌的远房表弟威廉·柯林斯牧师所有。要是那样处置遗产,伊丽莎白就只能自食其力,即基本上依靠其母亲5 000英镑陪嫁
里属于她的份额。根据柯林斯先生令人窘迫的估计,这份自主
的财产有1 000英镑。他假定她将从中获得4%的回报,即每年40
英镑。这是一个少得可怜的数字,大抵等于当时英国人均收入
的2倍,与一个勘测员或商船海员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当。
这便是权衡爱情和财富之所在。让我们从担心女儿幸福的
伊丽莎白母亲的角度考虑。第一种可能是,伊丽莎白可以嫁给达西先生,然后享有每年5 000英镑的收入(我们假设她没在金
钱方面对达西先生做出任何贡献,并且后者将其收入与伊丽莎
白平分)。而在另一种可能中,她会陷入在班内特夫人看来无
疑是永无止境的贫困之中,依靠每年不足50英镑的收入度日。
这两种结局间的收入之比超过100∶1,简直令人咂舌。面对这
样的成本,伊丽莎白选择不结婚,或一直等到理想的爱人在天
边出现,都完全是不可能的。除非真的憎恨达西先生,否则谁
也不可能拒绝他这笔不言而喻的交易!
但是我们可能会问,如今有何不同吗?若要将《傲慢与偏
见》置于当代的英国,我们只需看看眼下的收入分配格局即
可。2004年,税后收入排在前1‰的人平均每年挣40万英镑,前
1%的人平均挣8.1万英镑,而英国的人均收入是11 600英镑。拒
绝今天的达西先生的成本依然不菲,却没有那么不可承受:排
在收入分配前1‰的群体和两倍于人均收入的群体间的收入之比
约为17∶1,而不再是100∶1。
因此,简·奥斯汀不仅展示了爱情与财富之间司空见惯的
权衡,而且还让我们看到,虽然这种权衡本身可能是永恒的,但是其间的利害确实随着时间和所处社会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而变化。社会愈平等,在做出关乎婚姻的决定时,我们预期爱
情愈趋于战胜财富;而在很不平等的社会里,却往往相反。那
么,爱情在非常不平等的社会中就只能存在于婚姻之外吗?我
们接下来讨论这个问题。1. 感谢Michele de Nevers、Carol Leonard和Blanca Sanchez Alonso的评
论。
2. 一位当代评论家就此界定了2 000英镑的收入在简·奥斯汀书中的价
值:“年收入2 000英镑之下[这是《傲慢与偏见》中乡绅班内特先生和《理智
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 )中布兰登上校(Colonel Brandon)的情
形],一家人仍须节约用度,而在《傲慢与偏见》里因有五个女儿需要嫁妆,就
尤其如此。《理智与情感》里詹宁斯夫人(Mrs.Jennings)将布兰登上校的德
拉福德庄园(Delaford)描绘为‘没有债务,没有瑕疵,总之,每件事都称心
如意……哦,这真是个好地方’,其强调的就是2 000英镑下的宁静安怡之
乐”(Edward Copeland,“Money,”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ane
Austen ,edited by Edward Copeland and Juliet
McMast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136)。
3. 他有200 000英镑,而通常的年收益率是4%~5%。
4. 基于Patrick Colquhoun社会阶层收入表得出。小品1.2
安娜·伏伦斯卡娅?
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 但是阿历克赛·亚历山大罗维奇
·卡列宁和安娜真的那么独一无二吗?
诚然,《安娜·卡列尼娜》讲述的是一位有夫之妇爱上了
雅致洒脱、家财万贯的翩翩少年伏伦斯基伯爵的故事。在某种
程度上,这也是对社会规范与伪善的批判,因为要不是那
些“规矩”,安娜不会因为她与伏伦斯基的关系而被社会排
斥,并且会发现离婚更容易(虽然不清楚她是否真的想离婚,因为这么做会让她失去儿子的监护权)。如果他们结婚,我们
不能断言其就不会拥有幸福的婚姻——或者,套用托尔斯泰著
名的开场白, 成就一段美满的姻缘。当然,或也不尽然,因
为托尔斯泰展现的是,阻止安娜和伯爵幸福结合的不仅是社会
和社会规范,也包括他们自身的性格。
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发生在1875年前后的莫斯科、圣彼
得堡和周边的乡村,这与托尔斯泰自己的生活处于同一时代
(该小说1877年出版)。用最简略的话说,这本著作描写了安
娜·卡列尼娜与冷峻以至于常常无动于衷的高级公务员卡列宁
先生的不幸婚姻,以及与伏伦斯基先生的婚外情。这份爱情,始而隐秘,继而公开;始而浸满了兴奋与承诺,继而充斥着冲突、谎言与绝望,它毁掉了伏伦斯基的前途,最终导致两人痛
苦不幸的结局。
乍看之下,《安娜·卡列尼娜》和《傲慢与偏见》之间并
没有什么相同点。如果有人想通过两者的“特质”或“氛
围”比较它们,《傲慢与偏见》的气候应该是英国多变的夏
天,在那里灿烂的阳光与可怖的乌云相互交替。但是乌云和大
雨来去匆匆,读者记忆所及,还是夏日的明艳。相反,《安娜
·卡列尼娜》的开始如同俄国的大陆性夏季,大自然仿佛在人
们的眼前绽放,温暖耀眼,然后慢慢向阴郁的秋日转变,最终
落入漫长、黑暗、萧索而永无止歇的冬天,故而我们从书中感
受到的整体氛围更多的是冬季,而非夏日。这正如在12月中旬
寒冷的日子里,自然难以浮想刚刚过去的悠然自得的6月天。
但是,在收入与地位不平等这一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上,《安娜·卡列尼娜》与《傲慢与偏见》相似。在这两部小说
中,女主人公一开始都生活在十分富有、舒适而体面的家庭,只不过在其中一部里已婚,而在另外一部里待字闺中。然而在
两部作品的后续阶段,就财富而言,她们都凭借恋爱或婚姻扶
摇直上。《安娜·卡列尼娜》中无一字提及卡列宁先生的薪
俸,但是,我们可从他和安娜的哥哥斯特潘·奥布隆斯基的谈
话中了解到,他认为1万卢布是份很高的薪水,而我们从书中别
处可以得知这是银行董事的收入水平。 我们还知道收入高的
政府官员收入有3 000卢布,而同在政府任职但比卡列宁先生位
阶低的斯特潘·奥布隆斯基收入为6 000卢布。 由此,考虑
到卡列宁先生显赫的官场地位,我们可以推断其年收入大概在8000~9 000卢布。那么,富有的伏伦斯基伯爵如何呢?与达西先
生一样,“所有人”也都认定其年收入为10万卢布。但是,我
们可从后面了解到,如果他没有将遗产的一半给弟弟,这本应
是他正常的预期所得,因此伏伦斯基遇见安娜时的真实收入仅
约50万卢布。 后来,当他面临经济问题,重新获得曾经草率
允诺给弟弟的一半遗产时,伏伦斯基的收入大概恢复到10万卢
布的“正常”水平。
现在我们看到,安娜若与伏伦斯基结婚将会带来的财富剧
增,即人均收入从大约3 000卢布(她丈夫的大致收入在夫妇和
儿子之间分配)变为30 000卢布以上(再次假设她像伊丽莎白
·班内特那样对家用的贡献为零,而伏伦斯基先生则像达西先
生那样将自己的收入平分给妻子和女儿)。 由此,从本已富
丽堂皇、仆役成群的卡列宁家,安娜一跃而至像伏伦斯基那样
王侯般的生活,这意味着年收入至少扩大10倍。
对于俄国,我们缺少社会阶层收入表以确定伏伦斯基和卡
列宁先生 在当时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处的位置。但毫无疑问,卡列宁夫妇属于收入阶梯中的极高层(可能是前1%),而由此
伏伦斯基又像达西先生一样,肯定是富豪中的富豪,可能属于
最高的1‰或者更甚。请再次注意这将富裕与极端富裕区分开来
的巨大差距。
但是这对安娜·卡列尼娜的负面影响是什么呢?我们是不
是也能看到这种收入分配中较糟糕的一面呢?对于安娜,黯淡
无光的岁月是其过去的一页。我们知道她来自一个非常不起眼
的家庭, 可能每年仅靠人均几百卢布过活。 从社会地位的角度看,她嫁给卡列宁是占了便宜,致使其生活水平大约提
高了15倍。而另一段与伏伦斯基先生的婚姻,正如我们刚才看
见的,本可以使其收入再增加10倍。凭借这两段婚姻,安娜就
可能从收入分配的均值位置升至极高的位置,将其生活水平提
高约15×10,即150倍。
俄罗斯今天的情况变好了吗?是的。根据2005年的家庭调
查数据,我们发现俄国前1%的家庭人均收入为34万卢布,大约
是平均水平的6.5倍。我们估计在1875年的收入分配中,两个同
样位置(即卡列宁先生的家庭人均收入和全国人均收入)的收
入之比为15∶1,故而俄罗斯的收入差异也在缩小。另一个“安
娜”若要在今天的俄罗斯进入收入分配的高层,将肯定会被带
离其起点很远(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就是证据)。然而,尽管
我们时常瞩目于俄罗斯亿万富翁的财产,在这一过程中隐含的
收入增长将依然小于列夫·托尔斯泰笔下那部名著的时代。
1. Natalia Drozdova Petrova全面的评论令我受益颇多。
2. 这是指该小说的第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
各的不幸。”该小品的第一句话实际上正是借用于此。——译者注
3. Anna Karenina (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2000.Constance
Garnett translation revised by Leonard Kent and Nina Berberova),813.
4. Anna Karenina (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2000.Constance
Garnett translation revised by Leonard Kent and Nina Berberova),第
745页。
5. Anna Karenina (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2000.Constance
Garnett translation revised by Leonard Kent and Nina Berberova),第347页。
6. 基于对伏伦斯基与其弟弟谈话的解读及随后其支出的增加做出推断。
7. 这是假定安娜的儿子(安娜与卡列宁所生)与其父生活,而女儿(安娜与
伏伦斯基伯爵所生)与他们生活。
8. 原文为Messrs.,法语Messieurs的简写,即Gentlemen。——译者注
9. 我们间接察知。这是因为,首先,她与其富有的姑妈生活(想必远较其父
母富有);其次,就社会地位而言,她嫁给卡列宁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10. 我们从托尔斯泰那里对中产阶层的收入所知不多。书中提及的唯一“专业
人才”收入,是一个德国会计每年挣500卢布,而他的工资一定比同等的俄国会
计高(因此才会强调“德国”)。假定他要维持一个四口之家,则这种“中产
阶层”的人均收入仅略多于一百卢布。小品1.3
谁是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人?
比较过去与现在的收入并非易事。我们没有汇率可以将古
罗马的塞斯特斯(Sesterce)或阿斯(As), 或者卡斯蒂利
亚17世纪的比索转换成今天具有同等购买力的美元。甚
至,“同等购买力”在那种情况下究竟为何物都还远未可知。
它应该表示一个人能够用X古罗马塞斯特斯买到今天用Y美元购
买的同样一束商品和服务。但是,不仅商品束已经改变(古罗
马时期没有DVD),而且纵使限制商品束,令其只涵盖当时和现
在都有的商品,我们也很快就能发现其相对价格已发生了很大
变化。因为工资低,过去的服务相对便宜,而在如今的富裕国
家却价格高昂;就面包或橄榄油而言,情况则恰恰相反。
因此,要比较若干历史时期中大富豪的财富和收入,最为
合理的方法就是将之置于其历史情境中,依据他们在当时雇用
(平均技能)人力劳动的能力衡量其经济实力。在某种意义
上,给定数量的人力劳动是一个通用的计量单位,是我们衡量
福利的准绳。正如亚当·斯密两百多年前所言,“(一个人)
是富有或贫穷,取决于他能够支配的劳动力数量”。 此外,对于今天的比尔·盖茨这类人,由于其收入将根据目前美国居
民的平均收入衡量,上述数量体现了生产力和社会福利随时间
的提升。古罗马是一个自然的起点,因为我们拥有其富豪的数据,且其经济也足够“现代化”与货币化,以使我们能够将其与目
前或更晚近的过去做有价值的比较。我们可以考虑古典时代的
三个人。三个执政官之一的马尔库斯·克拉苏(Marcus
Crassus),其财产在公元前50年左右估计约为2亿塞斯特斯,富有得令人难以置信;在公元14年左右,皇帝屋大维·奥古
斯都(Octavian Augustus)的皇室财产估计有2.5亿塞斯特
斯; 最后,尼禄(Nero)治下的自由民马尔库斯·安东尼斯
·帕拉斯(Marcus Antonius Pallas)在公元52年据信拥有富
甲天下的3亿塞斯特斯。
以已与奢靡联系在一起的克拉苏为例(不要将之与希腊国
王克罗伊斯混淆,后者的名字已成为“财富”的代名词)。克
拉苏有2亿塞斯特斯,而年利率是6%(在古罗马的“黄金时
代”,即公元3世纪的通货膨胀前,这被认为是“正常”利
率),故年收入估计可达1 200万塞斯特斯。在公元14年屋大维
过世前后,一般认为罗马公民的年均收入约为380塞斯特斯,并
可假定它与60年前克拉苏在世时相同。 由是观之,克拉苏的
收入相当于32 000个人的年收入,如此庞大的人群大致可以塞
满半个斗兽场。
让我们快进到离今天更近的年代,将相同的逻辑运用到安
德鲁·卡内基、约翰·洛克菲勒和比尔·盖茨这三位美国财富
的化身上。卡内基的财富在1901年其购买美国钢铁公司时达到
顶峰,而他在该公司的股份为2.25亿美元,对此同样采用6%的
回报率,并使用282美元的美国人均GDP(据1901年价格水平计算),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卡内基的收入超过了克拉苏。事实
上,卡内基几乎可用其年收入轻而易举地买下大约48 000人的
劳动力。(注意在所有此类计算中,我们都假设富豪的财产保
持不变,他仅仅使用每年从财产中获得的收益购买劳动力。)
洛克菲勒在1937年以14亿美元达到了其财富的巅峰。 同
样的计算表明,洛克菲勒的收入与1937年大约116 000个美国人
的收入相等。因此,洛克菲勒的财富几乎相当于克拉苏的4倍,也是卡内基的2倍多。他能雇用的人可以轻易地装满帕萨迪纳
(Pasadena)的玫瑰碗球场,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只能留在
门外。
在这样的比较中,比尔·盖茨的表现又如何呢?据《福布
斯》杂志显示,比尔·盖茨2005年的财产为500亿美元,由此可
以估计其收入为每年30亿美元,并且由于该年美国人均GDP约为
40 000美元,那么他可以用其收入支配大约75 000名工人。这
使他跻身于卡内基与洛克菲勒之间的某个位置,却远远高
于“贫穷”的克拉苏。
然而,这种计算仍留下了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俄罗斯的
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和墨西
哥的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他们既是“全球”也
是“一国之内”的亿万富翁,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他们呢?在
霍多尔科夫斯基于2003年成为俄罗斯首富的时候,其资产估计
约为240亿美元。 就全球角度而言,他远不如比尔·盖茨富
有。但是,若我们再次运用之前的假设区域性地评估其财富,以俄罗斯平均价格计算,他能购买超过25万人一年的劳动力。换言之,对比其同胞相对低下的收入水平,霍多尔科夫斯基比
1937年美国的洛克菲勒更富有,可能也更有权力。也许正是后
者,即潜在的政治力量,招致克里姆林宫注意上了他。
如有必要,霍多尔科夫斯基无须动用一分钱的本金,就可
以建立一支25万人的军队。而且就如同一个国家,他既与美国
人也与中国人谈判建设新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这种潜在的势
力难逃克星,倒台和最终的牢狱之灾随之而来。然而,俄罗斯
的历史就是这样,两个政权间的最短路径往往得绕道西伯利
亚,而我们看到的也许并非最后一个霍多尔科夫斯基先生。
墨西哥人卡洛斯·斯利姆做得比他更好。同样根据《福布
斯》显示,他的财富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估计超过530亿美
元。运用与之前相同的计算,我们发现斯利姆在其收入的巅峰
时期可以支配约44万个墨西哥人,比霍多尔科夫斯基更多。由
此,就局部而言,他看起来已经是最富有的人了!甚至包括著
名的阿兹台克体育场在内,在墨西哥没有一个体育场能勉强容
纳斯利姆先生用其年收入可以雇用的所有同胞。
另一个可能的复杂之处是人口的规模。当克拉苏在世并支
配着32 000人的劳动收入时,罗马帝国的人口是这一数量的1
500倍。而与洛克菲勒的年收入对应的116 000个美国人,则占
据总人口中更大的比例,以至于每1 10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因
此,从绝对量和相对比例两方面来说,洛克菲勒都比克拉苏更
富有。那么我们能说谁是他们所有人之中最富有的吗?由于富人
也都倾向于“全球化”发展并将其财富与不同国家的其他富人
比较,考虑到洛克菲勒身处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而在那
里控制着数量最多的劳动力单位,所以魁首可能就是他。但是
当大富豪决定在自己的国家(不一定就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
家,比如俄罗斯和墨西哥)扮演政治角色时,那么他们在那里
的权力甚至可能会超过在全球意义上最富有的人。
1. 塞斯特斯和阿斯均为古罗马硬币。——译者注
2. 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Pelican Books,1970),133.
3. Aldo Schiavone,The End ofthe Past :Ancient Rome and the Modern
West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71.塞斯特斯意为“两
块半”(semithird),指其价值两个半的阿斯(另一种罗马硬币单位)。
4. Raymond Goldsmith在“An Estimate of the Size and Structure of the
National Product of the Early Roman Empire,”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30(September 1984)中估计奥古斯都的年收入为1 500万塞斯特斯;
以通常每年6%的利率计,这意味着其财富是2.5亿塞斯特斯。
5. Tacitus,Annals (New York:Penguin,1996),第十二卷第五十三章。在
塔西佗笔下,帕拉斯附助着尼禄,助纣为虐,直至其也被尼禄下令毒死(第十
四卷第六十五章)。
6. Goldsmith,“Estimate of the Size and Structure.”这是由Branko
Milanovic 、 Peter Lindert 和 Jeffrey Williamson 在 “Preindustrial
Inequality” ( Economic Journal ,forthcoming;previous version
published as Measuring Ancient Inequalit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3550[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October2007])中估计的,等同于1990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出的人均
GDP 633国际元(见散论二)。而Angus Maddison的估计稍低一些,为570国际元(Contours ofthe World Economy ,1-2003 A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chap.1)。
7. 这只是作为一个例子,实际上斗兽场建在克拉苏去世百年之后的罗马帝国
皇帝韦斯巴芗(Vespasian)和提图斯(Titus)治下。
8. 基于《纽约时报》1937年的讣告和维基百科,而Alan Nevins说这个数量并
没有超过9亿美元(Study in Power :John D .Rockefeller ,Industrialist
and Philanthropist ,2 vols.[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53],404-405)。
9. 见《财富》杂志2004年亿万富翁名单。
端的也正是这段时期。
(Gibbon)所言的罗马“衰亡”在学界声名远播,而标志其开
斯·奥利里乌斯(Marcus Aurelius)的儿子康茂德上台。吉本 帝”(five good emperors)统治结束,紧随其后的是马尔库
( 后 来 被 称 作 “ 奥 古 斯 都 ” ) 执 掌 大 权 到 公 元 180 年 “ 五 贤
期横跨了基督纪元的前两个世纪,即大约从公元前31年屋大维 让我们从帝国早期社会结构之大略开始。我们知道这一时
主要特征之一。 (免费书享分更多搜索@.)
的,是的,而且这是区分前现代化时期不平等与现代不平等的
存 。 这 两 种 景 象 是 否 可 以 同 时 成 立 呢 ? 正 如 下 面 我 们 将 看 到
工业社会的另一幅图景,在其中,底层的赤贫与上层的奢靡并
国)的不平等程度应该不高。但与这种观点相反,我们也有前
时,而前工业化社会(甚至包括它们之中最发达的,如罗马帝
形 , 因 此 不 平 等 应 该 只 出 现 在 社 会 进 入 持 续 的 现 代 化 进 程 之
为主变成以工业或“现代”产业为主时,不平等的图像呈倒U
品1.10)。作为不平等经济学的基础,它认为当经济从以农业
的理论,这就是提出于1955年的库兹涅茨假说(见散论一和小
关于前工业化经济中的收入不平等,我们的确有一个隐含
罗马帝国有多不平等?
小品1.4政治上,同时很大程度也在经济上,居于帝国早期顶端的
自然是国王。他,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和他的家族有多富有
呢?据估计,屋大维家族的年收入为1 500万塞斯特斯,约相当
于整个帝国总收入的0.08%(其时人口为5 000万~5 500万)。
换言之,以相对值计算,这大约是19世纪初大不列颠与爱尔
兰联合王国国王乔治三世所占比重的8倍。 (顺带指出,乔
治三世是《傲慢与偏见》故事发生时的国王,见小品1.1。)著
名的罗马史学家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
认为,屋大维去世后从私人和公共基金中捐赠给民众的财富总
和为4 350万塞斯特斯, 约为当时帝国GDP的0.2%。这就大致
好比布什总统在离任时自掏腰包,分发给美国公民大约300亿美
元。
屋大维的慷慨并非独一无二。公元33年,其继承者提贝里
乌斯(Tiberius)拿出大约GDP的0.5%(以当今美国的收入折合
为750亿美元)用于解决银行流动性危机,这和美国财政部2009
年的做法非常类似。塔西佗的记载在今天有了令人惊异的呼
应,唯一不同的是,它是由个人,而非政府支付这笔钱:
这个要求购销土地的法令……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因为
放高利贷者收回放款后便将之囤积起来,以便方便时购买土
地。大量的土地交易降低了其他商品的价格。然而,负债沉
重的债务人却发现难以把货物卖出,于是其中很多人便丧失
了财产,一同失去的还有他们的地位和声誉。这时提贝里乌
斯来拯救他们了。他将1亿塞斯特斯拨给尤为著名的银行,而借款人若能以贷款价值两倍的土地作为抵押的话,就可以得到免息三年的国家贷款。信贷就这样恢复了,而私下放款
的人也逐渐重新出现。
在公元36年,对于罗马遭受巨大火灾的人们,提贝里乌斯
拨了同样多的资金以弥补其损失。 尼禄延续了这一做法。塔
西佗在早期著作《罗马史》一书中,估算尼禄在其统治的14年
中捐赠总额高达23.2亿塞斯特斯,约为全年GDP的10%。这所有
的钱从何而来?是私有的还是公有的?皇帝在这两者间做了严
格的区分吗?或许没有。希腊-罗马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
(Cassius Dio)如此描述屋大维对公共和私人资金的处
理:“名义上公共收入和他自己的财产是分离的,但实际上他
也可以由着性子随支随取。” 正如最著名的罗马史学家之
一、斯坦福大学的沃尔特·谢伊德(Walter Scheidel)所言,皇帝的所作所为与如今的沙特统治者或萨达姆·侯赛因处理私
产和国库资金的方式大抵如出一辙。
毋庸置疑的是,皇帝极其富有,但并非帝国中唯一富有的
人。大量的财富来自对各省的管治和劫掠。用英国著名经济学
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比喻来说,“它是用剑挖掘的,而不
是铁锹”。 我们已由小品1.3了解到罗马帝国历史上最富有
的人可能并非君主。这样一个由富豪统治的社会,其阶层间的
划分以占据世袭爵位和持有大量流通财富这二者的结合为基
础。为了保证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对元老、骑士和市政官这
三个顶层阶层的财富有明确的评估登记。前两个阶层住在罗马
(或意大利其他地方),而第三个阶层,顾名思义,分布在帝
国各地。在帝国早期,对元老的财产要求为100万塞斯特斯,而骑士为25万塞斯特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数字,我们不妨看
看元老。这一阶层的平均财产可能在300万塞斯特斯左右,对此
采用每年6%的通行利率,则有18万塞斯特斯的年收入,而这大
约是估计的当时罗马平均收入的500倍。再以今天美国的情形而
言,这意味着那些元老的年收入(不是财产)约为2 100万美
元, 而如今美国的参议员则相对较穷:他们的年薪少于20万
美元,平均净资产估计约为900万美元。 假定财产有6%的收
益,再加上薪酬,他们的平均收入也大约只有不足70万美元,而这只是其古罗马同行很小的一部分。
然而,古罗马元老不多,也许只有约600位,而骑士则可能
有4万名。另外,由于各地富裕程度不同,对财产的要求在各城
市间有别,故而市政官的数量不那么确定,而且整个帝国所有
市政官的总数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对城市数量、市政议会
(municipal senate)规模等的估计。但若要给出市政官的大
体数目,我们可以认为大约有13万~36万人。无论如何,将这三
个最富有的阶层加在一起,得到的人数在20万~40万人之间。如
果还记得罗马帝国有5 000万~5 500万居民的话,正如我们所
见,金字塔顶端的人数相当少,仅代表着不到1%的总人口。
不足为奇的是,绝大多数人仅靠极低的收入苟延残喘,或
者免于饥饿而已,其间的梯度(即当我们从较为贫穷的收入阶
层向上攀升时收入增长的速度)比现代社会平坦,而在这一大
群人之间以收入比体现的差异很小,因此,该梯度在收入分配
中平缓地上升到很高的点。但随后,当我们接近分配的顶端
时,梯度会陡然上升,其变化之大远超现代社会。因此,不同于以梯度稳定增长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古罗马的中层与底层间
并没有太大差异。即使不是完全阙如,那里仍然缺少可被我们
(用当代术语)称作“中产阶层”的人。
我们先入为主地认为,古人之间既有普遍的平等,又有巨
大的收入差距,现在知道这两者都是正确的:它们只是代表了
收入分配的不同部分而已。当我们着眼于收入分配梯度的大部
分,或者观之以收入不平等的标准测度时,第一个观点(即贫
困中的平等)是成立的。因为这些测度是考虑到社会中所有人
收入的综合性指标,那么既然大部分人之间的收入并无太大差
别,此类不平等统计量也就不会非常高。根据基尼系数(见散
论一)这一我们最偏好的对不平等的测度,罗马帝国早期的基
尼系数估计在0.41~0.42之间。 这一水平与现在的美国和扩
大后的欧盟几乎完全相同(也见小品3.3)。但若着眼于分配中
的极端现象,第二个观点(即处处啼饥号寒之外却有人家财万
贯)也成立。这道横亘在两个极端之间的鸿沟比我们今天观察
到的要大得多。
罗马帝国还存在大范围的空间不平等。在我们考虑的这段
时间里,由单个中心统治的帝国扩张了巨幅领土,西起今天的
摩洛哥和西班牙,东至如今土耳其和亚美尼亚的最东端。沿南
北轴线,从英格兰绵延到波斯湾(尽管只是在图拉真治下的公
元98年到117年之间占有波斯湾,随后便从那里撤离)。其领土
覆盖340万平方公里,大约是美国大陆面积的34。在这片广袤
的土地上居住着5 000万~5 500万人口(由此可知其密度仅约为
当今美国的15),而他们有着不同的发展及收入水平。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估算了各地区收入的范围。 意大利半岛
是最富裕的,较帝国的均值高出约50%。接下来是帝国的粮仓埃
及,也略微比整个帝国的平均水平富裕。再次是希腊、小亚细
亚、非洲的部分地区(利比亚和今天的突尼斯)、西班牙南部
(大抵是现在的安达卢西亚)和法国南部(大致是如今的普罗
旺斯)。那些更加贫穷的地区间差异较小:一些岛屿(西西里
岛、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也许只稍微比高卢好一点,北非(今
天的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紧随其后,而排在最后的是东部
(多瑙河流域)诸省。最富庶和最贫穷地区间的收入之比相对
较低,约为2∶1。
如果看看那些曾属于早期罗马帝国的地区今天的收入,马
上便能发现其间的差距在今天明显大了许多。眼下排在顶端的
是瑞士、奥地利、比利时和法国,其人均GDP皆在35 000国际元
左右。 在另一端,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人均GDP在7 000~8
000国际元之间,而巴尔干半岛诸国只是略微好一些。因此,在
同样的土地上,今天的“省际”贫富之比已经攀升至5∶1,而
且各“省”的排位次序也发生了变化。大体而言,那时的南方
比北方富庶;现在,情况正好相反。然而,西欧相对于东欧的
优势如故。
1. Goldsmith,“An Estimate of the Size and Structureof the National
Product of the Early Roman Empire”。
2. Goldsmith,“An Estimate of the Size and Structureof the National
Product of the Early Roman Empire”,基于Colquhoun的社会阶层收入表与Lee Soltow 的 计 算 , “Long-run changes in British income
inequality,”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9(1968):7-29。
3. 塔西佗,《编年史》第一卷第八章。
4. 塔西佗,《编年史》第一卷第六卷(公元33年),第208页。
5. 数据来自塔西佗《编年史》一书。
6. Cassisu Dio,The Roman History :The Reign of Augustus ( New
York:Penguin Classics,1987),131.
7. 来自私人通信。
8. Alfred Marshall,Principles of Economics ,vol.2:notes,9th
edition(London:Mc Millan,1961),745,Marshall回答William Cunningham之
批评。
9. 这是美国人均GDP(2008年时约为4.2万美元)的500倍。
10. 见 Jessica Holzer,“Meet Senator Millionaire,”Forbes ,November
20,2006 , 可 访 问 http:www.forbes.com20061117senate-politics-
washingtonbiz-wash_cx_jh_1120senate.html。
11. Milanovic,Lindert and Williamson,“Preindustrial Inequality,”附
录。
12. Milanovic,Lindert and Williamson,“Preindustrial Inequality,”,及Walter Scheidel和Steven J.Friesen,“The Size of the Econom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the Roman Empire,”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99(2009):61-91。Milanovic、Lindert和Williamson是对公元14年的估计,而Scheidel和Friesen是对公元150年的估计。
13. Maddison,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30 AD ,53-55。
14. 最富庶的区域(意大利半岛)比均值高50%,而最贫穷的区域(多瑙河诸
省)比均值低25%。
15. 对国际元(PPP US)的定义,见散论二。小品1.5
在13世纪和今天,你应该住巴黎的哪个区?
很多人都被巴黎第十六区吸引,那里有维护良好的建筑、不俗的餐馆、宜人的小公园、鳞次栉比陈列雅致的商铺,以及
无处不在的温软靡丽之气。 的确,2007年法国政府的税收数
据显示,第十六区是巴黎最富足的区之一。连同第六区、第七
区和第八区,其人均应税收入(fiscal income,即报告给税务
机关的收入)是巴黎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 正如图1.1a和图
1.1b所示,深色阴影代表的富裕区覆盖了巴黎西部并横跨塞纳
河。在财富谱系的另一端,第十八区、第十九区和第二十区这
些最为贫穷的区则位于巴黎东北部的边缘,其人均应税收入不
足巴黎平均水平的23。这么几个简单的数字让我们认识到这些
区之间的差别有多大:以2.5除以那个小于23的数可知,顶层
与底层之比约为4∶1。
现在,这幅地图只包含官方所称的巴黎,即在环城大道内
这座城市管辖的20个区,其在几乎两个世纪内没有变化。郊外
既有更加富庶之处,也有穷得多的地方。前者如巴黎西部植被
繁茂的郊区纳伊(Neuilly),而后者则见之于郊外移民(通常
是阿拉伯人和非洲人)聚居区,那里在2005年的暴乱中火光冲
天。因此,如果我们考虑整个大都市区域的1 200万居民,而不是250万生活在市区的居民,则巴黎最富裕地区和最贫困地区间
的差距会大得多。
图1.1a 财富分配:13世纪以“教区”为单位的巴黎图1.1b 收入分配: 21世纪以“区”为单位的巴黎
资料来源: 1292年和2007年的财政数据。
最富有的区也最不平等,而最贫穷的区倒是最平等的。这
里存在着财富和平等相当单调的逆向关系,或者说,一个区愈
富庶,则其不平等愈明显。而这也意味着在最富有的区里也居
住着相对穷困的人群;换言之,就占有的财富多少而论,其间
的人群形形色色。的确,若将所有区的家庭放在一起,分为同
样规模的12个应税收入阶层, 则最低阶层占了第十六区全部
家庭的15,这与生活在贫困区同样阶层所占的比重没有多大区
别。不同之处在于富裕家庭所占的比重。生活在富有区的家庭
中大约15都属于应税收入的最顶层(即第12层),但在贫困区
中这样的富裕家庭几乎不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今天的巴黎,贫穷家庭相当均匀地分布在整个城市,而富裕家庭则集中
于少数的几个区,特别是第十六区,巴黎超过20%的富人住在那
里,而这个比例是平均水平的4倍。
因为年代久远,资料缺失,追寻城市漫长岁月中不断变化
的经济地理殊非易事。但巴黎是个例外。我们有巴黎自13世纪
末、14世纪初以来的税收数据,而近来耶路撒冷大学经济史学
家内森·苏斯曼(Nathan Sussman)已将之数字化并加以利
用。 和2007年的数据一样,这些古老的数据也来源于税收,它们提供了由每个家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每个炉灶
(foyer)]承担的平均财产税。反过来应用估计的税率,我们
就可以估算出总的财产。当然,那时的税收数据远没有现在可
靠。它们遗漏了人口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锦衣玉食却免
于纳税的贵族和牧师,以及身无长物而无从缴税的贫贱之躯。
此外,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财富分配,而不是收入分配。从大
量研究中可知,财富分配较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然而,仔细
比较是可能的,尤其是如果我们使用1292年的税收数据。事实
上,这一年的数据比其他年份的都要完整:在当时巴黎估计超
过100 000的人口中,税收数据涵盖了几乎15 000户家庭,即70
000人左右。
那时的巴黎被分成了24个教区,比现在小得多。第一幅地
图展现出这些教区的相对收入(和如今的行政区一样,越富有
的教区颜色越深)。最富有的[圣雅克(St.Jacques)教区,是
如今第一区的一部分]和最贫穷的教区[圣马塞尔(St.Marcel)
教区,在现在的第五区]间的收入之比约为6∶1,故而顶层与底层的差距似乎远高于现在。但是,我们须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一
结果,因为如下两种偏差或许会(幸运地)相互抵消:一方
面,1292年的数据涉及的是财富,其分配总是比收入分配更加
不平等;另一方面,正如我们看到的,数据遗漏了富有的贵族
和贫穷的游民这收入分配的两极,而该偏差降低了测量到的不
平等。
当时巴黎最富庶的地区是塞纳河右岸和西堤岛,但左岸却
贫穷得多,而今天的第十六区在13世纪时并非巴黎的一部分。
然而,即使粗略对比这两幅地图,我们也可以看出财富和贫穷
在地理上的变化。最富有的地区从巴黎中心和塞纳河右岸向
西“迁移”了很远并跨过塞纳河,因此也“提携”了左岸的部
分地区。那些大体上在左岸且曾经最穷困的区域,如今却处于
巴黎收入分配的中层甚至更高,而今天最窘迫的区则位于巴黎
东北边缘,相对远离市中心,而那里在1292年甚至还不属于这
座城市。
用什么来解释这种地理迁移?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
(CNRS)城市研究学者莫妮克·潘松-夏洛(Monique Pin?on-
Charlot)和米歇尔·潘松(Michel Pin?on)看来,原因在于
巴黎西部在相对较晚的19世纪才并入巴黎并开始城市化。 其
时,拿破仑三世掌权,经济勃兴,而“资产阶级权贵”蒸蒸日
上。他们渴望更多的空间、更舒适的公寓和宅院,而当时相对
落后的巴黎西部满足了他们的需求。较之于在市中心逼仄的住
宅区中花大价钱整修破旧的房屋,他们更倾向于修建自己的房
子。而由于脱离了行会的限制,圣安东尼郊区(FaubourgSaint-Antoine)所在的巴黎东部在传统上一直更为工业化,故
而对富人毫无吸引力,于是这进一步推动了“西迁”。富人由
此慢慢在巴黎西部重新安顿下来,而正如我们刚看到的,他们
现在依然生活在那里。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塞纳河左右两岸之间似乎存在已久的
区别。今天,塞纳河右岸是行政中心,要塞(即通常所说的卢
浮宫)、政府各部、证券交易所和豪华亮丽的商业街分布其
间,而左岸是学生和宗教会众的领地。这的确是13世纪后期税
收调查呈现的图景,也是巴黎的传统形象,即这座城市被塞纳
河分为实现不同功能的两部分:大体上,右岸关乎权力、贸易
和行政,而左岸关乎灵魂和思想。但情况总是如此吗?并不见
得。这样的分划在罗马时代古老的卢泰西亚(Lutetia,巴黎在
当时的罗马名字)是不存在的。其时虽然宫殿和庙宇坐落于西
堤岛(如今的巴黎圣母院就靠近原来一座罗马宫殿的位置),但诸如竞技场、剧院、浴场和广场等其他重要的建筑都在左
岸, 而右岸则没有城市的重要部分。我们可以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子尤利安(Julian)于公元362年对巴黎的描
述中了解这一点。这位曾尝试减缓帝国的基督教化,并且可以
想见也试图回到希腊-罗马式崇拜的皇帝,曾作为恺撒
(Caesar,这是仅次于皇帝的位置)在巴黎待了几年。由于钟
情于这座城市,他这样追忆其在巴黎的时光:
我正好在冬季营地,它就位于我心爱的卢泰西亚
(Lutetia)——凯尔特人 是这么称呼巴黎人的首府
的。这是一叶卧于河中的小岛,城墙紧拥,木桥联通两岸。河水不常涨落,不论冬夏,通常都在同一水位……百姓安居
于此,故不得不主要从河中引水。或许是由于来自海洋的温
暖,其冬季亦是别样温和……甜美可口的葡萄生长左右,甚
至有百姓在冬季借由覆以秸秆之类,设法种出了无花果
树……
的确,在早期,因为左岸不易受洪水之苦,故而是更好的
选择;而右岸则正如著名的区域“玛莱”(Le Marais)这个名
字迄今呈现的那样,有更多沼泽,以至于在12世纪,能够用来
建造房屋之前不得不先排涝。
因此,巴黎财富的地理分布似乎已从罗马时代以塞纳河中
游的岛屿(或许这是开始营造城市的天然所在)和其左岸为中
心,变为中世纪时集中于右岸,再变至当下的格局。今天,如
果你要与富人结邻,首选自然是巴黎西部。
1. 感谢Guillaume Daudin许多极好的建议和评论,其极大地改进了本文,同
时感谢Nathan Sussman提供的13世纪巴黎的数据和地图,以及Thomas Piketty
提供的2007年财政收入数据。
2. 事实上,第十六区是第二富裕的区,仅次于第七区(但是第十六区有更多
居民)。
3. 收入最低的阶层包括年收入低于9 400欧元的家庭[或曰“纳税
户”(foyerfiscal)],而最高的阶层则由年收入97 500欧元及以上的家庭组
成。
4. 对13世纪数据的分析是基于Nathan Sussman的论文“Income Inequality
in Paris in the Heyday of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未刊稿)。5. Income Inequality in Paris in the Heyday of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未刊稿),第3页。
6. 见http:www2.cnrs.frpressethema592.htm。
7. http:www.inshea.frRessource ProductionsSDAD
VTactimage_6ePagesPlanLutece.htm。
8. 凯尔特人是铁器时代和中世纪生活于欧洲的一些共享着某些文化和语言特
质而有亲缘关系的民族的统称。——译者注
9. 尤利安皇帝,The Mispogon 。小品1.6
谁从财政再分配中获益了?
谈及收入分配,我们几乎总是想到经济学中所谓“可支配
收入”的分配。正如字面所示,这是家庭在向政府支付完直接
税并从政府取得了如社会保障和失业救济金之类的现金收益之
后,留给其储蓄或消费的收入。但另一个“收入”概念不时也
是有用的,这就是“市场收入”(market income),即未经财
政参与(也就是说在纳税和接受政府转移支付之前)的来自工
资、利润、利息、租金等的收入。显然,市场收入很低的是那
些不能(或不愿)出售其劳动力,且缺少财产以赚取收入的
人。在发达国家,他们通常是失业者。顺带一提,国家出资的
养老金(如社会保障)或私人养老金被认为等同于工资收入
(只不过是延期的),因此也包含在市场收入内。
有了这些准备,我们就经常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政府以
税收和现金收益体现的再分配中,哪个收入群体受益最多?有
一种理论认为,在民主体制下,民众为再分配政策投票,其主
要受益者应该包括位于(市场)收入分配中间阶层的人。其理
由是:假设这个社会由三个人组成,其市场收入分别为低、中、高——市场收入在这里很重要,因为已经挣得的市场收入
决定你偏好的财政收支政策。穷人会倾向于偏好高税率和大量
的政府支出,因为他可能从中受益。出于完全相反的原因,富人会偏好低税率。那么,关键投票就掌握在中间阶层手中。不
论他支持哪一方,该方就会以2∶1胜出。中间选民(the
median voter),或者我们所称的“中产阶层选民”,由此成
为决定性的投票人。因为税率通常是累进的(也就是说,税率
随着市场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在再分配过程中中产阶层选民
可能不会比穷人获益更多,但在原则上获益是可以肯定的,因
为毕竟是他在选择税率以及随之而来的收益,而这意味着其境
遇在可支配收入下会比在市场收入下更好。
事实果真如此吗?现实并非完全如此,而相关证据也不是
始终一致。 首先,我们发现穷人从再分配中获益最多。就市
场收入而言,他们占的比重通常微乎其微,但在政府再分配之
后却有所增长;最终的份额虽仍然很小,但至少能说得过去。
比如,研究表明1980—2000年的大部分民主国家,最贫穷的十
分位阶层(即总人口的10%)在总的市场收入中的比重非常小,仅占1.2%。在政府再分配之后,相同群体的收入比重上升了;
就各国平均而言,这一比重达到了4.1%。因此,最贫穷阶层获
益将近3个百分点。次贫穷阶层相应的两个数据分别为3.6%和
5%,获益1.4个百分点。对每个紧随的(更富有的)阶层,获益
逐步减少,直到第五和第六阶层开始有了轻微的损失。当然,随后对更高阶层的负面影响愈发严重。图2以美国和德国为例,该图表明,最贫穷阶层在各国的收益也不尽相同。美国的最低
十分位阶层大约获益4个百分点(正如我们之前所见,这个数值
是分析所涉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在德国该受益大约是7个百分
点,显著而一致地高于前者。我们可以立刻得出两个明显的结论。首先,发达国家再分
配过程中的最大受益者“一开始”是最贫穷,即市场收入最低
的人。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令人意外的是我们预期会从再分
配中获益的第五和第六阶层这样的中产阶层,却未能如此,其
所占份额甚至稍有下降。此外,这个结果不仅对发达国家整体
有效,而且对每个单独的国家亦然:中产阶层收入份额的损失
程度因国家而异,因年代不同,但其存在却毋庸置疑。这就引
出了一个我们尚未很好地做出回答的问题:为什么理论上起决
定性作用的中产阶层选民会投票支持某种过程,使其最终只获
得国民收入中较原来更小的一部分?这里有两种可能,对此我
们不能断然肯定或拒绝。第一种可能是,中产阶层视某些再分
配政策为潜在的保险而投票。虽然在我们看到再分配结果的一
刹那,他并没有从中取得任何收益,但其当初的投票“只是以
防万一”。例如,若期望在需要失业救济金时他们能够符合条
件,中产阶层可能会为了积存这些救济金而接受对当前收入征
收更高的税款。这是一个合理假设,但是由于缺少逐年追踪同
一群人而获得的纵向数据(以便我们可以真正确定他们最终是
否从这些转移支付中获益),我们很难证明这种可能是否真
实。此外,即便追踪这些中产阶层家庭一辈子,假如发现他们
在再分配之后仍然遭受损失,我们也可对此做如下解释:就算
从中得不到一分一毫,他们为失业救济金投票似乎仍是有价值
的,因为这是一种保险政策。正如购买车险时,我们并不希望
能从中赚钱;如果我们真的得了钱,情况可能会比没有时更
糟。我们买的就是一个“安心”,同样的道理亦适用于此。图2 美国和德国的最贫穷十分位阶层在分配中的获益
注:当我们从市场收入转为可支配收入时计算获益。
第二种可能是存在主要由中产阶层享有的转移支付,但“可支配收入”这一概念却不能对此有恰当的反映,这对有
社会医疗体系和公共教育的欧洲福利国家来说尤为如此。从这
两者中获得的福利都未列入可支配收入。事实上,可支配收入
只是我们可以支出或储蓄的现金收入。如果我们得到了免费医
疗救助或免费教育,由于它们是以非货币形式获得的福利,因
而就不属于可支配收入。但是,免费医疗救助和免费教育是以
民众的直接税支付的。有可能虽然我们正确估计了中产阶层的
税收,但由于某些福利是以实物形式得到的,总的福利却被低
估了。因此,如果我们能以某种方式说明这些福利的现金价值,就可能发现中产阶层确实从政府再分配政策中获得了净收
益。
两种解释都有可能,但不幸的是我们缺少数据以清楚地证
明其中任何一个。我们还面临另一个有趣的问题。让我们回到
最贫穷的那些人,正如我们所见,他们是政府再分配的最大受
益者。假如现在这一最贫穷群体的境况变得更为悲惨,即他们
已有的非常微薄的市场收入份额进一步减小,这会如何?再分
配过程对其所占份额的下降会产生作用吗?事实证明,答案是
肯定的。在先进的民主国家,政府会通过更具再分配性质的税
收-转移支付政策尽数弥补最贫穷群体市场收入份额的下降。总
的来说,这是令人欣慰的消息,尤其是在危机之中。如果有人
不能出售其劳动力,或者不得不廉价出售,同时也没有任何资
产,因而处在收入最底层的话,那么他将遭受更多损失,税收-
转移支付体系会充分弥补这些损失。
因此,尽管我们看到发达国家在过去25~30年间在可支配收
入上的不平等程度大幅上升,尽管各国税收-转移支付体系存在
差异,但这些制度大致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即帮助那些起步于
最低地位的人中的大多数,并减少最富有群体所占的收入比
重。依然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在决定再分配的程度时扮演关
键角色的中产阶层并没有显示他们从这套体系里明显获益了?
这一结果或许也显示了经济分析的局限性,因为我们的投票行
为受意识形态、原则或价值观的影响,有时这甚至比经济因素
的影响更大。毕竟,我们不只是靠面包活着。1. 其间的依据是,一个人收到的养老金,原则上已由其工作生涯中的工资扣
除支付过了,因此只是工资收入在时间上的“重组”罢了。无须预缴的所谓社
会养老金则是个例外,它支付给诸如从来没有工作过也因此不能获得退休收入
的贫困老人。
2. Branko Milanovic,“The Median Voter Hypothesis,Income
Inequality,and Income Redistribution:An Empirical Test with the
Required Data,”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6,no.3(2000):367-410.
之内,若称人与人之间总的收入不平等为甲,则其可以分解为
收入不平等定然极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在一国
共和国间较高的平均收入差异。这意味着在各共和国内部人际
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整体上较低的人际不平等竟伴随着各
指的是个人之间较低的收入差异。
并不矛盾——前者指的是各共和国之间平均收入的差异,后者
我认为总的收入不平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很低,而这两种观点
当谈到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区域收入差异时,需说明的是,.)
密 联 系 中 寻 找 解 体 的 根 本 原 因 。 ( 免 费 书 享 分 更 多 搜 索 致。我们必须从收入与宗教之间或者收入与种族之间暗合的紧
此外,收入的沟壑与种族的沟壑一致,有时也与宗教的沟壑一
每一个联盟内,我们真正面对的是多个国家及多个发展水平。
所称的“共和国”的收入水平参差不齐,相去甚远。因此,在
实(尽管对捷克斯洛伐克并非如此):构成这两国的州或后来
解释。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对苏联和南斯拉夫成立的一个事
治、宗教等方面的原因,甚至包括纯粹的情境之中前因后果的
解 , 人 们 已 花 了 很 多 笔 墨 详 加 说 明 , 提 出 了 种 族 、 历 史 、 政
就 苏 联 、 南 斯 拉 夫 、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这 些 国 家 联 盟 突 然 瓦
若干国家可存于一体吗?
小品1.7两部分,这就是乙:区域间的不平等,即由区域间平均收入差
异导致的不平等,以及丙:各区域内的人际不平等(见散论
一)。因此,若苏联的甲相对较小而乙相对较大,那么丙必定
非常小。
苏联由15个共和国组成。在1991年解体时,以人均GDP衡
量,最富有的共和国(俄罗斯)与最贫穷的共和国(塔吉克斯
坦)之间的比值大致是6∶1。我们将会看到(见小品3.3),在
美国,最富有和最贫穷的州之间的比值仅为1.5∶1。让我们看
其他几个例子。在以区域不平等臭名昭著的意大利,其最富有
的区域(位于北部的瓦莱达奥斯塔大区,与瑞士接壤)和最贫
穷的区域(位于东南部的卡拉布里亚大区)之间的比值是3∶1;
在区域关系不时紧张的西班牙,其最富有的区域(马德里)和
最贫穷的区域(埃斯特雷马杜拉自治区)之间的比值是1.7∶1;
在法国,这一比值是1.6∶1(即环绕巴黎的法兰西岛大区较之
于北部加来海峡大区);而在德国,则是1.4∶1(柏林较之于
图林根州)。可见,苏联的区域不平等现象比任何这些国家都
要严重得多。
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和俄罗斯,比整个苏联的平均收入要
高出许多,而剩下的11个共和国比平均水平低。 这一差距并
未随着时间减小。尽管要构建各苏维埃共和国一致的数据序列
会面临许多困难,并且在做结论时得相当审慎,但通过1958年
首次可用的数据,我们发现俄罗斯(也是当时最富有的共和
国)和最穷的中亚共和国之间的差距仅为4∶1。因此,共和国之间的差距不仅大,而且在二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一差距
极有可能在不断加大。
解体之时,苏联可视为一个联合体,在其疆域之内容纳着
收入差异巨大的国家,而它们竟如韩国与科特迪瓦一般。 如
果没有大量的再分配来帮助贫穷的成员以巩固国家的团结统
一,这个联合体能存在吗?几乎不可能。但是,那么大范围的
再分配可行吗?那些为这种财富转移掏钱的富裕成员,难道不
会最终因此心生怨怼?这确实在俄罗斯发生了。当叶利钦当选
为其最高领导人时,它仍是苏联的一部分。他支持那些反对进
一步补贴的力量。于是,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和波罗的海诸
国成为苏联最激烈的分裂主义者。富裕的共和国极欲决绝出
去,而贫穷的共和国除了默认,别无他法。
前南斯拉夫的例子更具戏剧性,这不仅因为其瓦解的方
式,更在于虽然它整个领土仅相当于苏联极小的一部分,但其
各共和国间的收入差异却比苏联更大,因而也更令人侧目。人
们或许能够理解苏联内部存在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毕竟它是
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面积约为美国的2.5倍。异乎寻常的是,南
斯拉夫的面积跟密歇根州一般大,但其共和国之间的收入比竟
达到8∶1。 在欧洲,再没有别的国家的区域收入不平等达到
这般水平。南斯拉夫最发达的地区是位于西北的斯洛文尼亚,在1991年解体时,其人均收入水平与西班牙相当。而最不发达
的科索沃省地处东南,其人均收入与洪都拉斯相仿。因此,在
如密歇根州那样大的国家里,中央政府不得不让这两种收入水
平的人都满意。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在南斯拉夫,尽管有由联邦出资的机构进行适度的再分配,但共和国之间的差距却不断
增加。比如,在二战后的南斯拉夫,当其统计数据于1952年首
次可以获得时,以人均GDP计,斯洛文尼亚的富裕程度仅为科索
沃的4倍。40年之后,正如我们看到的,其间的差距业已翻倍。
我们从共产主义联邦政府的瓦解可以看到,解体的一个重
要原因是,尽管它们的政策成功地控制和降低了人际不平等,却不能缩小其各组成部分间由历史遗留的巨大收入差距。再回
到小品标题中提出的问题,它还会困扰其他许多国家。比如中
国的区域收入差距正在迅速加大。欧盟可以不断吸纳更穷的成
员国,却不危害其自身的团结统一和生存发展吗(见小品
3.3)?尼日利亚各州的种族和宗教截然不同,且它们间的人均
收入差异约为4∶1,它又该怎样在其间协调石油收益的分配
呢?
1. 白俄罗斯的位置不清楚。根据某些统计,其收入水平高于苏联平均收入水
平,但据另一些统计则相反。
2. 原文为Ivory Coast(“象牙海岸”),这是科特迪瓦共和国的别称。——
译者注
3. 除了六个共和国,我还使用了两个省(较共和国为低的行政级别)的数
据。小品1.8
中国的不平等
中国目前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中国的不平等不
仅几乎已经翻倍,其基尼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不到0.30
上升至2005年的0.45,而且这一问题还体现在其构成方式上。
为简化计,我们可以把不平等分为两种类型(见小品
3.3):“美国式”不平等是一种较高的不平等,其富人和穷人
较为均等地分布于全国,而没有在地理上集中于特定的州。显
然,富人和穷人的确生活在不同社区,但在第一级行政单位
( 即 “ 州 ” ) 间 并 不 存 在 “ 收 入 隔 离 ” ( income
segregation)现象。究其实质,即“只有”穷人和富人之分,而没有穷州和富州之别。欧盟扩张之后的不平等是另一种类
型,即主要源于其成员国平均收入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产生
的穷人和富人在地理上的集中。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中
国增长的焦点转移到城市地区,其发展逐渐造成了后一种不平
等,即产生了贫穷和富有的省,而这可能更易导致社会的不稳
定(见上一小品)。
中国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沿海省份。不考虑有很高人均GDP的
上海、北京、天津这3个城市, 让我们来看看沿海的另外5个
富裕且发展迅速的省。这些省份从北到南相邻,依次为:山
东,相较于中国的其他部分,其人均GDP从1990年的1左右(意味着它大约等于当时中国的平均水平)增长到2006年的1.3;江
苏,从1.3增长到1.6;浙江,从1.3增长到1.8;福建,从1增长到
1.2;而广东,则从1.5增长到1.6。在过去的15年间,这里的每
个省大致比中国平均增长水平快了20%。据2006—2007年的数
据,这些省份的总人口是3.4亿,大致是整个中国人口的14,然而却创造了其GDP的40%。
如果再加入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这4个直辖市,我们看
到,这5个省和4个直辖市的产出占了中国全部产出的50%以上。
我们可以轻易地把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视为这一现象自然
而然也更极端的扩展。由此,这个“5+6”的省市组合形成
的“集团”,在地理上大致相连,以贸易为导向,相较中国内
陆越来越富足,开始代表一个分离群体。
在另一端,20世纪90年代以来,贵州、甘肃和云南这最贫
穷的三个省的状况都相对下滑。后两个省的人均GDP曾是中国平
均水平的70%,而现在只有50%。最穷的贵州省,最初为中国平
均水平的一半,但现在只有13。富裕的省发展得比平均速度
快,而贫穷的省却比平均速度慢,不出所料,这使最高收入和
最低收入之比急剧增加。1990年大范围的工业改革之初,这个
比例为7∶1,而到2006年已上升到10∶1。而且,以上结果还没
有考虑西藏的收入。鉴于西藏可能是中国最穷的省,这自然会
愈发拉大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间的鸿沟。
这至少为10∶1的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比,较苏联当时的
6∶1(见上一小品)还要高出许多。当然,在别的方面,情况
有所不同。名义上苏联是一个国家联盟,故而在其经济的沟壑之上,是种族、语言以及宗教上的沟壑。但尽管语言存在差
异,中国的汉族可被视为一个民族,而且较之于波罗的海诸国
的民众与俄罗斯人,或者塔吉克人与俄罗斯人,汉族生活于单
个政府之下的历史更长。 然而,至少对广西、内蒙古、宁
夏、新疆和西藏这五个最贫穷的自治区而言,非汉族人口是重
要的少数族裔,甚至还占据多数。以汉族为主的中国(Han
China)的确也曾四分五裂,尤其是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
纪的战国时期,接着是3世纪的三国时期,最近一次是在20世纪
30年代,当时日本在中国北方建立了伪满洲国,而中国的其余
部分则分裂成多个战时政府,在其中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权
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最为声名远播。
因此,就经济和对外部世界的看法而言,繁荣的沿海11省
市和中国其余地区之间渐行渐远。这里潜藏着的危险既难以消
除,也不可忽视。
1. 虽然它们不都是官方定义的“省”(实为23个),为简便讲,我将其均称
为“省”。
2. 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的官方资料,主要是不同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3. 重庆是在1997年之后才成为单独的行政单位,即直辖市。
4. 虽然我们不应忘记,波罗的海诸国并入沙皇俄国始自18世纪(大体而言,对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这是在1721年瑞典—俄国战争之后,而立陶宛是在
1772年波兰解体之后)。小品1.9
研究不平等的两个学者:
帕累托和库兹涅茨
读者可能会惊讶,在个体收入分配的构成及其随时间演变
方面,没有多少理论或理论性的洞见。 考虑到早在1817年,现代经济学开创者之一大卫·李嘉图在其出版的极具影响力的
《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就已将收入分配放在经济学的核心位
置,这就更令人奇怪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至少可从两方面解释。其一,李嘉图关
注的是所谓功能性收入分配,或者说如何分配国民收入以形成
各大阶级的收入:对资本家是利润,对地主是租金,对工人是
工资。而我们这里感兴趣的是人际收入分配,也就是如何在个
体之间分配国民收入,而不论其主要收入是源于财产还是劳
动。现在,只要所有(或大多数)财产拥有者都富有,而所有
(或大多数)劳动者都贫穷,则功能性分配和人际分配看起来
就是相当一致的。我们知道,如果资本家获得了更大部分的收
入,则总的不平等就极有可能上升,而相反的结论对工资亦成
立。因此,对人际收入分配的关注湮没于对功能性收入分配的
关注,或者更准确地说,前者被纳入后者之下。但随着中产阶层的出现,由于其收入主要来自劳动,事情
就发生了变化,不再可能维持收入的功能性分配与人际分配的
一致性。经济学家必须建立理论来解释收入是如何在民众之间
分配的,而不仅仅是研究总收入的多大比例归于资本家,多大
比例归于工人。就是在这里,我们的第一个主人公维尔弗雷多
·帕累托发出了声音。
但在介绍帕累托之前,有必要提一下研究人际不平等不甚
受追捧的第二个原因,这在台面上常常是看不到的。虽然经常
被明智地忽略,但道理其实相当简单:富人不是特别欣赏对不
平等问题的研究。华盛顿某声名赫赫的智库的负责人曾告诉
我,他们的委员会几乎不会资助任何题目中含有“收入不平
等”或“财富不平等”的研究。的确,他们会资助任何消除贫
穷的工作,但不平等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何以如此?因
为“我”对他人贫困的关心将会突显我的古道热肠:我时刻准
备用自己的钱来帮助他们。慈善是好事,因为这会让自尊心膨
胀,而且即便是对穷人极小数额的帮助,也会赚得不少令名。
但是不平等就不同了,事实上一提起它就会引发另外的问题,即我自己的收入是否正当或合法?如果有人认为我拿的是不义
之财,那么我的慈善或许就不会那么讨喜了。因此,对不平等
最好是避而不谈。 类似地,世界银行并没有将其关于此议题
的核心报告冠名以“不平等”,而是更含蓄地称之为关于“平
等”的报告。近来,就对贫穷热切关注与对不平等不闻不问间
的反差,英国历史学家大卫·凯纳斯顿(David Kynaston)做
了极好的总结:“人人都愿意谈论消除贫穷,因为这看起来是对不平等问题可钦可佩、合乎道德的回应,但问题是他们对权
利结构避而不谈。”
不愿谈论不平等并非仅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当我开始对收
入不平等感兴趣时,我生活工作在社会主义社会。当时不平等
被婉称为“敏感”话题,而原因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看似不
同,实则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下,任何关于收入分配的实证研
究都表明其存在收入差异。这使国家统治者感到不安,因为其
在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建立在他们宣传的理念之上,即已开创
了一个没有阶级的平等社会。安全的做法是相信它,而不是对
此深入研究。
让我们把目光回到维尔弗雷多·帕累托身上。他是个充满
矛盾的人。帕累托在欧洲1848年革命时期出生于巴黎一个侯爵
家庭,他的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法国人。帕累托在19世纪
后期的自由环境中长大,精通意大利语和法语,并使用这两种
语言写作和教学(在现代边际学派经济学创始人之一里昂·瓦
尔拉斯退休之后,帕累托接替他在洛桑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
席)。然而,其观念却是贵族一派,强烈地反对社会主义。
他一直是个有争议的学者。正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
所言,在一定程度上,帕累托使老师和学生都感到不舒服。
他鄙视平民,以至于去解释所有的宗教和道德信仰如何在本
质上全是非逻辑的情绪,与作为科学之特征的逻辑-实验方法毫
不相关。然而,他认为又必须保护并传授它们,以使世人有所
信仰,否则他们就只会回到自然的原始状态。他大胆宣称“我
只是在探究现象间的一致性”,而“并不想说服任何人”。之后,他也许是在社会科学史上独一无二地又警告潜在读
者:“怀有其他目的的人很容易找到令其无比满意的作品;这
样的东西有很多,他们大可不必阅读此书。” 就这样,他将
这些潜在读者拒之门外。阿隆解释说,帕累托这种莫名的不安
源自他的某种态度,即就本质而言,教授传授的东西全都是谬
误。但帕累托认为,由于传授真理对任何社会秩序都是致命
的,而平民只能多少听懂那些谎言,因此教授必须在这种错误
中孜孜以求。用他的术语来说,社会均衡需要信奉那些非逻辑
的情绪。
下面是约瑟夫·熊彼特在其不朽之作《经济分析史》中对
帕累托的描述:
他怀有强烈的激情,这种激情实际上使他只能看到政治
问题的一面,或者也因此只能看到文明的一面。他接受的古
典教育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此种性情,并且使他对古老
世界就像对他自己的意大利和法国一样熟悉,而世界上的其
余事物仅仅只为他而存在。
帕累托写了两本颇有影响的经济学著作,也可说是教材,而他在今天的经济学界主要以两项贡献闻名,即“帕累托改
进”(或“帕累托最优”)和帕累托收入分配“铁律”。第一
个术语几乎每天都被经济学家使用,已成为经济学不可或缺的
工具之一。究其实质,帕累托改进指出,对于社会状态的某种
改变,只有每个人的福利都由此增加或至少保持不变,这种改
变才会为社会接受。简言之,必须要有人获益且无人受损。要找到这样的经济政策(或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总有人
会有损失,故而帕累托改进的要求相当严苛。在现实之中,这
无异于维持现状(见散论一)。
帕累托的收入分配“定律”来自对经验的观察。他一开始
学工程,其数学能力出众,最终发现了下面的统计规律。取收
入水平Y,然后找出收入超过Y的人,记其数量为N,然后将收入
水平Y增加比如10%,那么有多少人的收入超过Y(1+10%)呢?
显然,其数量会小于N。帕累托认为他发现了一个规律,或者说
一个定律:收入每增加10%,人数就会减少14%~15%,由此帕累
托常数[或曰“截断常量”(guillotine)]为1.4~1.5。 他
以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十几个欧洲国家和城市的税收数据为样
本,发现使用帕累托常数得到的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当吻合。
就意识形态而言,这个发现给了帕累托极大安慰。在其社
会学论文中,他主张社会的特点就是精英的更迭交替。在《共
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声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
的历史”;似乎是对马克思这一著名论断故意而间接的挑战,帕累托宣称“人类社会的历史……是贵族演替的历史”。 当
然,和马克思不一样,他认为这势必还将继续下去。在帕累托
看来,尽管社会主义式的“均等化”常常是时代聚讼纷纭的政
治话题,但其间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真正上演的,是一部分
官僚或工人领袖代替资本家而已。他们会成为新的精英,然而
也还是精英,不会比在原政权下有更多的平等。经验证明他似
乎是对的:不论选择什么样的国家或城市,收入分配看起来都
极为相似,并且当我们沿着收入分配的阶梯往上爬,几乎同样比例的人便会被淘汰。正如他自己所言,帕累托认为这才揭示
了收入分配的“铁律”。
收入分配研究的第二个使徒西蒙·库兹涅茨与帕累托完全
不同。1901年,库兹涅茨出生于俄罗斯帝国(具体的位置在今
天的白俄罗斯)。1922年,他逃离俄国,移居美国,然后在北
美多所大学读书从教,包括晚年在哈佛大学。他是国民经济研
究局(NBER,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该机构致力于对经济周期
的研究)的发起者之一。库兹涅茨筛查其时相当稀少的证据,以不同方式展示并分析研究数据,总之,其工作是相当经验性
的。在经济学家中,他是少有的一类。相对而言,他的文笔生
动有趣,即使时光流逝,在今天看来也常常充满洞见。然而若
想要引述他的话,却十分困难。在他的行文中,随处可见谨慎
的提示,又包含大量从句和省略句,这使人们基本上无法引用
原文或轻易得其精要。若想要从库兹涅茨的文字中得到简短透
彻的陈述,我们就得将其内容删掉23。在帕累托鞭辟入里、确
信无疑地——有时是存心言辞犀利、无所顾忌——写作的内容
上,库兹涅茨却会小心翼翼地避免错误;当帕累托宣称根据少
量数据已经发现了规律,库兹涅茨却对每一个数字满腹狐疑;
前者以贵族式特立独行的学者形象示人,后者却是一位典型的
教授。
根据上述稀疏的材料,库兹涅茨于1955年提出了现代收入
分配理论的主要框架,其地位至今依旧。这一假说认为,社会
在其发展早期以农业为主,因为大多数农民大抵仅能果腹,故
不平等程度很低。然后,随着工业的发展,人们开始往城市迁移。在那儿,一方面非农业领域的生产力水平和收入水平更
高,另一方面是其中有更多职业,而技能也更多元化,故而城
市里有更大的收入差别,不平等现象也就愈发严重。最后,随
着社会进一步发展,增加的财富使更多人可以接受教育,这减
少了过去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获得的额外好处。新增的财富
也使诸如社会保障、失业救济等阶级间的再分配成为可能。简
而言之,库兹涅茨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不平等呈现为
大的倒U形曲线,即从平等变为不平等,再从不平等回到平等。
这与帕累托收入分配的铁律截然不同。在帕累托看来,不
论社会发展与否,也无论是社会主义抑或资本主义,全无不
同。变化的只是不同的精英阶层,但分配格局如故。而在库兹
涅茨看来,不同发展阶段对应着不同的不平等水平。
谁的理论是正确的?帕累托的有一点点,库兹涅茨的稍微
更多一些。前者的方法中有价值的是,最高收入水平和相应的
人数的确表现出和帕累托“定律”相似的规律。这一数值可能
不会总是1.4或1.5,但是收入的“截断”效应相当清晰,屡试
不爽。然而,这仅适用于最富有的1%或至多2%。在其他情况
下,帕累托定律根本不存在。同时,显而易见的是,不平等与
国家和社会制度有关,且会随着时间改变。帕累托深信的一成
不变的收入分配并不存在。
那么,库兹涅茨的倒U形曲线又如何呢?关于它已有成百上
千的文章,支持和反对者几乎持平。在某一时点上,当绘出不
同收入水平国家对应的基尼系数值后,我们发现它看起来像某
种倒U形。但的确,只有竭力端详它才会如此,因为一眼望去它根本就是没有形状的散点图。尽管如此,仍然有人认为,这个
模糊的倒U形曲线是据拉丁美洲国家数据有意为之的产物,这些
国家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其严重的不平等更多是因为殖民历史
而不是出于库兹涅茨理论解释的原因。就是它们“制造”了驼 ......
您现在查看是摘要介绍页, 详见PDF附件(9969KB,231页)。